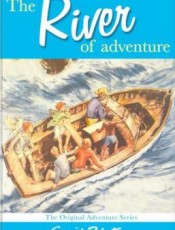女房东
比利·威夫搭下午的慢车,从伦敦出发,在雷丁站换乘,到达巴斯时已是晚上九点,月亮
早就高高挂在车站口对面房屋上方的澄澈夜空中。天气冷得要命,风像冰冷的刀子一样刮在
他脸上。
“请问,”他说,“离这里不远的地方,有没有一家便宜点的旅馆?”
“到‘铃铛和龙’去问问吧。”搬运工指着路上回答,“他们可能会让你住下。离这里大概四
分之一英里,在马路对面。”
比利谢过他,拎起箱子,开始步行四分之一英里,前往“铃铛和龙”。他以前没来过巴
斯,不认识住在这里的人。不过伦敦总部的格林斯拉德先生告诉他,巴斯是一座美妙的小
城。“自己找地方住吧,”他说,“安顿下来之后,就去找分部经理报到。”
比利十七岁,戴一顶崭新的褐色软毡帽,穿一件崭新的海军蓝大衣,里面是一套崭新的
褐色西装,自我感觉很好。他走在街道上,脚步轻快。最近,他做一切事情都尽量轻快。轻
快,他认为,是所有成功商人都有的性格特征。总部的那些大亨,每时每刻都是百分之百的
轻快敏捷。他们简直令人咋舌。
他走的这条街很宽,但是没有店铺,两边都排列着高大的房屋,而且每座房子都一样。
有门廊、柱子,有四五级台阶通向前门,显然曾经有一个时期,这些房子都是非常豪华的住
宅。然而现在,即使在黑暗中,比利也能看出门窗的木头已经油漆剥落,那些漂亮的白色门
脸因为疏于维护,出现了道道裂纹,变得斑斑驳驳。
突然,在不到六码开外,一盏路灯照亮了一扇底楼的窗户,比利看见一张打印的招贴支
在上层的一块玻璃上。招贴上写着“住宿加早餐”。一盆黄灿灿的菊花就放在招贴下面,高高
的,十分美丽。
比利停住脚步。他凑近了一点。绿色的窗帘(好像是天鹅绒质地的)挂在窗户两侧。窗
帘之间,那盆菊花看上去非常奇妙。比利走上前,透过窗户往房间里看,第一眼看见的是壁
炉里明亮的旺火。炉火前面的地毯上趴着一只漂亮的腊肠狗,鼻子埋在肚子里,睡得正香。
在昏暗的光线中,比利可以看到房间里摆满舒适宜人的家具。一架袖珍三角钢琴,一张大沙
发,以及几把鼓鼓囊囊的扶手椅;在房间的一角,他还看见一只关在笼子里的大鹦鹉。一般
来说,在这样的地方,动物总是个好的兆头,比利对自己说;总之,他觉得住在这么一座房
子里应该是很不错的,肯定要比那个“铃铛和龙”舒服。
不过,酒馆会比旅馆更让人开心。那里晚上会供应啤酒,还可以掷飞镖,有许多人可以
聊天,而且,价钱可能也会便宜许多。他以前在一家酒馆住过两晚,很是喜欢。他从没有住
过旅馆,说实在的,心里对旅馆有一点点害怕。光是听到旅馆这两个字,就能想象到水煮白
菜、抠抠搜搜的女房东,还有客厅里的那股臭咸鱼味儿。
比利在寒风里这样犹豫了两三分钟,决定继续往前走,到“铃铛和龙”去看看再做决定。
他转身想走。
就在这时,出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他正准备退回来,从窗口离开时,突然,鬼使神差
地,他的眼睛被那张小小的招贴牢牢吸引住了。“住宿加早餐”……“住宿加早餐”……“住宿加
早餐”。每个字都像一只黑色的大眼睛,透过玻璃盯着他,抓住他、逼着他、强迫他留在这
里,不要离开这座房子,还没等反应过来,他竟然真的从窗口走向房子的前门,踏上那几级
台阶,伸手去摸门铃。
他按响了门铃,听见铃声在房屋深处的一个房间里响起,接着,说时迟那时快——这肯
定是立刻发生的,因为他还没来得及把手指从门铃上收回——门突然打开,门里站着一个女
人。
正常情况下,你按响门铃,起码得等上半分钟,门才会开,这女人却像一个玩偶盒子,
比利一按门铃——她就跳出来了!比利吃了一惊。
女人大约四十五到五十岁,一看见比利,就朝他露出一个亲切、热情的微笑。
“请进来吧。”女人和颜悦色地说。她让到一边,把门开得大大的,比利发现他不由自主
地开始往前走。跟着女人走进这座房屋的冲动,更准确地说,是欲望,简直强烈得出奇。
“我看见窗户里的招贴了。”他克制着自己,说道。
“是的,我知道。”
“我想知道有没有房间。”
“都给你准备好了,亲爱的。”女人说。她有一张红扑扑的圆脸,一双非常温柔的蓝眼
睛。
“我正要去‘铃铛和龙’。”比利对她说,“但碰巧看到了你窗户里的那张招贴。”
“亲爱的孩子。”她说,“外面天气这么冷,你为什么不进来呢?”
“房费多少?”
“一晚上五先令六便士,含早餐。”
便宜得令人难以置信,比他愿意支付的价钱少了一半多。
“如果嫌贵,”女人又说,“也许我可以再降一点儿。你早餐想吃一个鸡蛋吗?眼下鸡蛋很
贵的。如果减掉那个鸡蛋,就少收六便士。”
“五先令六便士没有问题。”比利回答,“我非常愿意住在这里。”
“我就知道你会愿意。快进来吧。”
她看上去特别和蔼可亲,完全就像你最好的同学邀请你到他家去过圣诞节时,他妈妈长
的那个样子。于是,比利摘下帽子,跨过了门槛。
“就挂在那儿好了。”女人说,“我来帮你脱大衣。”
大厅里没有别的帽子或大衣。也没有雨伞,没有拐杖——什么都没有。
“这里只有我们俩。”女人说,一边领路往楼上走,一边扭头笑微微地看着比利,“你也看
到了,我的这个蜗居是很少接待客人的。”
这位大妈有点儿神神道道,比利对自己说。可是一晚上只收五先令六便士,管那么多干
吗?“我还以为你这里挤满了想入住的人呢。”比利礼貌地说。
“哦,是这样,亲爱的,当然是这样。但问题是,我习惯性地有那么点儿挑剔和苛求——
希望你明白我的意思。”
“啊,明白。”
“但是我时刻做好准备。在这座房子里,从早到晚一切就绪,指望着万一有个中意的年轻
人能过来呢。偶尔,我打开门,看见站在那儿的正是理想中的人,那可真是一件高兴的事,
亲爱的,一件非常非常令人高兴的事。”她走到楼梯一半,手扶着栏杆,停下身,转过头,看
着比利,苍白的嘴唇含着微笑。“就像你这样的。”她加了一句,一双蓝眼睛慢慢地扫视比利
的全身,一直看到他的双脚,再一点点往上看。
到了二楼平台,女人对比利说:“这层归我。”
他们又上了一层。“这层全都归你。”女人说,“这是你的卧室。希望你会喜欢。”她把比
利领进一间虽然小但很温馨的正面卧室,打开了灯。
“早晨的阳光会从窗户照进来,珀金斯先生。是珀金斯先生,没错吧?”
“不是。”比利说,“我姓威夫。”
“威夫先生。真好。我在被子里放了一个暖水瓶,去去潮气,威夫先生。在一张陌生的床
上,有干净的床单,有一个热乎乎的暖水瓶,真是太舒服了,是吧?你如果感到冷,可以随
时打开煤气取暖炉。”
“谢谢你。”比利说,“真是太谢谢你了。”他注意到,床上的床罩拿掉了,被子的一侧被
整齐地掀开,等着人钻进去。
“你来了我真高兴。”女人热切地端详着他的脸,说道,“我开始时还担心你不进来呢。”
“不会的。”比利欢快地答道,“你不用为我担心。”他把箱子放在椅子上,动手打开。
“亲爱的,晚餐想吃什么?你来这儿之前,有没有弄点什么东西吃吃?”
“我一点儿也不饿,谢谢你。”比利说,“我想尽快上床睡觉,因为明天要早起,到办事处
去报到。”
“那好。我这就离开,让你把箱子里的东西拿出来。不过,在你睡觉前,能不能麻烦你到
一楼的客厅去一下,在登记簿上签个字?每个人都得签字,这是地方法律的规定,在目前这
个阶段,我们可不能违反法律啊,是不是?”她朝比利轻轻挥了挥手,快步走出房间,关上了
门。
这位女房东似乎有点儿精神不正常,但是比利没有感到丝毫的不安。毕竟,这女人不仅
没有危险——这是毫无疑问的——而且一眼就能看出是个善良和慷慨的人。比利猜她可能在
战争中失去过一个儿子,或者有过类似的遭遇,一直没有从打击中恢复过来。
几分钟后,比利拿出了箱子里的东西,洗了洗手,便快步来到楼下,走进客厅。女房东
不在,但壁炉里火光熊熊,那条小腊肠狗仍趴在炉前睡得正香。房间里有种说不出的温馨和
舒适。我是个幸运的人。他搓着双手,想道。感觉真不错。
他发现房客登记簿摊开放在钢琴上,便掏出钢笔,写下自己的姓名和地址。这一页在他
前面只登记了两个人。每个人面对房客登记簿时都会多看几眼,他便也看了起来。一位是来
自卡迪夫的克里斯托弗·姆霍兰德,另一位是来自布里斯托尔的格里高利·w. 坦普尔。
真奇怪,他突然想。克里斯托弗·姆霍兰德。这名字听起来有点耳熟。
是学校里的某个男生?不对。也许是姐姐交往过的众多男青年之一,或者是爸爸的一位
朋友?不是,不是,都不是。他又低头看了一眼登记簿。
克里斯托弗·姆霍兰德,卡迪夫,大教堂路231号
格里高利·w. 坦普尔,布里斯托尔,梧桐道27号
实际上,现在仔细想来,他觉得这第二个名字似乎也和第一个一样,听上去有那么几分
耳熟。
“格里高利·坦普尔?”他大声念出来,一边在记忆中搜索,“克里斯托弗·姆霍兰德?……”
“多么迷人的小伙子。”后面一个声音回答,比利转过身,看见女房东轻飘飘地走进房
间,双手端着一个很大的银托盘。她把托盘平端在面前,举得高高的,就好像托盘是两根拴
住一匹活泼野马的缰绳。
“他们的名字有点儿耳熟。”他说。
“是吗?真有意思。”
“我几乎可以肯定,我以前在什么地方听过这两个名字。这太奇怪了,不是吗?也许是在
报纸上看到过。他们不是什么名人吧?我是说有名的板球手、足球运动员之类的?”
“名人?”女人说着,把托盘放在沙发前面的矮桌上,“哦,不是,我认为他们没什么名。
但是他们帅得不可思议,两个都是,这点我可以向你保证。都是高个子,年轻、英俊,亲爱
的,跟你完全一样。”
比利又低头扫了一眼登记簿。“你看这儿,”他注意到了日期,说道,“最后的登记日期是
两年前。”
“是吗?”
“是的,没错。克里斯托弗·姆霍兰德还要早差不多一年——三年多以前了。”
“天哪。”女人说,摇了摇头,发出一声优雅的轻叹,“我真是没想到。对我们每个人来
说,时间过得多快啊,是不是,威金斯先生?”
“我姓威夫,”比利说,“威——夫。”
“哦,是的,是的!”女人大声说,在沙发上坐了下来,“我真是糊涂了。我总是左耳朵
进、右耳朵出的,我必须道歉。威夫先生。”
“你知道吗?”比利说,“这件事真的非常蹊跷,你知道为什么吗?”
“哦,亲爱的,我不知道。”
“是这样的,这两个名字——姆霍兰德和坦普尔——我好像不仅分别记得它们每一个,而
且,不知怎的,它们似乎还以某种特殊的方式联系在一起。似乎这两个人都因为一件同样的
事情而出名,但愿你明白我的意思——就像……嗯……打个比方吧,就像登普西和滕尼,或
者丘吉尔和罗斯福。”
“真有意思。”女人说,“好了,过来吧,亲爱的,和我一起坐在沙发上,我给你倒一杯好
茶,拿一块姜味饼干,然后你再去睡觉。”
“你真的不必麻烦。”比利说,“太让我过意不去了。”他站在钢琴边,注视着女人摆弄那
些茶杯和茶托。他注意到,女人有一双纤小的、动作敏捷的手,指甲是红色的。
“我几乎可以确定,我在报纸上看到过他们。”比利说,“我很快就能想起来。肯定能想起
来。”
记忆中的某个东西,就在大脑外围的某个地方徘徊,没有什么比这更诱人的了。比利不
愿放弃。
“请等一分钟,”他说,“等一分钟。姆霍兰德……克里斯托弗·姆霍兰德……不就是那个伊
顿公学男生的名字吗?他到西南部去远足,突然之间……”
“加奶吗?”女人说,“加糖吗?”
“好的,多谢。突然之间……”
“伊顿公学的男生?”女人说,“哦,不对,亲爱的,那不可能,我的那位姆霍兰德先生上
我这儿来的时候,肯定不是伊顿公学的男生。他是剑桥的本科生。好了,过来,坐在我身
边,在这可爱的炉火前暖暖身子。来吧。你的茶都给你准备好了。”她拍了拍身边沙发上的空
位,然后坐在那里笑眯眯地看着比利,等着他走过来坐下。
比利慢慢地走向房间那边,轻轻坐在沙发边缘。女人把他的茶杯放在他面前的桌上。
“可以喝茶了。”女人说,“这感觉多么温馨,多么舒适啊,是不是?”
比利开始小口喝茶。女人也是。有半分钟左右,两人谁也没有说话。但是比利知道女人
在看他。她把身体微微转向他,他能感觉到她的目光停留在他脸上,从她茶杯的边缘上注视
着他。时不时地,比利闻到一股奇特的气味,像是从她身体里直接散发出来的。这气味丝毫
也不令人反感,使比利想起了——好吧,他也不确定自己想起了什么。腌核桃?新皮革?还
是医院的走廊?
最后,女人说话了:“姆霍兰德先生酷爱喝茶。我这辈子从没见过有谁像可爱可亲的姆霍
兰德先生一样,喝那么多的茶。”
“我猜他是最近才离开吧。”比利说。他脑子里还在琢磨那两个名字。现在可以确定,他
曾在报纸上看到过它们——被写在标题里。
“离开?”女人说着,扬起了眉毛,“我亲爱的孩子,他从未离开。他还在这儿。坦普尔先
生也在这儿。他们都在四楼,两个人在一起。”
比利把茶杯慢慢放在桌上,眼睛盯着女房东。女房东笑眯眯地看着他,然后伸出一只白
皙的手,宽慰地拍了拍他的膝盖。“亲爱的,你多大了?”她问。
“十七。”
“十七!”她喊了起来,“哦,多么完美的年龄!姆霍兰德当时也是十七。但我认为他比你
矮一点点;实际上我敢肯定他没有你高,而且牙齿也远没有这么白。你有一口绝顶美丽的牙
齿,威夫先生,你知道吗?”
“其实并没有看上去这么好。”比利说,“后面好多颗牙都是补过的。”
“当然啦,坦普尔先生年龄大了点儿。”女人没有理会比利的话,兀自说道,“他竟然有二
十八岁了。不过,要不是他亲口告诉我,我这辈子都不会猜得到。他的身体没有一点瑕疵。”
“没有什么?”比利说。
“他的皮肤简直像婴儿一样。”
片刻的停顿。比利拿起茶杯,又喝了一口,然后又把杯子轻轻放在茶托上。他等着女人
再说点什么,可是她似乎又一次陷入了沉默。比利坐在那儿,咬着下唇,目光直视着前方,
看向房间那头的角落。
“那只鹦鹉,”最后他说,“你知道吗?我第一次透过窗户看见它时,完全被它骗过了。我
敢发誓说它是活的。”
“唉,已经不是了。”
“把它做成这样,手也真是太巧了。”比利说,“它看上去一点也不像已经死了。是谁做
的?”
“我。”
“是你做的?”
“当然。”女人说,“你也见过我的小巴赛了吧?”她冲那只舒舒服服趴在炉火前的腊肠狗
点点头。比利看着腊肠狗。突然,他意识到这条狗也像鹦鹉一样,一直安安静静,一动不
动。他伸出一只手,轻轻摸了摸腊肠狗的身体。后背又硬又冷,他用手指把狗毛拨到一边,
看到了下面的皮肤,灰黑色的,已经风干了,但保存完好。
“天哪。”他说,“这太神奇了。”他把目光从腊肠狗身上转过来,十分崇拜地盯着跟他同
坐在沙发上的小个子女人。“要完成这样一件事,肯定是非常困难的。”
“一点也不。”女人说,“我所有的小宠物离世后,我都把它们做成标本。你要不要再喝一
杯茶?”
“不了,谢谢你。”比利说。茶里有一股淡淡的苦杏仁味,他不太喜欢。
“你在登记簿上签过名了,是吗?”
“哦,是的。”
“很好。以后,我万一忘记了你叫什么名字,就能随时下楼来查一查。直到现在,我还几
乎每天都要查一查姆霍兰德先生和……和……”
“坦普尔先生。”比利说,“格里高利·坦普尔。我冒昧问一句,在最近两三年,除了他们,
还有过别的房客吗?”
女人一只手高高举起茶杯,脑袋微微偏向左边,用眼角的余光看着比利,又给了他一个
温柔的浅笑。
“没有,亲爱的。”她说,“只有你。”
首次发表于《纽约客》 1959.1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