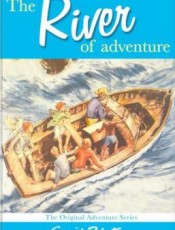威廉与玛丽
威廉·佩尔死后没有留下多少钱财,遗嘱也很简单。除了对亲戚有一些少量的遗赠,他把
所有财产都留给了妻子。
在律师事务所,律师和佩尔夫人把财产清点了一遍,事情办完后,这位遗孀起身准备离
开。就在这时,律师从桌上的文件夹里拿出一个封口的信封,递给他的客户。
“我遵嘱把这个交给您。”他说,“是您的丈夫在过世前不久派人送来的。”律师脸色苍
白、神情拘谨,出于对一位遗孀的尊敬,他说话时脑袋偏向一边,目光低垂。“这似乎是私密
性质的,佩尔夫人。您肯定想拿回家独自阅读。”
佩尔夫人接过信封,出门来到外面的街道上。她在人行道上停住脚,摸了摸指间的那个
信封。是威廉写的一封告别信?很有可能。一封正式的信。——肯定很正式——冠冕堂皇、
一本正经。那男人不可能有别的表现。他这辈子从来没做过非正式的事情。
我亲爱的玛丽,我相信你不会允许我告别人世,让你心绪烦乱,但是你会继续遵守
在我们共同生活的这么多年妥善引导你的那些戒律。在任何事情上都勤勉努力、不失尊
严。厉行节俭。注意千万不可……等等,等等。
一封典型的威廉风格的信。
或者,有没有可能他在最后一刻放下身段,给她写了些优美动听的话?这也许是一封充
满浓情蜜意的信,类似某种情书,以充满感情的笔触感谢她用人生中的三十年陪伴他,熨了
一百万件衬衫、做了一百万顿饭、铺了一百万次床,这封信她可以一遍遍地反复品读,至少
每天读一次,她会把它永远珍藏在她梳妆台的匣子里,跟她的胸针放在一起。
谁也不知道人之将死会做些什么,佩尔夫人对自己说。于是她把信封夹在胳膊下,匆匆
返回家中。
她打开前门走进去,直接去了客厅,坐在沙发上,帽子没摘,大衣也没有脱。她拆开信
封,抽出里面的东西。她看到共有十五到二十张白色横格纸,对折着,左上角别着一根回形
针。每张纸上都密密麻麻写满了字,那种向前倾斜的字体,她再熟悉不过,可是她注意到信
的内容这么多,写得这么公事公办、整整齐齐,而且第一页的开头就不像一封令人愉悦的
信,她便开始心生疑虑。
她移开目光,给自己点了一支烟。她深吸一口,把烟放在了烟灰缸里。
她扫了一眼壁炉另一边的威廉的空椅子。那是一把褐色的皮扶手椅,座位上有个凹坑,
是这么多年他的屁股坐在上面形成的。在椅背的高处,皮革表面有一块椭圆形的深色斑痕,
是他脑袋曾经倚靠的地方。他经常坐在那张椅子里阅读,而她总是坐在他对面的沙发上,缝
纽扣、补袜子,或给他的一件上衣的臂肘处打补丁,时不时地,会有一双眼睛从书上抬起,
落在她身上,凝神注视,却又异样地毫无表情,似乎在盘算着什么。她从来都不喜欢那双眼
睛。淡蓝色的、冷冰冰的,很小,而且两眼离得很近,中间有两道深深的、透着不满的竖纹
把它们分开。这两只眼睛盯了她一辈子。即使此刻,独自在这房子里住了一星期之后,她有
时仍有一种不安的感觉,似乎它们还在那儿,到处跟着她,从门口、从空椅子、从半夜的窗
户盯着她看。
慢慢地,她把手伸进坤包,掏出眼镜戴上。然后,她把那些纸高高地举在面前,就着从
身后的窗户透进来的黄昏的光,开始看了起来:
我亲爱的玛丽,这封信是写给你一个人的,将会在我死后不久交到你手上。
看到这么多内容,请你不要惊慌。其实没有什么,我只是想要准确地向你解释兰迪
将会对我做的事情、我为什么同意他的做法,以及他的理论和他的愿景。你是我的妻
子,你有权了解这些事情。实际上你也必须知道详情。在过去的几天里,我曾非常努力
地试图跟你谈谈兰迪,但你十分坚决地不听我说。我已经告诉过你,这种态度是非常愚
蠢的,而且我发现也是不无自私的。它的根源多半在于无知,我绝对相信,只要你意识
到所有的事实,就会立刻改变想法。所以我希望,当我不在你身边时,当你不再感到心
烦意乱时,你能安下心来,仔细听听我通过这些纸告诉你的话。我向你保证,你读完我
的故事之后,心中的反感就会消失,取而代之的将是热忱。我甚至敢冒昧地希望,你会
为我所做的事情感到一点骄傲。
你在继续读信时,必须尽可能原谅我这种冷冰冰的风格,因为我知道只有用这个办
法才能清楚地向你传达我的意思。你知道,随着大限越来越近,我的内心自然充满了人
间的各种复杂情感。我每天都越来越沉湎于黯然神伤,特别是在傍晚,我必须严密地监
视自己,以免我的情感会在这些信纸上泛滥。
比如,我希望写一写你,写一写你是个多么令人满意的妻子,伴我度过这么多年,
我向自己保证,如果还有时间,如果还有气力,我下次一定会写。
我还有一种渴望,想谈谈我在过去十七年里生活和教学的牛津大学,谈谈这所大学
的辉煌,并且如果可能的话,稍稍解释一下能有幸在这里工作意味着什么。此时此刻,
在这间昏暗的卧室里,我所深爱的所有事情和地方,都潮水般向我涌来,那么明亮和美
丽,一如既往。今天,因为某种原因,我比任何时候都能更清楚地看到它们。伍斯特学
院花园里的湖畔小路,那是拉芙蕾丝经常漫步的地方。位于彭布罗克的校门。从马达兰
高塔上西眺所见的城市景致。基督教堂的宏伟大厅。圣约翰分校的小假山庭院,我在那
里数出了十几种不同的风铃草,包括稀罕而精致的聚花风铃草。可是,你瞧!还没有开
始说正文,我就已经落入了陷阱。好吧,让我言归正传。亲爱的,请你慢慢地读,不要
带有任何忧伤或不满的情绪,那可能会干扰你的理解。请向我保证,你会读得很慢,而
且在开始前会让自己处于一种冷静和耐心的心境中。
我人到中年突然遭遇病魔,关于疾病的细节你已全然知晓,在此我就不必再费笔墨
——我只想承认,当初没有早些去看医生是何等的愚蠢。癌症是现代医药不能治愈的几
种顽疾之一。如果尚未快速扩散,是可以进行手术的。然而,我不仅发现得太迟,而且
癌细胞厚颜无耻,竟然攻击了我的胰腺,使我既无法手术,也无法继续存活。
因此,我只剩下大约一到六个月的生命,随着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我的心情
越来越忧郁——接着,突然之间,兰迪来了。
那是六星期前一个星期二的上午,时间很早,还不到你的探视时段,他一走进来,
我就知道有一件疯狂的事情即将发生。他不像我的其他探视者那样,踮着脚轻轻地进
来,怯生生的,神色尴尬,不知道说些什么。他踌躇满志、面带微笑地走进来,大步走
到床前,站在那里低头看着我,眼睛里闪烁着野性的亮光,然后他说:“威廉,我的孩
子,这太完美了。你正是我想要的人!”
也许我应该向你解释一下,约翰·兰迪从未去过我们家,你即使见过他,次数也很有
限,但是在最近九年里,我本人跟他关系很友好。我首先是一位哲学教师,这自不用
说,但你知道,我近些年对心理学也有大量的涉猎。因此,兰迪的兴趣和我有着少许的
重叠。他是一名出色的神经外科医师,属于出类拔萃者之一,最近,他非常慷慨地让我
学习他的某些研究成果,特别是脑前额叶切除术对各种精神病患者的不同影响。因而你
就能明白,当他在星期二上午突然闯进我病房时,我们俩绝对不能算是素昧平生。
“瞧瞧,”他拖了把椅子在我床边坐下,说道,“再过几个星期,你就要死了。对
吗?”
这个问句从兰迪嘴里说出来,似乎并没有特别的恶意。从某个方面来说,有一位探
视者勇敢地触及这个禁忌的话题,倒令人精神为之一振。
“你将会在这间病房里咽气,然后他们会把你抬出去,实行火葬。”
“土葬。”我说。
“那就更糟糕了。然后呢?你相信自己会进天堂吗?”
“我感到怀疑,”我说,“不过这么想想的话倒是令人欣慰。”
“或者会下地狱?”
“我不太明白他们为什么要把我送去那儿。”
“你永远不会知道,我亲爱的威廉。”
“说这些话有什么意义?”我问。
“是这样的,”他说,我能看到他在密切地观察我,“从个人角度来说,我不相信在你
死亡之后,你还能再听到你自己的消息——除非……”说到这里,他停住了,笑微微地凑
上前来,“……除非,当然啦,你明智地把自己交到我的手里。你愿意考虑一个建议
吗?”
他那样专注地凝视我、研究我,带着某种异样的渴望评估我,就好像我是柜台上的
一块特级牛排,他已经买下,正等着别人把它包起来。
“我是郑重其事地在问你,威廉。你愿意考虑一个我的建议吗?”
“我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
“那就听我详细告诉你。你愿意听吗?”
“你愿意说就说吧。反正我听了也不会损失什么。”
“正好相反,你将会得到很多东西——特别是在你去世之后。”
我相信他以为我听了这话会惊跳起来,但不知怎的,我对此早有准备。我静静地躺
着,注视着他的脸,看着他慢慢绽开一口白牙的微笑,他笑起来嘴巴左边总会露出套在
犬齿上的那颗假牙的金环。
“威廉,我为这件事已默默工作了好几年。这家医院也有一两个人在帮我,特别是莫
里森,我们已用实验动物完成了许多比较成功的试验。在目前这个阶段,我准备好了在
人身上做尝试。这是一个宏伟的想法,起初可能听起来有点儿不靠谱,但是从外科手术
的角度来看,似乎没有任何理由不认为它或多或少是可行的。”
兰迪探身向前,把两只手都放在我的床沿。他的脸很周正,有一种骨感的英俊,丝
毫没有平常医生的那种样子。你知道那副神情,大多数医生都有。他们的眼球朝你闪
着,露出那副神情,像一个毫无生气的电子招牌,上面印着“只有我能救你”。可是约翰·
兰迪的眼睛又大又亮,眼眸中间闪烁着点点兴奋的光。
“很久以前,”他说,“我看过一个医疗短片,是从俄国带过来的。那片子相当恐怖,
但很有趣。在片子里,一只狗的脑袋完全从身体上切断,但是依靠一颗人造心脏,通过
动脉和静脉维持着正常的血液供给。关键在于:那只狗的脑袋,孤零零地放在某种托盘
上,仍然活着。大脑还在运作。他们通过几个实验证明了这点。比如,当把食物抹在狗
的嘴唇上时,舌头会伸出来把它舔掉;有人在房间里走动时,狗的眼睛会跟着转动。
“似乎有理由从中得出结论,头和大脑不需要跟身体其他部分相连才能继续存活——
当然啦,条件是要能维持适当的含氧血的供给。
“重点来了。看这部片子使我产生了一个想法,就是把一个人的大脑从颅骨里取出
来,作为一个独立部件,让它在那人死后无限的时间里继续存活和运转。比如,你的大
脑,在你死去之后。”
“我不愿意。”我说。
“别打断我,威廉。让我把话说完。我从接下来的实验中可以看出,大脑是一件特别
能够自给自足的东西。它自己制造脑脊液。大脑内部进行思维和记忆的神奇过程,显然
并不会因为肢体、躯干,甚至颅骨的缺失而受损,只要,就像我说的,在合适的条件下
不断泵入正确的含氧血。
“我亲爱的威廉,请稍微考虑一下你自己的大脑吧。它形状完美无缺。里面塞满了你
一辈子的学识。你多少年埋头治学,才造就了它现在这样子。它刚刚开始产生一些一流
的创新思想。然而,它很快就要随着你身体的其他部分一起死去,就因为你那愚蠢的小
胰腺被癌细胞所侵蚀。”
“不了,谢谢。”我对他说,“你可以打住了。这是一个令人厌恶的想法,即使你能做
到——对此我深感怀疑,也基本上是毫无意义的。如果我不能说话,没有感觉,听不见
也看不见,让我的大脑活着有什么用呢?就我个人来说,我想不出比这个更让人反感的
事了。”
“我相信你肯定能够跟我们交流。”兰迪说,“说不定你还能拥有一定的视力。不过慢
慢来吧。我稍后再过来商量细节。事实是不管发生什么,你过不了多久就会死去,我的
计划是到你死亡之后才需要触碰你。考虑一下吧,威廉。真正的哲学家都不会反对把自
己的尸体用于科学事业的。”
“这并没有完全说服我。”我回答,“在我看来,当你在我身上动完手脚之后,将会很
难判断我到底是死是活。”
“是啊,”他微微笑着说,“我估计这点你是对的。但我认为你不应该这么快就回绝
我,你还是多了解一点再答复我吧。”
“我说了我不想听。”
“抽支烟吧。”他说,把烟匣子递了过来。
“我不抽烟,你知道的。”
他自己拿出一支,用一个小巧玲珑、跟一先令硬币差不多大的银质打火机把它点
燃。“这是给我做仪器的人送的礼物。”他说,“很别致,是不是?”
我仔细看了看打火机,然后递了回去。
“我可以继续说了吗?”他问。
“还是不说为好。”
“你就静静地躺着听吧。我认为你会发现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事。”
我床边一个盘子里有一些蓝色的葡萄。我把盘子放在我的胸口,开始吃葡萄。
“在死亡的那一刻,”兰迪说,“我必须站在旁边,这样才能立即上前采取措施,让你
的大脑保持存活。”
“你是说把它留在脑袋里?”
“一开始是的。只能这样。”
“在那之后你把它放在哪儿?”
“如果你想知道,我不妨告诉你,放在一个盆里。”
“你真的没开玩笑吗?”
“我当然没开玩笑。”
“好吧。接着说。”
“我想你大概知道,当心脏停止跳动,大脑缺少了新鲜的血液和氧气,它的组织会迅
速死亡。在四到六分钟里,整个大脑就会死去。即使只过了三分钟,也有可能遭到某种
程度的损害。因此,我必须迅速采取措施,阻止这种情况的发生。但是在机器的帮助
下,这应该是很容易的。”
“什么机器?”
“人造心脏。我们对亚历克西·卡雷尔和林德伯格的创造发明做了巧妙的改良。它能给
血液供氧,保持合适的温度,在适当的压力下泵出血液,还能做许多其他必要的事情。
真的一点儿也不复杂。”
“告诉我,在死亡的那一刻你会做什么?”我说,“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你了解大脑的动脉和静脉结构吗?”
“不了解。”
“那就听着,这不难理解。大脑的血液供给主要来自两个渠道,颈内动脉和椎动脉。
它们各有两条动脉,一共是四条。听懂了吗?”
“懂了。”
“回送系统就更简单了。血液通过两条大静脉,颈内静脉,流出去。这样你就有四条
上行的动脉——当然,它们通到颈部——和两条下行的静脉。它们在大脑周围自然分流
到其他渠道,但那些跟我们无关。我们永远不会触碰它们。”
“好吧。”我说,“想象一下我刚刚咽气。现在你会怎么做?”
“我应该立刻切开你的脖颈,找到那四条动脉,颈动脉和椎动脉。然后我应该对它们
进行灌注,也就是说,我会往每条动脉里插入一根大空心针。这四根针都通过管子与人
造心脏相连。
“接着,我快速行动,把左侧和右侧的颈内静脉都解剖出来,也与人造心脏相连,完
成整个循环。现在开动机器,合适的血液已经预先准备好了,大功告成。你大脑中的血
液循环将会恢复。”
“我就会跟那条俄国狗一样。”
“我认为不会。首先,你死后肯定会失去意识,我非常怀疑很长一段时间你恐怕都醒
不过来——最终能不能苏醒还不一定。但是,不管有没有意识,你都会处于一个非常有
趣的状态,是不是?你将会拥有一具冰冷的身体和一个活着的大脑。”
兰迪停住话头,咂摸这令人愉快的前景。此人被这整个想法迷住了,简直如痴如
醉,显然很难相信我会有另外的感觉。
“然后我们就不着急了,可以慢慢来。”他说,“请相信我,我们会需要很多时间。我
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你推进手术室,当然啦,那台机器也得跟着,它必须一刻也不
停止地泵动。接下来的问题是……”
“好了,”我说,“够了。我不必听具体细节。”
“哦,你必须听。”他说,“你应该准确地了解你从头到尾会经历什么,这很重要。事
后,当你恢复了意识,如果能够回忆起自己是在什么地方,又是怎么在那里的,从你的
角度来说就会安心得多。就算是只为了你自己内心的宁静,你也应该知道。你同意吗?”
我静静地躺在床上,注视着他。
“所以,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把你的大脑完整无损地从你的尸体上移除。尸体已经没
有用了,实际上它已经开始腐烂。颅骨和脸也毫无用处,它们都是累赘,我不需要它
们。我需要的只有大脑,干净、漂亮的大脑,十全十美,依然活着。因此,当我把你搬
到桌上时,我会拿起一把锯子,一把小小的摆锯,用它开始锯掉你的整个头颅。这时候
你仍然没有意识,所以我无须使用麻药。”
“你这该死的。”我说。
“你完全没有知觉,我可以向你保证,威廉。别忘了你几分钟前刚刚咽气。”
“没有人能不用麻药就把我的头颅锯下来。”我说。
兰迪耸了耸肩。“这在我看来没什么区别。”他说,“如果你想要,我很愿意给你一点
普鲁卡因。只要能让你高兴一点,我可以用普鲁卡因浸透你的整个头皮,整个脑袋,从
脖子往上。”
“非常感谢。”我说。
“你知道,”他继续说道,“有时候会发生一些很蹊跷的事。就在上个星期,一个男人
神志不清地被带进来,我没用任何麻药就给他开颅,清除一小块血栓。我还在头颅里忙
活着呢,他突然醒了,开始说话。
“‘我在哪儿?’他问。
“‘在医院里。’
“‘哟,’他说,‘真想不到。’
“‘请告诉我,’我问他,‘我的动作会让你感觉到难受吗?’
“‘没有,’他回答道,‘一点也没有。你现在在做什么呢?’
“‘我在清除你脑子里的一块血栓。’
“‘是吗?’
“‘老实躺着,不要动。我快要完事了。’
“‘看来就是这讨厌的东西害得我动不动就头疼。’那人说。”
兰迪停住话头,想起当时的情景,露出了微笑。“这是那个人的原话。”他继续说
道,“不过,第二天他完全不记得这件事了。大脑真是个奇怪的玩意儿。”
“我要普鲁卡因。”我说。
“你会如愿的,威廉。我刚才说到,我会拿一把小小的摆锯,小心翼翼地锯下你的整
个颅盖——也就是整个颅骨。这样一来,大脑的上半部就暴露在外了,准确地说,暴露
的是包裹大脑的外壳。不知你是否了解,大脑周围有三层独立的覆盖膜——外面一层叫
硬脑膜,中间一层叫蛛网膜,里面一层叫软脑膜。外行人多半以为,大脑是一个赤裸的
东西,漂浮在你脑袋里的液体中。其实不是。它被这三层结实的膜包裹得严严实实,脑
脊液实际上是在两层内膜的狭小缝隙间流动,这缝隙被称为蛛网膜下腔。就像我刚才告
诉你的,这个脑脊液是大脑产生的,通过渗透进入静脉系统。
“我很想把这三层膜都留下——它们的名字是不是很可爱?硬脑膜、蛛网膜、软脑膜
——我会让它们都保持完好无损。这么做有许多原因,尤其是硬脑膜里存在着静脉通
道,它们把大脑里的血液送入颈静脉。”
“现在,”他继续说道,“我们已经把你颅骨的上半部拿开,露出了包裹在硬脑膜里的
大脑顶。接下来的一步非常棘手:把整个大脑剥离出来,使它能够干净利落地被拎起
来,下面悬着四根供血动脉和两条静脉的断根,准备重新连接到机器上。这是一项极为
繁琐和复杂的工程,涉及细致地凿去许多骨头,切断许多神经,剪断并扎紧数不清的血
管。要想成功地完成这件事,唯一的办法是拿一把咬骨钳,慢慢地咬掉你剩下来的颅
骨,像剥橘子一样把它往下翻,直到脑膜的侧面和底部全部暴露出来。其中所涉及的难
点是高度技术性的,我在此就不一一赘述了,但我有相当的把握,这项工作能够完成。
这是个手术技术和耐心的问题。别忘了我有的是时间,要多少有多少,因为人造心脏会
一直在手术台旁边泵动,让大脑保持存活。
“好了,让我们假设我已经把你的颅骨成功剥离,把大脑周围的其他东西统统清除。
现在大脑只有底部与身体相连,主要是通过脊柱和两条大静脉,以及给大脑供血的四条
动脉。接下来怎么办呢?
“我会切断第一颈椎上方的脊柱,同时格外当心不要损坏那个区域的两条椎动脉。你
千万别忘了,这地方的硬脑膜是敞开接纳脊柱的,所以我必须缝合硬脑膜的边缘,关闭
这个开口。那样就没有问题了。
“这个时候,我将准备采取最后一个步骤。在旁边的一张桌子上,我放着一个特殊形
状的盆,里面盛满了我们所谓的林格氏液。那是神经外科用于冲洗的一种专门液体。现
在我要切断供血的动脉和静脉,把大脑完整地剥离出来。然后我只要用双手把它捧起
来,送到盆里去就行了。在整个过程中,这是唯一需要切断血流的环节。一旦到了盆
里,只需片刻就能把动脉和静脉的断根与人造心脏相连接。
“然后就大功告成了。”兰迪说,“你的大脑在盆里,依然活着,没有任何理由不会继
续存活很长时间,只要我们仔细留意血液和机器,年复一年地活着也有可能。”
“它会再运行吗?”
“亲爱的威廉,我怎么能知道呢?我甚至无法得知它会不会恢复意识。”
“如果恢复了呢?”
“那太好了。”兰迪说,“会非常神奇!”
“是吗?”我说,不得不承认我心存疑虑。
“那还用说!在那里,你的思维过程将美丽地进行,还有你的记忆……”
“却不能看见、不能触摸,闻不到、听不见,也不能说话。”我说。
“啊!”他喊道,“我就知道我忘了点什么!我没有跟你说眼睛的事。听着。我要争取
让你的视神经保持完好,还有眼睛本身。视神经是一个很小的东西,像体温计那么粗,
大约两英寸长,连接在大脑和眼睛之间。它妙就妙在其实根本不是一根神经,它是大脑
本身的一个外囊,硬脑膜顺着它延伸,与眼球相连。因此,眼球后部与大脑的接触非常
密切,脑脊液直接流向眼球。
“这一切都非常符合我的目的,使我有理由推测我能成功地保留你的一只眼睛。我已
经制作了一个装眼球的小塑料匣子,代替你自己的眼窝,当大脑被放进盆里,浸没在林
格氏液中时,匣子里的那个眼球将会浮在液体表面。”
“瞪着天花板。”我说。
“是的,我想是这样的。说来遗憾,不会有任何肌肉让眼球得以转动。不过,静静
地、舒舒服服地躺在那里,从你的盆里望着这个世界,可能也是某种乐趣呢。”
“真滑稽。”我说,“再给我留一只耳朵怎么样?”
“这次我还是不考虑耳朵了。”
“我要一只耳朵。”我说,“我坚持要一只耳朵。”
“不行。”
“我想听巴赫。”
“你不理解那个难度有多大。”兰迪温和地说,“听觉器官——也就是所谓的耳蜗——
是比眼睛复杂得多的一种精密构造。更麻烦的是,它被骨头所包裹。耳朵与大脑相连的
听觉神经也有一部分在骨头里。我不可能把这一整套东西完好无损地凿出来。”
“你就不能让它包在骨头里,然后再把那块骨头放进盆里吗?”
“不行。”他坚决地说,“这件事本身已经够复杂的了。而且,只要眼睛管用,听力其
实根本没有什么关系。我们完全可以把信息举在你眼前让你读。你真的必须让我来判断
什么是可能的,什么是不可能的。”
“我还没有说我同意这件事呢。”
“我知道,威廉,我知道。”
“我不能肯定我很喜欢这个想法。”
“你难道情愿死去,彻底死去?”
“也许吧。我现在还不知道呢。但到时候我也没法说话,对吗?”
“当然。”
“那我怎么跟你交流呢?你怎么知道我有意识呢?”
“我们很容易就能知道你是否恢复了意识。”兰迪说,“普通的脑电图描记器就能告诉
我们这点。我们会把电极直接连在盆里你大脑的前额叶上。”
“你真的能够知道?”
“哦,这是肯定的。任何一家医院都可以做到这点。”
“可是我无法跟你交流。”
“事实上,”兰迪说,“我相信你可以。伦敦有一个人叫韦特海默,他在思想交流方面
做一些有趣的研究,我一直跟他有联系。大脑思考时会释放电子和化学物质,这点你是
知道的吧?它们是以波的形式释放的,类似于无线电波。”
“我对此略知一二。”我说。
“好吧,韦特海默制造出一种仪器,与脑部造影有几分相似,不过要灵敏得多,他声
称这仪器能在一定范围内帮助他辨读一个大脑正在思考的确切想法。仪器产生某种图
表,似乎可被翻译成文字或思想。你愿意我请韦特海默过来看看你吗?”
“不用。”我说。兰迪已经想当然地以为我接受了这件事,我对他的这种态度很反
感。“你走吧,让我清静清静。”我对他说,“你的催促是不会有任何结果的。”
他立刻站起身,朝门口走去。
“有一个问题。”我说。
他站住了,一只手放在门把手上。“请说,威廉。”
“这个问题很简单。你本人真的相信,我的大脑到了盆里之后,我的思维还能够完全
像目前这样运转吗?你真的相信,我能够像现在这样思考和推理,并且还能保持着记忆
的能力?”
“我认为是可以的。”他回答,“大脑还是同一个大脑。它还活着,没有受到损坏。实
际上,它完全未被触动。我们连硬脑膜都没有打开。当然啦,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切断
了通向它内部的每一根神经——除了那根视神经——这就意味着,你的思考不再会受你
感官的影响。你将生活在一个特别纯净、超凡脱俗的世界里。没有任何东西来干扰你,
甚至没有疼痛。你不可能感受到疼痛,因为没有了感知疼痛的神经。在某种程度上,那
简直是一种完美的状态。没有忧虑,没有恐惧,也没有饥饿。甚至没有任何欲望。只有
你的记忆和你的思想,如果留下来的那只眼球碰巧还管用,那你还能够看书。在我听来
这是相当令人愉悦的。”
“果真如此?”
“是的,威廉,是的。特别是对一位哲学博士来说,那将是一种无比精彩的体验。你
将能够以尚未有任何人企及的超然和宁静,反思这个世界的一切。到那时候,谁知道有
什么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呢?你也许会产生伟大的思想和方案,那些了不起的想法可能
会彻底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也未可知!你尽力想象一下你将能达到的那种专注的程度
吧!”
“以及失望的程度。”我说。
“胡说。不可能有任何失望。没有欲望就没有失望,而你是不可能有任何欲望的。至
少没有肉体的欲望。”
“我肯定能够记得我以前在这个世界的生活,我也许渴望返回其中。”
“什么,返回这个烂摊子!离开你那个舒适的盆,回到这个疯人院!”
“再回答一个问题吧。”我说,“你认为你能让它存活多久呢?”
“大脑?谁知道呢?也许年复一年,很久很久。条件将是十分理想的。拜那个人造心
脏所赐,大多数能引起变质的因素都不存在。血压始终保持恒定,这种情况在现实生活
中是不可能的。温度也是恒定不变的。血液里的化学成分接近完美。里面不会有任何杂
质,也没有病毒或细菌,什么都没有。当然啦,我不该妄加猜测,但我相信在这样的环
境下,一个大脑可以存活两三百年。现在我告辞了,”他说,“明天我会再来看你。”他快
步走了出去,而我,你可能会猜到,难免有点心烦意乱。
他离开后,我的第一反应是对整件事的强烈反感。总之,这听起来绝对不是一件好
事。我的所有智力完好无损,却要沦为一小坨发灰的、黏糊糊的东西,浸在一摊水里,
这想法有一些极端令人厌恶的东西,是荒谬、龌龊、邪恶的。还有一件事令我感到不
安,一旦兰迪把我弄进那个盆里,我肯定会体验到一种无助感。在那之后将没有退路,
没有办法抗议或解释。只要他们让我存活,我就只能被迫活着。
如果,打个比方,我无法忍受呢?如果发现那是极度痛苦的呢?如果我变得歇斯底
里呢?
没有腿可以逃跑。没有嗓子可以尖叫。什么也没有。我只能强颜欢笑,默默忍受两
个世纪。
我也没有嘴能够强颜欢笑。
就在这时,我突然冒出一个奇怪的想法:一条腿被截肢的人,不是经常会产生那条
腿还在的错觉吗?他不是告诉护士,他的那些不再拥有的脚趾痒得要命,如此等等吗?
这样的事情就在不久前我还听说过呢。
是啊。在同样的前提下,我的大脑,孤零零地躺在那个盆里,有没有可能产生关于
我身体的类似错觉呢?那样的话,我平常所有的病痛和不适都会潮水般涌来,我甚至不
能服下一颗阿司匹林来缓解症状。我可能会时而幻想自己腿部抽筋或严重消化不良,时
而又很容易地感觉到我那可怜的膀胱——你了解我的——胀得那么满,如果不赶紧排
空,肯定就会爆炸。
但愿不会。
我躺在病床上,久久地想着这些可怕的念头。突然,就在中午前后,我的心情开始
发生变化。我不再那么关心此事令人不快的方面,而发现自己能够从一个更理性的角度
审视兰迪的建议。我问自己,想到我的大脑不必在几个星期后死亡和消失,是不是多少
令人感到一丝欣慰呢?确实如此。我很为自己的大脑感到骄傲。它是一个敏感、通透、
肥沃多产的器官,蕴含着惊人的信息储备,而且仍然能够产生富有想象力和创新性的思
想。说一句大言不惭的话,作为大脑来说,它是绝对出类拔萃的。而我的身体,我这具
可怜的破身体,兰迪想要丢弃的旧皮囊——是啊,就连你,我亲爱的玛丽,也不得不同
意我的看法:它确实不再有任何值得保存的价值了。
我仰面躺着,吃着一颗葡萄。真好吃啊,里面有三粒小小的籽,我从嘴里取出来,
放在盘子的边缘。
“我同意做。”我轻声说,“是的,苍天在上,我同意做。等到兰迪明天再来看我的时
候,我就立刻告诉他,我同意做。”
就这么迅速地决定了。从那以后,我的感觉大有好转。我狼吞虎咽地吃下分量惊人
的午餐,令每个人都感到吃惊,不久之后,你就像平常一样来探视我了。
你对我说,我看上去气色真好。那么愉快、活泼、容光焕发。发生了什么事吗?有
什么好消息吗?
是的,我说,确实有事。然后,不知你是否记得,我请你坐下来,尽量坐舒服一
些,我立刻开始用尽量委婉的口气向你解释将要发生的事。
然而,你根本不听。我刚讲了几个最明显的细节,你就大为恼火,说这件事恶心、
可怕、令人厌憎、不可想象,我还想继续往下说,你却大步走出了病房。
是啊,玛丽,就像你知道的,在那以后我曾多次试图谈论这个话题,可是你固执地
拒绝听我说话。因此,我只能希望你能明智地让自己读读这封信。我写它花了很长时
间。从我草草写下第一行文字,已经过去了两个星期,现在我比那个时候虚弱多了,我
恐怕没有力气再说更多。当然啦,我不会跟你诀别,因为有一种可能,有一种很小很小
的可能,兰迪的计划会成功,我以后真的还能再见到你,我是说如果你有勇气过来看望
我的话。
我吩咐他们在我死亡一星期后把这些纸交给你。因而,此刻你坐在这里读这些文字
时,兰迪采取行动已经有七天了。你恐怕都不知道结果如何。如果你真的不知道,如果
你故意保持距离,不愿意与此事有任何瓜葛——我怀疑可能会是这种情况——那么请你
现在就改变主意,给兰迪打个电话,看看我的状况怎样。这是你至少能做到的事。我已
经对他说过,在第七天可能会接到你的电话。
你忠实的丈夫
威廉
又及:我离开后你要循规蹈矩,永远记住做一个寡妇比做一个妻子更难。不要喝鸡
尾酒,不要乱花钱,不要抽烟,不要吃油酥点心,不要抹口红,不要买电视机;夏天把
我的玫瑰花坛和假山庭院的杂草剪除干净。顺便提个建议,你把电话线拔掉吧,我不会
再使用它了。
威
佩尔夫人把最后一页手稿慢慢放在身边的沙发上。她的小嘴紧紧地噘了起来,鼻孔周围
有点泛白。
说真的!她还以为熬了这么多年之后,一个寡妇有权利得到一点点清静呢。
整件事情想起来实在太可怕了,残忍而可怕,令她不寒而栗。
她把手伸进包里,又掏出一支烟。她把烟点燃,深深吸了一口,在房间里吞云吐雾。烟
雾中,她可以看见那台漂亮的电视机,崭新、气派、闪着光泽,挑衅般地、同时又有点儿心
虚地盘踞在威廉曾经的工作台上。
如果他此刻看见那个,会怎么说呢?她猜想着。
她停下来,想起了他最后一次看见她抽烟的情景。那大约是一年以前,她坐在厨房敞开
的窗口,想在他下班前匆匆地抽一支。她让收音机大声播放舞曲,然后她转过身,想给自己
再倒一杯咖啡,却突然发现他站在门口,那么魁梧而阴鸷,那双可怕的眼睛向下盯着她,每
个眼眸中间闪着一个愤怒的小黑点。
在那之后的四个星期,他亲自支付家用开支,一分钱也没有给她,当然啦,他不知道她
在水池橱柜下的一个肥皂箱里,藏了六镑多的私房钱。
“怎么回事?”有一次吃晚饭时她问他,“你是担心我患上肺癌吗?”
“不是。”他回答。
“那我为什么不能抽烟?”
“因为我不喜欢,这就是原因。”
他还不喜欢孩子,其结果就是他们一直没有自己的孩子。
她的这位威廉,这个专门与她作对的家伙,此刻在哪里呢?
兰迪还在等她电话呢。她一定要给兰迪打电话吗?
其实也不一定。
她抽完烟,立刻又用烟蒂点燃了一支。她看着放在工作台上电视机旁边的电话。威廉叫
她打电话。他特意要求她读过信之后马上给兰迪打电话。她迟疑着,努力对抗着她还不敢完
全摆脱的那种根深蒂固的责任感。然后,她慢慢地站起身,走向房间那头工作台上的电话。
她在电话簿上找到号码,拨了过去,等待着。
“我想跟兰迪医生说话。”
“请问您是哪位?”
“佩尔夫人。威廉·佩尔夫人。”
“请您稍等。”
几乎立刻,兰迪就在电话那头说话了。
“是佩尔夫人吗?”
“我是佩尔夫人。”
短暂的停顿。
“我很高兴您终于来电话了,佩尔夫人。我希望您一切都好。”那声音温和、礼貌,不带
任何感情,“不知您是否愿意到医院来一趟?然后我们可以稍微聊聊。我猜您一定迫切地想知
道结果如何。”
她没有回答。
“我现在可以告诉您,总的来说,一切都进展得非常顺利。实际上比我所希望的还要好得
多。它不仅活着,佩尔夫人,而且具有意识。它第二天就恢复了神志。这是不是很有意思?”
她等待他继续往下说。
“眼睛也能看见了。这点我们确有把握,因为当我们把东西举在它前面时,脑电图上的挠
度立刻发生了变化。现在我们每天都给它看报纸。”
“什么报纸?”佩尔夫人尖锐地问。
“《每日镜报》。标题很大。”
“他讨厌《镜报》,给他看《泰晤士报》。”
那边停顿了片刻,然后医生说道:“没问题,佩尔夫人。我们会给它看《泰晤士报》的。
我们当然希望能尽我们所能让它感到快乐。”
“是他,”她说,“不是它。是他!”
“是他。”医生说,“是的,请您原谅。让他感到快乐。这也是我建议您尽快到这儿来的原
因之一。我认为,能看见您对他是有好处的。您可以表现出您是多么高兴再次见到他——比
如,朝他微笑,对他抛个飞吻什么的。知道您就站在旁边,对他来说肯定是一个安慰。”
长时间的停顿。
“好吧,”佩尔夫人终于说话了,她的声音突然变得温顺和疲惫,“我想,我最好过去看看
他怎么样了。”
“太好了,我就知道您会这样。我在这里等您。直接来我二楼的办公室。再见。”
半小时后,佩尔夫人到了医院。
“看到他的样子,您千万不要惊讶。”兰迪陪她走在一条过道里,说道。
“我不会的。”
“一开始您肯定会受到一点冲击。恐怕他目前的状态不是特别令人愉悦。”
“我不是因为他的相貌才嫁给他的,医生。”
兰迪转过身,凝神望着她。一个多么古怪的小女人,他想,一双大眼睛,神情里透着阴
沉和怨气。她的五官,曾经无疑是非常妩媚动人的,现在却已风韵殆尽。嘴巴松弛,两颊松
垂下坠,整张脸给人一种印象:经过这么多年不愉快的婚姻生活,它已然缓慢地、确定无疑
地松散成了碎片。他们默默地往前走了一会儿。
“您进去后,不用着急。”兰迪说,“只有当您把脸直接置于他的眼睛上方时,他才会知道
您的存在。那只眼睛一直睁着,但无法转动,所以他的视野非常狭窄。目前我们让它直视着
天花板。当然啦,他现在什么也听不见。我们可以爱聊什么就聊什么。就在这里面。”
兰迪打开一扇门,让她进入一个方形的小房间。
“如果是我,暂时不会靠得太近。”兰迪说着,把一只手放在她的胳膊上,“先跟我在这里
待一会儿吧,等你完全适应了再过去看他。”
房间中央一张高高的白桌子上,有一个洗脸盆那么大的超大白色搪瓷碗,六七根细细的
塑料管从碗里通出来。这些塑料管跟一大堆玻璃管相连,可以看见血液从玻璃管里流出和流
进那个心脏机器。机器本身发出一种低低的、有节奏的搏动声。
“他就在那里面。”兰迪指着那个盆说。盆太高了,她看不见里面的东西。“稍稍凑近一点
吧。不要靠得太近。”
他领她往前走了两步。
佩尔夫人伸长脖子,现在能看见盆里的液体表面了。液体很清,静止不动,表面浮着一
个椭圆形的小容器,约有一个鸽子蛋那么大。
“那里面是眼睛。”兰迪说,“您能看见吗?”
“能。”
“据我们所知,它仍然保持完好无损的状态。这是他的右眼,那个塑料容器上有一个透
镜,类似他自己曾经使用的眼镜。此时此刻,他可能看得跟以前一样清楚呢。”
“天花板没有什么可看的。”佩尔夫人说。
“这点不用担心。我们正在制订一个完整的计划,让他保持兴趣,但是一开始不想动作太
快。”
“给他一本好书。”
“我们会的,会的。您感觉还好吧,佩尔夫人?”
“是的。”
“那我们就再往前走一点,好吗,然后您就能看清全貌了。”
他领着她往前走,最后站在离桌子只有两米远的地方,现在她能直接看见盆里了。
“好了,”兰迪说,“这就是威廉。”
他比她想象的大得多,颜色也更深。表面布满了沟沟壑壑,她感到活像一颗巨大的腌核
桃。她可以看见四根大动脉和两根静脉的断根从他底部伸出来,巧妙地与那些塑料管相连。
随着心脏机器的每一次搏动,所有的管子都同时颤动一下,然后血液就会被推送进管子里。
“您必须探身向前,”兰迪说,“让您漂亮的脸庞位于他的眼睛上方,然后他就会看见您。
您可以对他微笑,朝他抛个飞吻。如果我是您,还会说几句好听的话。他不会听见,但我相
信他能明白大致的意思。”
“他讨厌别人朝他抛飞吻。”佩尔夫人说,“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有我自己的办法。”她
走向桌子边缘,探过身去,让她的脸位于盆的上方,然后往下直视着威廉的眼睛。
“你好,亲爱的。”她轻声说,“是我——玛丽。”
那只眼睛,跟以前一样明亮,以一种奇特的、凝神的专注,盯着她看。
“你好吗,亲爱的?”她说。
那个塑料容器是通体透明的,所以整个眼球都能看见。眼球底部与大脑相连的那根视觉
神经,看上去就像一截短短的灰色意大利面条。
“你感觉好吗,威廉?”
丈夫只有眼睛而没有脸,盯着这只眼睛,使人产生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她所要看的仅是
这只眼睛,于是她目不转睛地盯着它,慢慢地,它越变越大,最后成了她唯一能看见的东西
——似乎它本身就成了一张脸。眼球的白色表面纵横着一些细小的红色血管,在淡蓝色的虹
膜里,有三四条漂亮的浅黑色条纹从中间的瞳孔发散出来。瞳孔很大很黑,它的一旁映出一
个小小的光点。
“我收到了你的信,亲爱的,就立刻过来看看你怎么样了。兰迪医生说你的状态非常理
想。如果我说话慢一点,你也许能通过读我的唇语,多少理解一点我在说什么。”
毫无疑问,那只眼睛在注视着她。
“他们在想尽一切办法照顾你,亲爱的。这台奇妙的机器在一刻不停地泵动,我相信它比
我们其他人愚蠢的破心脏强多了。我们的心脏随时都可能崩溃,但你的心脏会永远跳动。”
她仔细端详着那只眼睛,想弄清是什么使它具有这样一种奇异的外观。
“你看上去很好,亲爱的,确实很好。真的。”
这只眼睛,看上去比他原来的那两只眼睛好得多,她对自己说。它似乎有那么一种柔
软,有一种平静、善良的特质,是她以前从未见过的。也许这跟眼睛正中间的那个点——瞳
孔——有关。以前威廉的瞳孔总是呈两个黑黑的小点,它们总是朝你射着光,刺入你的大
脑,把你直接看穿,它们总是立刻知道你要做什么,甚至知道你在想什么。而她此刻看着的
这只眼睛,却是大大的,柔软、温和,几乎像母牛的一样。
“您真的确定他是有意识的?”她问,并未抬起目光。
“是的,完全确定。”兰迪说。
“而且他能看见我?”
“毫无问题。”
“那不是太棒了吗?我猜他正在纳闷是怎么回事。”
“丝毫不会。他完全知道自己在哪里,为什么会在那里。他是绝不可能忘记这点的。”
“您是说他知道自己在这个盆里?”
“当然。如果他有说话的能力,也许此时就能跟您进行十分正常的对话。据我所知,这里
的这个威廉,跟你以前在家里认识的那个威廉,在精神上绝对不会有任何区别。”
“天哪。”佩尔夫人说,她停下来思考这个有趣的方面。
“你知道吗?”她对自己说,此刻她看着那只眼睛的后面,使劲盯着那样平静地躺在水下
的一大坨灰乎乎的烂核桃,“我丝毫不能确定我是否更喜欢他目前这种状态。事实上,我相信
我可以跟这样一位威廉非常舒服地共同生活。我完全能够应对这一位。”
“他很安静,是不是?”她说。
“他自然是很安静的。”
没有争吵和批评,她想,没有动辄发出的警告,没有必须服从的规矩,没有对抽烟的禁
令,晚上没有那双不满的、冷冰冰的眼睛从一本书上方盯着我,没有衬衫需要清洗和熨烫,
没有一日三餐需要准备——什么也没有,只有心脏机器的搏动,这声音听着还蛮令人舒心
的,肯定不会响到足以干扰电视的声音。
“医生,”她说,“我相信我突然对他产生了极为强烈的感情。这听起来奇怪吗?”
“我认为这完全可以理解。”
“他躺在这个小盆的水面下,看起来多么无助和沉默啊。”
“是的,我知道。”
“他就像一个婴儿,真的。他完全就像一个小小的婴儿。”
兰迪一动不动地站在她身后,注视着。
“好吧,”她盯着盆里,轻声说道,“从此以后,玛丽将会独自照顾你,你没有任何需要担
心的事情。医生,我什么时候可以带他回家?”
“您说什么?”
“我说,他什么时候可以回家——回到我自己的家里?”
“你在开玩笑。”兰迪说。
她慢慢地转过头,直视着他。“我为什么要开玩笑?”她问。她的脸上光彩熠熠,圆圆的
眼睛像两颗钻石一样明亮。
“他不可能被搬动。”
“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这是一个实验,佩尔夫人。”
“这是我的丈夫,兰迪医生。”
兰迪的嘴角出现了一抹奇怪的、不安的浅笑。“这个嘛……”他沉吟着。
“这是我的丈夫,您知道。”她的声音里没有怒气。她的话音很轻,似乎只是在提醒他一
个简单的事实。
“这是个很棘手的问题。”兰迪说着,舔了舔嘴唇,“您现在是一个寡妇,佩尔夫人。我认
为您必须接受这个事实。”
她突然从桌旁转过身,朝窗口走去。“我是认真的。”她说,伸手到包里去掏香烟,“我要
让他回去。”
兰迪注视着她把香烟叼在唇间点燃。难道是他完全弄错了?这个女人似乎有点古怪,他
想。看她的样子,她简直很高兴丈夫待在那个盆里。
他试着想象,如果是他妻子的大脑躺在那里,是她的眼睛从那个容器里盯着他看,他自
己会有什么样的感觉。
他不会喜欢。
“现在我们可以回我的办公室了吗?”他说。
她站在窗口,抽着香烟,看上去十分平静和放松。
“好的。”
她经过那张桌子时,停下来,再一次探头看着盆里。“玛丽现在要离开了,亲爱的。”她
说,“你丝毫也不用担心,明白吗?我们这就把你带回家,然后我们会尽快好好地照顾你的。
听着,亲爱的……”说到这里她顿住了,把香烟送到唇边,准备吸一口。
立刻,那只眼睛闪了一下。
她此刻正直视着它,她看见就在它的正中间,有一个细小的、但十分明亮的光点,那是
瞳孔缩小成的一个极度愤怒的微小黑点。
起初她没有动弹。她俯身站在盆边,把香烟高高举在唇边,注视着那只眼睛。
然后,她非常缓慢地而且刻意地,把香烟叼在双唇间,长长地吸了一口。她吸入得很
深,让烟在她的肺里停留了三四秒钟。接着,突然,呼——两股细细的烟从她鼻孔里喷出,
撞击盆里的水,翻滚着掠过水面,形成一团浓浓的青烟,笼罩了那只眼睛。
兰迪站在门边,背对着她,等待着。“快走吧,佩尔夫人。”他大声说。
“别这么气呼呼的,威廉。”她轻声说道,“怒气冲冲没什么好处。”
兰迪扭过头来看她在做什么。
“不会再有用了。”她耳语般地说,“因为从现在起,我的宝贝,玛丽叫你做什么,你就得
做什么。你明白吗?”
“佩尔夫人。”兰迪说着,朝她走过来。
“所以,别再淘气了,好吗?我的乖乖。”她说着,又抽了一口烟,“如今淘气的孩子是会
受到最严厉的惩罚的,这一点你应该知道的。”
此刻兰迪已站在她身边,抓住她的胳膊,开始温和而坚决地把她从桌旁拖走。
“再见啦,亲爱的。”她喊道,“我很快就回来。”
“别闹了,佩尔夫人。”
“他是不是很可爱?”她大声说,一双明亮的大眼睛抬起来看着兰迪,“他是不是很可亲?
我简直等不及要把他带回家了。”
首次出版于《吻了又吻》 19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