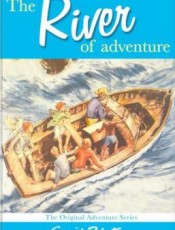升上天堂
这一辈子,福斯特夫人对于错过火车、飞机、轮船,甚至剧场开幕都有一种近乎病态的
恐惧。在其他方面,她并不是个特别神经质的女人,但只要一想到自己在这些事情上会迟
到,她就立刻紧张得不行,忍不住开始抽搐。倒也不严重——只是左眼角有一块小小的肌肉
在抽动,就像在偷偷眨眼——但恼人的是,要等她稳稳地赶上那趟火车、飞机或其他什么的
约莫一小时后,这抽动才会消失。
说来也很特别,对某些人来说,对赶不上火车这种事情的简单恐慌竟能成为一种严重的
困扰。还有半小时才到离家去车站的时间呢,福斯特夫人就已从电梯里走出来,做好了出发
的准备。她穿着大衣,戴着帽子和手套,完全坐不下来,心神不定、烦躁不安地从一个房间
游荡到另一个房间,直到她的丈夫——他一定十分清楚她的状态——终于从他的私密空间出
来,用一种冷淡、漠然的口吻提出,他们也许应该出发了,是不是?
福斯特先生可能有权对妻子的这种愚蠢感到恼火,但是他绝对没理由毫无必要地让她久
等,增加她的痛苦。当然,没有办法确定他是故意这么做的,但是每次他们要去什么地方,
他总是把时间掐得那么精确——是的,只晚那么一两分钟——而且他的态度那么冷漠,让人
很难相信他不是故意在暗地里恶毒地折磨这个不幸的女人。有一点他肯定心知肚明——她从
来不敢大声嚷嚷,催他赶紧。他在这方面把她调教得太好了。他肯定也知道,如果他故意一
直挨到超过保险时间的最后一刻,准会把她逼得几近歇斯底里。在他们婚后这些年里有过一
两次,他简直好像巴不得误了火车,就为了加剧这个可怜的女人的痛苦。
假设(不过谁也说不准)丈夫真的心存恶意,他这种态度就显得很不合理了,因为除了
这个无法控制的小缺点,福斯特夫人一向都是个贤惠、温柔的好妻子。三十多年来,她对丈
夫百依百顺,忠心耿耿,这点是毫无疑问的。她虽是个很谦逊的女人,但对此也心中有数。
这么多年以来她一直不让自己相信福斯特先生会故意折磨她,可是最近有许多次,她发现自
己心头开始产生了怀疑。
尤金·福斯特先生年近七旬,跟妻子一起生活在东六十二街一座六层楼的大房子里,用着
四个仆人。家里气氛沉闷,很少有人来串门。不过在一月里这个特殊的日子,家里充满活
力,一派忙忙碌碌的景象。一个女仆把一卷卷防尘布送到各个房间,另一个女仆把它们盖在
家具上。男管家把箱子拎到楼下,放在门厅里。厨子不停地从厨房窜出来,跟男管家说上一
句话。福斯特夫人自己穿着一件老式皮草大衣,戴着一顶黑帽子,从一个房间跑到另一个房
间,假装在监督这些行动。实际上她一心只想着如果丈夫不赶紧从书房出来,做好出发的准
备,她就赶不上飞机了。
“什么时间了,沃克?”男管家经过时,她问道。
“九点十分,夫人。”
“车来了吗?”
“来了,夫人,正等着呢。我这就把行李放进去。”
“到机场要一小时。”夫人说,“我的飞机十一点钟起飞。我必须提前半小时赶到那儿办手
续。我要迟到了。我就知道我肯定要迟到了。”
“我认为您来得及,夫人。”男管家亲切地说,“我提醒过福斯特先生,您必须在九点一刻
出发。还有五分钟呢。”
“是的,沃克,我知道,我知道了。拜托了,快把行李搬进车里吧。”
她开始在门厅里踱来踱去,每次男管家经过,她都要问他时间。她不停地告诉自己,这
一趟飞机绝对不能错过。她花了几个月才说服丈夫允许她远行。如果错过飞机,丈夫很有可
能认为她应该取消整个旅行。麻烦的是,他坚持要亲自送她去机场。
“仁慈的上帝啊,”她大声说,“我赶不上了。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肯定赶不上
了。”左眼角的那一小块肌肉此刻那么剧烈地抽动着。一双眼睛也马上就要落泪了。
“什么时间了,沃克?”
“九点十八分,夫人。”
“完了,这下我真的赶不上了!”她喊道,“哦,真希望他快点过来!”
这对福斯特夫人来说是一次很重要的旅行。她要独自去巴黎看望她的女儿,那是她唯一
的孩子,嫁给了一个法国人。福斯特夫人不怎么喜欢法国人,但她很爱自己的女儿,更重要
的是,她一直那么渴望亲眼见到她的三个外孙。她只在照片上看见过他们,她收到了许多照
片,把它们摆放在家里各个地方。那三个孩子都很漂亮。她对他们爱得发狂,每次收到一张
新的照片,她都要把它拿走,一坐很长时间,慈爱地盯着照片,寻找富有深意、令人欣慰的
血缘上的相似之处。最近她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她真不愿意在这样一个地方度过一生,在
这里她无法靠近那三个孩子,也不能让他们来看望自己,不能带他们去散步,给他们买礼
物,亲眼看着他们一天天长大。当然啦,她知道有这些想法是错误的,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是
不忠的,因为丈夫还活着呢。她还知道,丈夫虽然在他的许多企业里不再活跃,但永远不会
同意离开纽约,去巴黎生活。这次他竟然同意让她独自飞过去看望他们,并在那里待六个星
期,简直是一个奇迹。然而,哦,她多么希望能永远住在那里,跟孩子们近在咫尺啊!
“沃克,几点钟了?”
“九点二十二分,夫人。”
就在他说话时,一扇门开了,福斯特先生走进了门厅。他站立片刻,专注地看着妻子,
妻子也看着他——看着这个身材矮小,但仍然十分精悍的老男人,那张胡子拉碴的大脸庞,
与安德鲁·卡耐基的那些老照片惊人地相似。
“我说,”他说,“如果你想赶上那趟飞机,我认为也许我们应该很快就出发。”
“是的,亲爱的——是的!一切都准备好了。车正等着呢。”
“很好。”他说。他把脑袋偏到一边,凝神注视着她。他有一个奇怪的习惯,经常会把脑
袋往旁边一歪,并伴随着一连串快速的小抖动。他的这个姿势,还有他把双手交握在胸口的
样子,使他有点像一只松鼠站在那儿——中央公园里一只精明的老松鼠。
“沃克给你把大衣拿来了,亲爱的,穿上吧。”
“我很快就来。”他说,“只是去洗个手。”
她等着他,高个子男管家站在她身边,手里拿着大衣和帽子。
“沃克,我会误机吗?”
“不会的,夫人。”男管家说,“我认为您能赶上。”
接着,福斯特先生又出现了,男管家服侍他穿上大衣。福斯特夫人匆匆走到外面,钻进
了租来的凯迪拉克里。丈夫跟在后面,但他走下门前的台阶时步履缓慢,还停下来察看天
空,嗅了嗅清晨凛冽的空气。
“似乎有点起雾了。”他钻进车里,在她身边坐下时说道,“机场那儿的天气情况总是更糟
糕。如果那趟航班已经被取消,我也不会感到吃惊。”
“别这么说,亲爱的——拜托。”
他们不再说话,直到汽车过河驶往长岛。
“我把仆人们都安排好了。”福斯特先生说,“他们今天全都离开。这六个星期我付他们一
半的薪水,我对沃克说了,我们需要他们回来的时候会给他发电报。”
“是的,”她说,“他告诉我了。”
“我今晚就搬进俱乐部。住在俱乐部里,换换环境也不错。”
“是的,亲爱的。我会给你写信的。”
“我也会时不时地回到家里看看,确保一切都正常,顺便收收邮件。”
“可是,你真的不认为应该让沃克留下来,里里外外地照应一下吗?”她弱弱地问。
“说什么呢?根本没有这个必要。而且,这样我还得付他全额的薪水。”
“噢,是的。”她说,“当然。”
“更重要的是,把人单独留在家里,你永远不知道他们会闹出什么幺蛾子来。”福斯特先
生斩钉截铁地说,然后掏出一支雪茄,用一把小银刀剪去雪茄头,用金质打火机把它点燃。
夫人一动不动地坐在车里,双手在毯子下面紧紧攥在一起。
“你会给我写信吗?”她问。
“看情况吧,”他说,“不一定。你知道我对写信没什么兴趣,除非有什么特别的事情要
说。”
“是的,亲爱的,我知道。那就不用费事了。”
汽车顺着皇后大道继续往前开,靠近机场所在的那片开阔的沼泽地时,雾越来越浓,他
们不得不减慢车速。
“哦,天哪!”福斯特夫人喊道,“这下我肯定赶不上飞机了!现在几点了?”
“别大惊小怪。”老男人说,“反正也没关系。现在航班肯定要取消了。他们从来不在这样
恶劣的天气起飞。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还要出来白费工夫。”
她仿佛觉得他的语气里突然有了一种新的情绪,但她不能肯定,于是她转过脸看着他。
他的胡子太浓密了,很难看得清表情的变化。重要的是那张嘴。她希望能清楚地看见那张
嘴,这是她经常产生的愿望。他的眼睛从不会显露什么,除非在他发怒的时候。
“当然啦,”他继续说道,“万一飞机真的起飞了,那么我赞同你的意见——即使现在去也
肯定赶不上了。你为什么还不甘心放弃呢?”
她扭过脸,透过车窗看着大雾。车子越往前开,雾气越浓,现在她只能勉强分辨出马路
牙和路旁草地的边缘。她知道丈夫还在看着她。她又扫了一眼丈夫,这次她隐隐有些恐惧地
注意到,丈夫正专注地盯着她左眼角的那一小块地方,她可以感觉到那儿的肌肉在抽动。
“你会吗?”他说。
“我会什么?”
“现在肯定赶不上飞机了。在这样大雾弥漫的天气,车子不能开快。”
之后,他没有再对她说话。汽车像蜗牛似的往前爬。车上有一盏黄灯照着道路边沿,使
司机能继续往前开。其他的车灯,有的白色,有的黄色,不断地从雾中出现,朝他们逼近,
还有一盏特别明亮的车灯,一直紧紧地跟在他们后面。
突然,司机把车停下了。
“瞧!”福斯特先生喊道,“我们动不了啦。我就知道。”
“不,先生。”司机说着,转过身来,“我们已经到了。这就是机场。”
福斯特夫人一言不发地下了车,匆匆穿过入口处,走进机场。里面人山人海,大多是郁
郁不乐的乘客围在值机柜台旁边。她挤过去,跟那个职员说话。
“是的,”那人说,“您的航班暂时推迟了。但是请不要离开,我们估计这场大雾随时都会
消散。”
她回到仍坐在那里的丈夫身边,把这消息告诉了他。“你就别等了,亲爱的。”她说,“这
么做毫无意义。”
“我不等了。”他回答,“希望司机能送我回去。司机先生,你能送我回去吗?”
“我认为可以。”那人说道。
“行李拿出去了吗?”
“是的,先生。”
“再见了,亲爱的。”福斯特夫人说着,靠在车上,在丈夫被灰色大胡子遮盖的面颊上轻
轻吻了一下。
“再见。”他回答,“旅途愉快。”
对她来说,这一天剩下的时间简直像一场噩梦。她坐在尽量靠近航空公司柜台的一张板
凳上,坐了一小时又一小时,每过三十分钟左右,就起身上前去问职员情况有无变化。每次
都得到同样的回答——她必须继续等待,因为大雾随时都会散去。直到晚上六点过后,大喇
叭里才终于播出通知,说这趟航班被推迟到了第二天上午十一点。
听到这消息,福斯特夫人一时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她在板凳上又坐了至少半个小时,疲
惫地、恍恍惚惚地想着,她可以在哪儿打发这一夜。她不愿意离开机场。她不希望看见自己
的丈夫。她害怕他最终会以某种方式阻止她飞往法国。她真想就留在这里,在这板凳上坐一
整夜。这是最安全的。可是她已经精疲力竭,而且她很快就意识到,对于一个上了年纪的女
人来说,这么做是很荒唐的。于是,最后她走到电话前,给家里打了电话。
接电话的是她丈夫,他正准备离开家去俱乐部。她把情况告诉了丈夫,并问仆人们是否
还在家里。
“他们都走了。”他说。
“那样的话,亲爱的,我就自己去找一个房间过夜好了。你完全不用为此费心。”
“那样太傻了。”他说,“这儿有一栋大房子供你使用呢。过来住吧。”
“可是,亲爱的,房子里没有人。”
“那我就留下亲自陪你。”
“家里没有吃的。简直一无所有。”
“那你就吃过晚饭再回来。别这么愚蠢,女人。你不管做什么,似乎都想小题大做。”
“是的,”她说,“真对不起。我在这里给自己买个三明治,然后我就回家。”
外面,大雾已经散去了一点,但出租车还是慢慢地开了很久,她再次回到位于东六十二
街的家里时,已经很晚了。
丈夫听见她进门,便从书房里走了出来。“那么,”他站在书房门口,说道,“巴黎怎么样
啊?”
“明天上午十一点钟起飞。”她回答,“这是确定的。”
“你是说如果大雾消散的话。”
“已经在消散了。现在起风了。”
“你看上去很累。”他说,“你这一天肯定过得很焦虑。”
“确实不太舒服。我想直接去睡觉了。”
“我已经订了明天上午的车。”他说,“九点出发。”
“哦,谢谢你,亲爱的。我真心希望你不用大老远的再送我去机场了。”
“是的,”他慢悠悠地说,“我不送你去机场。不过,恐怕你没有理由不顺路把我送到俱乐
部。”
她看着他,在那一刻,他似乎站在离她很远的地方,远在某种界限之外。他突然变得那
么小、那么远,使她完全无法确定他在做什么、他在想什么,甚至不确定他是什么人。
“俱乐部在市中心。”她说,“不在去机场的路上。”
“但是你还有足够的时间,我亲爱的。你不愿意把我送到俱乐部吗?”
“哦,愿意——当然。”
“很好。那么我明天上午九点钟跟你碰面。”
她来到三楼自己的卧室,这一天把她累得够呛,刚躺下没多久就睡着了。
第二天,福斯特夫人很早就起床了,八点半的时候,她在楼下做好了出发的准备。
九点刚过,丈夫出现了。“你煮咖啡了吗?”
“没有,亲爱的。我以为你会在俱乐部吃一顿像样的早餐。车已经来了,正等着呢。我一
切都准备好了。”
他们站在门厅里——最近他们似乎总是在门厅里见面——她戴着帽子、穿着大衣、拿着
钱包,他身着一件款式奇怪的高翻领的爱德华式上衣。
“你的行李呢?”
“都在机场。”
“啊,是的。”他说,“当然。如果你要先送我去俱乐部,我们恐怕应该很快就出发,是不
是?”
“是的!”她大声说,“哦,是的——拜托了!”
“我要先去拿几支雪茄,很快就来。你先上车吧。”
她转身走到外面,司机站在那里,看到她走过来,为她打开了车门。
“几点了?”她问司机。
“差不多九点一刻吧。”
五分钟后,福斯特先生出来了,她看着他慢慢走下台阶,注意到他穿着那条窄窄的烟管
裤,两条腿很像山羊的腿。他跟前一天一样,半路停下来嗅了嗅空气,抬头察看天空。天气
仍然没有完全放晴,但迷雾中透出了一缕阳光。
“也许你这次能交到好运。”他一边说着,一边钻进车里,坐在她身边。
“拜托你快开车。”她对司机说,“不用管毯子了,毯子我自己来调整。快出发吧,我要迟
到了。”
那人坐回驾驶座,发动了引擎。
“再等一下!”福斯特先生突然说,“司机先生,稍等片刻,好吗?”
“怎么了,亲爱的?”她看见他在大衣口袋里找来找去。
“我有一件小礼物,想让你捎给艾伦。”他说,“咦,到底在哪儿呢?我相信我下楼时还拿
在手里的。”
“我没看见你手里拿着东西。是什么礼物?”
“一个白纸包着的小盒子。我昨天忘记给你了,今天可不能再忘记了。”
“一个小盒子!”福斯特夫人喊了起来,“我从没见过什么小盒子!”她开始在汽车的后座
上焦急地寻找。
丈夫继续在他的大衣口袋里找来找去。接着,他解开大衣的纽扣,在上衣里到处摸
索。“真该死,”他说,“我准是把它落在卧室里了。我去去就来。”
“哦,求求你!”她喊道,“我们没时间了!求求你别管它了!你可以邮寄过去。反正也不
过是一把那种没用的梳子,你总是送给她梳子。”
“我请问一句,梳子有什么问题吗?”他说,看到她竟然破天荒地出言不逊,他大为恼
火。
“没什么问题,亲爱的,肯定。可是……”
“等在这儿!”他吩咐道,“我去拿一下。”
“快点儿啊,亲爱的!哦,求求你快一点!”
她一动不动地坐着,等啊,等啊。
“司机先生,几点了?”
男人戴着手表,他看了看,“快到九点半了。”
“我们一小时能赶到机场吗?”
“差不多吧。”
就在这时,福斯特夫人突然发现在丈夫刚才坐的那侧座位的缝隙间,露出一个白色东西
的一角。她伸出手,抽出个用纸包着的小盒子,同时她忍不住留意到小盒子插得很紧、很
深,似乎是被人故意塞进去的。
“在这里!”她喊道,“我找到了!哦,天哪,他会在楼上找个没完没了!司机先生,快
——拜托你跑进去,叫他赶紧下来,好吗?”
那位司机长着一张桀骜不驯的爱尔兰人的小嘴,不太乐意做这种事情,但他还是下了
车,走上房子门前的台阶,接着他又转身回来了。“门锁着。”他大声说,“你有钥匙吗?”
“有——等一下。”她火烧火燎地在钱包里寻找。那张小脸因为焦虑而皱得紧紧的,嘴唇
像小孩子一样噘着。
“在这儿呢!不——我自己去吧。那样会快一些。我知道他会在哪儿。”
她匆匆下了车,走上门前的台阶,一只手里拿着钥匙。她把钥匙插进锁眼,刚要转动
——突然她停住了。她仰起脑袋,完全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整个身体凝固在这个急于转动
钥匙、进入家门的动作中,她等待着——五秒、六秒、七秒、八秒、九秒、十秒,她等待
着。看她站在那里的样子,脑袋高高仰起,身体绷得那么紧,似乎她在倾听中等待某种声音
再次响起——她刚才听见那声音从房子深处很远的地方传出。
没错——她显然是在倾听。她的整个身体都是倾听的姿势。看上去她确实把一只耳朵越
来越近地凑向房门。现在耳朵已经贴在门上了,她将这个姿势又保持了几秒钟,脑袋仰起,
耳朵贴着门,手放在钥匙上,准备进去但没有进去,而是凝神屏息地想要听到并且揣摩从房
子深处那个地方隐隐传来的声音,或者表面上看来是这样。
突然,她在瞬间行动起来。她把钥匙从门里抽回来,快步跑下了台阶。
“太晚了!”她对司机喊道,“我不能等他了,真的不能等了。我要赶不上飞机了。快抓紧
吧,司机先生,快!去机场!”
司机如果仔细地观察她,可能会注意到她的脸色变得煞白,整个神情都突然有了改变。
她脸上不再是那种非常柔顺的、傻乎乎的表情,她的五官有了一种奇怪的刚毅。那张一向那
么松弛的小嘴,现在紧紧地抿成一条线,她的眼睛发亮,说话时声音里透出一种新的权威。
“快点,司机先生,快点!”
“您丈夫不跟您一起旅行吗?”男人惊讶地问。
“当然不!我只是要把他送去俱乐部。没关系,他会理解的。他可以叫一辆出租车。别坐
在那儿废话了,先生!快开车!我还要赶飞机去巴黎呢!”
福斯特夫人在后座上催促着,司机一路开得很快,她提前好几分钟上了飞机。不一会
儿,她就飞到了大西洋的上空,舒舒服服地倚靠在飞机的座椅上,听着引擎的嗡嗡声,终于
要去巴黎了。那种新的情绪仍没有消失。她现在觉得自己格外强大,而且说来奇怪,感觉非
常美妙。当然啦,她有点儿喘不过气来,但纯粹是因为对自己所做的事情感到惊讶,而不是
其他原因,随着飞机离纽约、离东六十二街越来越远,一种异常的平静逐渐把她笼罩。当她
终于到达巴黎时,她已经如自己所愿,变得十分强大、冷静和镇定了。
她见到了三个外孙,他们比照片上还要美丽,一个个就像天使一样。她对自己说,好漂
亮啊。她每天带他们去散步,喂他们吃蛋糕,给他们买礼物,给他们讲动听的故事。
每个星期二,她都要给丈夫写一封信——写一封亲切的、唠唠叨叨的信——聊八卦,说
闲话,最后的结尾总是“一定要按时用餐,亲爱的,我担心在我不在的这段时间里,你可能不
会好好吃饭”。
六个星期过去了,她不得不回到纽约,回到丈夫身边。大家都感到依依不舍,只有她自
己好像并不难过。令人惊讶的是,她似乎不像人们以为的那样黯然神伤,当她跟他们吻别
时,她的行为态度以及她所说的那些话,似乎暗示着在不太遥远的将来,她还有可能回来。
不过,作为一个忠诚的妻子,她一天也没有多待。来到巴黎整整六个星期之后,她给丈
夫发了封电报,登上了返回纽约的飞机。
到了纽约的机场,福斯特夫人饶有兴趣地观察到并没有车来接她。她或许暗暗感到有点
好笑也未可知。但是她出奇地平静,对那个帮她把行李搬进出租车的脚夫,她并没有多给小
费。
纽约比巴黎冷,街道的排水沟里堆着肮脏的残雪。出租车在东六十二街的那座房子前停
住,福斯特夫人请司机帮她把两个大箱子搬到台阶顶上。她付钱让他离开后,按响了门铃。
她等待着,但无人应答。为了保险起见,她又按了一次,可以听见铃声在房子后部的食品储
藏室里刺耳地响着。但仍然没有人来开门。
于是她掏出钥匙,自己把门打开了。
她走进门,第一眼看到的是地板上有一大堆邮件,都是塞进邮箱后掉下来的。房子里昏
暗、阴冷。那台老爷钟上仍然盖着防尘布。虽然阴冷,气氛却是出奇的压抑,空气里有一股
淡淡的异味儿,是她以前从未闻到过的。
她快步走过门厅,往左一拐,绕到房子后部,消失了一会儿。这个行为有一种深思熟虑
的意味,目的性很强,她那样子似乎是去调查一个谣言或证实某种怀疑。几秒钟后,她回来
了,脸上隐约闪烁着一丝满意。
她在门厅中央停了停,似乎在考虑下一步该做什么。突然,她转过身,穿过门厅,走进
丈夫的书房。她在桌上发现了丈夫的地址簿,在里面查找了一会儿,然后拿起电话,拨了一
个号码。
“喂。”她说,“请听我说——这里是九大道东六十二街……是的,没错。您能尽快派个人
过来吗?是的,好像是卡在二楼和三楼之间了。至少指示灯上是这么显示的……现在就来?
哦,太感谢了。要知道,我的腿脚不太灵便,爬不了太高的楼梯。真是谢谢您了。再见。”
她把听筒放回原处,坐在丈夫的桌边,耐心地等待着很快就会来修电梯的那个人。
首次发表于《纽约客》 1954.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