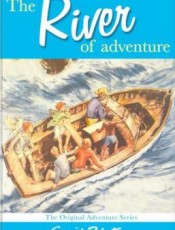征服者爱德华
路易莎抓着一块抹布,走出房子后面的厨房门,来到沁着凉意的十月阳光里。
“爱德华!”她喊道,“爱德华!午饭做好了!”
她顿了顿,侧耳细听,然后走到草坪上,并顺着草坪继续往前走——身后跟着一个小小
的影子——绕过玫瑰花坛,边走边用一根手指轻轻触碰着那个日晷。她是一个胖墩墩的矮个
子女人,但走起路来非常优雅,脚步轻快活泼,肩膀和胳膊轻柔地摆动。她经过那棵桑树,
走到砖路上,顺着砖路一直往前走,来到可以看见大花园尽头那一片坑洼处。
“爱德华!吃午饭!”
现在她能看见他了,约莫八十码 [1] 开外,在树林边坑洼处——那个瘦瘦高高的身影,穿
着卡其布裤子和墨绿色运动衫,双手拿着耙子,在一堆大篝火旁边干活,把荆棘耙到大火堆
顶上。火势熊熊,橘色的火焰跳动着,冒出乳白色的烟,烟飘回来笼罩花园,带有一股秋天
和焚烧落叶的好闻气味。
路易莎走下斜坡,朝丈夫走去。她如果愿意,完全可以再喊几声,让丈夫听见,但不知
怎的,那堆美妙的大篝火似乎在吸引着她往前,她走得很近,能感觉到热浪扑来,能听到噼
噼啪啪的声音。
“吃午饭。”她走上前去说。
“哦,是你。行——好的,我这就来。”
“这篝火真漂亮。”
“我决定把这地方彻底清理干净。”丈夫说,“这么多的荆棘,真让人厌烦透顶。”他的长
脸上汗津津的,胡子上沾着无数细小的汗珠,就像露珠一样,两道汗水顺着他的喉咙淌下
来,浸湿了运动衫的圆领。
“你最好当心点,别弄得太累了,爱德华。”
“路易莎,真希望你能别把我当成一个八十岁老人。活动活动腿脚不会有什么坏处。”
“是的,亲爱的,我知道。哦,爱德华!看!快看!”
男人转过身,看着路易莎,路易莎正指着篝火的另一侧。
“快看,爱德华!那只猫!”
一只很大的猫,颜色十分怪异,蹲在地上,离篝火那么近,有时候火舌似乎都舔到它身
上了。它一动不动,脑袋偏向一侧,鼻子高高竖着,用冷冰冰的黄眼睛注视着男人和女人。
“它会被烧着的!”路易莎喊道,她扔下抹布,飞快地冲过去,用两只手抓起那只猫,抱
着它迅速跑开,放在远离火焰的草地上。
“你这只疯猫。”她掸了掸双手,说道,“脑子发昏了吗?”
“猫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丈夫说,“你永远不会看到一只猫在做自己不愿做的事。永远不
会。”
“这是谁家的猫?你以前见过它吗?”
“没有,从没见过。这颜色真奇怪。”
猫已经蹲坐在草地上,正斜着眼睛打量他们。那双眼睛有一种模糊不清的内敛表情,似
乎无所不知又满含抑郁,十分奇怪,鼻子周围透着一种极为含蓄的轻蔑,似乎看到这两个中
年人——一个矮矮胖胖、脸蛋红润,另一个高高瘦瘦、满身是汗——是一件多少令人惊讶的
事,但又完全无关紧要。作为一只猫,它的颜色确实非常罕见——纯银灰色,没有夹杂一点
蓝色——而且猫毛很长,丝绸般柔顺。
路易莎弯下腰,抚摸它的脑袋。“你必须回家去。”她说,“乖乖地听话,回自己家里去
吧。”
男人和妻子开始爬上坡,往家里走去。那只猫站起身,跟在后面,起初保持着一定的距
离,但是慢慢地越挨越近。不一会儿,它就跟他们并排了,然后它跑在前面,领头穿过草
坪,走向房子,看它走路的派头,似乎这片地方整个都属于它。它的尾巴直直地竖在空中,
像一根桅杆。
“回家去,”男人说,“回家去。我们不收留你。”
可是,他们走进家门时,它跟他们一起进来了,路易莎在厨房里给了它一些牛奶。吃午
饭的时候,它跳到他们俩中间那把空椅子上,脑袋只比桌面高出一点,那双深黄色的眼睛不
停地慢慢从女人移向男人,再从男人移向女人,注视着整个用餐过程,直到结束。
“我不喜欢这只猫。”爱德华说。
“哦,我认为它是一只漂亮的猫。真希望它能留下来陪我们待一阵子。”
“你听我说,路易莎。这只猫不能留在这儿。它是别人的猫,走失了。如果它今天下午还
想赖在这里不走,你最好把它送去交给警察。他们会帮它找到家的。”
吃过午饭,爱德华继续去收拾花园。路易莎像往常一样走向钢琴。她是一位出色的钢琴
演奏者,是一位真正的音乐爱好者,几乎每天下午都会花一小时左右独自弹琴。那只猫此时
躺在沙发上,路易莎走过时停下来抚摸了它一下。猫睁开眼睛,打量了她一会儿,然后又闭
上眼睛,接着睡觉。
“你真是一只特别乖的猫,”路易莎说,“而且颜色这么漂亮。真希望我能留下你。”她用
手指抚摸猫头上的皮毛,突然摸到一个小小的肿块,就在右眼上面一点。
“可怜的猫。”她说,“你这漂亮的脸上有肿块了。你一定上了年纪。”
她走过去,坐在长长的琴凳上,但并没有立刻开始弹琴。她有一个独特的小乐趣,就是
把每天都当成开音乐会的日子,精心安排一份非常具体的节目单,然后再开始弹琴。如果弹
完一曲还要停下来考虑下一曲该弹什么,就破坏了弹琴的乐趣,那是她绝对不愿意的。每一
曲弹完后,她只需要一个短暂的停顿,让观众热烈鼓掌、大声叫好。幻想底下坐着观众真是
太美妙了。偶尔她弹琴的时候——那是在运气好的日子里——房间会开始晃动、隐去、逐渐
变暗,然后她就看到一排排的座椅,以及无数张白色的脸庞仰起来看着她,观众们听得全神
贯注、如痴如醉。
她有时是凭记忆弹琴,有时是看着乐谱。今天她想只凭记忆,她愿意这样。节目单该怎
么制定呢?她坐在钢琴前,一双小手叠放在大腿上,她是个面色红润的小胖子,有一张圆圆
的、但仍很漂亮的脸,头发在脑后盘成一个整整齐齐的圆髻。她看了一眼右边,发现那只猫
蜷在沙发上睡着了,在紫色沙发靠垫的衬托下,那银灰色的猫毛那么美丽。就用巴赫的曲子
开头怎么样?或者,维瓦尔第的更好。巴赫改编的《d小调大协奏曲》,好的——这是第一支
曲子。然后,也许可以来一点舒曼,《狂欢节》?那肯定很有趣。再往后——对了,弹点儿
李斯特换换风格吧,挑一首《彼特拉克十四行诗》,就挑第二首——这是最美的一首——e大
调。然后再来一点舒曼,就挑一支他的欢快曲目——《童年情景》。最后,作为返场曲目,
挑一支勃拉姆斯的圆舞曲,如果到时候感觉好,说不定会弹两支。
维瓦尔第、舒曼、李斯特、舒曼、勃拉姆斯。一份很漂亮的节目单,她可以不看乐谱,
轻松地弹下来。她把身体往钢琴前凑了凑,停顿了一下,等待观众席里的某个人——她已经
感觉到今天是一个运气好的日子——等待观众席里的某个人最后咳嗽一声。然后,带着几乎
伴随着她一举一动的那种舒缓和优雅,她把双手笼在琴键上,开始弹琴。
在那特定的时刻,她并没有看着那只猫——实际上,她已经忘记了猫的存在——但是,
当维瓦尔第的第一组深沉的音符在房间里轻柔地响起时,她通过眼角的余光注意到,她右边
的沙发上突然出现一片忙乱、一阵闪动。她立刻停止弹琴,“怎么回事?”她说,把目光转向
那只猫,“出什么事了?”
那只猫几秒钟前还睡得很香,此刻在沙发上坐得笔直,神情十分机警,它的全身都在颤
动,耳朵竖起,眼睛睁得大大的,紧盯着钢琴。
“我吓着你了吗?”路易莎温和地问,“也许你以前从没听过音乐。”
“不,”她对自己说,“我认为不是这样。”她又想了想,觉得猫的反应不像是出于恐惧,
它没有瑟缩,也没有后退。要说有什么不同,反而是它向前探过身,表现出一种热切,而且
那张脸——是啊,那张脸上的表情相当奇怪,似乎混杂着惊讶和错愕。当然啦,一只猫的脸
很小,几乎没有什么表情,但是如果你仔细观察眼睛和耳朵的同步动作,特别是一侧耳朵下
面那一小块活动的皮肤,你就能偶尔看到非常强烈的情感反应。路易莎此刻密切地注视着这
张脸,接着,因为她好奇地想看看第二次会有什么反应,就把双手放到琴键上,又开始弹那
首维瓦尔第。
这次,猫已经有所准备,一开始只是身体绷得更紧了点,但随着音乐逐渐饱满、加速,
进入赋格曲引子第一段的激越节奏,一种奇怪的、渐渐升华为狂喜的神情开始出现在猫的脸
上。它的两只耳朵刚才就直直地竖了起来,此刻慢慢往后缩,眼睑低垂,脑袋偏到一边。在
这一刻,路易莎可以发誓这只猫真是在欣赏音乐。
她看见的(或者她以为自己看见的)是她多次在那些全神贯注地听一段音乐的人们脸上
看到过的神情。当音乐完全把他们吸引住,使他们沉溺其中时,他们脸上就会出现一种独特
的、极度兴奋的表情,像微笑一样很容易识别。就路易莎所见,这只猫现在就几乎完全是这
样一副表情。
路易莎弹完了赋格曲,开始弹西西里舞曲,她一直留神注视着沙发上的猫。音乐停止
时,她终于得到了猫在听音乐的最后证据。猫眨眨眼睛,活动了一下身体,伸了伸一条腿,
换了一种更舒服的姿势,快速地扫了一眼房间,然后期待地看着路易莎这边。这完全就是一
个常去听音乐会的人,在交响乐的两个乐章之间的空隙暂时放松下来的样子。这做派活脱脱
像个人,使她胸口产生了一种焦躁的感觉。
“你喜欢这个?”她问,“你喜欢维瓦尔第?”
话一出口,她就感觉到荒唐,但是并没有——这么说她有点儿阴险——并没有她原来以
为会感觉到的那样荒唐。
好吧,暂时不管这个,还是接着弹奏节目单上的第二支曲子吧,那是《狂欢节》。她刚
开始弹,猫就又绷紧身体,坐得笔直。然后,它慢慢地、满怀喜悦地被音乐所笼罩,陷入那
种古怪的、忘乎所以的情绪,似乎跟溺亡和做梦有关。这只银灰色的猫坐在沙发上,被音乐
弄得这样心醉神迷,这真是夸张的一幕,也是滑稽的一幕。更加诡异的是,路易莎心想,猫
看似如此喜爱的这支曲子其实非常深奥、非常古典,是世界上大多数人都无法欣赏的。
也许,她想,猫并不是在欣赏音乐。也许,这只是一种催眠反应,就像蛇那样。是啊,
既然能用音乐给一条蛇催眠,猫为什么不行呢?但成千上万的猫每天都在收音机、留声机和
钢琴上听到这些音乐,而据她所知,从来没有哪只猫做出这只猫这样的行为。看这只猫的反
应,它似乎在专心欣赏每一个音符呢。这真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
但这不同时也是一件十分奇妙的事吗?确实如此。是啊,除非她弄错了,这简直就是个
奇迹啊,是那种一百年才会出现一次的动物奇迹。
“我看得出你喜欢这支曲子。”曲子弹完后,她说道,“真是对不起,我今天弹得不太好。
你最喜欢哪一支——是维瓦尔第的还是舒曼的?”
猫没有回答,于是,路易莎生怕失去这位听者的注意力,赶紧开始弹节目单上的下一支
曲子——李斯特的《彼特拉克十四行诗》第二首。
这时,一件非常反常的事情发生了。她刚弹了三四个小节,猫的胡须就开始明显地抽
搐。它慢慢地把身体挺得格外笔直,把头偏向一边,接着又偏向另一边,用一种凝神蹙眉的
神情盯着前面,似乎在说:“这是什么?别告诉我。我对它太熟悉了,只是一时好像有点想不
起来。”路易莎被迷住了,她半张着小嘴,微笑着,继续弹奏,等着看接下来到底会发生什么
事。
猫站起来,走到沙发的一头,又坐下了,接着听了一会儿。随后它突然跳到地板上,噌
地一下蹿上了琴凳,坐在她身边,专心致志地听着这首优美的十四行诗,此时它已不再如梦
如醉,而是非常警醒,那双大大的黄眼睛盯着路易莎的手指。
“结束!”路易莎说着,弹出最后一个和弦。“怎么,你过来坐在我身边了,是吗?跟沙发
相比,你更喜欢这里?好吧,我就让你留在这儿,但你必须一动不动,不许乱蹦乱跳。”她伸
出一只手,轻轻抚摸猫的后背,从脑袋一直摸到尾巴。“刚才是李斯特。”她继续说道,“听
着,他有的时候庸俗得可怕,但是在这一类曲子里,他真的很有魅力。”
她开始喜欢这种奇怪的动物哑剧了,于是便接着弹节目单上的下一支曲子:舒曼的《童
年情景》。
刚弹了一两分钟,她就意识到猫又挪了窝,此刻已回到沙发上的老地方。她刚才一直注
视着自己的手,大概就是因为这点没注意到猫的行为。不过,猫的动作肯定是极为迅捷而无
声的。猫仍然盯着她看,仍然一副专心聆听音乐的样子,可是在路易莎看来,它不像刚才听
前一支李斯特的曲子时那样充满狂热的激情了。而且,离开琴凳、回到沙发,这本身就是表
示一种委婉而坚决的失望。
“这是怎么了?”一曲终了,她问,“舒曼有什么问题?李斯特有那么神奇吗?”猫用两只
黄色的眼睛直盯着她,眼睛中间有一道漆黑的小竖条。
路易莎对自己说,事情真的开始变得有趣了——仔细想想,还有那么一点诡异可怕。但
是她看了一眼坐在沙发上的猫,它那么机敏、那么专注,显然正等着听更多的音乐,于是她
很快放下心来。
“好吧。”她说,“我把我的打算告诉你。我要专门为你调整我的节目单。你看上去这么喜
欢李斯特,我就再给你弹一支吧。”
她迟疑着,在记忆中搜寻李斯特的代表作,然后开始轻轻弹奏《圣诞树》的十二首小作
品之一。她一边弹,一边非常密切地注视着那只猫,首先她注意到猫的胡须又开始抽搐了。
猫从沙发跳到地毯上,一动不动地站立片刻,偏着脑袋,浑身兴奋地颤动,然后,它迈着缓
慢、柔滑的步子,绕过钢琴,一下子跳上琴凳,坐在了她身边。
就在这个时候,爱德华从花园回来了。
“爱德华!”路易莎喊道,一跃而起,“哦,爱德华,亲爱的!听听这个!听听发生了什么
事!”
“又怎么啦?”爱德华说,“我想喝点茶。”他长着一张有着尖鼻子的窄脸,脸色微微有些
发紫,整张脸上汗津津的,汗珠像一粒粒湿漉漉的长葡萄。
“是这只猫!”路易莎喊道,指着静静坐在琴凳上的猫,“你等着听刚才发生了什么吧!”
“我记得我叫你把它交给警察的。”
“可是,爱德华,听我说。这简直太让人兴奋了。这是一只懂音乐的猫。”
“哦,是吗?”
“这只猫能欣赏音乐,而且能理解音乐。”
“好了,别再胡言乱语了,路易莎,看在上帝的分上,快去沏点茶吧。我在外面砍荆棘、
生篝火,早就又热又累了。”他在一张扶手椅里坐下,从身边的盒子里取出一支烟,用盒子旁
边一个硕大的漆皮打火机把烟点燃。
“你还不明白呢,”路易莎说,“你在外面的时候,我们家里发生了一件特别令人兴奋的事
情,一件可以说是……嗯……简直是了不得的大事。”
“对此我毫不怀疑。”
“爱德华,拜托!”
路易莎站在钢琴旁,粉红的小脸比往常更红,两边面颊上各泛起一抹深红色。“如果你真
的想知道,”她说,“我就把我的想法告诉你。”
“我听着呢,亲爱的。”
“我认为,我们此时此刻可能面对着——”她停住话头,似乎突然意识到这个想法的荒
谬。
“什么?”
“你可能认为很荒唐,爱德华,但我真是这么想的。”
“看在上天的分上,我们面对着谁?”
“面对着弗朗兹·李斯特本人!”
她的丈夫缓缓地使劲抽了一口香烟,把烟喷向天花板。他皮肤紧绷,面颊凹陷,就像一
个戴了多年全口假牙的人,每吸一口烟,面颊都陷得更深一点,脸上的骨头突出,活像一具
骷髅。“我不明白。”他说。
“爱德华,听我说。根据我今天下午亲眼看到的情形,这真的可能是某种转世轮回。”
“你是说这只讨厌的猫?”
“求求你别这么说话,亲爱的。”
“你没生病吧,路易莎?”
“我一切都好,非常感谢。我只是有点儿迷糊——这一点我承认,但谁经历了这样的事
情,会不犯迷糊呢?爱德华,我向你发誓——”
“请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路易莎告诉了他。当她说话的时候,丈夫四仰八叉地躺在椅子里,两条腿伸在前面,吸
着香烟,把烟喷向上面的天花板。他嘴角含着一丝讥讽的笑。
“我没看出这有什么不同寻常的。”路易莎讲完后,他说,“没什么大不了——这是一只会
耍把戏的猫。它学会了耍把戏,仅此而已。”
“别说傻话了,爱德华。每次我一弹李斯特,他就兴奋不已,跑过来挨着我坐在琴凳上。
但是只有李斯特。没有人能教一只猫懂得李斯特和舒曼的区别。就连你自己也搞不清。可是
这只猫每次都这样。就连李斯特比较含蓄的曲子也不例外。”
“两次,”丈夫说,“他只这么做了两次。”
“两次就够了。”
“我们再看他做一次。来吧。”
“不,”路易莎说,“绝对不行。如果他真是李斯特——我相信是的,或者是李斯特的灵魂
什么的回来了,那么,绝对不应该让他做一大堆荒唐的测试,这甚至是很不人道的。”
“我亲爱的夫人!这是一只猫——一只相当愚蠢的灰猫,今天上午在花园里差点儿被篝火
烧掉了皮毛。而且,关于转世轮回你又知道些什么?”
“只要他的灵魂在,对我来说就足够了。”路易莎坚决地说,“那才是最重要的。”
“那么好吧。我们来看看他的表演。我们来看看他怎么区分他自己的东西和别人的东
西。”
“不,爱德华。我刚才对你说过了。我拒绝让他再做荒唐的马戏团测试。他这一天的表现
已经够了。不过我会告诉你我要做什么。我要再给他弹一些他自己的音乐。”
“那很能证明问题。”
“你仔细看着。有一点是确定的——他一听出是哪支曲子,就不会再肯离开他现在坐的那
张琴凳。”
路易莎走到乐谱书架前,拿下一本李斯特作品,快速地翻了翻,挑选了他的另一支练习
曲——b小调奏鸣曲。她本来只想弹作品的第一部分,可是开始之后,她看到猫坐在那里喜悦
得浑身发颤,用那种热烈而专注的眼神盯着她的双手,她就不忍心停止了。她把整支曲子弹
完。然后,她抬头看了一眼丈夫,微微笑了。“怎么样?”她说,“你不能否认他绝对热爱这支
曲子。”
“他只是喜欢这声音,仅此而已。”
“他热爱这曲子。是不是啊,亲爱的?”她说着,把猫抱到了怀里。“哦,天哪,如果他能
说话该多好啊。想想吧,亲爱的——他年轻的时候见过贝多芬!他认识舒伯特、门德尔松、
舒曼、柏辽兹、葛利格、德拉克洛瓦、安格尔、海涅和巴尔扎克。而且,让我想想……我的
天哪,他还是瓦格纳的岳父!我怀里居然抱着瓦格纳的岳父!”
“路易莎!”她丈夫严厉地说道,并一下子坐得笔直,“镇定一点。”他声音里有一种新的
情绪,说话嗓音也提高了。
路易莎飞快地抬头看了她丈夫一眼。“爱德华,我认为你是在嫉妒!”
“哦,当然,我当然是在嫉妒——嫉妒一只讨厌的灰猫!”
“那就别这么一副脾气暴躁、尖酸刻薄的样子。如果你一直是这个态度,最好还是回去干
你的园丁活儿,让我们两个清清静静地待着。这对我们大家都好,是不是呀,亲爱的?”她一
边对猫说着,一边抚摸着它的脑袋。“今天晚上,我们一起再欣赏一些音乐,你和我,再挑几
个你自己的作品。哦,对了,”她说,在猫的脖子上亲了几口,“我们还可以弹一点肖邦。你
不用告诉我——我碰巧知道你喜爱肖邦。你曾经跟他是亲密的朋友,是不是,亲爱的?实际
上——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你就是在肖邦的公寓里认识了你生命中的真爱,某某某夫
人。还跟她有了三个私生子,是不是?没错,没错,你这个淘气的家伙,你可不许否认。所
以,你还要听一些肖邦,”她说着,又亲了亲猫,“那可能会让你回忆起各种美好的往事,是
不是?”
“路易莎,立刻给我停止!”
“哦,别这么古板,爱德华。”
“你的表现像个十足的白痴,女人。而且,你忘了我们今晚要出去,要到比尔和贝蒂家去
打牌。”
“哦,但我现在不可能出去了。这是毫无疑问的。”
爱德华慢慢从椅子里站起身,然后弯下腰,把香烟用力捻灭在烟灰缸里。“跟我说实话
吧,”他轻声说,“你不是真的相信这些——相信你说的这些胡言乱语吧?”
“我当然相信。我想现在这已经没有任何疑问了。而且,我认为这赋予了我们一种非同小
可的责任,爱德华——赋予了我们俩。你也有份。”
“你知道我怎么想吗?”爱德华说,“我认为你应该去看医生。越快越好。”
说完,他便转过身去,大步走出了房间,跨过落地长窗,回到了花园。
路易莎注视着他大步走过草坪,走向他的篝火和他的荆棘,她一直等到他在视野中消
失,然后转过身,跑向前门,怀里仍然抱着那只猫。
她很快地钻进车里,驱车到镇上去。
她把车停在图书馆门前,把猫锁在车里,匆匆登上大楼的台阶,径直朝参考书阅览室走
去。她开始搜寻两大类图书的卡片——转世轮回和李斯特。
在转世轮回的类别中,她找到一本《生命轮回——寻踪探秘》,作者是密尔顿·威利斯,
出版于一九二一年。在李斯特的类别中,她找到两本传记。她把这三本书都借了出来,返回
车里,开车回家。
回到家中,她把猫放在沙发上,拿着三本书坐在猫的旁边,准备认真地读一读。她决定
先读密尔顿·威利斯的那本书。书不厚,还有点脏,但拿在手里感觉沉甸甸的,作者的名字有
一种很权威的味道。
她读到,转世轮回之道,是灵魂不断进化到更高的动物形式。
例如,人不可能重生为一个动物,就像成年人不会重新变成小孩子一样。
她把这段话又读了一遍。但他是怎么知道的呢?他怎么能这么肯定呢?不可能。这样的
事情,谁也不可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然而,下面这段话又使她大为泄气。
在我们每个人的意识核心周围,除了愚钝的外部身体,还有另外四种身体,肉眼不
可见,但是那些对于超物质世界事物的感知能力格外强大的人,却完全能看见……
她完全不知所云,但坚持往下读,很快,她读到了有趣的一段,说的是一个灵魂通常要
离开人间多长时间才能进入别人的身体,轮回转世。灵魂种类不同,时间长短也不一样,威
利斯先生给出了下面这个分类表:
酒鬼和失业者40—50年
非技术工人60—100年
技术工人100—200年
资产阶级200—300年
中上阶层500年
最高阶层的乡绅600—1000年
启蒙道路上的人1500—2000年
她立刻查了查另外两本书中的一本,弄清李斯特死了多长时间。书上说李斯特于一八八
六年死于拜罗伊特。那就是六十七年前。那么,根据威利斯先生的说法,这么快就转世轮回
的必须是一位非技术工人。那似乎根本对不上。另外,她认为作者的分类法不太合理。根据
他的分类,“最高阶层的乡绅”差不多是人间最高等级的生灵了。可那些人穿红夹克、喝饯行
酒、野蛮残酷地虐杀狐狸。不,她想,那不对。发现自己对威利斯先生开始产生怀疑,她很
高兴。
她在书的后面还读到一份名单,是一些比较著名的转世轮回实例。书上说,埃皮克提图
作为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返回了人间;西塞罗变成格莱斯顿回归,阿尔弗雷德大王变成维多
利亚女王,征服者威廉变成基奇纳勋爵;公元前二十七年的印度国王阿育王,变身为亨利·斯
蒂尔·奥尔科特上校——一位受人尊敬的美国律师;毕达哥拉斯回归时成了库图弥大师,就是
那位跟布拉瓦茨基夫人和奥尔科特上校(那位受人尊敬的美国律师,又名印度的阿育王)一
起创办了通神学会的人。书上没说布拉瓦茨基夫人曾经是谁。不过它说“西奥多·罗斯福”——
作为举足轻重的领袖人物多次转世轮回……古代迦勒底皇家后裔就是由他始传,大
约公元前30000年,他被时任波斯统治者的恺撒大帝任命为迦勒底总督……罗斯福和恺撒
大帝多次转世轮回为军事和行政领导人,好几千年前的一次,他们曾为一对夫妻……
路易莎不用再往下看了,密尔顿·威利斯显然是在胡编乱猜。她认为他那些自以为是的断
言都不可信。这家伙的路子可能是对的,但是他的断言太夸张了,特别是第一条关于动物
的。很快,她就能拿出人可以托生为低等动物的证据,驳倒整个通神学会。而且,能够在一
百年内转世轮回的,不一定必须是一位非技术工人。
她拿起李斯特的一本传记,随意地扫了几眼,这时她丈夫就从花园回来了。
“你又在做什么?”他问。
“哦——只是随便查点东西。听我说,亲爱的,你知道西奥多·罗斯福曾经是恺撒大帝的妻
子吗?”
“路易莎,”爱德华说,“我说——我们是不是别再谈这些疯话呢?我不愿意看到你这样闹
笑话。快把那只该死的猫给我,我亲自送到警察局去。”
路易莎似乎没有听见他的话。那本书放在她腿上,她盯着书上李斯特的一张肖像,吃惊
地张开了嘴。“哦,上帝!”她喊道,“爱德华,快看!”
“什么?”
“你看!他脸上的肉瘤!我都把它们忘记了!他脸上有这些大肉瘤,这是一件人人都知道
的事。他的学生甚至故意在自己脸上同样的地方留出一撮撮小胡子,就是为了模仿他。”
“这跟这件事有什么关系?”
“没什么关系。我的意思是说,跟那些学生没关系,但是跟肉瘤有关系。”
“哦,上帝。”男人说,“哦,万能的上帝啊。”
“这只猫也有肉瘤!看,我指给你看。”
她把猫抱到腿上,开始仔细检查它的脸。“找到了!这儿有一个!这儿还有一个!等一
等!我相信它们是在同样的位置!那张照片呢?”
那是音乐家老年一张很出名的肖像,精致而刚毅的脸,浓密的灰色长发盖住他的耳朵,
一直垂到脖子上面。那张脸上的每一个大肉瘤都被忠实地复制了出来,一共有五个。
“看到吗,肖像的右眉毛上面有一个。”她端详着猫的右眉毛上面,“没错!在这儿呢!位
置完全一样!左边还有一个,在鼻子尖上。这儿也有!下面还有一个,就在面颊上。还有两
个挨得比较近的,在右侧下巴的底部。爱德华!爱德华!快来看啊!完全一模一样。”
“这证明不了什么。”
她抬头看着丈夫,丈夫站在房间中央,穿着绿色运动衫和卡其布裤子,仍然在大量出
汗。“你害怕了,爱德华,是不是?你害怕失去你那宝贵的面子,害怕人们觉得你平生第一次
出了洋相。”
“我不愿意为这事失去理智,仅此而已。”
路易莎把目光转回书上,开始继续往下读。“真有趣,”她说,“这里写着李斯特热爱肖邦
的所有作品,只有一个例外——降b小调诙谐曲。他似乎很讨厌这支曲子,称之为‘家庭教师
诙谐曲’,说应该把它只留给那个行业的人。”
“那又怎么样?”
“爱德华,听我说。既然你一味坚持这种讨厌的态度,我不妨告诉你我要做什么。我现在
就来弹这支诙谐曲,你可以留在这里,看看会有什么反应。”
“然后你大概就肯屈尊给我们做点晚饭了。”
路易莎站起身,从书架上抽出一本绿色大厚书,里面收了肖邦的所有作品。“有了。哦,
没错,我记得它。确实很难听。好了,仔细听——准确地说,是仔细看。留意他的反应。”
她把乐谱放在钢琴上,坐了下来。她丈夫仍然站着,双手插在口袋里,嘴里叼着香烟,
眼睛不由自主地盯着那只正在沙发上打盹的猫。路易莎开始弹琴,最初的效果跟以前一样非
常戏剧化。猫突然跳了起来,好像被蜇了一下似的,一动不动地站了至少一分钟,耳朵竖
起,整个身体微微颤抖。然后,它变得坐立不安,开始在沙发上来来回回地走。最后,它跳
到地板上,鼻子和尾巴都翘得高高的,它昂首阔步,慢慢地走出了房间。
“看到了吧!”路易莎大喊一声,跳起来去追它,“成功了!确实得到了证明!”她把猫抱
回来,重新放在沙发上。她兴奋极了,整个脸上容光焕发,两个拳头攥得发白,后脑勺上的
小发髻松了,歪到了一边。“怎么样,爱德华?你还有什么话可说?”她说话时发出紧张的笑
声。
“我不得不说,确实蛮好笑的。”
“好笑!我亲爱的爱德华,这是有史以来最奇妙的一件事!哦,我的天哪!”她喊道,又
把猫抱起来,紧紧搂在胸口,“想想吧,弗朗兹·李斯特住在我们家里,是不是太美妙了?”
“好了,路易莎。别这么歇斯底里。”
“我忍不住,我就是忍不住。想象一下吧,他要永远跟我们生活在一起了!”
“你说什么?”
“哦,爱德华!我兴奋得说不出话来。你知道我接下来要做什么吗?全世界的每个音乐家
都想要来拜见他,这是肯定的,向他打听他认识的那些人——贝多芬啊、肖邦啊、舒伯特啊
——”
“他不会说话。”丈夫说。
“那个——好吧。但他们还是想来拜见他,就为了能看见他,抚摸他,弹奏他们的音乐给
他听,那些是他以前从未听到过的现代音乐。”
“他没有那么伟大。话说,如果是巴赫或者贝多芬……”
“别打断我,爱德华,拜托。所以,我要通知世界各地所有活着的重要作曲家。这是我的
责任。我要告诉他们,李斯特在这里,我要邀请他们来拜访他。然后,你知道吗?他们会从
世界的各个角落飞过来。”
“就为了看一只灰猫?”
“亲爱的,这没什么两样。就是他。谁也不会在意他看上去什么样。哦,爱德华,这会成
为有史以来最激动人心的事!”
“他们会认为你疯了。”
“你就等着瞧吧。”她把猫抱在怀里,温柔地抚摸着,眼睛却看着她的丈夫,爱德华此刻
走向落地长窗,站在那里朝花园眺望。暮色正在降临,草地慢慢地由绿色转为黑色,远处,
能看见他的篝火冒出一股白烟,袅袅升入空中。
“不,”他头也不转地说,“我不同意。不同意在这个家里搞这一套。那样的话,我们俩都
成了十足的傻瓜。”
“爱德华,你是什么意思?”
“就是这个意思。我绝对不允许你把这样一件蠢事搞得沸沸扬扬。你只是碰巧找到了一只
会耍把戏的猫。好——没问题。如果你愿意,就养着它好了。我没意见。但我不希望你再闹
出别的花样。你明白吗,路易莎?”
“闹出什么花样?”
“我不想再听到这些胡言乱语。你的表现像个疯子。”
路易莎慢慢地把猫放在沙发上。然后她慢慢地尽量挺直矮小的身体,往前跨了一步。“你
真该死,爱德华!”她跺着脚,大声喊道,“在我们的生活里,破天荒第一次出现了一件真正
激动人心的事,可是你却吓得要死,不敢跟它扯上关系,生怕别人会笑话你!是这么回事
吧?你无法否认,是不是?”
“路易莎,”她丈夫说,“不要再闹了。赶紧镇静下来,立刻停止吧。”他走过来,从桌上
的匣子里拿了一支香烟,用那个硕大的漆皮打火机把烟点燃。他的妻子站在那里注视着他,
此刻泪水已经开始从她眼角流出来,把面颊上的香粉冲出两条亮晶晶的痕迹。
“最近我们的这种场面太多了。”爱德华说,“不,不,别打断我。听我说。我充分考虑
到,这可能是你人生中的一个尴尬时期,而且——”
“哦,我的上帝!你这个白痴!你这个自大的白痴!你难道看不出这是不一样的,这是
——这是一个奇迹吗?这点你难道看不出来吗?”
这时,他从房间那头走过来,用力抓住她的双肩。他唇间叼着刚点燃的香烟,她隐约看
到他皮肤上有大量出汗被吹干后的斑斑印迹。“听着。”他说,“我饿了。我放弃了打高尔夫
球,一整天都在花园里干活,现在又累又饿,想吃一些晚饭。你也是。赶紧到厨房去,给我
们俩弄点好东西吃吃。”
路易莎退后一步,用两只手捂住了嘴。“我的天哪!”她喊道,“我完全忘记了。他一定早
就饿坏了。他来了后只喝过几口牛奶,我什么也没有给他吃。”
“谁?”
“哎呀,当然是他。我必须立刻去做一些很不一般的东西。我真希望知道他以前最爱吃的
菜是什么。你认为他最喜欢吃什么呢,爱德华?”
“该死,路易莎!”
“好了,爱德华,拜托。那么我就按我的方式去做吧。你待在这里。”她一边说着,一边
弯下腰,用手指轻轻碰了碰猫,“我很快就回来。”
路易莎走进厨房,站了一会儿,考虑做什么特色美食。蛋奶酥怎么样?一道美味的奶酪
蛋奶酥?没错,那肯定很有特色。当然啦,爱德华不太爱吃,但那也没办法。
她的厨艺只是差强人意,对蛋奶酥做出来的效果一向没有把握,但这次她格外用心,等
了很长时间,确保炉子完全加热到合适的温度。蛋奶酥烤着的时候,她到处寻找跟它相配的
东西,突然想到李斯特可能一辈子都没尝过鳄梨和西柚,于是决定给他把这两样同时做在沙
拉里。到时候观察他的反应会很有意思。肯定。
一切就绪,她把美食放在托盘上,端进了客厅。就在她进来的那一刻,她看见丈夫从花
园跨过落地长窗进来了。
“这是他的晚饭。”路易莎说,把托盘放在桌上,朝沙发转过身来,“他在哪儿?”
丈夫进来后,关上花园的门,走到房间这头,给自己拿香烟。
“爱德华,他在哪儿?”
“谁?”
“你明知道是谁。”
“啊,是的。是的,没错。好吧——我告诉你。”他俯身点烟,双手拢住那个硕大的漆皮
打火机。他抬头扫了一眼,发现路易莎正看着他——看着他的鞋子和卡其布裤子的裤脚,因
为在长长的草地上走过,鞋子和裤脚都沾湿了。
“我刚才去看看那堆篝火怎么样了。”他说。
她的目光慢慢往上抬,停在他的双手上。
“仍然烧得很好。”他继续说,“我认为烧一整夜没问题。”
然而,她盯着他的那种眼神使他感到了不安。
“怎么啦?”他说,放下了打火机。然后他垂下目光,第一次注意到自己一只手背上那道
斜斜的、又长又细的抓痕,从指关节一直延伸到手腕。
“爱德华!”
“是的,”他说,“我知道。那些荆棘太可怕了。简直能把你撕成碎片。喂,等一下,路易
莎。出什么事了?”
“爱德华!”
“哦,看在上帝的分上,女人,快坐下来,保持冷静。没有什么好激动的。路易莎!路易
莎,坐下!”
首次发表于《纽约客》 1953.10.31
[1]英美制长度单位,1码等于0.9144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