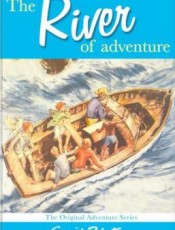非洲的故事
对于英国来说,战争是在一九三九年九月开始的。英伦小岛上的人们立刻就知道了,开
始做好准备。在较远的地方,人们是几分钟后才得到消息,他们也开始做好准备。
在东部非洲,在肯尼亚的殖民地,有一位青年是白人职业猎手,他热爱平原、山谷,以
及乞力马扎罗山坡上清凉的夜晚。他也听到了要打仗的消息,也开始做好准备。他长途跋涉
前往内罗毕,报名参加英国皇家空军,要求当一名飞行员。他们接收了他,他在内罗毕机场
开始接受训练,开那种小型的虎蛾机,飞得相当不错。
五个星期后,他差点上了军事法庭,因为他开飞机后,并没有遵照命令练习绕圈和旋
转,而是飞往纳库鲁的方向,去看平原上的野生动物。途中他以为看见了一头黑马羚,这可
是非常稀罕的物种,他立刻兴奋起来,把飞机降下去,想看得更清楚些。他正从驾驶舱的左
侧低头打量那头黑马羚,所以没有看见右侧的那只长颈鹿。飞机右舷的前缘砍中了长颈鹿的
脖子,正好就在它的脑袋下面一点,一下子就砍穿了。他当时飞得就是那么低。机翼损坏
了,但他勉强返回了内罗毕,然后,就像我前面说的,他差点上了军事法庭,因为那样的事
情是搪塞不过去的,你不能说是撞上了一只大鸟,机翼和支架上还沾着长颈鹿的碎皮和长颈
鹿的毛呢。
六个星期后,他第一次获得了越野单飞的机会,从内罗毕飞到一个名叫埃尔多雷特的地
方,那是高原上一个海拔八千英尺的小镇。可是他又交了厄运。半路上发动机出了故障,因
为燃料箱里进了水。他还算冷静,来了个漂亮的紧急迫降,飞机没有损坏。离降落处不远的
地方有一个小棚屋,孤零零地立在高地平原上,周围杳无人烟。这是一片荒凉的乡村。
他朝棚屋走去,发现有个老人独自住在里面,只靠一小片甘薯地、几只褐色母鸡和一头
黑奶牛过活。
老人对他很好。给了他吃食、牛奶和睡觉的地方,飞行员跟老人一起待了两天两夜,后
来一架救援机从内罗毕飞来,看见了地面上他的飞机,便降落在它旁边,弄清了故障原因,
返回去取来清洁汽油,使他得以起飞、返航。
在飞行员逗留期间,那个老人——他一直孤零零地生活,好几个月看不见一个人——很
喜欢有他做伴,有个人可以说说话。老人说得很多,飞行员耐心地听着。老人谈到孤寂的生
活,谈到夜里跑来的狮子,谈到住在西边山上的那头离群的野象,谈到白天的炎热,以及夜
半的寒意和寂静。
第二天夜里,他谈到了他自己,讲了一个很长、很奇怪的故事。老人讲述的时候,飞行
员觉得他通过讲这件事似乎正在卸去肩头一个沉重的包袱。老人讲完后,说他从来没有把这
件事告诉过任何人,而且以后也不会再对别人讲。然而那个故事太奇怪了,飞行员一回到内
罗毕,就把它写在了纸上。他不是用老人的话写故事,而是用他自己的话,把老人作为故事
里的一个人物讲述那个故事,因为那是最好的方式。他以前从未写过故事,错误在所难免。
他也不懂得任何文字技巧——作家们像画家使用绘画技巧一样使用着那些技巧,然而,在他
写完后,当他放下铅笔,起身到飞行员食堂去喝一杯啤酒时,他留下的是一篇罕见而有力的
故事。
两星期后,他在训练中遇难,我们清点他的遗物时,在箱子里发现了这篇故事,因为他
似乎没有亲属,也因为他是我的朋友,我就收下这份手稿,替他保存。
下面就是他写的。
老人走出门,来到明亮的阳光里,他拄着拐杖站了一会儿,打量着周围,在强烈的光线
下眨着眼睛。他脑袋偏向一边,眼睛往上看着,倾听他刚才仿佛听见的声音。
他矮墩墩的,有七十多岁了,但看上去更像八十五,因为风湿病使他的身体佝偻成一
团。他脸上布满灰色的胡子,嘴巴只有半边能动。他不管在屋里还是屋外,头上总戴着一顶
脏兮兮的白色遮阳帽。
他在耀眼的阳光里定定地站着,眯起眼睛,听着那个声音。
没错,又来了。老人的脑袋轻快地一转,看向一百码开外牧场上的那个小木屋。这次没
有半点疑问了:是一只狗的叫声,是一只狗遭遇巨大危险时发出的高亢、尖利刺耳的吠叫
声。狗又叫了两声,这次声音不像是吠叫,而更像是一种哀嚎。声音凄厉,更加刺耳,似乎
是从身体里某个狭窄的地方迅速挤压出来的。
老人转过身,瘸着腿快步走过草地,朝贾德森住的小木屋走去,并推开门走了进去。
那只小白狗躺在地上,贾德森双腿叉开站在旁边,黑头发披散在他那长长的红脸膛上。
他高个子,瘦骨嶙峋,站在那里喃喃自语,汗水浸湿了他油渍斑斑的白衬衫。他的嘴巴奇怪
地耷拉着,一副毫无生气的样子,似乎下巴对他来说太重了,一滴滴口水从下巴中间轻轻滴
落。他站在那里,看着躺在地上的小白狗,用一只手慢慢地捻着自己的左耳朵,另一只手里
拿着一根沉甸甸的竹子。
老人没有理会贾德森,他俯身跪在他的狗身边,用瘦巴巴的双手轻轻抚摸狗的身体。狗
一动不动地躺着,抬起一双泪汪汪的眼睛看着他。贾德森没有动弹,他注视着狗和老人。
慢慢地,老人站起身,他用双手撑着拐杖头,十分费力地缓缓直起身子。他打量着木屋
里。远处墙角的地上铺着一张肮脏的、皱巴巴的垫子,那张木头桌子是用包装箱做的,上面
放着做饭用的简易炉和一个裂了口的蓝色搪瓷平底锅。地板上有一些鸡毛和泥巴。
老人看见了他需要的东西。一根沉重的铁条靠在床垫旁边的墙上,他一瘸一拐地走过
去,拐杖咚咚地砸着空洞的木地板。他瘸着腿走向房间那头,狗的眼睛一直跟着他。老人把
拐杖换到左手,用右手拿起铁条,踉踉跄跄回到狗的身边,毫不迟疑地举起铁条,重重地砸
向狗的脑袋。他把铁条扔在地上,看着贾德森,贾德森双腿叉开站在那里,口水滴在下巴
上,眼角周围在抽搐。老人走到贾德森面前,开始说话。他的话说得很轻、很慢,带着可怕
的怒气,说话时只有半边嘴巴在动。
“你打死了它。”他说,“你打断了它的背。”
接着,随着怒气的上升,他有了气力,也有了更多的话要说。他抬起头,对准高个子的
贾德森脸上啐了一口,贾德森眼角周围抽搐着,朝墙边退去。
“你这个肮脏、卑鄙的杂种,竟然打狗!这是我的狗。你他妈的有什么权力打我的狗,你
说。回答我,你这个流口水的疯子。快回答我。”
贾德森把左手的手掌在衬衫前襟上慢慢地上下擦了擦,现在他的整张脸都开始抽搐了。
他没有抬眼,说道:“它不停地舔它爪子上的那块地方。我受不了它发出的声音。你知道我没
法忍受那种声音,吧嗒,吧嗒,吧嗒。我叫它别舔了。它抬起头,摇晃着尾巴,可接着又继
续舔。我实在是没法忍受,就打了它。”
老人什么也没说。一时间,他似乎想把这家伙狠狠揍一顿。他微微抬起胳膊,接着又垂
下了,朝地上啐了一口,转过身,一瘸一拐地走出门,走进阳光里。他穿过草地,走向站在
小金合欢树的树荫下反刍的那头黑奶牛,奶牛注视着他从小木屋瘸着腿走过草地。它继续反
刍,嘎吱嘎吱地咀嚼,下巴机械地、有规律地动着,像一台慢速的节拍器。老人一瘸一拐地
走过去,站在奶牛身边,抚摸它的脖子。然后,他靠在奶牛的肩膀上,用拐杖头挠它的后
背。老人在那里站了很长时间,靠在奶牛身上,用拐杖给它挠后背。偶尔,他会跟奶牛说
话,压低声音说悄悄话,就像一个人在把秘密告诉另一个人。
金合欢树下很阴凉,而且几场大雨过后,肯尼亚高原上的草长得郁郁葱葱,老人的周围
一片翠绿,景色十分宜人。每年的这个时候,雨季过后,这里像世界上的任何草地一样青翠
和丰美。北边的远处就是肯尼亚山,山顶积雪覆盖,一道细细的白雾环绕山巅,那是凛冽的
寒风形成的风暴,吹散了山顶上白色的雪粉。下面,在那座山的山坡上,有狮子和大象,夜
里有些时候,还能听见狮子抬头望月时的咆哮。
日子一天天过去,贾德森默默地在农场里干活,像一台机器一样,收玉米,刨甘薯,给
那头黑奶牛挤奶,老人待在屋里,躲避酷烈的非洲阳光。只有到了傍晚,空气开始变得清
凉,不那么闷热了,他才摇摇晃晃地走到外面,他总是走向他的黑奶牛,陪它在金合欢树下
消磨一小时。一天,他出来时发现贾德森站在奶牛身旁,用奇怪的眼神打量它,他站姿很特
别,一只脚在前,一只脚在后,右手轻轻地捻着自己的耳朵。
“又怎么啦?”老人瘸着腿走过去,说道。
“奶牛嚼个不停。”贾德森说。
“它在反刍呢。”老人说,“别管它。”
贾德森说:“那声音,你听不见吗?嘎吱嘎吱的,就好像在嚼石子儿,其实不是,它只是
在嚼草和唾沫。你看看它,它不停地嚼啊嚼,嘎吱,嘎吱,嘎吱,其实就是草和唾沫。这声
音直往我的脑袋里钻。”
“滚。”老人说,“滚,别让我看见你。”
天亮的时候,老人像往常一样坐了起来,看着窗外,注视着贾德森从他的小木屋出来,
去挤牛奶。他看见贾德森睡眼惺忪地走过田地,边走边喃喃自语,拖着双脚,在湿漉漉的草
地上留下一道墨绿色的脚印,手里提着那个四加仑 [1] 的旧煤油桶,那是他的挤奶桶。太阳从
悬崖顶上升起来了,男人、奶牛和小金合欢树后面拖了长长的影子。老人看见贾德森放下煤
油桶,又看见他从金合欢树旁拿过那个木箱子,坐在上面,准备挤奶。老人看见他突然跪下
来,用双手抚摸奶牛的乳房,与此同时,老人从他坐的地方注意到,奶牛已经没有奶了。他
看见贾德森站起身,快步朝棚屋走过来。贾德森走过来站在老人坐着的窗户根旁,抬起了
头。
“奶牛没有奶了。”他说。
老人从敞开的窗户探出身去,双手撑在窗台上。
“你这个下作的混蛋,准是你偷的。”
“我没有偷。”贾德森说,“我一直在睡觉。”
“就是你偷的。”老人把身子又往窗外探出一些,用半边嘴巴轻声说道,“我要把你打得屁
滚尿流。”他说。
贾德森说:“夜里有人偷奶,是当地人,基库尤人。要么就是奶牛病了。”
老人觉得贾德森说的是实情。“再看看吧,”他说,“看它今天晚上有没有奶。现在,看在
基督的分上,快从我眼前消失。”
晚上,奶牛的乳房满了,老人注视着贾德森从它身下挤出两夸脱浓稠的好牛奶。
第二天早晨,奶牛没有奶。到了晚上,它乳房是满的。第三天早晨,它又没有奶了。
第三天夜里,老人去站岗。天刚一擦黑,他就坐在敞开的窗口,腿上放着一杆十二号口
径的旧滑膛枪,等着夜里来偷偷挤奶的那个小偷。一开始,四下里漆黑一片,他连奶牛都看
不见,但是不一会儿,四分之三个月亮升上了山坡,周围有了光亮,几乎像白天一样了。天
气很冷,因为高地的海拔有七千英尺,放哨的老人打着哆嗦,把褐色的毛毯拉上来,紧紧裹
住肩膀。现在他可以清楚地看见奶牛了,清楚得就像白天一样,那棵小金合欢树在草地上投
下黑黑的影子,因为月亮在它的后面。
整整一夜,老人坐在那里盯着奶牛,中间只起身过一次,瘸着腿回房间里去再拿一条毛
毯,除此之外,他的眼睛一刻也没离开过奶牛。奶牛静静地站在小树下,眼望着月亮,慢吞
吞地反刍。
天亮前一小时,它的乳房满了。老人看得很真切。他一直在注视着它,虽然没有看见它
鼓涨的过程,就像看不见钟表上时针的移动一样,但是他意识到牛奶正流下来把乳房灌满。
还有一个小时天就亮了。月亮悬得很低,但月光并未消失。他能看见奶牛、小树和奶牛周围
绿色的草地。突然,他脑袋一挺。他听见了动静。没错,他听见的是一种响动。是的,又出
现了,一阵沙沙声,就在他坐着的窗户根下的草地上。他迅速站起身,靠在窗台上朝地面望
去。
他看见了。一条黑色的大蛇,曼巴蛇,足有八英尺长,有男人的胳膊那么粗,正爬过潮
湿的草地,直奔奶牛而去,爬的速度很快。它那梨形的小脑袋从地面上微微抬起一点,身体
贴着湿草移动,发出清晰的沙沙声,就像喷气式飞机正在喷气一样。老人举枪准备射击。几
乎就在同时,他又把枪放下了,不知道为什么,他坐在那里没有动,注视着曼巴蛇慢慢靠近
奶牛,听着它爬过时发出的声音,看着它爬到奶牛身边,等着它发起攻击。
但是蛇并没有攻击。它抬起头,把头轻轻前后摇晃了几下,然后把黑色身体的前半截高
高抬起,凑到奶牛的乳房下,用嘴轻轻叼住一个粗大的奶头,开始喝奶。
奶牛没有动。四下里听不到一点声音,曼巴蛇的身体从地面优美地抬起来,悬吊在奶牛
的乳房下。黑色的蛇,黑色的奶牛,在月光下显得那么清晰。
足足半个小时,老人注视着曼巴蛇吸走奶牛的奶。他看见它一口口吸出乳房里的奶液,
黑色的身体轻柔地波动,过了一阵,他看见蛇从一个奶头换到另一个奶头,直到把奶吸得一
滴不剩。然后,曼巴蛇把身体轻轻落回地面,在草地上顺着原路往回爬。它爬行时又一次发
出清晰的沙沙声,又一次从老人坐着的窗户下经过,在湿漉漉的草地上留下一条细细的深色
痕迹。然后,它就消失在了棚屋后面。
月亮慢慢地沉落到肯尼亚山的后面。几乎就在同时,太阳从东边的悬崖上升起,贾德森
从他的木屋里出来,手里提着那个四加仑的煤油桶,他在露水深重的草地上拖着脚,睡眼惺
忪地走向奶牛。老人注视着他走过来,等待着。贾德森弯下腰,用手摸了摸奶牛的乳房,这
时老人大声朝他喊话。贾德森听到老人的声音,跳了起来。
“又没了。”老人说。
贾德森说:“是啊,没有奶了。”
“我想,”老人慢悠悠地说,“我想,准是一个基库尤男孩干的。我打了个盹儿,醒来正好
看见他逃走。我没法开枪,因为奶牛挡在中间呢。他从奶牛后面逃走了。今晚我再等着他。
今晚我要抓住他。”老人加了一句。
贾德森没有回答。他拎起他的四加仑煤油桶,走回了他的小木屋。
那天夜里,老人又坐在窗口监视奶牛。对他来说,这次是含着几分喜悦期待着即将看到
的一幕。他知道他还会看见那条曼巴蛇,但他想确保万无一失。于是,当日出前一小时,黑
色的大蛇在草地上爬向那头奶牛时,老人把身子探出窗台,目光紧盯着曼巴蛇靠近奶牛的身
影。他看见大蛇在奶牛的肚皮下等了一会儿,让蛇头慢慢地前后摇摆了六七下,然后终于把
身体从地面上直起来,用嘴叼住奶牛的奶头。老人看见它喝了半小时,把牛奶喝得一滴不
剩,然后他看见它把身体落回地面,顺着原路爬过草地,返回棚屋后面去了。老人注视着这
一切时,用半边嘴巴发出了轻轻的笑声。
太阳从山丘后面升起来了,贾德森从他的小木屋里出来,手里拎着那个四加仑的煤油
桶,但是这次他直接走向棚屋的窗户,老人正裹着毛毯坐在那里。
“发生了什么事?”贾德森说。
老人从窗户低头看着他。“没有。”他说,“什么事也没发生。我又打了个盹儿,那混蛋趁
我睡着时过来偷走了牛奶。听我说,贾德森,”他接着说道,“我们必须抓住那小子,不然你
的牛奶就短缺了,这对你倒没什么损害,但我们必须把他抓住。我不能开枪,因为那小子太
机灵了,总是有奶牛挡在中间。只能由你去抓他了。”
“我抓他?怎么抓?”
老人语速非常缓慢。“我想,”他说,“我想你必须藏在奶牛身旁,就在奶牛的边上。只有
这样,你才能把他抓住。”
贾德森用左手揉搓着自己的头发。
“今天,”老人继续说道,“你就在奶牛身边挖一个浅坑。如果你躺在坑里,如果我用干草
和青草把你盖住,那么,小偷必须走到近旁才会发现你。”
“他可能有刀。”贾德森说。
“不,他不会有刀。你拿上你的棍子,别的就不需要了。”
贾德森说:“好的,我拿上我的棍子。等他来了,我就扑上去,用我的棍子打他。”突
然,他似乎想起了什么。“它嚼个不停怎么办?”他说,“我可受不了它嚼上一整夜,嘎吱,嘎
吱,嘎吱,嚼唾沫和青草,就像嚼石子儿似的。一整夜都这样,我可受不了。”他又开始用手
捻他的左耳朵。
“少废话,叫你做什么就做什么。”老人说。
那天,贾德森在奶牛的身边挖坑,奶牛被拴在那棵小金合欢树上,以免它在农场上乱
跑。夜幕降临了,贾德森刚要在坑里躺下过夜,老人走到他棚屋的门口,说道:“等明天凌晨
再行动也不迟。奶牛的奶满了,他们才会来。到屋里来等着吧,这儿比你那脏兮兮的小木屋
暖和。”
贾德森从来没有受邀进入过老人的棚屋。他跟着老人进屋,庆幸自己不用整夜躺在那个
坑里。房间里点着一根蜡烛。蜡烛插在一个啤酒瓶的瓶口,啤酒瓶放在桌上。
“沏点茶吧。”老人说,指着地板上那个做饭的简易炉。贾德森点着炉子,沏了茶。两人
在两个木头箱子上坐下,开始喝茶。老人喝滚烫的茶,边喝边发出很响的吸气声。贾德森不
停地吹自己的茶,谨慎地小口喝着,从杯子边缘注视着老人。老人继续吸着气喝茶,最后,
贾德森突然说道:“停。”他的话音很轻,几乎有些哀怨,话一出口,他的眼角和嘴巴周围便
开始抽搐。
“什么?”老人问。
贾德森说:“那声音,你发出的那种吸气声。”
老人放下茶杯,静静地端详了对方片刻,然后说道:“你这辈子打死了多少只狗,贾德
森?”
没有回答。
“我问你呢,多少只?多少只狗?”
贾德森开始把他茶杯里的茶叶捞出来,一根根贴在自己的左手背上。老人从木箱上探过
身。
“多少只狗,贾德森?”
贾德森捞茶叶的速度加快了。他把几根手指戳进空茶杯,捞起一片茶叶,迅速地贴在手
背上,然后迅速地再去捞另一片。茶杯里已不剩多少茶叶,他没有马上捞到一片,就埋下
头,专注地盯着杯子里,想找到剩下的茶叶。端着杯子的那只手的手背上,贴满了湿漉漉的
黑茶叶。
“贾德森!”老人大喊一声,他的半边嘴巴像老虎钳一样一开一合。蜡烛的火苗跳了一
下,又静止不动了。
然后,他压低声音、轻言细语、语速缓慢,就像在对一个小孩子说话。“你这辈子,到底
打死过多少只狗?”
贾德森说:“我凭什么要告诉你?”他没有把眼睛抬起来。他把手背上的茶叶一片片捏
起,放回茶杯里。
“我想知道,贾德森。”老人说话的口气非常缓和,“我对这件事也很着迷。我们聊一聊
吧,制订一些更有趣的计划。”
贾德森抬起目光。一股唾液滚下他的下巴,在空中悬了一会儿,断了,掉落在地板上。
“我是因为声音才打死它们的。”
“这件事你做了多少次?我很想知道有多少次。”
“许多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怎么做的?说说你以前是怎么做的。你最喜欢哪种方式?”
没有回答。
“跟我说说,贾德森。我很想知道。”
“我不明白为什么要说。这是个秘密。”
“我不会说出去的。我发誓不说出去。”
“好吧,既然你能保证。”贾德森把座位往前挪挪,压低了声音说,“有一次,我等一只狗
睡着了,就搬起一块大石头砸在它脑袋上。”
老人站起身,又给自己倒了杯茶。“但你并不是这样弄死我的狗的。”
“我当时来不及。那声音太可怕了,吧嗒,吧嗒,我必须赶紧让它住嘴。”
“你没有干脆把它打死。”
“我把那声音止住了。”
老人走到门口,往外看了看。天黑了。月亮还没有升起,星星很多,夜空清冽、寒冷。
东边的天际有一小片白色,就在他注视的当儿,白色越来越大,放射出耀眼的光亮,扩展到
整个天空,这光亮映在高地草坡上的一颗颗小露珠里,被它们噙住。慢慢地,月亮升到了山
坡上。老人转过身,说道:“做好准备吧。谁说得准呢,今晚他可能来得早。”
贾德森站起身,两人走到屋外。贾德森在奶牛身边的浅坑里躺下,老人给他盖上青草,
最后只有他的脑袋露出地面。“我也会从窗口看着的。”他说,“我一喊,你就跳起来抓住
他。”
他摇摇晃晃地走回棚屋,来到楼上,用毛毯裹住身体,在窗口坐定。时间还很早。月亮
几乎是满的,正一点点往上爬。它映照着肯尼亚山顶上的白雪。
过了一小时,老人朝窗外喊道:“你还醒着吗,贾德森?”
“醒着,”他回答,“我醒着呢。”
“可别睡着了。”老人说,“不管怎样,都不能睡着了。”
“奶牛一直在嘎吱嘎吱。”贾德森说。
“很好,如果你现在站起来,我就朝你开枪。”老人说。
“你朝我开枪?”
“我说的是‘如果你现在站起来,我就朝你开枪’。”
从贾德森躺的地方传来一阵轻轻的啜泣声,一种奇怪的大喘气的声音,就像一个孩子拼
命忍着不哭,在这喘气声中,只听贾德森的声音说道:“我需要动一动,请你让我动一动吧。
这惹人厌的嘎吱声。”
“如果你站起来,”老人说,“我就朝你的肚子开枪。”
啜泣声又持续了一小时左右,突然停止了。
将近四点钟的时候,天气变得十分寒冷,老人把毛毯裹得更紧一些,大声喊道:“你在外
面冷吗,贾德森?你冷吗?”
“冷,”贾德森回答,“太冷了。但我不在乎,因为奶牛不再嘎吱了。它睡着了。”
老人说:“你抓住了小偷,打算拿他怎么办?”
“我不知道。”
“你会杀死他吗?”
顿了顿。
“我不知道。我只管把他抓住。”
“我会看着的。”老人说,“应该很有意思。”他把胳膊撑在窗台上,从窗口探出身子。
接着,他听见窗台下面有沙沙声,抬眼一看,看见了那条黑色的曼巴蛇,在草地上蜿蜒
地朝奶牛爬去,速度很快,脑袋从地面上微微抬起一点。
曼巴蛇爬到五码开外时,老人喊了起来。他把双手拢在嘴边,喊道:“他来啦,贾德森。
他来啦。快把他抓住。”
贾德森迅速抬起脑袋往上看。就在他这么做的时候,他看见了曼巴蛇,曼巴蛇也看见了
他。就在那短短的一秒,也许是两秒,蛇停住了,把头一缩,然后身体的上半段陡然升到空
中。说时迟那时快。一道黑光一闪,“砰”的一声轻响,它击中了贾德森的胸口。贾德森发出
尖叫,一声长长的、高亢的尖叫,没有抑扬顿挫,保持着同样的音调,渐渐地隐入虚无,归
于平静。他已经站了起来,撕扯开自己的衬衫,摸着胸口的那个地方,轻轻地哭泣着、呜咽
着,嘴巴张得大大的,呼吸粗重。在这过程中,老人一直静静地坐在敞开的窗口,探出身
子,眼睛一刻也没有离开下面的那个人。
被黑色曼巴蛇咬过之后,一切都会发生得很快,毒性几乎立刻就开始发作。贾德森被撂
倒在地,弓起后背在草地上打滚。他不再发出声音。四下里十分安静,似乎一个力大无比的
人正在跟一个看不见的巨人摔跤,似乎那个巨人正把他扭成一团,不让他站起来,把他的胳
膊拉长了塞过两腿之间,把他的膝盖推上去抵在下巴底下。
然后,他开始用手拔地上的草,又过了不久,他仰面躺着,轻轻踢蹬着双腿。但是他并
没能撑多久。他快速蠕动了一下,又弓起后背,同时翻了个身,接着便趴在地上不动了,右
膝弯上去压在胸口下,双手伸过了头顶。
老人仍坐在窗口,即使一切都结束之后,他还是坐在那里没有动弹。金合欢树下的阴影
里有了动静,曼巴蛇慢慢地朝奶牛爬去。它往前爬了一段,停住了,昂起头,等待着,又把
头垂下去,再次爬到了奶牛的肚皮下面。它把身子升到空中,用嘴叼住一个褐色的奶头,开
始吮吸。老人坐在那里注视着曼巴蛇吸奶牛的奶,他又一次看见它一口口吸出乳房里的奶
液,它黑色的身体轻柔地波动着。
蛇还在吸奶的时候,老人站起身,离开了窗口。
“他的那份归你。”他轻声说,“没关系,他的那份归你。”说着,他回头扫了一眼,又看
见曼巴蛇黑色的身体蜿蜒地从地面升起,与奶牛的肚子连在一起。
“是的,”他又说了一遍,“没关系,他的那份归你。”
首次出版于《献给你》 1945
[1]英美制容量单位,1英制加仑=4.546092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