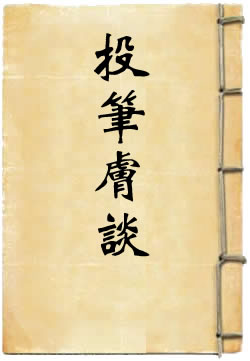“变文”影响的巨大——讲唱故事的风气的大行——所谓“说话人”——说话的四家——说话人的歌唱的问题——“银字儿”与“合生”——今存的宋人小说——“词话”与“诗话”——《清平山堂话本》及“三言”中的“词话”——白话文学的黄金时代——从《唐太宗入冥记》到宋人词话—烟粉灵怪传奇——公案传奇——《杨思温》与《拗相公》——《取经诗话》——《五代史平话》——《宣和遗事》——《梁公九谏》——“说话人”在后来小说上的影响的巨大
一
在北宋的末年,“变文”显出了她的极大的影响。“变文”的名称,在那时大约是已经消失了。讲唱“变文”的风气,在那时也似已不见了。但“变文”的体制,却更深刻地进入于我们的民间;更幻变的分歧而成为种种不同的新文体。在其间,最重要的是鼓子词和诸宫调二种。这在上文已经说过了。但变文的讲唱的习惯还不仅结果在鼓子词和诸官调上。同时,类似变文的新文体是雨后春笋似的耸峙于讲坛的地面。讲坛的所在,也不仅仅是限于庙宇之中了;讲唱的人,也不仅仅是限止于禅师们了。当然禅师们在当时的讲坛上还占了一部分的势力,像“说经”“说诨经”“说参请”之类。当时,讲唱的风气竟盛极一时;唱的方面也百出不穷;讲唱的人物也“牛鬼蛇神”无所不有;讲唱的题材,更是上天下地,无所不谈。这种风尚,也许远在北宋之末以前已经有了。不过,据我们所知道的材料,却是以北宋之末为最盛。这风尚直到了南宋之末而未衰,直到了元、明而仍未衰。而至今日也还不是完全绝了踪迹。讲唱的势力,在民间并未低落。讲坛也还林立在庙宇与茶棚之中。这可见,变文的躯骸,虽在西陲沉埋了千年以上,而她的子孙却还在世上活跃着呢;且孳生得更多,其所成就的事业也更为伟大。
在北宋之末,变文的子孙们,于诸宫调外尚有所谓“说话”者,在当时民间讲坛上,极占有权威。“说话”成了许多专门的职业;其种类极为分歧。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记载北宋末年东京的“伎艺”,其中已有“孙宽、孙十五、曾无党、高恕、李孝祥等讲史;李情、杨中立、张十一、徐明、赵世亨、贾九等小说;吴八儿,合生...霍四究说三分;尹常卖《五代史》”的话。其后,在南宋诸家的著述,像周密的《武林旧事》,耐得翁的《都城纪胜》及吴自牧的《梦粱录》,所记载的“说话人”的情形,更为详尽。《都城纪胜》记载“瓦舍众伎”道:
说话有四家。一者小说,谓之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说公案,皆是搏刀赶棒及发迹变泰之事;说铁骑儿,谓士马金鼓之事。说经,谓演说佛书;说参请,谓宾主参禅悟道等事。讲史书,讲说前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最畏小说人。盖小说者能以一朝一代故事,顷刻间提破。合生与起令、随令相似,各占一事。
《梦粱录》所记,与《都城纪胜》大略相同。《武林旧事》则历记“演史”“说经、诨经”等职业的说话人的姓名。“演史”自乔万卷以下到陈小娘子,凡二十三人;“说经、诨经”自长啸和尚以下到戴忻庵,凡十七人:“小说”自蔡和以下到史惠英(女流)凡五十二人;“合生”最不景气,只有一人,双秀才。大约“说话人”的四家,便是这样分着的。其中,“小说”最为发达,分门别类也最多。大约每一门类也必各有专家。故其专家至有五十余人之多。“演史”也是很受欢迎的。《东京梦华录》既载着霍四究、尹常等以说“三分”“五代史”为专业,而《梦粱录》里也说着当时“演史”者的情况道:“又有王六大夫,元系御前供话,为幕客请给,讲诸史俱通。于咸年间,敷演《复华篇》及《中兴名将传》,听者纷纷。盖讲得字真不俗,记问渊源甚广耳。“
凡说话人殆无不是以讲唱并重者,不仅仅专力于讲。——宋代京瓦中重要的艺伎盖也无不是如此——这正足以表现出其为由“变文”脱胎而来。今所见的宋人“小说”,其中夹入唱词不少,有的是诗,有的是词,有的是一种特殊结构的文章,惯用四言、六言和七言交错成文的,像:
黄罗抹额,锦带缠腰。皂罗袍袖绣团花,金甲束身微窄地。剑横秋水,靴踏狻猊。上通碧落之间,下彻九幽之地。业龙作祟,向海波水底擒来;邪怪为妖,入山洞穴中捉出。六丁坛畔,权为符吏之名;上帝阶前,次有天丁之号。
—《西山一窟鬼》
我们读到这样的对偶的文章,还不会猛然地想起《维摩诘经变文》《降魔变文》来吗?但唐人的对偶的散文的描状,在此时却已被包纳而变成为专门做描状之用的一种特殊的文章了。大约这种唐人用来讲念的,在此时必也已一变而成为“唱文”的一种了。又宋人亦称“小说”为“银字儿”。而“银字”却是一种乐器之名(见《新唐书·礼乐志》及《宋史·乐志》)。白乐天诗有“高调管色吹银字”,和凝《山花子词》有“银字笙寒调正长”,宋人词中说及“银字”者更不少概见。也许这种东西和“小说”的唱调是很有关系的。在“讲史”里,也往往附入唱词不少。最有趣的是“小说”中,像《快嘴李翠莲记》(见《清平山堂话本》),像《蒋淑贞刎颈鸳鸯会》(见《清平山堂话本》及《警世通言》),几皆以唱词为主体。《刎颈鸳鸯会》更有“奉劳歌伴:先听格律,后听芜词”及“奉劳歌伴,再和前声”的话。那么,说话人并且是有“歌伴”的了。“合生”的一种,大约也是以唱为主要的东西。《新唐书》卷一百十九《武平一传》叙述“合生”之事甚详。但据《夷坚志》八《合生诗词》条之所述,则所谓“合生”者,乃女伶“能于席上指物题咏,应命辄成者”之谓,其意义大殊。唯宋词中往往以“银字合生”同举,又“合生”原是宋代最流行的唱调之一;诸宫调里用到它,戏文里也用到它(中吕宫过曲)。这说话四家中的一家“合生”,难保不是专以唱“合生”这个调子为业的;其情形或像张五牛大夫之以唱赚为专业,或其他伎艺人之以“叫声”“叫果子”为专业一样吧。至于“说经”之类,其为讲唱并重,更无可疑。想不到唐代的“变文”,到了这个时代,会生出这么许多的重要的文体来。
二
“合生”和“说经、说参请”的二家,今已不能得其只字片语,故无可记述。至于“小说”,则今传于世者尚多,其体制颇为我们所熟悉。“讲史”的最早的著作,今虽不可得,但其流甚大,我们也不能不注意及之。底下所述,便专以此二家为主。
“小说”一家,其话本传于今者尚多。钱曾的《也是园书目》(《也是园书目》有《玉简斋丛书》本),著录“宋人词话”十二种。王国维先生的《曲录》尝把她们编入其中,以为她们是戏曲的一种。其后缪荃孙的《烟画东堂小品》把残本的《京本通俗小说》刊布了。《也是园书目》所著录的《冯玉梅团圆》《错斩崔宁》数种,竟在其中。于是我们才知道,所谓“词话”者,原来并不是戏曲,乃是小说。为什么唤作“词话”呢?大约是因为其中有“词”有“话”之故罢。其有“诗”有“话”者,则别谓之“诗话”,像《三藏取经诗话》是。
钱曾博极群书,其以《冯玉梅团圆》等十二种“词话”为宋人所作,当必有所据。《通俗小说》本的《冯玉梅团圆》,其文中明有“我宋建炎年间”之语,又《错斩崔宁》文中,也有“我朝元丰年间”的话。这当是无可疑的宋人著作了。其他《也是园书目》所著录的十种:
《灯花婆婆》《风吹轿儿》《种瓜张老》
《李焕生五阵雨》《简帖和尚》《紫罗盖头》
《小亭儿》(“小”当是“山”之误)《女报冤》《西湖三塔》《小金钱》
想也都会是宋人所作。在这十种里,今存者尚有《种瓜张老》(见于《古今小说》,作《张古老种瓜娶文女》),《简帖和尚》(见于《清平山堂话本》,又见《古今小说》,作《简帖僧巧骗皇甫妻》),《山亭ル》(见于《警世通言》,作《万秀娘仇报山亭ル)),《西湖三塔》(见于《清平山堂话本》)等四种。又在残本的《京本通俗小说》里,于《错斩崔宁》《冯玉梅》二作外,更有下列的数种:
《碾玉观音》《菩萨蛮》《西山一窟鬼》《志诚张主管》《拗相公》
缪氏在跋上说:“尚有《定州三怪》一回,破碎太甚;《金主亮荒淫》两卷,过于秽亵,未敢传摹。”今《定州三怪》(“州”一作“山”)见录于《警世通言》(作《崔衙内白鹞招妖》);《金主亮荒淫》也存于《醒世恒言》中(作《金海陵纵欲亡身》),则残本《京本通俗小说》所有者,今皆见存于世。唯《京本通俗小说》未必如缪氏所言的是“影元写本”。就其编辑分卷的次第看来,大似明代嘉靖后的东西(详见《明清二代平话集》,郑振铎著)。故其中所有,未必便都是宋人所作,至少《金主亮荒淫》一篇,其著作的时代决不会是在明代正德以前的(叶德辉单刻的《金主亮荒淫)系从《醒世恒言》录出,而伪撰“我朝端平皇帝破灭金国,直取三京。军士回杭,带得虏中书籍不少”的数语于篇首,故意说他是宋人之作)。其中所叙的事迹,全袭之于《金史》卷六十三《海陵诸要传》。《金史》为元代的著作,这一篇当然不会是出于宋人的手笔的。或以为,也许是《金史》抄袭这小说。但那是不可能的。元人虽疏陋,决不会全抄小说入正史,此其一。以小说与正史对读之,显然可看出是小说的敷衍正史,决不是正史的截取小说,此其二。我以为《金主亮荒淫》笔墨的酣舞横恣,大似《金瓶梅》;其意境也大相谐合。定哥的行径,便大类潘金莲。也许二书著作的时代相差得当不会很远吧。《金瓶梅》是颇有些取径于这篇小说的嫌疑。也许竟同出于一人之手笔也难说。但其他六篇,则颇有宋人作品的可能。《警世通言》在《崔待诏生死冤家》题下,注云:“宋人小说,题作《碾玉观音》”;又在《一窟鬼癞道人除怪》题下,注云:“宋人小说,旧名《西山一窟鬼》”;在《崔衙内白鹞招妖》题下,注云:“古本作《定山三怪》,又云《新罗白鹞》。”冯梦龙指它们为“宋人小说”,当必有所据。所谓“古本”,虽未必定是“宋本”,却当是很古之作。又《菩萨蛮》中有“大宋高宗绍兴年间”云云,《志诚张主管》文中,直以“如今说东京汴县开封府界”云云引起,《拗相公》文中,有“后人论我宋之气,都为熙宁变法所坏,所以有靖康之祸”云云,皆当是宋人之作。就其作风看来,也显然的可知其为和《冯玉梅团圆》诸作是产生于同一时代中的。
但宋人词话,存者还不止这若干篇。我们如果在《清平山堂话本》《古今小说》《警世通言》及《醒世恒言》诸书里,仔细地抓寻数过,便更可发现若干篇的宋人词话。在《清平山堂话本》里,至少像《陈巡检梅岭失妻记》(文中有“话说大宋徽宗宣和三年上春间,皇榜招贤,大开选场,去这东京汴梁城内虎异营中一秀才”的话),像《刎颈鸳鸯会》(一名《三送命》,一名《冤报冤》,文中引有《商调醋葫芦》小令十篇,大似赵德麟《商调蝶恋花》鼓子词的体制,或当是其同时代的著作吧),像《杨温拦路虎传》,像《洛阳三怪记》(文中有“今时临安府官巷口花市,唤作寿安坊,便是这个故事”的话),像《合同文字记》(文中有“去这东京汴梁离城三十里有个村”的话)等篇,都当是宋人的著作,且其著作年代有几篇或有在北宋末年的可能(像《合同文字记》)。在《古今小说》里,像《杨思温燕山逢故人》(文中有“至绍兴十一年,车驾幸钱塘,官民百姓皆从”的话),像《沈小官一鸟害七命》(文中有“宣和三年,海宁郡武林门外北新桥”的话),像《汪信之一死救全家》(文中有“话说大宋乾道淳熙年间,孝宗皇帝登极”的话),其作风和情调也很可以看得出是宋人的小说。《警世通言》所载宋人词话最多,在见于《京本通俗小说》《清平山堂话本》者外,尚有《三现身包龙图断冤》《计押番金鳗产祸》《皂角林大王假形》《福禄寿三星度世》等篇,也有宋作
的可能。在《醒世恒言》里,像《勘皮靴单证二郎神》《闹樊楼多情周胜仙》《郑节使立功神臂弓》等数篇,也很可信其为宋人之作。
三
就上文所述,总计了一下,宋人词话今所知者已有下列二十七篇之多(也许更有得发现;这是最谨慎的统计,也许更可加入疑似的若干篇进去)。这二十七篇宋人词话的出现,并不是一件小事。以口语或白话来写作诗、词、散文的风气,虽在很早的时候便已有之(像王梵志的诗、黄庭坚的词、宋儒们的语录等等)。但总不曾有过很伟大的作品出现过。在敦煌所发现的各种俗文学里,口语的成分也并不很重。《唐太宗入冥记》是今所知的敦煌宝库里的唯一的口语小说,然其使用口语的技能,却极为幼稚。试举其文一段于下:
“判官名甚?”“判官恶,不敢道名字。”帝曰:“卿近前来。”轻道:“姓崔名子玉。”“朕当识。”才言讫,使人引皇帝至院门。使人奏曰:“伏唯陛下且立在此,容臣入报判官速来。”言讫,使者到厅前拜了:“启判官,奉大王处□太宗生魂到,领判官推勘。见在门外,未敢引口。”
但到了宋人的手里,口语文学却得到了一个最高的成就,写出了许多极伟大的不朽的短篇小说。这些“词话”作者们,其运用“白话文”的手腕,可以说是已到了“火候纯青”的当儿,他们把这种古人极罕措手的白话文,用以描写社会的日常生活,用以叙述骇人听闻的奇闻异事,用以发挥作者自己的感伤与议论;他们把这种新鲜的文章,使用在一个最有希望的方面(小说)去了。他们那样的劲健直接的描写,圆莹流转的作风,深入浅出的叙状,现在都可以见出其艺术的成就是很为高明的。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用白话文来描叙社会的日常生活的东西。而当时社会的物态人情,一一跃然地如在纸上,即魔鬼妖神也似皆像活人般地在行动着。我们可以说,像那样的隽美而劲快的作风,在后来的模拟的诸著作里,便永远地消失了。自北宋之末到南宋的灭亡,大约便可称之为话本的黄金时代吧。姑举《简帖和尚》的一段于下:
那僧儿接了三件物事,把盘子寄在王二茶坊柜上。僧儿托着三件物事,入枣槊巷来。到皇甫殿直门前,把青竹帘掀起,探一探。当时皇甫殿直正在前面交椅上坐地。只见卖馉蚀的小厮儿,掀起帘子。猖猖狂狂探一探了便走。皇甫殿直看着那厮,震威一喝,便是当阳桥上张飞勇,一喝曹公百万兵。喝那厮一声,问道:“做甚么?”那厮不顾便走。皇甫殿直拽开脚两步赶上,捽那厮回来,问道:“甚意思,看我一看便走?”那厮道:“一个官人教我把三件物事与小娘子,不教把来与你。”殿直问道:“甚么物事?”那厮道:“你莫问。不教把与你。”皇甫殿直搭得拳头没缝,去顶门上屑那厮一道:“好好的把出来,教我看!”那厮吃了一,只得怀里取出一个纸裹儿,口里兀自道:“教我把与小娘子,又不教把与你。”皇甫殿直劈手夺了纸包儿,打开看,里面一对落索镮儿,一双短金钗,一个柬帖儿。皇甫殿直接得三件物事,拆开简子看时,...皇甫殿直看了简帖儿,劈开眉下眼,咬碎口中牙,问僧儿道:“谁交你把来?”僧儿用手指着巷口王二哥茶坊里道:“有个粗眉毛,大眼睛,蹶鼻子,略绰口的官人,教我把来与小娘子,不教我把与你。”皇甫殿直一只手捽着僧儿狗毛,出这枣塑巷,径奔王二哥茶坊前来。僧儿指着茶坊道:“恰才在楼里面打底床铺上坐地底官人,教我把来与小娘子,又不交把与你,你却打我!”皇甫殿直再摔僧儿回来,不由开茶坊的王二分说。当时到家里。殿直焦躁,把门来关上,来了。唬得僧儿战作一团。殿直从里面叫出二十四岁花枝也似浑家出来道:“你且看这件物事!”那小娘子又不知上件因依,去交椅上坐地。殿直把那简帖儿和两件物事,度与浑家看。那妇人看着简帖儿上言语,也没理会处。殿直道:“你见我三个月日押衣袄上边,不知和甚人在家吃酒?”小娘子道:“我和你从小夫妻。你去后何曾有人和我吃酒。”殿直道:“既没人,这三件物从哪里来?”小娘子道:“我怎知!”殿直左手指,右手举,一个漏风掌打将去。小娘子则叫得一声,掩着面哭将入去。
这和《唐太宗入冥记》的白话文比较起来,是如何的一种进步呢!前几年,有些学者们,见于元代白话文学的幼稚,以为像《水浒传》那样成熟的白话小说,决不是产生于元代的。中国的白话文学的成熟期,当在明代的中叶,而不能更在其前。想不到在明代中叶的二世纪以前,我们早已有了一个白话文学的黄金时代了!
四
这些“词话”,其性质颇不同,作风也有些歧异。当然绝不会是出于一二人的手下的。大抵北宋时代的作风,是较为拙质幼稚的,像《合同文字记》之类。而《刎颈鸳鸯会》叙状虽较为奔放,却甚受“鼓子词”式的结构的影响,描写仍不能十分的自由。但到了南宋的时代却不然了。其挥写的自如,大有像秋高气爽,马肥草枯的时候,驰骋纵猎,无不尽意;又像山泉出谷,终日夜奔流不绝,无一物足以阻其东流。其形容世态的深刻,也已到了像“禹鼎铸奸,物无遁形”的地步。在这些“小说”里,大概要以叙述“烟粉灵怪”的故事为最多。“烟粉”是人情小说之别称,“灵怪”则专述神鬼,二者原不相及;然宋人词话,则往往渗合为一,仿佛“烟粉”必带着“灵怪”,“灵怪”必附于“烟粉”。也许《都城纪胜》把“烟粉灵怪”四字连合着写,大有用意于其间吧。我们看,除了《冯玉梅团圆》寥寥二三篇外,哪一篇的烟粉小说不带着“灵怪”的成分在内。《碾玉观音》是这样,《西山一窟鬼》《志诚张主管》是这样,乃至像《定山三怪》《洛阳三怪》《西湖三塔记》《福禄寿三星度世》等,无一篇不是如此。唯像《碾玉观音》诸篇,其描状甚为生动,结构也很有独到处,可以说是这种小说的上乘之作。若《定山三怪》诸作,便有些落于第二流中了。自《定山三怪》到《福禄寿三星度世》,同样结构和同样情节的小说,乃有四篇之多;未免有些无聊,且也很是可怪。也许这一类以“三怪”为中心人物的“烟粉灵怪”小说,是很受着当时一般听者们所欢迎,故“说话人”也彼此竞仿着写吧。总之,这四篇当是从同一个来源出来的。宋人词话的技巧,当以这几篇为最坏的了。
像“公案传奇”那样的纯以结构的幻曲取胜者,在宋代词话里也为一种最流行的作风。这种情节复杂的“侦探小说”一类的东西,想来也是甚为一般听众所欢迎的。在这种“公案传奇”里,最好的一篇,是《简帖和尚》。而《勘皮靴单证二郎神》的一作,也穷极变幻,其结构一层深入一层,更又一步步地引人入胜,实可调之伟大的奇作。像《错折崔宁》《山亭儿》之类,不以结构的奇巧见长其描写却是很深刻生动的。《合同文字记》当是这一类著作的最早者。《沈小官一鸟害七命》则其结局较为平衍(《古今小说》里有《宋四公大闹禁魂张》一篇,其作风颇像宋人;叙的是一个大盗如何地戏弄着捕役的事,和《勘皮靴单证二郎神》一篇恰巧是很有趣的对照)。
《杨温拦路虎传》大约便是叙说“搏刀赶棒及发迹变泰的事”的一个例子吧。但“搏刀赶棒及发迹变泰的事”和“说公案”毫不相干。“说公案”指的是另一种题材的话本(《清平山堂话本》于《简帖和尚》题下,明注着“公案传奇”四字)。杨温的这位英雄,在这里描写的并不怎样了不得;一人对一人,他是很神勇,但人多了,他便要吃亏。这是真实的人世间的英雄。像出现于元代的《水浒传》上的李逵、武松、鲁达等,又《列国志传》上的伍子胥,《三国演义》上的关羽、张飞等,却都有些超人式的或半神式的。大约在宋代,说话人所描写的英雄,还不至十分的脱出人世间的真实的勇士型ae.
《汪信之一死救全家》有点像杨温的同类,但又有点像是“说铁骑儿”的同类。这是一篇很伟大的悲剧。像汪信之那样的自我牺牲的英雄,置之于许多所谓“迫上梁山”的反叛者们之列,是颇能显出在封建社会里被压迫者的如何痛苦无告。
最足以使我们感动的,最富于凄楚的诗意的,便要算是《杨思温燕山逢故人》一篇了。这也是一篇烟粉灵怪”传奇,除了后半篇的结束颇为不称外,前半篇所造成的空气,乃是极为纯高,极为凄美的。“今日说一个官人,从来只在东京看这元宵。谁知时移事变,流离在燕山看元宵。”这背景是如
何的凄楚呢!杨思温当金人南侵之后,流落在燕山,国破家亡,事事足以动感。“心悲异方乐,肠断《陇头歌》”,恰正好形容他的度过元宵的情况吧。他后来在酒楼上遇见故鬼,终于死在水中,那倒是极通俗的结局。大约写作这篇的“说话人”,或是一位“南渡”的遗老吧,故会那么的富于家国的痛戚之感。
《拗相公》是宋人词话里唯一的一篇带着政治意味的小说;把这位厉行新法的“拗相公”王安石骂得真够了。徒求快心于政敌的受苦,这位作者大约也是一位受过王安石的“绍述”者们的痛苦的虐政的,故遂集矢于安石的身上吧。
五
“词话”以外,别有“诗话”。但二者的结构却是很相同的;当是同一物。“诗话”存于今者,仅有《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三卷,亦名《三藏法师取经记》(《取经诗话》有上虞罗氏珂罗版印本;又《取经记》见于罗氏所印的《吉石庵丛书》中)。共分十七章,每章有一题目,如《行程遇猴行者处第二》《入王母池之处第十一》之类,正和《刘知远诸官调》的式样相同。这是“西游”传说中最早的一个本子,其中多附诗句,像:
僧行七人次日同行,左右伏事。猴行者因留诗曰:“百万程途向那边,今来佐助大师前。一心祝愿送真教,同往西天鸡足山。”三藏法师答曰:“此日前生有宿缘,今朝果遇大明仙。前途若到妖魔处,望显神通镇佛前。”
《取经话》以猴行者为“白衣秀才”,又会作请,大似印度史《罗摩衍那》里的神猴哈奴曼(hanuman)。哈奴曼不仅会飞行空中,而且会作戏曲。相传为他所作的一部戏曲,今尚有残文存于世上。
宋代“讲史”的著作,殆不见传于今世。曹元忠所刊布的《新编五代史平话》(《五代史平话》有武进董氏刊本,有商务印书馆铅印本),说是宋版,其实颇有元版的嫌疑。惜不得见原书以断定之。《新编五代史平话》凡十卷,每史二卷,唯《梁史》及《汉史》俱缺下卷。其文辞颇好。大抵所叙述者,大事皆本于正史,而间亦杂入若干传说,恣为点染,故大有历史小说的规模。其中,像写刘知远微时事,郭威微时事,都很生动有趣。其白话文的程度,似更在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之上。
又有《大宋宣和遗事》(《大宋宣和遗事》有《士礼居丛书》本,有商务印书馆铅印本)者,世多以为宋人作;但中杂元人语,则不可解。“抑宋人旧本,而元时又有增益”(此语见《中国小说史略)第十三篇)耶?书分前后二集,凡十段,大似“讲史”的体裁,唯不纯为白话文,又多抄他书,体例极不一致。所叙者以徽、钦的被俘,高宗的南渡的事实为主,而也追论到王安石的变法,其口吻大似《拗相公》。开头并历叙各代帝王荒淫失政的事,以为引起。其中最可注意者则为第四段,叙述梁山泺聚义始末。其中人物姓名以及英雄事迹,已大体和后来的《水浒传》相同:当是《水浒》故事的最早的一个本子。唯吴用做吴加亮,卢俊义作李进义为异耳。
又有《梁公九谏》(《梁公九谏》有《士礼居丛书》本)一卷,北宋人作,文意俱甚拙质。叙武后废太子为庐陵王,而欲以武三思为太子。狄仁杰因事乘势,极谏九次。武后乃悟,复召太子回。当是“说话人”方起之时的所作罢。
话本的作者们,可惜今皆不知其姓氏。《武林旧事》虽著录说“小说”者五十余人;却不知这些后期的说话人们曾否著作些什么。讲史的作家们,今所知者有霍四究(说“三分”)、尹常(卖“五代史”)及王六大夫(说《复华篇》及《中兴名将传》)等,而他们所作却皆只字不存。
为了“话本”原是“说话人”的著作,故其中充满了“讲谈”的口气,处处都是针对着听众而发言的。如“说话的,因甚说这春归词”(《碾玉观音》);“自家今日也说一个士人,因来行在临安府取选”(《西山一窟鬼》);“这员外姓甚名谁?却做出甚么事来”(《志诚张主管》)。也因此,而结构方面,便和一般的纯粹的叙述的著作不同。最特殊的是,在每一篇话本之前,总有一段所谓“入话”或“笑耍头回”,或“得胜头回”的,或用诗词,或说故事,或发议论,与正文或略有关系,或全无关系。这到底有什么作用呢?我们看,今日的弹词,每节之首,都有一个开篇(像《倭袍传》),便知道其消息。原来,无论说“小说”或“讲史”,为了是实际上的职业之故,不得不十分地迁就着听众。一开讲时,听众未必到得齐全,不得不以闲话敷衍着,延迟着正文的起讲的时间,以待后至的人们。否则,后至者每从中途听起,摸不着那场话本的首尾,便会不耐烦静听下去的了。
到了后来,一般的小说,已不复是讲坛上的东西了——实际上讲坛上所讲唱的小说也已别有秘本了——然其体制与结构仍是一本着“说话人”遗留的规则,一点也不曾变动。其叙述的口气与态度,也仍是模拟着宋代说话人的。说话人的影响可谓为极伟大的了!
参考书目
一、《清平山堂话本》明洪梗编刊,有明嘉靖间刊本,有古今小品书籍刊行会影印本。
二、《京本通俗小说》不知编者,有残本,编入《烟画东堂小品》中,又有石印本,铅印本。
三、《古今小说》四十卷明绿天馆主人编,传本极少,唯日本内阁文库有之。其残本曾被改名为《喻世明言》(?)。
四、《警世通言》四十卷明冯梦龙编,有明刊本。今流行于世者皆三十六卷本,佚去其后四卷。
五、《醒世恒言》四十卷明冯梦龙编,有明刊本,有翻刻本(翻刻者缺《金海陵纵欲亡身》一回)。
六、《中国小说史略》鲁迅著,北新书局出版。
七、《明清二代平话集》郑振铎著,载《小说月报》二十一卷七月号及八月号。
八、《宋朝说话人的家数问题》孙楷第著,载《学文》第一期。
九、《东京梦华录》宋孟元老著,有《学津讨源》本。
十、《都城纪胜》宋耐得翁著,有《楝亭十二种》本。
十一、《梦粱录》宋吴自牧著,有《武林掌故丛编》本。
十二、《武林旧事》宋周密著,有《武林掌故丛编》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