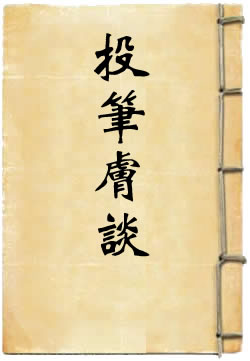近代文学的时代——划分“近代文学”的意义——政治上的黑暗——四个时期——小说戏曲的大时代——短篇平话的复活——长篇小说的进展——诗坛上的诸派争鸣——鸦片战争以来的外患内乱与文学——林纾的翻译与梁启超的散文——以上海为中心的文坛——文学革命的前夜
一
近代文学开始于明世宗嘉靖元年(公元1522年),而终止于五四运动之前(民国七年,公元1918年)。共历时三百八十余年。为什么要把这将近四个世纪的时代,称之为近代文学呢?近代文学的意义,便是指活的文学,到现在还并未死灭的文学而言。在她之后,便是紧接着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文学。近代文学的时代虽因新文学运动的出现而成为过去,但其中有一部分的文体,还不曾消灭了去。她们有的还活泼泼地在现代社会里发生着各种的影响,有的虽成了残蝉的尾声,却仍然有人在苦心孤诣地维护着。
中世纪文学究竟离开我们是太辽远一点了;真实地在现社会里还活动着的便是这近代文学。她们的呼声,我们现在还能听见,她们的歌唱,我们现在还能欣赏得到;她们的描写的社会生活,到现在还活泼泼地如在。所以这一个时代的文学,对于我们是格外地显得亲切,显得休戚有关,声气相通的。
在这四个世纪的长久时间里,我们看见一个本土的最伟大的作曲家魏良辅,创作了昆腔;我们看见许多伟大的小说家们在写作着许多不朽的长篇名著;我们看见各种地方戏在迅速地发展着;我们看见许多弹词、宝卷、鼓词的产生。在这四个世纪里,我们的文学,又都是本土的伟大的创作,而很少受有外来影响的了。虽然在初期的时候,基督教徒的艺术家们曾在中国美术上发生过一点影响;——但中国文学却丝毫不曾被其影响所熏染到。
虽然在最后的半个世纪,欧洲的文化,也曾影响到我们的封建社会里,连文学上也确曾被其晚霞的残红渲染过一番;——然究还只是浮面的影响,并不曾产生过什么重要的反应。她们激动了千年沉睡的古国的人们。这些人们似乎都已醒过来了;但还正是睡眼蒙眬,余梦未醒,茫茫无措地站在那里,双手在擦着眼,还不曾决定要走哪一条路,要怎么办才好。认清楚了,已经完全清醒了的时代,当从五四运动开始。所以近代文学,我们可以说,还纯然是本土的文学。这四百年的文学,实在是了不得的空前的绚烂。
二
但在政治上却又是像中世纪似的那么黑暗。我们的民族方才从蒙古族的铁骑之下解放出来不到一百六十年,便又遇到一个厄运,那便是倭寇的侵略。虽不过是东南几省的遭受蹂躏;文化的被破坏的程度,却是很可观的。再过一百二十余年,一个更大的压迫便来了。清民族以排山倒海之势,侵入中国本部。先蚕食了整个辽东,然后以讨伐李自成为名,利用着降将与汉奸,安然地登上了北京的金碧辉煌的宫庭里的宝座(公元1644年)。不到一年,又陷了南京,擒了福王。第二年又打到汀洲,捉了唐王。到了公元1658年,攻云南,整个的中国,便都归伏听命于爱新觉罗氏的指挥了。几个伟大的政治家,立下了严厉的统治的训条。整个汉民族,驯良的在被统治之下者凡二百六十余年。但清民族不久也渐渐地腐败了。他们吸收了整个的汉文化。当西洋人屡次的东来叩关时,他们便也无法应付了。从公元1842年(道光二十二年)鸦片战争失败,签订南京条约,割香港、辟福州等五口为通商口岸起,几乎是无时不在外国兵舰的威胁之下。
公元1850年到1864年间的太平天国的起义,曾掀起了大规模的社会革命运动,但为期甚短,不能开花结果。甲午(1894年)中日战争之后,中国几成了四面楚歌的形势。要港纷纷地被列强租借去。北方几省虽有义和团的反抗外力运动,其努力却微薄之极,经不起“八国联军”的打击。但因此屡败的结果,革新运动却在猛烈地进行着,从军备的改革,新机械的采用,到教育制度、政治制度的革命,其间不过四十年。公元1911年的大革命,产生了中华民国,恢复了汉民族的自由,开始了中华各民族的团结。革新运动总算得到一个结果。自此以后,国运也并不怎样向上发展。以个人主义为中心而活动的军阀们,几有使中国陷入更深的泥泽中之概。因了欧洲大战和日本哀的美敦书的刺激,便又产生了一次比戊戌更伟大的革新运动,那便是1919年的五四运动。近代文学便告终于五四运动的前夜。
五四运动以后的文学是一个崭新的东西,和旧的一切很少衔接的。五四运动的绝叫,直是快刀斩乱麻似地切断了旧的文学的生命。所以近代文学的终止,也便要算是几千年来的旧式的文学的闭幕、收场。以后的现代的文学,便是另一种新的东西了。这么猛烈的文学革命运动,这么绝叫着的“在一夜之间易赵帜为汉帜”的影响,使那崭新的若干页的中国文学史,其内容便也和以前的整个两样。
【哀的美敦书,源于拉丁语,意思是谈判破裂前的“最后的话”。即所谓“最后通牒”。】
三
就其自然的趋势看来,这将近四个世纪的近代文学,可划分为下列的四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从嘉靖元年到万历二十年(1522~1592)。这是一个伟大的小说和戏曲的时代。我们看见由平凡的讲史进步到《西游记》、《封神传》;更由《西游》、《封神》而进步到产生了伟大的充满了近代性的小说《金瓶梅》。我们看见昆腔由魏良辅创作出来,影响渐渐地由太湖流域而遍及南北。我们看见许多跟从了昆腔的创作而产生的许多新声的戏剧,像《浣纱记》、《祝发记》、《修文记》之类,我们看见雄据着金、元剧坛的杂剧的没落,渐成为案头的读物而不复见之于舞台之上。在诗和散文一方面,这时代比较显得不大活跃,但也并不落寞。我们看见正统派的古文作家们和拟古的诗文家们在作争夺战;我们也看见新兴的公安派势力的抬头。而李卓吾、徐渭诸人的出现,也更增了文坛的热闹。
第二个时期,从万历二十一年到清雍正之末(1593~1735)。这仍是一个小说和戏曲的大时代,但诗文坛也更为热闹。虽然中间经过了清兵的入关,汉民族的被征服,但文坛上的一切趋势,却并不因之而有什么变更,只不过增加了若干部悲壮凄凉的遗民的著作而已。诗和散文都渐渐由粗豪、怪诞、纤巧,而转入比较恢宏伟丽的局面中去。但因了清初的竭力网罗人才;因了若干志士学人的遁入“学问坛”里去避祸,去消磨时力,明末浮浅躁率之气却为之一变。——虽然在明末的时候,风气也已自己在转变。
小说有了好几部大著,像《三宝太监西洋记》、《隋炀艳史》、《醒世姻缘传》之类;但究竟以改编重订的讲史为最多。因了冯梦龙的刊布“三言”,短篇的平话的拟作,一时大盛,此风到康熙间而未已。戏曲是这时期最可骄人的文体;伟大的名著,一时数之不尽。沈璟、汤显祖为两个中心,而显祖的影响尤大。“四梦”的本身固是不朽的名著,而受其影响者也往往都是名篇巨制。在这个时候,传奇写作的风尚,似乎始被许多的真正的天才们所把握到。他们的创作力有绝为雄健的,像李玉、朱佐朝等,所作都在二十种以上。洪异、孔尚任所作也是这时代光荣的成就。
第三个时期,从乾隆元年到道光二十一年(1736~1841)。这时期戏曲的气势已由绝盛的时代渐渐向衰落之途走去,昆腔的过于柔靡的音调,已有各种土产的地方戏,不时地在乘隙向她逆击。终于古老的昆腔不能不退避数舍——虽然不曾完全被驱走。张照诸人为皇家所编的空前宏伟的《劝善金科》、《九九大庆》、《忠义璇图》、《鼎峙春秋》诸传奇,一若夕阳之反照于埃及古庙的残存的巨像上,光景虽阔大,而实凄凉不堪。蒋士铨、杨潮观们所作,虽短小精悍,不无可喜,而也已不能支持着将倾的大厦了。
小说却若有意和戏曲成反比例似的更显出新鲜活泼、充满精力的气象来。《红楼梦》、《绿野仙踪》、《儒林外史》、《镜花缘》等等,几乎每一部都是可注意的新东西。诗坛的情形,也极为热闹。几个不同的宗派,各在宣传着,创作着,也各自有其成绩。散文又为复活的古文运动的绝叫所压伏。但同时潜伏了许久的六朝赋、骈俪文的活动,也在进行着。万派争竞,都惟古作是式;却没有明代的拟古运动那么样的“生吞活剥”。宋学与汉学也不时的在作殊死战。由几位学士大夫们所提议的从《永乐大典》里搜辑“逸书”的事业,廓大而成为四库全书馆的设立;《四库全书》的编纂,虽然毁坏了不少名著,改易了不少古作的面目,但使学者们得以传抄、刊布、阅读,却是“古学”普遍化的一个重要的机缘。明人的浅易的风气,至此殆已一扫而光。然而一个急骤的变动的时代快要到来了。这个古学的全盛,也许便是所谓“陈胜、吴广”般的先驱者们罢?这时代在北京和山东所刊布的《霓裳续谱》和《白雪遗音》却是极重要的两部民歌集,保存了不少的最好的民间诗歌,且也是搜辑近代民歌的最早的努力。叶堂的《纳书楹曲谱》和钱德苍《缀白裘合集》的流布,恰似有意地要结束了昆腔的运动似的。
第四个时期,从道光二十二年到民国七年(1842~1918)。就是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前一年。这是中国最多变的一个时代。都城的北京,两次被陷于英、法、美等帝国主义者们的联军之手(1860年英、法联军陷北京;公元1900年八国联军入北京)。东南、西南的大部分,全陷入太平天国起义以后所生的大混乱之中。外国的兵舰大炮,不时地来叩关,来轰炸。继而有甲午的大败,要港的被强占。但那些事实,可惜都不曾留下重要的痕迹于文学中。太平天国的建立与其失败,是一件可泣可歌的大事,却只产生了一部不伦不类的《花月痕》。义和团的事变,也只见之于林纾的《京华碧血录》及一二部短剧里。文人的异样的沉寂,实在是一个可怪的现象!西方文学名著的翻译,最后,也继了声、光、化、电诸实学的介绍而被有名的古文家林纾所领导。虽还不曾发生过什么很大的影响,至少是明白了在西方文学里是有了和司马子长同等的大作家存在着的。散文,因了时势的需要,特别的有了长足的发展。
梁启超的许多论文,有了意料以外的势力。他把西方思想普遍化了。他打破了古文家的门堂。他开辟了“新闻文学”的大路。他和黄遵宪们所倡导的“新诗”运动,也经验到在旧瓶中装得下新酒的成绩。但这一切,都还不能够有着重要的伟大的影响。他们所掀起的风波,要等到五四运动以来,方才成为滔天的大浪呢。小说和戏曲在这时,俱有复由士大夫之手而落到以市民为中心之概。其一是昆腔的消沉与皮黄戏的代兴;其二是武侠小说与黑幕小说的流行。文坛的重镇,渐渐地由北京的学士大夫们而移转到上海的报馆记者们与和报馆有密切关系的文人们,像王韬、吴沃尧辈之手。这正足以见到新兴的经济势力,正在侵占到文学的领域里去。上海在这时期的后半,事实上已成了出版的中心。
这时期,正预备下种种的机缘,为后来伟大的文学革命运动的导火线,成为这个革命运动的前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