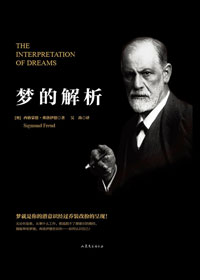米哈伊尔·契诃夫
契诃夫的故乡塔干罗格,在安东·契诃夫的文学作品中得到了反映。这在《套中人》里很明白地显示着,它的主题人物毕里珂夫,便是取自亚历山大·狄珂诺夫。这人是塔干罗格初级学校的教员兼学监,契诃夫是那里的学生。狄珂诺夫一直干了三十多年这个差使,他教出来的许多学生都做了学校的教员或校长了,许多学生成了他的同事—但是他一直没有变化,连他的生活方式也依然如故。他仍然是十年或十五年前的老样子,他穿着如学生所说的“有花纹的”裤子,同样的外衣,住在同样的一间屋子里,说着同样的一套话。他走路的步子很轻,因此学生叫他“蜈蚣”。没有人能够说出他的错处,每个人都和他很熟悉,对他所说的每一个字都那样熟悉,因此,反而注意不到他的优点了。他在学校里开头常说的一句口头禅是:“见你的鬼!”假如他在他的生命中有一次没有说过这句话,那么必定是经过事先考虑的。他并不严厉,但是他也不放松任何规则。一句话,他是一架机器,走路,说话,动作,完成任务,然后炸裂了。狄珂诺夫一生都穿着套鞋,好天气也是如此,总是带着雨伞。
在《套中人》中关于五月节的描写,即学生们跟着他们先生离开市镇到森林中去,也正是塔干罗格的风俗。杜柏克森林离市镇二里地,契诃夫非常喜欢那些五月节,常常喜欢回忆它们。在《姚尼奇》内所描写的公墓,就是塔干罗格的公墓。
许多纯粹是塔干罗格的人物现身在契诃夫的长篇小说《我的生活》当中。他有个姨母叫费多莎·雅佳维列维娜,是他母亲的妹妹,她赋性善良,不仅爱她的亲戚,便是对外人,也是如此。她非常穷困,在一个名叫蒲列克菲·阿列赛耶维契的屠夫那里租一间屋子住。屠夫的母亲管家。但是他对费多莎·雅佳维列维娜比对他母亲更喜爱些,常常把他的钱财全部交给她保管。在《我的生活》中契诃夫生动地描写了屠夫和我们的姨母费多莎:“我们的妈妈,我一定要照顾你。在我有生之日,我一定养你到老;当你死时,我要尽我的财力来埋葬你。”
这些都是蒲列克菲·阿列赛耶维契真说过的话。在小说结尾,契诃夫写道:“他受到一次鞭笞的处罚,因为他在自己的铺子里当众辱骂了医生。”这个事件确实发生过。不过不是在塔干罗格,而是在尼耶尼·诺维哥尔德。那时正流行霍乱,臭名昭著的巴忒诺夫做总督,掌握着最高的统治权。有一个好脾气的店铺掌柜卡得耶夫在和他的顾客的私人谈话中这样表示了他的意见:“你不要信他们那一套,我们城里并没有什么霍乱;那是医生的胡说。”立刻有人在巴忒诺夫将军那里告了密,他命令鞭笞老卡得耶夫,并且把他送到医院里去看视霍乱病人,使他信服这里确是有霍乱流行。这一事件,我记得曾激怒了契诃夫。
1879年的冬天,契诃夫把他的处女作《给我的邻居的一封信》投到《飞龙》上去。我记得他是多么不耐烦地等着编者在报上的“代邮”栏中给他回信。回信来得很快:“还不算怎么坏,我们鼓励你的进一步的努力。”从这里开始了契诃夫的文学生涯。我认为《给我的邻居的一封信》是用我父亲写给我祖父的一封信做底子的。契诃夫在1878年所抄录的这封信直到现在(1923)仍然保存在我的姐姐玛丽手里。
契诃夫的哥哥伊凡·契诃夫在莫斯科附近的伏斯卡尔斯卡当小学教员,那是个像大村的镇子。那里的生活照老样子进行着,生活水平很低,镇上的居民没有破坏它。镇上驻扎着一个炮兵中队,它的头目是b.i.马耶维斯基上校,这是个有力的社会人物。著名的斯拉夫派分子v.d.高洛卡维斯托夫也住在这里,他的太太曾给彼得堡和莫斯科的官立剧院写过剧本。每年契诃夫一家到这里和伊凡消夏,而且就住在伊凡的学校里。伊凡是马耶维斯基的孩子们的教师,他虽然和炮队的官员与莫斯科的知识界混得很熟,但是他总是在伏斯卡尔斯卡度过暑假,在这些日子里,契诃夫一家和这些人交上了朋友,当契诃夫在1884年从医科毕业来到伏斯卡尔斯卡的时候,他立刻熟识了更多的一群人。这个地方的生活中心是马耶维斯基家,他们的孩子安妮、苏亚、阿列霞,都和契诃夫成了好朋友,他把他们描写在小说《孩子们》中。从这里他获得了军事生活的知识,他把它应用在《三姐妹》的剧本里。
这时,安东为彼得堡的幽默杂志《断片》写稿。不多久,他又为莫斯科的小报写稿,不过,这一切写作都只算用笔头开玩笑。那时,初学写作者的稿子能在彼得堡的报纸上登出来,是不常见的。事情是这样发生的:《断片》的发行人,著名的幽默家列金(n.a.lakin)去莫斯科拜访他的朋友、诗人巴列明(l.i.palmin)。他们俩坐在一辆马车里,他们看见有一个长发青年在马路上走着,巴列明对列金说:“这是一个有才华的小伙子。”列金问:“他是谁呢?”“那是契诃夫,你应该向他拉稿。”列金于是来找契诃夫,要他为他的报纸写稿。新的前途这时展开在这个青年作家的前面了:他的作品可以进入彼得堡的报纸了,他的作品不仅要在莫斯科的酒馆里被阅读,而且将要被文学界所重视;那么,他必须做进一步的努力才行。他需要新的材料,于是他开始体验周围的生活。离伏斯卡尔斯卡一里半地是契克诺·塞姆斯忒弗医院,那里的首脑人物是有名的医生p.d.阿尔琴格列斯基,他的名字,作为一个治疗家,是非常有声望的,医科学生和青年大夫都愿意在他的手下工作。安东·契诃夫也是如此。他立即和阿尔琴格列斯基成了朋友,开始诊视病人,为医院帮忙。医院使安东密切地接触病人和下级医务人员。下述事件供给了安东的小说《手术》的材料:有一次,当阿尔琴格列斯基正在忙碌的时候,他吩咐一个医科学生(显然是名医s.p.y)替一个病人拔牙。这个没有经验的学生拿着钳子,费了一番力气以后,竟拔了一个好牙出来。
“不要紧,”阿尔琴格列斯基鼓励他,“能拔掉一个好牙,那你或者就能拔下那个坏的。”
这个学生找到了坏牙,把齿盖敲碎了。病人出言不逊地走掉了。
医生奥斯本斯基常常从忒维尼哥尔德到这个医院来,他会玩种种把戏,能够很滑稽地转动自己的脑袋,用“您”称呼每个人。
“您听着,安东,”他有一次对契诃夫说,“我就要离开了,那里没有人接我的手。必须有一个好小伙子才能接替我的位子。我的蒲拉加亚一定照应您。那里给您准备着一只六弦琴……”
安东·契诃夫同意了,带着我到了忒维尼哥尔德。这个小镇离伏斯卡尔斯卡约有十五里地,是个县的行政中心。作为忒维尼哥尔德·塞姆斯忒弗医院的行政负责人,安东依据职位,奉行本城行政机关训令,诸如验尸,为法院做鉴定,等等。他常常出席县会(参看小说《妖妇》),使他立即熟悉了乡下人、官吏和职员的生活。他在伏斯卡尔斯卡和忒维尼哥尔德的生活,在他的文学工作中作用很大。他的忒维尼哥尔德的观感是他的一系列作品的基础—《尸身》、《验尸》等等。伏斯卡尔斯卡的邮政局长安德烈·雅伏哥罗耶契,后来被描写在小说《应考》中。
契诃夫的小说《流浪者》,包括了许多他1887年在南俄旅行的个人体验。在他的旅行中,特务们监视着他的行动,一个特务接替一个特务跟随他到每一个地方。有一个特务,借口说寺院旅馆没有房间,留宿在契诃夫的屋子里。他把这描写在《流浪者》中,不过把环境完全改变了。
在我看来,《主教》和下列的一些事实是有联系的。
1888年到1889年之间,契诃夫一家住在莫斯科一座二层楼的房子里,房主是加尔内耶夫博士。安东和我住在地下室。我在莫斯科大学上学。我们的母亲和妹妹住在楼上,楼下是会客室。那座大的木头房子,加尔内耶夫博士住着的,充满了大学生,由于博士在莫斯科大学充任副学监,私人招来了房客。在这些大学生当中,有一个是斯提芬·塞尔盖耶维契·k,文科学生。这是一个严肃的、信仰宗教的青年人。我们这伙大学生彼此住得既然这么接近,所以都成了朋友,那个信仰宗教的斯提芬·s.k,便是常常来我们家走动的一个。
我得到法律学位以后,立即在图拉省得到一个位置。斯提芬·s.k也得到了他的学位。不久,我们惊奇地知道他竟当了教士。最后,他当了方丈,后来又做了主教。斯提芬·s.k建立了这种教会中的声名,大约是在他三十岁的时候。我相信他是那时俄国主教中最年轻的一个。作为一个受过大学教育的青年人,他立即发现了主教生活的黑暗的一面。他变成反对派,受到打击,被褫夺了职位,给送到高加索一座冷僻的修道院中去“休息”。当他还在做主教的时候,那个尊贵的教皇常常莅临克里米亚来医治神经痛,他的毛病是由于劳累过度而引起的。在这些会见中,他一定要来看契诃夫,安东这时正住在雅尔达附近的阿提加房子里,生着肺病。这些会见为契诃夫的小说《主教》提供了题材。
下面的事件供给了契诃夫小说《蚱蜢》的背景。
大约在1888年,莫斯科住着一位军医,名叫狄米特·波伏洛维契·k。他的太太是苏菲·皮托维娜。狄米特·波伏洛维契从早忙到晚,苏菲·皮托维娜在他不在家的时间内学绘画。她是个天赋很高的女人,有着一个艺术家的敏感的灵魂。她长得并不好看,但是有着一种极为动人的品格。他们家里聚集着许多人:艺术家、音乐家、作家、医生。我们契诃夫家的人常常喜欢去这里。整个夜间,尽是嘈杂的谈话,音乐和歌唱,在客人堆中是找不到主人的。但是,一到夜半,房门开了,医生的高大的身影出现了,他一只手里拿着叉子,另一只手里拿着刀子,沉静地宣布道:
“太太们,先生们,请过来用点什么吧。”
大家拥到餐室里去,对于食品的质量和花样,都感到惊异。桌子周围简直毫无空隙。苏菲·皮托维娜跑到她的丈夫跟前,捧着他的头,冲动地喊:“狄米特!k!(她常是喊他的乳名)瞧呀,朋友们,这是一张多么出色的脸孔呀!”
有两个艺术家常常到这个家庭里来。一个是风景画家i.i.列维坦,俄国风景油画派的创始人;一个是动物画家s.s。他们不久都成了狄米特·波伏洛维契的好朋友。他们老是隐退在什么地方,一块坐着谈话和喝红酒。其他客人,正如我说的那样,只能在夜半看到狄米特·波伏洛维契·k,当他打开房门请他们去吃宵夜的时候。但是列维坦关于他的不得不出面,有着一种高见,所以他常常被太太们包围着,高声地重复着,卖弄地说:“我疲倦了。”
后来,苏菲·皮托维娜跟着列维坦学画。
莫斯科的艺术家们夏天往往去伏尔加或忒维尼哥尔德附近的苏汶斯基·斯洛卜达作画,而且在那里集体生活几个月。列维坦去到伏尔加,和他同去的是苏菲·皮托维娜。她在那里度过了整个夏日。下一个夏季,她又和列维坦到了苏汶斯基·斯洛卜达。朋友们和相识她的人们开始风言风语了。然而苏菲·皮托维娜每次回家以后,总是照常地快乐地跑到她丈夫跟前,抓着他的手喊:
“狄米特!k!让我抓紧你的洁白的手。看呀,朋友们,多么高贵的一张面孔呀!”
而列维坦仍然继续去看他们,仍然重复地说着:“我疲倦了。”
列维坦和苏菲·皮托维娜之间的亲密,使得画家s厌恶,他向狄米特·波伏洛维契·k倾吐出他的心思,狄米特·波伏洛维契·k也必然早就疑心这种亲密了。显然,契诃夫也讨厌这件事。我记得他嘲骂苏菲·皮托维娜,称她为“沙弗”,并且笑话列维坦。最后,他终于克制不了自己,写了小说《蚱蜢》,他在这里描写了所有这些人,改了名字,用了不同的结局。
这篇小说的出现,在契诃夫和狄米特·波伏洛维契·k的朋友之间,引起了议论。有的人义愤填膺地攻击契诃夫,有些人恶意地冷笑。列维坦阴沉沉地跑来找契诃夫,要他解释。有人说,他甚至要求和契诃夫决斗。但是一切都安然过去了,安东把它当作一场笑话。但是,正如平常那样,在这后面是一种辛辣的、讽刺的笑声。一句话:一切照常,安东·契诃夫和列维坦依然是好朋友。
1891年夏天,我住在图拉省的一个小镇阿列森,我接到安东的一封信,要我找一处房子,他和全家要来这里过夏。我在奥加河岸上找到一座平房。河岸、森林、群山、原野,一切都是美丽的。我选择的这座平房,原来是很蹩脚的一座,后来竟变成了寻找另一处的因素。命运竟好像是来帮助我们的。艺术家列维坦和l.s.米斯诺夫小姐,我们的好朋友,从莫斯科来看望我们,他们从萨卜克哈夫开始乘船走,在船上碰到本地的青年地主n.d.白列姆—克鲁苏维斯基,他正在回到他的距阿列森不远的庄园巴葛弗鲁夫去。他被契诃夫用毕鲁克洛夫名字描写在《住在二层楼的人家》里,“一个青年人,早晨起得极早,穿一件长袍,在晚上喝啤酒,老是说,他始终没有在任何人身上或任何地方碰到过同情”。白列姆—克鲁苏维斯基和他的太太阿妮美莎住在一起,她在小说中的名字是柳勃夫·伊凡诺维娜。他喜欢冗长的谈话,谈我们的时代病—悲观主义。他是一个好人,但是聒絮得使人害怕。
“这是个一望无际的、荒凉的、单调的、烧毁了的草原,”契诃夫这样写道,“当他坐下谈话的时候,不能像人类那样地沉思一下,谁也不知道他将怎样处理自己。”当他知道列维坦和米斯诺夫小姐是去看安东·契诃夫,这个他所敬佩的作家,而且住得离他的庄园又极近的时候,他请求他们去看他。当天晚上,他打发来两部马车,我们大家都到了白列姆—克鲁苏维斯基先生那儿。
我们所碰到的事物简直出乎我们意料之外!这是一片古老的、不为人所注意的庄园。邸宅是凯萨琳一世时的建筑物,是一所巨大的二层楼房子,每间屋子是那么宽大而深长,我们的母亲要从这间屋子走到那间屋子的时候,必须在中途坐下休息一会才成。安东非常欢喜这个地方,这座邸宅围绕着一个古老的花园,有着一眼望不到头的菩提树大道,富于诗意的河流,磨坊,险峻的堤岸,渔场。这一切迷惑了他。他立即向白列姆—克鲁苏维斯基租来这座房子。翌日,我们便搬来这里消夏。安东这样写着:“大厅里有许多圆柱,除了一排长椅以外,没有什么家具,我在长椅上睡觉,在桌子上玩牌。这儿即使在平静的日子里,也常常从老火炉那里发出一种呜呜的声音,暴风雨的时候,整个屋子都战栗着,好像要裂成碎片。这里多少有些恐怖,尤其当夜间那十面大窗户忽然被灯光照亮的时候。”(《住在二层楼的人家》)
在这座房子的大厅里,契诃夫写了他的《决斗》,并着手写《萨哈林岛》(库页岛)。
我不大明白《海鸥》的素材来源,但是那些细节我很熟悉。
在离罗宾斯珂—巴罗葛夫附近的一所阔气的采地上,列维坦在那里过夏。他纠缠在一件爱情的纠纷中,那结果是他想自杀。他确实用枪打过自己,但是子弹在头部轻轻擦过,并没有伤了头盖骨。这个恋爱事件中的吃惊的女主人公,知道契诃夫是个医生,又是列维坦的朋友,并且不愿意把事情公开,她打电话请契诃夫去。契诃夫搭火车去了,情形怎样我不知道,但是后来契诃夫告诉我说,他碰到列维坦头上包着黑色绷带,当这个艺术家向太太们解释的时候,才撕掉了它,扔在地板上。列维坦于是拿了一支枪到湖上去了。他回到他太太身边的时候,带着一只被枪打死的海鸥,扔在她的脚旁。这两段情节出现在《海鸥》里。数年以后,我在报纸上读到一些回忆契诃夫的文章,在这里面一位和我们家相识的太太谈到《海鸥》的情节,她自称就是这个事件中的女主人公。这是不实在的。我曾把前面所说的关于列维坦的情形提出来作为更正。“这个戏,”契诃夫写给一个朋友的信里说,“联系着我的一个最不愉快的回忆,我对此感到厌恶;它的内容与任何东西毫无关系,这对我来说是不聪明的。”
在《海鸥》出版约十五年以后,我遇到一个极美丽的、事先毫不相识的女人,当她知道我是契诃夫弟弟的时候,她告诉了我关于列维坦的故事,和他的失败的自杀。从她的第一句话里,我就明白了她和这个事件是密切相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