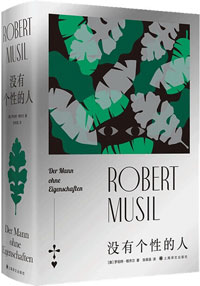美国人认为缅怀过去是对时间的浪费,然而他们对未来却充满了热情,他们认为推荐一种意见或做法的最有效方式是直截了当地说那是大家都准备采纳的意见或做法。这种对他们所认可的东西的期待,或者说对期待的东西的认可,带来了乐观主义的态度。这种乐观是开拓者必备的素质。
英格兰与美国共同的语言与传统类似于其他的家族纽带关系:在生活遭遇大的危机时,他们将会团结在一起,但有时也会闹些小摩擦或是彼此挑点毛病。英美两国社会基础很相似,因此他们相处融洽,息息相通,都会本能地抵制那些阻碍这种和谐关系的东西。如果由于某种错误或是出于某人的失误使得两国之间出现一些分歧,这种分歧常会显得反常。他们都会按照自己的标准评判对方而不会像对待其他外国人那样必须发挥想象力从而站在对方的立场去考虑问题。
在道德、社会风俗和艺术方面,假如按照优点的大小把两国分处高下就有可能会伤害一些人的虚荣心,这种将两国相互比较的危险不仅仅会招致不满,更重要的是这种比较会损害理解,因为实际上优秀品质分很多种,各不相同,而且人们对待自由生活的态度也有所不同。比较是那些无法洞察所比较事物真谛的人所采用的权宜之计,哲学如果只能从某事物与另一事物的关系中去找其本质,那就太肤浅、太注重自我了。其实在美国自然存在的事物的核心都有某种独特的、与其他事物不可比的东西。这就好比一粒种子,它要靠本身的意志力在其特定的环境中竭力发芽、生长。变化是不受约束的结果,反过来自由又是精神上哪怕微小的根本性变化的先决条件。我奉劝读者不要在美国和其他国家之间进行比较,而要忘掉自我,去感受美国生活的内在特征、去观察美国人如何自然地形成其情感与判断,去如实报道在美国这块新的自由天地里所出现的一切事物,也就是说我们有可能做到由表及里。
但美国人并不只有一个,而有好几百万,分布在东南西北各地,有男有女,有老有少,种族、职业以及宗教也有差异。诚然,我所举的那个美国人是虚构的,但是在阐述这类问题时运用寓言式的手法是必要的,而且不妨承认这一点。讨论自然存在的事物时,我们常会感到力不从心,讲求实际的人也许注意不到这一点,但是事实上人类的言论本来就不是针对自然存在的事物的,而是针对概念的本质,针对思想所提出、所戏弄的诗歌似的言词或逻辑术语。当命运或必然性把我们的注意力从这种惬意的概念游戏转移到赤裸裸的事实和亟待解决的问题上时,我们才会放弃华而不实的思想,去关注生活中那些大事的标志。我们只得用自己想出的标准去考虑世界上的一切活动与价值观。我所提到的典型的美国人就是这些标志之一。如果我要谈论按照迂腐传统进行分类的群体或是概念化的个体,我仍然要依靠标志来表达,创造出道德上的标准和虚伪的简便。碰巧,概念化的美国人与实际情形十分符合。虽然在美国生活着一些黑人,个体美国人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但是他们所处的环境以及习俗、性情、思想却有很明显的一致性。他们都离别了故土与祖坟,毅然决然地一起投入了一个新的生活漩涡,而这个漩涡所在处原本是个空荡荡的地方。做一个美国人这本身就意味着一种新的道德状态,新的教育和新的生涯,因此哪怕是一点点唯心主义的虚构都足以掩盖每个美国人性格中的大部分特点,或掩盖大多数美国人在社会见解和政治判断上的总体取向。
托马斯·杰斐逊
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1743—1826),美国《独立宣言》的推动者,第三任总统。他曾游历欧洲,记下新成立的美国所要避免的任何东西,对美国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美洲的发现为欧洲人提供了一种新的迁徙选择,除了黑人以外,所有的殖民者都是自愿放逐自己的。那些幸运者、守旧者和懒惰者难离故土,而具有不安分天性的人或者被他人排斥的人则很想去开辟新的天地。从这一点来看,美国人是最具冒险精神的人,或说是欧洲那些最具冒险精神的人的后裔。他们骨子里未必明智,但一定是社会上的激进分子。对于他们来说,过去的东西,特别是久远的过去的东西不仅没有权威,而且是跟现实无关的、拙劣的、陈腐的。美国人认为缅怀过去是对时间的浪费,然而他们对未来却充满了热情,他们认为推荐一种意见或做法的最有效方式是直截了当地说那是大家都准备采纳的意见或做法。这种对他们所认可的东西的期待,或者说对期待的东西的认可,带来了乐观主义的态度。这种乐观是开拓者必备的素质。当然这样的性格不可能仅靠继承存在于某个国家。对传统的继承往往会使一个民族变得平庸,使那个民族屡屡出现返祖现象。美国人的特性得以保持且普国认同源自社会的传播功能或民主制度中极大的社会压力。然而有些美国人不那么幸运,他们或者生来保守,或者对富有诗意的微妙、虔诚的静修、令人愉快的激情感兴趣,不过这些人的耳边总是充斥着诸如要出色地工作、要发展、要进取、要变革、要繁荣的话语——每扇门都只朝这个方向敞开,所以他们要么封闭自己,在某个不被人注意的角落自生自灭(有时我们会在一些偏僻的地方发现这样的孤独、憔悴的唯心主义者),要么他们会直赴牛津、佛罗伦萨或蒙玛特尔[1]去拯救自己的灵魂,或许也可能是去躲避拯救。
先驱者的乐观主义精神并不只局限于对自身的看法以及对自己未来的展望,而会继续发展。因为他充满自信、感到安全、心情舒畅,所以他总是微笑着友善地对待周围的人和事。人们常认为个人主义、粗莽和自恃总与自私和无情相随相伴,但我认为这是一种偏见。伤害我们睦邻关系的应该是依赖性、不安全感和互不相让。当人们感到失望时(他们肯定会很快感到失望)对人们爱心的奢求就会导致怨恨和最终的卑鄙。只要盛奶的容器不摇晃,分别放在凉爽的地方,也不常打开盖子,那么人类的善良之奶就不容易变质。美国人并不多愁善感,但他的感情却很深沉,待人总是很友善。假如让我观察某个人的内心深处,却找不到友善的影子,那我敢断定这个人一定不是美国人。但是由于美国人是个人主义者,他的友善也绝非并无所图。美国人生性和善,他敬重每一个人,希望人人都幸运。但他也有衡量友谊的大致尺度,他希望每个人都自强自立,并且在轮到他帮助别人时也能不吝援手。在他向邻居提供了一次机会之后,他认为这已经足够了。但在他看来提供一次机会还是责无旁贷的。
18世纪中期的波士顿
正如自信有可能发展成自负一样,乐观、仁慈和友善也会演变成对一切事物的糊涂的滥爱。对于心地善良的美国人民而言,很多东西是神圣的:性是神圣的,女人是神圣的,孩子是神圣的,生意是神圣的,美国是神圣的,共济会的集会地是神圣的,大学俱乐部也是神圣的。这种崇敬之情出自美国人对这些事物抱有的良好愿望,而且正是因为有了这份崇敬之情,这样的良好愿望才得以延续。如果美国人并没有把这些事物看成神圣的,他也许就会有时怀疑它们是否完美。贫寒的单身女人的唯心思想也属于这种情况,她们能够从丑陋的事物中看出美的内涵,她们感到十分幸福,因为她们的老狗有那么哀婉的眼睛,牧师的话那么感人,只有三棵向日葵的花园那么赏心悦目,已故的朋友曾经那么忠诚,自己的远亲那么富有。
美国的一所教堂
美国是一个宗教色彩很浓的国家,有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信教。美国人认为很多东西都是神圣的:性是神圣的,女人是神圣的,孩子是神圣的,美国是神圣的……
现在来想想美国的空荡荡吧,这不仅是指某些尚无人涉足的有形的空荡荡以及北美大陆尚存的主要的空旷特征,而且还有精神上的空荡荡。一个移民点的人,甚至他们那种家很容易就能迁往其他地方,几乎没有人在他的出生地长久地生活下去,也没有人相信上学时老师的教导。美国人并非一气之下抛弃了这些累赘的东西,只不过是他东奔西走时不知不觉地就忘了那些东西。广袤的土地给精神和身体都带来了一种自由。你可以随意在任何地方支起帐篷,或者如果你想搭建点什么,你可以随心所欲地把它建成任何你喜欢的风格。你有足够的空地、现成的材料,而且不受任何固定模式的约束也不会遭到任何批评。你相信自己的经验,不仅因为你别无选择,还因为你发现你可以安心地而且很顺利地这么做。对一个想去开拓、探索的人来说,决定运气的东西并不太复杂。正因为你可以轻装就道,所以你花钱似流水,但是也取得了令你高兴的经验。失去一切身外之物其实算不上失去了什么,因为你仍然毛发无损还是原样的自己。同时你的进取心会给你提供应付新情况、不断创新的机会。此外,进取心还能教会你如何明智地处理问题。你的生活与思想将会变得简单、直截了当,没有什么可喜的起色和变化。你所做的一切都很刻板、很重实效,你不明白人们有什么必要为了所谓的优雅(也就是本能或习俗)而作出那些无关紧要的牺牲。在你看来,美术是传统的奢华,就跟希腊语和梵语一样,都是用来取悦贵妇人和阔小姐的。因为虽然你十分欣赏办事慷慨的风格,你却并不承认办那些事不是为了利益。遗憾的是艺术制作从本质上说也应该是慷慨的并令人愉快的,因此艺术的问题并不在其明确的专业追求上(因为这时美术便成了一种实际的任务和某种生意),而在于其影响广泛的魅力上,天才的艺术家都追求这种魅力,这种魅力也是人类一切行为合格的标准。精致比简约更受喜爱,精致需要造诣,而简约则是最基本的标准;风格会受些许损失,表现能力损失最大。对于美国人而言,想用新奇方法尽快处理问题的急切心情和赶紧收获成果的热情使他不愿追求历经曲折才会得到的享受。取得成功的路必须是捷径,而象征只能仅仅是象征。如果他的妻子渴望奢华,她当然可以得到;如果他有某种恶习,那也是允许的,但所有这一切都必须分门别类地记录下来。
同时,美国人还富于想象力,通常生活紧张的地方,人们的想象力也格外丰富。人们如果缺乏想象,就无法生活。但是他的想象力是现实的,所预测的未来也是很直接的,在数字、度量、设计、经济以及速度等方面他都根据自己的经验,用最明确的措词来说明自己的想法。他在处理问题时是个唯心论者,但在理解了事物的物质潜力之后,他却可以成功地发明创造,稳妥地改革,迅速地应付紧急情况。一生中他总是能够及时投入并及时退出,从不会落伍也不会付出很大的代价。有种热情使他能够有分寸地驾驭物质力量,这种热情甚至使他收敛了平时的偏执秉性。好的工匠很难将自己的能力和自己的艺术意向分辨清楚,也分辨不清自己的潜力与能够实现自己意向的东西之间的差别。据此他的理想也会以某种预感或预言的形式出现,其中一些谨慎作出的预言通常会成为现实。美国人快乐工匠式的理想便是如此。当他是个穷孩子时,他也许会梦想能够上学,后来他真的就上了学,或者至少得到了一个学位;他梦想腰缠万贯,后来他真的变得很富有,也许在速度和程度上并未如他所愿;他梦想能够娶到他所爱的拉结(《圣经·旧约》中,雅各的第二个妻子,他第一位妻子利亚的妹妹),而实际上他娶到的是利亚,即便如此,他仍会在利亚身上看到拉结的影子。他梦想能为支持并推动一个庞大、活跃和进步的社会的发展作出贡献,后来他的确做到了。与自然紧密相连的理想差不多总能实现,美国人自信且满怀主宰意识地微笑着,他相信上帝和自然都在帮助他。
自信的美国人
图为1773年,第一位真正的“西部人”丹尼尔·布恩率领一批人向美国西部进发。“美国人自信且满怀主宰意识地微笑着,他相信上帝和自然都在帮助他。”
据此美国人的唯心论总是与对现实的满足和对未来的憧憬携手同行。美国人不是革命家,他相信自己正沿着正确的道路走向美好的未来。而对那些革命者来说,对现实的不满是唯心论的基础和表现形式。在他们看来,现存的事物只是一些无理性的事件和恶习的荒谬混合,他们希望未来基于推理而且是他们所奉行的行为准则的完全体现。他们对与现实截然不同或完全不可能的事物(如果他们想象得出的话)有热情,这种事物很单纯,他们喜欢并且相信这种事物,因为他们的本性有这种需求。革命者认为只有消灭掉生活中的一切官僚机构才会有生活的自由,因此在寄托希望时他们是极端的唯心主义者,但在涉及感知和记忆时,他们则远不像诗人和艺术家那么唯心。在文明社会中他们对一切隐现的美好事物颇为麻木,因此在对现实的事物的看法上,他们往往是粗心的现实主义者;他们对道德世界的无知和缺乏经验表明他们不善于接受教育(除非那无知和无经验是运气不好造成的)。正是缺少教育和内在活力的共同作用催生了唯心论。在理性方面,我们应受谴责的是我们爱用想象的东西永远取代事物本身的面貌;如果扩大一点来说,我们应受谴责之处还在于我们总爱先验地空想,然而这种空想却使我们勇敢而固执地追求我们所谓的美好的东西——也就是能满足我们本性需要的东西,哪怕命运为这种追求提供的机会很少。但是革命者缺乏对过去和现在事物的洞察力,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对未来的唯心主义判断,从而使他们对未来的梦想难以实现。对人类而言,经验对于正确的具体思想的形成是至关重要的,而对其他动物来说也许并非如此,因为它们的思想比我们的更早定型。甚至我们原始的本能也是在遇到了诱发它们的时机才得以表现出来的,而且这些本能可能刚一得到部分的满足就会发生变化。因此不能完善经验而只去完善先验的空想的人不具备准确预言的能力。他的梦想都是痴心妄想,他的意见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正相反,美国人的唯心论则极其有益,与可行的变革息息相关。美国人的烦恼源于无益的或与变革无关的事物的干扰,无论那干扰是唯心论还是惰性,因为那会使他所期待的很容易得到的成就付诸东流。
美国人是活力十足的,他的活力并不总能找到合适的表现形式,这令美国人在表面上显得焦躁不安,他总是夸张地表现自己过剩的精力。但美国人的活力并不脆弱,那是一种内在的动力,其反应像磁针那么敏感、迅速。美国人好奇心强,并且总能立即回答自己提出的问题,但是如果有人试图教他们处理那些他们不感兴趣的事情,他们会格外地抵触与健忘。因此,美国人总是在一些方面非常在行,而在另一些方面则十分愚钝。他们并没把人类可悲的历史放在心上,总之,美国人还不成熟,还很年轻。
我们都觉得美国人还很年轻,这有没有道理呢?他们的国家跟任何其他国家一样也有许多上了年纪的人,他们也是亚当的子孙或者是亚当的达尔文主义对手的子孙,这跟他们的欧洲远亲没什么两样。他们的观念也并非总是很新。像小孩子一样,他们的头脑里并没多少陈腐、僵化的道德与宗教方面的戒律,却知道不少适用的古老政治知识。他们虽然十分熟悉这种古老的政治知识,却并不等于十分理解它。把传统的观点隔离起来不加以任何批评,这种做法本身即是一种不成熟的表现。一个规规矩矩的年轻人自然是保守的,他会对没经过自己亲身检验的所有问题都持毫不怀疑的态度。在美国,涉及政治、婚姻或文学的自由看法比较少见,那些方面的问题往往是女士们闲谈的内容,女士们通常会毫不客气地予以抨击,而男人们则只顾埋头干自己的工作。因此,尽管美国人的观念一般说来是守旧的,但他们显然还比较幼稚。我想这大概有两种原因。一种原因是他们主要关心的是周围的环境和眼前的事情,另一种原因是他们对周围环境的反应时常是本能的、不露声色的、轻松的、自信的。他们的观念还很单纯,他们的意志还未消沉或改变。然而,跟在其他方面一样,他们的观念和意志目前也许会发生大的变化,因为他们可能正迈向成年。我所说的这一切或许并不符合他们的现状,更不符合他们的未来。我只是就我的了解发表对他们的看法。无论他们身上的精神力量今后变得有多大,我也会很高兴在他们尚不成熟时便认识了他们。即便青春有点不那么稳重,可是其魅力却在于它常有本性的冲动,它能毅然地服从那种单纯的、富于潜在生命力的原则,正是那种原则塑造了身体及身体的器官并且总是在指导它们的动作,除非恶习或必要迫使那原则让它们扭曲或中止它们的作用。即便岁月必然使人外表变老,可是精神却可以永远年轻,只要精神能找到突破口,它还会立即返老还童。虽然跟最有朝气的美国人一样,在内心里我们都很年轻,但是美国种子却落在了处女地上,它可以在那里更勇敢地迅速生长,不必顾虑参天大树的面子。当一个民族自然成长的青春期为较多的所有物和先入为主的观念所累时,它就会显得比较老,会念念不忘那些自己失去的或错过的东西。美国人则没有这种毛病。
美国的第一面国旗
美国的国旗是由贝特西·格丽思康于1776年根据华盛顿等人的要求设计的,国旗上有十三颗星和十三条条纹,象征着全新的“国家格局”。桑塔亚那认为这个年轻的国家充满了活力。
在美国,人们对存在有一种虽未明言却很乐观的看法,即存在越多越好。无情的批评家也许会竭力争辩,认为“量”只属于物理范畴,并不意味着“质”优,然而无论好坏,“量”至少提供了充足的机会。年轻人总是满怀好奇心和渴望,他把存在看作美好事物的前程,他的生存本能决定了他相信无论自己将成为什么、将看到什么、将做什么都是有价值的。因此,重视量并不是对“巨大”的幼稚的欢欣和惊奇,那是渔夫面对一大网鱼的喜悦,他自然会觉得要好好享用它们。这样的乐观主义是温良的乐观主义。造物主没能让我们在人生之初就很精明、很有见识,但是她鼓励我们用自己的能力去获取成功并从中享受乐趣,那种乐趣往往使我们忘记了辛劳,正像垂钓者的乐趣往往在于钓鱼而不是吃鱼,他总是耐心地等待鱼儿咬钩,常常误了吃晚饭的时间。开拓者必须专心致志地为成功做好准备工作,他必须为未来而尽心尽力。为了工作而敬业是有益的同时也是他应尽的责任。此外,除非他所有的行为都为最终目的的实现起到了一定的实际作用,否则他就有变成一台活机器的危险,那样的机器只会可笑地徒然运转。针对工作的唯心论可以掩盖针对生活的认真的唯物论。既然人是有理性的动物,那么他就不可能仅靠面包生活,也不可能每天只是干活。他必须让吃饭和工作达到理想的和谐并且让这种和谐贯穿终生,而这种和谐的实现有赖于吃饭与工作相关联的方式,或者说有赖于它们共同的最终目的。否则,尽管他那专门的哲学将自己称作唯心主义,其实在行为标准上他却是个唯物主义者。他尊重东西,因为它们有使用价值,他尊重自己因为自己有力气。就连感觉论者、艺术家、享乐主义者也比他明智,因为即使他们的唯心主义是杂乱无章的或者是腐朽的,他们却得到了某种理想的东西,并且只重视那些有实际作用的东西。尽管他们也许目光短浅,却并不违反道德标准。当我们不把知觉当成行为的信号而是抓住并仔细察看它实际反映的东西时,就会发现知觉指示了某种概念性的东西——一种颜色、一种形状或一种声音。如果根本不去考虑它们的实质意义,只把目光停留在这些东西的存在层面上,那便是美学上的唯心主义或梦幻的唯心主义。从这种唯心主义转向对物质的认识是理智上的一大进步,也关系到对世界的支配,因为在使用工艺中,人的思想对准的是较大的对象,这就需要思想更有深度、更有潜力。具备了这样的思想才会使人觉得所谓的物质世界是真实的,而理想的世界并不真实。物质世界当然是真实的,因为否认物质存在的哲学家就像否认荷马的批评家。如果从来没有过荷马这么一位诗人,那么一定有过许多文才不亚于荷马的其他诗人。如果物质并不存在,那么一定存在着其他东西的结合体,这种结合体会具有同样的物质性。然而,如果物质没能带来精神成果,那么物质世界的严酷现实就会阻止它成为我们眼中令人生厌的废物,或者甚至成为恐怖的深渊。实际上,物质的确带来了精神成果,否则我们也就不可能挑剔它的毛病,提出与之相反的理想的东西的标准了。大自然是物质性的,然而却不是唯物主义的,有大自然才有我们的生活,她哺育出各种激情和闲置的美的东西。除了大自然的精神成果之外,我们认为其无意识的辛劳与混乱也都具有精神唯物主义的性质,而对其精神成果的不断感知和热爱则是精神唯心主义——这里指的是非物质的东西带来的欣喜与融洽,例如喜爱、思索、宗教信仰以及其他一切美的表现形式所给我们的感受。
美国人的生活环境迫使他们接受了精神唯物主义,因为在他们与物质的东西打交道时,他无暇停下来欣赏那些东西中合理的因素(那些因素是理想的),也不会立即懂得它们最终的用途(那些用途也是理想的)。与诗人相比,他们是世俗的。人们通常认为这种唯物主义给人印象最深的表现是美国人对万能的美元的热爱。然而那只是一种外国的无知的看法。美国人总是提到钱,因为钱是他能够很方便地衡量成功、智慧和能力的标志。可是单纯就钱本身来说,他可以挣钱、失掉钱、花钱、不当一回事地把钱赠人。在我看来,他的唯物主义给人印象最深的表现是他对“量”的偏爱。例如,如果你去参观尼亚加拉瀑布,你可能会想肯定能听到美国人介绍这个大瀑布每秒钟有多少立方英尺或公吨的水从山崖泻下,又有多少座城镇(以及多少城镇居民)的照明和动力之源是这个大瀑布,以及得益于这种动力的工业的年产值有多少,这个世界最大奇迹的水力资源取之不尽,依靠它而生产的工业也不会伤害旅游业的发展。抵达靠近瀑布的布法罗市时,我很有把握地认为会听到这样的介绍,可是我错了。我听到美国人介绍的第一件事是布法罗所拥有的柏油人行道的英里数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城市都多。这种对“量”的偏爱并不仅体现在工商界人士身上。有个学期刚开学不久,哈佛学院的院长遇见了我,他问我教的班的情况如何。我回答我觉得他们学得还不错,学生们似乎都比较好学,也很聪明。院长打断了我的话,好像我正浪费他的时间。他说道:“我的意思是你班上的学生的人数是多少。”
美国的巨头们
四位巨头分别是:安德鲁·卡内基、约翰·皮尔蓬特·摩根、约翰·d.洛克菲勒、安德鲁·梅隆。他们都是美国财富大亨。美国人总是提到钱,因为钱是他们能够很方便地衡量成功、智慧和能力的标志。可是单纯就钱本身来说,他们可以挣钱、失掉钱、花钱、不当一回事地把钱赠人。
我想我们会发现这种对“量”的爱有个常保持沉默的伙伴,这是位对于“质”总不好意思开口的伙伴。民主的良心对任何有特权味道的东西都采取躲避态度,它唯恐将不适当的特权赠给了什么追求或什么人,便把对所有东西的认定尽可能压低到“量”这个有共性的标准上。数字不会撒谎,但是假如涉及对美国哲学各种理想的美与英国哲学各种理想的美进行比较的问题,那该由谁来决定呢?大学里所有的学科都不错(否则还要大学干什么?),可是那些吸引学生数量最多的学科却应该得到最大的鼓励。院长所提问题的根由即在于此。对“质”不好意思开口的民主信仰把教育的缰绳丢在了学生的脖子上,就像堂吉诃德把缰绳丢在了瘦马驽骍难得的脖子上那样,让天赐的直觉自行其是。
美国人还从未面对过《圣经》故事中约伯所遭遇的那么多危难的考验。他们已经有了成功地克服大危机(如南北战争)的经验。既然他们已经再次成功地战胜了大危机,他们可能会像另一次那样完全致力于发展企业、争取富足。然而,假如严重的无法克服的苦难突然降临,他们会是什么态度呢?到那时我才能发现其性格深处是唯物主义的还是唯心主义的。同时,他们的脑子也不会总是运转而不休息。他们喜欢幽默,甚至喜欢风趣的言词。幽默是精神上无束缚的一种表现。他们热爱自然景色、热爱人类、热爱知识。他们发现至少音乐是一种他们真正喜欢欣赏的艺术。在音乐和自然景色中,在幽默和友善里,他们真切地感受到了理想,或许比他们在乏味的学院派唯心主义和繁忙的宗教里所感受到得更真切,因为甚至连美国的宗教都整天忙着开会、筹集房屋建筑基金、开办学校、组织慈善机构、建俱乐部、搞野餐活动(英国是否也是如此呢?)。为了简朴而生活得穷一点,为了产品更精美,同时也是为了让人们省点心并摆脱废物之累,而少生产一些产品——美国人的脑子里还没有这种理想。然而我好像在各处都能听到人们的叹息声,那是不堪天天忙碌和社会压力的呻吟。这种渴望压力减少的重要证据是那些大众化宗教的新的变异,它们并不仅仅是传统的变异,而是新出现的花样,例如基督教的奋兴运动、唯灵论、基督教科学派、新信念派。目前有些外界的或精神上的力量尚未被人类所利用,无论我们是否能通过某些途径利用它们(在这方面没有什么事是完全不可能的),我们无疑可以尽量消除生活进程中的阻力与浪费。我们可以松弛病态的过度紧张、解除对本能的束缚、抚平心灵上的伤痕,让自己变得朴实、可爱、心平气和。这些宗教运动正是朝着这种有益于人类健康的目标努力前进的。虽然这些运动是平民的运动,没有什么伟大的指导思想,也并不企图把人从平庸、单调、世俗的生活状态下解脱出来,不过它们却有可能在这个较低的基础上让人变得心身健康,并且正在做着这样的追求。这才是真正的道德规范。像各种动物的天赋一样,我们各种生活和思想的尊严价值也是相对的。势利小人只敬慕一种人,他敬慕的人也颇能说明势利眼的偶像是什么样的;或者势利小人对他们既羡慕又憎恨,这种态度本身即是势利眼的态度。正相反,向圣弗兰西斯、狄更斯那样真正热爱生活的人就晓得在每一座泥巴住宅里,无论其主人天资如何、地位怎样,却可能生活得十分美满。就像不应有地狱惩罚的威胁那样,也不应有逼迫工作、逼迫前进、逼迫改革的命令与威胁。如果一个人的灵魂不自由,那么世界的解放对他又有什么好处呢?思想自由来不得虚假,因为理想即是心愿也是理智的表现。在生活中,我们真正需要的是经常暂停奔波忙碌去享受生活,是使我们的思想感情升华到能欣赏真正美好的事物的境界,那么一旦我们发现并喜欢上了那些美好的事物,无论发生了什么其他事,都不会影响我们的幸福感。这种自然理想主义并不意味着我们不重视物质,只说明我们有朝气、有活力。美国人民有正常的理智。当理智处于正常状态时,它便已经摆脱了一半的束缚、其本身即已经变成了一种乐趣。美国人民有副热心肠。正直的古道热肠必有善报。好人的心不应总是单纯为血液的循环而辛勤地工作,时间及其本身的跳动将为它安上翅膀。
* * *
[1] 蒙玛特尔,法国巴黎北部一座小山,位于右岸区,因其夜生活与凡·高、土鲁斯-劳特累克和尤特里洛等艺术家有关联而著名,原属蒙玛特尔村,于1860年并入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