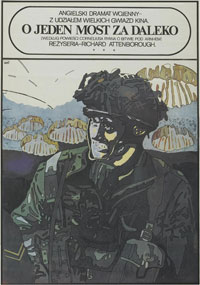哈登·钱伯斯[1]。今天早上我听说哈登·钱伯斯前天早上死了,我说了一句:“可怜的家伙,我很难过。”但我立即意识到我说这话完全是照着很蠢的惯例。在哈登·钱伯斯自己看来,他这一辈子过得相当成功。他很好地享受了自己的生活。他大势已去,除非他那洋洋得意的脾性能给他找到哲思来源,不然这世上也没什么东西可以吸引他这种脾气的人了,他不会有什么盼头了。他死得正是时候。如果将来人们还能记得他的话,那不是因为他的戏剧,而是因为他创造的说法:“the long arm of coincidence(无巧不成书)”,很可能英语能存在多久,这句话就能熬多久。他个头极小,一套时髦的衣服松松垮垮地套在干瘪的身上,好像一片枯叶。而就像落叶一样,他常常飘进自己常去的地方,停留片刻,你还没觉得他有一刻的安定,他就又漫无目标地飘走了。他似乎对哪里都没有多大的眷恋。他来了,又走了,好像听命于随意的机遇。他乍看上去还算年轻,但再仔细看时,就会发现他其实老矣,老得很啦;他的眼睛静下来便显得很疲惫,他得拼着意志力才能让两眼炯炯有神;他的脸平滑得不自然,像是做了按摩,敷了雪花膏来滋养;他看上去像是个埋在地下多年的人,然后又被挖了出来。这让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老得多。他从来不说自己的年龄。他生命中的头等大事就是显得年轻,对于其他事他从未如此严肃对待。他有“情圣”的名声,且极其看重这一点,远甚于他看重他的戏给他带来的声誉。他无数风流韵事中至少有一件是闹得尽人皆知,这件事有这么大的名气,他一直到死都引以为荣。他总喜欢装出一副他在和什么人暗通款曲的样子,时不时含沙射影一下,给一点暗示,说话只说半截,挤眉弄眼,耸肩摆手,让你充分了解他仍在追求自己的风流大计。但是当他从俱乐部里出来,穿着对他来说太年轻了的衣服,一副潇洒派头,摆出要去约会的架势时,你会忽然觉得他其实是要去索霍区[2]某个餐馆的后屋吃晚饭,在那里他不会碰上认识的人。既然他是写剧本的,我想大概得算他是个文人,但真没有哪个文人这么不在乎文学的。我不知道他是否读书,但他和人谈话绝对从没讨论过书。他唯一还感点兴趣的艺术是音乐。他一点不在乎自己写的那些剧本,但当有人把他最好的戏剧《霸道的眼泪》当成是奥斯卡·王尔德写的时候,他却恼火不已。犯这样错误的居然还大有人在,我实在是想不通。只要稍微对对话有点感觉或是对幽默有点品位的话,就不可能犯这种错误。奥斯卡·王尔德的对话简洁精炼、尖锐率直,而他的幽默则是温文尔雅、文质彬彬;《霸道的眼泪》里对话松散,恰当却一点都不精彩,一点都没有警句那样的精辟透彻;它的幽默像是酒吧而不是沙龙里出来的。它的趣味在于应景,而不是因为它措辞方面有什么高明之处。它一看就是哈登·钱伯斯写出来的,具有其鲜明的特质。他是个喜爱交际的家伙,当我想要总结他的典型特征时,我就会看到一个衣冠楚楚的小个子男人,泡在酒吧里,和一个泛泛之交就能愉快地攀谈起来,谈女人,谈马、谈科文加登[3]上演的歌剧,可又一副在等人的架势,好像随时可能有人走进门来见他。
* * *
[1] 哈登·钱伯斯(haddon chambers,1860—1921),一位剧作家,出生在澳大利亚,1882年移居英国后一直活跃在当地戏剧界。
[2] 索霍区(soho)是伦敦的一个区,以餐馆多而闻名。
[3] 科文加登(covent garden)是英国伦敦的一个广场,现为皇家歌剧院所在地,是英国国家歌剧和芭蕾舞团的起源地。原为威斯敏斯特的本笃会女修道院花园,1630年规划为住宅区广场,在1670—1974年间一直是伦敦主要水果、花卉和蔬菜市场。早先的剧场称为皇家剧院,建于1732年,上演各种戏剧、哑剧和歌剧。曾被大火焚毁两次,后又重建,其间先后改为皇家意大利歌剧院(1847)和皇家歌剧院(18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