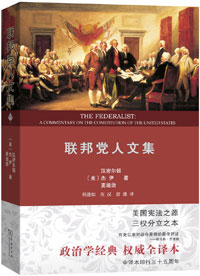又是太阳。海面闪闪发光,远山露出烟蓝色的轮廓。这一切都渐渐留到下边——公路蜿蜒着越盘越高了。
小城远远地在下边闪着白色,显得越来越小,渐渐消失了。防波堤就像用铅笔画的一条细线似的,笔直地把碧蓝的海湾勾绘出来。留下来的格鲁吉亚轮船,发着黑色。不能把这些随身带走——真可惜得很。
不过,就是没有这些,得到的各种东西也不少了。运着六千发炮弹,三十万发子弹。精壮的格鲁吉亚马匹,套着油黑的绳索,拉着十六门格鲁吉亚大炮。格鲁吉亚马车上,载着各种各样的军用品——野战电话、帐篷、铁蒺藜、药品;救护车在走着——都是满载而去。只缺粮食和马料。
马饿得摇着头,忍着饿走着。战士们紧紧勒着肚子,可是都很高兴——每人腰里都带着二三百发子弹,在飞扬的灼热的白色尘雾里,精神百倍地前进。跟着行军跟惯了的,时时不离的苍蝇,成群地飞舞。在灿烂的阳光里,大家都和着步调唱起来:
酒楼的——女主——人哟——酒少,
啤酒也少,蜜也少……
大小马车、两轮车、轿车,都无穷无尽地吱吱作响。瘦弱的孩子的小脑袋,在红枕头中间晃来晃去。
徒步的人仍旧戴着鸭舌帽、荷叶边的破草帽和毡帽,拄着棍子,女人穿着破裙子,光着脚,抄着盘山公路中间的捷径走着。可是已经没有一个人再用树条赶牲口了——没有牛,没有猪,也没有家禽,就连狗也饿得不知下落了。
无穷无尽的蜿蜒的长蛇,转动着无数的环节,从深沟、悬岩、山峡旁边走着,往荒凉的石岩上爬着,向山口爬去,他们要翻过山头,重新下到那有粮食和马料,有自己人在等着的草原上去呢。
抛开了不幸和悲哀,
将要饮酒而行乐……
骑士啊,勇敢些吧!骑士……
在城里弄到一些新唱片。
高不可攀的山顶,耸入蔚蓝的天空。
小城隐没在下面一片苍茫里。海岸也消失了。海洋好像一堵碧蓝的墙壁出现在那儿,公路逐渐被树顶遮住。暑热、灰尘、苍蝇,路旁是冲积的碎石和森林,荒芜的森林,野兽的巢穴。
傍晚时候,不断吱吱响着的马车上传来一片叫喊声:
“妈妈……吃……给吃的……吃!……”
骨瘦如柴的母亲们,脸黑得像鸟嘴一般,伸着脖子,用红肿的眼睛,望着那越盘越高的公路,跟着马车,匆忙移动着光脚,她们没有什么话可以回答孩子们。
越上越高了,森林稀疏起来,终于都留到下面了。荒凉的石岩、山峡、岩缝、崩塌的巨石,都向一块合拢了。每一种声音,马蹄声、轮转声,都引起各处的回音,怪声怪气地响起来,把人声都遮住了。常常得绕过倒下的马匹走。
突然间,一下子凉爽起来;风从山顶上吹来;一切都变灰了。一下子就变成夜间了。倾盆大雨从变黑了的天空里,倾泻下来。这不是雨,而是乱响的、叫人站不住脚的倾泻下来的水,是狂暴的、充满了旋卷的、黑暗的水旋风,从四面八方倾泻下来。水顺着褴褛的衣服,顺着粘在一起的头发流下来。都迷了方向,失了联络。人、车、马,都隔开了,仿佛这些中间隔着汹涌澎湃的空间一样,看不见,也不知道周围都是些什么,都是谁。
有人被冲走了……有人在喊着……可是这时候会有人声吗?……水在咆哮,是风吗?是漆黑的怒吼的天空吗?或者是山崩了吗?……也许全部辎重、马匹、车辆,都被冲走了……
“帮帮忙吧!”
“救——命——吧!……世界的末日!……”
他们自以为是在叫喊,而事实上不过是在发呛,轻轻地掀动着苍白的嘴唇罢了。
被洪水冲走的马,把车辆和孩子都拉着滚到沟里去,可是人在空空的地方走了好久,还以为是跟着马车走呢。
孩子们都钻到湿透了的枕头和衣服下边:
“妈妈!……妈妈!……爸爸!……”
他们以为自己是在拼命叫喊,可是事实上,这不过是汹涌的水在咆哮,看不见的石头从看不见的石岩上滚下来,风在用那活人似的声音吼着,仿佛一桶桶水不断倒下来一样。
疯人院里发号施令的人,突然把巨幕拉开了,于是在幕开前,在这无边黑夜里的一切,都在剧烈的难忍的蓝色的战栗中发抖。起伏的远山、齿状的悬岩、崩塌的岩边、马耳,都在刺目的蔚蓝里战栗。在这疯狂的战栗中,更可怕的是那些在战栗中凝然不动的一切:空中倾泻的水柱,泡沫飞溅的洪流,抬起要走的马腿,人刚迈了半步的腿,都凝然不动;说了半句话的乌黑的人嘴,湿枕头上的孩子们的苍白小手,都凝然不动。一切都在这死寂的惊厥的战栗中,凝然不动。
这种致命的蔚蓝的战栗,继续了一整夜;可是当这天幕,用同样突如其来的速度闭上时,才觉得不过只一刹那罢了。
庞大的夜,把一切都吞没了,马上山崩地裂,把这“妖精成亲” 32 盖了起来,从地心里发出霹雳似的一声,庞大的夜,容不下这巨大的声音,于是就崩成圆圆的碎块,再继续分裂着,向四面八方滚去,越响越高,充满了望不见的山峡、森林、山谷——人都震聋了,孩子们死死地躺着。
辎重、部队、大炮、弹药箱、难民、两轮车,在这倾泻的急流里,在青蓝色的闪电里,在这不断响着的雷声里,全都停止了——再没力气了。一切都停止了,都听天由命地把一切交给狂风暴雨、闪电雷鸣去摆布吧。流水比马膝还深。这狂暴的夜,简直是无穷无尽、无边无际啊。
第二天早晨,又是晴朗的太阳;天空亮晶晶的好像洗过一样;蔚蓝的山,都显得轻飘飘的。只有人是乌黑、枯瘦、眼睛凹陷;他们鼓着最后的力气,帮助马拉着。马头都瘦成干骨头了,肋骨历历可数地突起着,毛被冲洗得一干二净。
向郭如鹤报告道:
“郭如鹤同志,三辆大马车连人带马完全冲到沟里了。山上滚下来的石头,把一辆两轮车砸碎了。两个人被闪电打死了。第三连两个人失踪了。死了几十匹马,公路上倒的都是。”
郭如鹤望着冲洗得一干二净的公路,望着那严峻的重重叠叠的石岩,说:
“不宿营,继续前进,兼程并进!”
“马受不住了,郭如鹤同志。草料连一点儿也没有。在森林里走的时候——还可以喂树叶,可是现在全是光石头。”
郭如鹤沉默了一下。
“继续前进!要是咱们一停止——所有的马匹都会丢掉呢。写命令吧。”
多么好,多么清新的山间空气啊,他们能够呼吸一下多好呢。千千万万的人群,却顾不得去呼吸空气;都不作声地望着自己脚下,跟着马车,跟着大炮,在路边走着。骑兵下了马,拉着背后的马缰绳走着。
周围尽是重重叠叠的荒凉不毛的石岩。窄窄的山缝,显得黑漆漆的。无底的深谷在期待着死亡的人。雾在荒凉的山峡里浮动。
乌黑的石岩、山缝、山峡,都充满了不断响着的马车声、轮转声、马蹄声、轰隆声、铁的叮当声。从各处传来的千万次回声,汇成连绵不断的怪声怪气的怒吼。都默默走着,可是,如果谁要拼命大叫一声,人声反正是无影无踪地沉没到连绵数十俄里的喧嚣的行动里。
孩子们不哭,也不要面包了,只有苍白的小脑袋,在枕头中间摇晃着。母亲们不去哄孩子,不去照料孩子,也不喂孩子吃奶了,只疯狂地望着蜿蜒的、无穷尽地伸入云端的公路,公路上是汹涌的人流。她们跟着马车走着;她们的眼睛都是干巴巴的。
马一停的时候,那不能抑制的非常的恐怖,便燃烧起来。大家都像野兽一般疯狂地抓住车轮,用肩顶着,怒气冲冲地用鞭子抽着马,用非人的声音喊着,可是他们这一切紧张、挣扎,都安然而从容地被那千万次发着回声的、千万次翻来覆去的、永无休止的轮转声吞没了。
马走了一两步,站不住了,倒下去,把车杆也压断了,已经抬不起来了;马伸直腿,露出牙来,这活生生的一天,在紫色的眼里消失了。
都把孩子们抱下车。大一点的,母亲疯狂地打着叫他们赶路,小的抱到手中,或背在背上。可是如果孩子多的话……如果多的话——就把最小的一个或两个留在扔掉的马车上走了,两只干巴巴的眼睛,连回头看一眼都不看就走了。后边的人,也连看都不看,慢慢走着,前进的马车,绕过甩掉的马车,活马绕过死马,活孩子绕过留下的活孩子走着。无数的马车的吱吱声,千万遍地发着喧闹的回响,若无其事地吞没了这惨景。
抱着孩子,走了好多俄里路的母亲,蹒跚起来,两腿发软了。公路、马车、石岩都在浮动着。
“不……我不走了。”
就在路边的碎石堆上坐下来,望着、摇着自己的孩子,无穷无尽的马车,从她跟前过去。
孩子发干的、发黑的小嘴张着,淡青色的眼睛,死死地望着。
她绝望地说:
“没有奶了,我的心肝,我的亲人,我的小花朵……”
她疯狂地亲着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命根子,自己最后的欢欣。可是眼睛却干巴巴的。
发黑的小嘴,一下也不动;乳色薄膜的眼睛,一下不动地望着。她把这可爱的,无可奈何地冷下去的小嘴,紧贴在胸口上。
“我的孩子,我的亲爱的,你再不受罪了,再不受着罪等死了。”
手里抱着渐渐冷了的小小的身体。
挖开碎石堆,把自己的小宝贝放到坑里,把贴身戴的十字架,连那用汗浸透了的细绳,从脖子上卸下来,从沉甸甸的冰冷的小脑袋上套到脖子上,埋起来,祈祷着、无休止地祈祷着。
人群连看都不看就从旁边走着、走着。马车在川流不息地行动着,千万人的声音,反映着千万种饥荒的吱吱声,在这饥荒的石岩中间,轰轰响着。
骑兵下了马,在很远的前边,在先头部队里,拉着马缰绳走着。用力拉着在背后勉强走动的马,马耳朵都好像狗耳朵一样垂下来。
热起来了。大群苍蝇,在雷雨交加时,一个也不见了——都静悄悄地贴到车杆下面——现在却黑云一般飞舞起来。
“喂,小伙子们!为什么你们都像偷吃了肉的猫一样,耷拉着尾巴呢?唱一曲吧!……”
没一个人搭腔。都仍旧牵着马,疲惫地慢慢走着。
“唉哈,你妈妈的!把留声机上起来,让它来一曲也好……”
自己伸手到装唱片的袋子里,随手掏出一张来,按字母辨认着:
“布……布布……布……衣……布衣……木木,比木,布布……奥——比木——勃木……这是什么怪玩意?……可可……尔尔尔……可尔……奥……恩……可乐翁……原是唱哈哈大笑的小丑啊……好极了!唔,唱一回吧。”
他把绑在马鞍上的留声机上紧,放上片子,放起来。
突然间,他脸上现出了由衷的惊愕,后来眼睛都皱成了一条缝,嘴都咧到耳朵上了,牙齿闪着光,发出一阵诱惑人的传染性的大笑。惊愕的大笑,代替了留声机喇叭筒里的歌声,轰轰响起来:两个人哈哈大笑起来,有时这个人笑,有时那个人笑,有时两个人对笑。用出人意料的非常尖细的声音大笑着——好像胳肢小孩子似的笑着,有时使着牛劲笑着——周围人都哈哈大笑起来;都大笑着,喘着气,挥着手;好像得神经病打滚的女人一样大笑着;疯狂得把肚子都要笑破了;笑得好像止都止不住了。
周围走着的骑兵们,望着奇怪的、像发疯一样用各种调子哈哈大笑的喇叭筒,也都微笑起来。笑声在行列里传开了;后来他们忍不住了,自己也仿着喇叭里大笑的声调笑起来,笑声越来越大,在行列里流传着,越传越远了。
笑声传到慢慢走的步兵跟前,那里也笑起来。他们自己也不知道笑什么——这儿听不见留声机;这是被前边的哈哈大笑声引起来的。连这大笑声也制止不住地滚到后边去了。
“为什么他们都哈哈大笑呢?中邪了吗?……”于是自己也都摇着头,挥着手,哈哈大笑起来。
“他的爹老子的尾巴插到鼻孔里了……”
全体步兵边走边哈哈大笑,辎重队哈哈大笑,难民哈哈大笑,母亲们含着眼泪,疯狂地恐怖地哈哈大笑着。在那荒凉的石岩中间,穿过那不停的饥荒的车轮的吱吱声,连绵十五俄里长的人群,都哈哈大笑着。
这哈哈大笑声传到郭如鹤跟前时,他脸色苍白了,发黄了,黄得像短皮衣的熟皮子一般,这是他在行军期间第一次脸色苍白了。
“怎么一回事?”
副官忍着引起自己发笑的笑声说:
“谁知道他们是怎么一回事!大概是发疯了。我现在去了解一下。”
郭如鹤从他手里把马鞭和缰绳夺过来,拙笨地跨上马,拼命抽着马肚子。瘦马垂着耳朵,慢慢走着,可是鞭子把马皮都抽破了。马勉强跑着,周围滚着哈哈大笑声。
郭如鹤觉得自己的双颊都在跳动,他咬着牙。最后,他到了哈哈大笑着的先头部队跟前。狠狠地骂了一顿,用鞭子抽着留声机。
“都别作声!”
抽坏了的留声机片,吱咛一声不响了。这沉寂消灭着笑声,传到行列里。于是那疯狂的、无边无际的、反映着千万种的吱吱声、噼啪声、轰轰隆隆的回声,都又响起来。荒凉的山峡的乌黑的齿状石岩,都从旁边向后退去了。
一个人说道:
“山口啊!”
公路打了一个弯,就盘着绕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