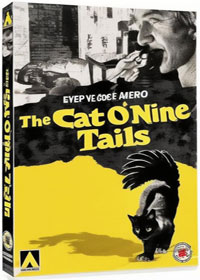1
艾萨克·麦卡斯林,人称“艾克大叔”,早过七十都快奔八十了,他也就不再实说自己的年纪了,如今是个鳏夫,半个县的人都叫他大叔,但他连个儿子都没有[1]
这里要说的并非他亲身经历甚至亲眼目睹的故事,经历与目睹的是年纪比他大的表亲麦卡斯林·爱德蒙兹,此人乃是艾萨克姑妈的孙子,说起来是家族中女儿一支的后裔,不过却是产业的继承人,到一定时候又会是赠予人,这份产业原先有人认为而现在仍然有人觉得该是艾萨克的,因为当初从印第安事务衙门那里得到土地所有权状的是姓他那个姓的人,而住在这儿的他父亲手下的奴隶的有些后裔直到如今仍然姓他的这个姓。可是艾萨克本人却不作此想:——二十年来他一直是个鳏夫,他一生中所拥有的东西里,无法一下子塞进衣袋并抱在手里拿走的就是那张窄窄的铁床和那条沾有锈迹的薄褥子,那是他进森林野营时用的,他去那里打鹿、猎熊、钓鱼,有时也不为什么,仅仅是因为他喜欢森林;他没有任何财产,也从来不想拥有,因为土地并不属于个人而是属于所有的人的,就跟阳光、空气和气候一样;他仍然住在杰弗生镇一所质量低劣的木结构平房里,那是他和他女人结婚时老丈人送的,他女人临死时把房子传给了他,他装作接受了,默许了,为的是讨她喜欢,让她走的时候心里轻松些,不过尽管临终有遗言关照,这房子并非他的由法院判定有正式遗嘱规定而具有永久所有权的产业,正式说法是不是这样可不清楚,反正是这么回事,而他留着房子仅仅是为了让他小姨和那几个外甥有地方住,他老婆死后他们便跟他住在一起,也是为了自己可以住其中的一间,老婆在世时他就是这样住的,她那时也愿意他这样住,如今小姨和外甥们也这样,他们愿意他这样住,直到他去世,至于死后
这并非他亲身经历甚至亲自记得的,仅仅是从表外甥麦卡斯林处听来的,是耳闻而得的陈年旧事,他这外甥出生于一八五〇年,大他十六岁,由于艾萨克这棵独苗儿出生时父亲已年近七十,所以与其说麦卡斯林是他外甥还不如说是长兄,或者说简直就是他父亲而非外甥与哥哥,这故事发生在早年间,那时候
* * *
[1] 本节原文除第一个词(issac)系大写之外,每段首词均为小写,而每段结尾处均无句号。作者的用意想是表示出此节与以下各节时间上的差异。这一节可以看作是故事正文之前的“楔子”。
2
他[1]和布克大叔发现托梅的图尔又逃走了,便跑回到大房子里去,这时候,他们听见布蒂大叔在厨房里诅咒和吼叫,接着狐狸和那些狗冲出厨房,穿过门厅进入狗房,他们还听到它们急急穿过狗房进入他和布克大叔的房间接着看见它们重新穿过门厅进入布蒂大叔的房间,然后听见它们急急穿过布蒂大叔的房间重新进入厨房,到这时听起来像是厨房的烟囱整个儿坍塌了,而布蒂大叔大叫得直像条汽艇在拉汽笛,这时狐狸、狗群外加五六根劈柴一起从厨房里冲出来把布蒂大叔裹挟在当中而他手里也拿着根劈柴瞅见什么就揍什么。真是好一场精彩的赛跑呀。
当他和布克大叔跑进他们的房间去取布克大叔的领带时,那只狐狸已经蹿到壁炉架上的钟后面去了。布克大叔从抽屉里取出领带,把几只狗踢开,揪住狐狸脖颈上的皮,把它拎下来,塞回床底下的柳条筐里,接着他们走进厨房,布蒂大叔正在那里把早饭从炉灰里捡起来,用他的围裙擦干净。“你们这究竟算什么意思,”他说,“把这天杀的狐狸放出来让一群狗满屋子的追撵?”
“别提那骚狐狸了,”布克大叔说,“托梅的图尔又跑了。快让我和卡斯胡乱吃点早饭。没准我们能赶在他到达那边之前把他逮住。”
这是因为他们非常清楚托梅的图尔是往哪儿跑的,但凡有机会可以开溜,一年总有两回吧,他总是朝休伯特·布钱普先生的庄园跑去的,就在县界的另一边,休伯特先生(跟布克大叔和布蒂大叔一样,他也是个老光棍)的妹妹索凤西芭小姐至今还想让大家称那地方为“沃维克”,这是英国一个府邸的名称,她说休伯特没准是真传的伯爵,只不过他从来没有那份傲气,更没有足够的精力,去争取恢复他的正当权利。托梅的图尔是去那儿跟休伯特先生的女奴谭尼厮混的,他总是在那儿泡着直到有人前去把他抓回来。他们无法从休伯特先生手里买下谭尼,用这个办法来稳住托梅的图尔,因为布克大叔说他和布蒂大叔手底下黑鬼已经太多,弄得都没法在自己地里自由走动了,他们又不能把托梅的图尔卖给休伯特先生,因为休伯特先生说他不但不想买托梅的图尔,也不想让自己的家里有这个天杀的白皮肤的(他身上有一半麦卡斯林家血液[2])小伙子,白送不要,即使布克大叔和布蒂大叔肯倒贴房饭钱也不要。若是没人立即去把托梅的图尔领回来,休伯特先生就会自己把他押来,还和索凤西芭小姐一起来,他们会待上一个星期或甚至更久,索凤西芭小姐住在布蒂大叔的房间里,而布蒂大叔就得干脆搬出房子,睡到小木屋区去,那是麦卡斯林的外曾祖父在世时黑奴们住的地方,外曾祖父死后,布克大叔和布蒂大叔就让所有的黑鬼都搬进外曾祖父来不及装修完毕的大房子里去,而黑鬼们住在那儿时,布蒂大叔连做饭也不上那儿去做,甚至连屋子也不再进去,只除了晚饭后在前廊上坐坐,在黑暗里坐在休伯特先生与布克大叔之间,过了一会儿,连休伯特先生也敛住了话头,不再说等索凤西芭小姐出嫁时他还要往给她的陪嫁上增添多少口黑奴和多少英亩土地,而是就去睡觉了。去年夏季有一天半夜里,布蒂大叔偶然醒来,恰巧听见休伯特先生驾车离开庄园的声音,等他叫醒大家,大家让索凤西芭小姐起床、穿戴好,再把车套好出发,赶上休伯特先生,天都快亮了[3]。因此,总是他卡斯和布克大叔出发去逮托梅的图尔的,因为布蒂大叔是从来不出门的,他不愿进城,就连到休伯特先生那里把托梅的图尔领回来也不愿去,虽然大伙儿知道布蒂大叔冒起风险来要比布克大叔胆大十倍。
他们匆匆忙忙把早饭吃完。布克大叔趁大伙儿朝空地跑去抓马儿时赶紧把领带打上。抓托梅的图尔是他唯一需要打领带的时候,而他从去年夏天那个晚上之后就再未把它从抽屉里取出来过,当时布蒂大叔在黑暗里把他弄醒,说:“起来,得赶快。”布蒂大叔则是连一根领带都没有的;布克大叔说布蒂大叔根本不愿费这份心,即使在他们这样的地区,感谢上帝这儿女士是如此稀少,一个男人可以骑马沿着一根直线走上好几天,也无需因见到一位而躲躲闪闪。他的奶奶(亦即布克大叔和布蒂大叔的妹妹;他自幼失母,是姥姥把他一手领大的。他的教名,麦卡斯林,也由此得来,而他的全名是卡洛瑟斯·麦卡斯林·爱德蒙兹)说布克大叔和布蒂大叔两人合用一根领带,无非是堵别人的口的一种办法,不让他们说两人像双胞胎,因为即使年届六十,他们仍然一听人说分不出他俩谁是谁就要跟人打架;这时麦卡斯林的父亲就说了,任何人只要跟布蒂大叔打过一次扑克,就再也不会把他当作布克大叔或是任何人了。
乔纳斯[4]已经给两匹马备好鞍,等在那里了。布克大叔登上马背的动作一点儿也不像个六十岁的人,他瘦削灵活得像一只猫,头颅圆圆的,一头白发留得很短,一双灰眼睛又小又冷酷,下巴上蒙着一层白胡楂,他一只脚刚插进马镫,那匹马就挪动步子了,等来到开着的院门口就已经在奔跑了,到这时,布克大叔才往马鞍上坐了下去。爱德蒙兹不等乔纳斯托他上去,便胡乱爬到那匹矮小些的马的背上,用脚跟夹了夹,让小马跑起它那僵僵的、两下两下连得挺紧的小步,出了院门去追赶布克大叔,这时布蒂大叔(麦卡斯林甚至都没注意到他在场)从院门里跨出来一把抓住马嚼。“看着他点儿,”布蒂大叔说,“看着梯奥菲留斯。一旦有什么不对头,赶紧骑马回来叫我。听见了吗?”
“听见了,大叔,”麦卡斯林说,“快让我走吧。我连布克大叔都要撵不上,更别说托梅的图尔——”
布克大叔骑的是“黑约翰”,因为只消他们能在离休伯特先生家院门至少一英里的地方看见托梅的图尔,“黑约翰”就能在两分钟以内撵上他。因此当他们来到离休伯特先生家大约三英里的那片长洼地时,瞧,托梅的图尔果然正在前面大约一英里外端坐在那匹叫“杰克”的骡子背上往前赶路呢。布克大叔伸出胳膊往后一挥,勒紧缰绳,蹲伏在他那匹大马的背上,圆圆的小脑袋和长有瘤子的脖子像乌龟那样伸得长长的。“盯住[5]!”他悄没声地说,“你躲好,别让他见到你惊跑了。我穿过林子绕到他前面去,咱们要在小河渡口把他两头堵住。”
他等着,直到布克大叔消失在林子里。然后他继续往前走。可是托梅的图尔看到他了。他逼近得太早了;也许是因为生怕赶不上看见图尔被撵上树[6]。那真是他有生以来所见过的最精彩的一次赛跑。他从未见过老杰克跑得这么快,而托梅的图尔平时走路总不慌不忙的,即使骑在骡背上也这样,谁也没料到他也能快跑。布克大叔在林子里呼啸了一声,对准猎物冲去,紧接着只见黑约翰从树丛里蹿出来,急急奔着,伸直身子,平平的,像只鹰隼,这时布克大叔简直就趴在它耳朵后面,一边在大声吼叫,看上去活像一只大黑鹰[7]驮着只麻雀,他们穿过田野,跳过沟渠,又穿过另一片田野,这时这孩子也动起来;还不等他明白过来,那匹母马已在全速飞奔,他自己也吼叫起来。照说作为黑人,托梅的图尔一见他们本该从牲口背上跳下,用自己的双脚跑的。可是他没这样做;兴许是托梅的图尔从布克大叔处溜走已有点历史,所以已习惯于像白人那样逃跑了。仿佛是人和骡把托梅的图尔平时走路的速度和老杰克生平发挥得最好的速度加到了一起,而这速度恰好足以使他赶在布克大叔之前到达渡口。等孩子和小马赶到时,黑约翰已经喘得不行,浑身冒汗,布克大叔下了马,牵着它遛圈儿,好让它缓过劲儿来,这时他们已能听到一英里外休伯特先生家招呼进午餐的号角声了。
不过,眼下托梅的图尔好像也不在休伯特先生的庄园里。那黑孩子仍然坐在门柱上,在吹号——院门早就没有了,光剩下两根门柱,一个个头跟他差不多的黑孩子坐在一根门柱上,正在吹一把猎狐小号;这就是索凤西芭小姐仍然在提醒人们其名称为沃维克的那个庄园,虽则人们早已清楚她要这样称呼用意何在,到后来一方面人们不愿意叫它沃维克而她呢甚至都不想知道他们在讲的是什么,于是听上去就像是她和休伯特先生拥有的是两个各不相干的庄园,却占据着同一块地方,仿佛是一个叠在另一个之上。休伯特先生正坐在“泉房”里,脱了靴子,双脚浸在泉水里,一边啜饮甜酒[8]。不过那边的人谁也没看见托梅的图尔;有一阵子好像休伯特先生甚至连布克大叔所说的那人是谁都对不上号。“哦,那个黑鬼,”他终于明白过来了,“咱们吃过午饭去找他就是了。”
不过看上去他们也还不打算吃饭呢。休伯特先生和布克大叔干了一杯甜酒,这时休伯特先生总算派人去关照门柱上的那孩子可以不必吹了,接着他和布克大叔又干了一杯,而布克大叔仍在不断地说,“我只不过是想找回我的黑小子。然后我们就得动身回家。”
“吃了午饭再说吧,”休伯特先生说,“要是咱们没能在厨房左近把他轰出来,咱们就放狗出去搜他。只要那臭挨刀的沃克种狗[9]嗅得出来,就不愁逮不住他。”
可是终于有一只手从楼上百叶窗破洞里伸出来,开始挥动一块手帕或别的什么白布。于是他们穿过后廊,走进宅子,休伯特先生跟往常一样,再次警告他们要留神他还顾不上修的一处朽坏的地板。这以后他们站在门厅里,过不多久传来一阵环佩丁当与衣裙窸窣的声音,他们开始闻到香气,原来是索凤西芭小姐下楼来了。她把头发拢在一顶带花边的软帽里;她穿的是星期天穿的出客服装,一根珠链和一条红缎带系在脖子上,有个黑小妞给她拿着扇子,孩子静静地站在布克大叔身后一点儿的地方,注视着她的嘴唇,一直盯到双唇张开,他看见了那颗有黄斑的牙齿。他以前从未见到过有谁牙齿带黄斑,他还记得有一回他姥姥和他爸爸谈到布蒂大叔和布克大叔,他姥姥说索凤西芭小姐有一阵子也还算好看。也许她好看过。他可说不准。他才只九岁啊。
“唷,是梯奥菲留斯先生呀,”她说。“还有小麦卡斯林,”她说。她从不把眼光投向他,这时也不是在对他说话,这他很清楚,虽然他做好了准备,也平衡好身子,等布克大叔脚往后退时也把他的脚向后退。[10]“欢迎光临沃维克呀。”
他和布克大叔把脚退了退。“我无非是来把我的黑小子领回去,”布克大叔说,“完了我们就得动身回家。”
接下去索凤西芭小姐讲了一通一只大黄蜂的事,不过他记不清是怎么讲的了。话说得太快,也说得太多,耳环与珠链的碰击声犹如小体型的骡子一路小跑时它那小挽链发出的音响,而香气也更咄咄逼人了,好像耳环与珠链每一晃动都能把香水喷雾似的喷向别人似的,他还盯视着那颗变色的牙齿在她的唇间轻叩并闪光;反正是在说布克大叔像只从一朵又一朵花里吮吸蜜汁的蜜蜂,从不在一处久留,而积贮的蜜都虚掷在布蒂大叔的荒凉的空气里了[11],她把布蒂大叔叫作阿摩蒂乌斯先生,就像把布克大叔叫作梯奥菲留斯先生一样,要不,说不定这蜜汁是留待一位女王莅临时享用的吧,那么这位幸运的女王又是谁,将于何时莅临呢?“什么,小姐?”布克大叔说。这时候休伯特先生接茬说了:
“哈。一只雄蜂[12]啊。我看等他把双手揪住那黑小子的时候,那黑小子会觉得布克是只雄赳赳的大黄蜂[13]哩。不过我想布克眼下最需要的还是尝点肉汁,吃点饼干和喝上一杯咖啡。我自己也饿了呢。”
他们走进餐厅吃起来,这时索凤西芭小姐说真不像话,只隔开半天骑马路程的邻居如今也不常来往,布克大叔就是这样,于是布克大叔说是的,小姐,接着索凤西芭小姐说布克大叔打从生下来躺在摇篮那会儿起就是个铁了心的浪荡单身汉,这一回布克大叔竟停止了咀嚼,把眼睛抬起来说,是的,小姐,他的确是这样,而且天生如此,现在太晚了,再改也难了,不过至少他可以感谢上帝没有哪位女士必须受和他与布蒂大叔一起生活的罪,这时索凤西芭小姐又说了,呀,也许布克大叔仅仅是至今还未遇到这样一位女士吧,她会不但愿意接受布克大叔愿意称之为受罪的那种生活,而且还会使布克大叔觉得连自己的自由也只不过是值得为之付出的一个很小的代价呢,这时布克大叔说,“是啊,小姐。还没有遇到。”
接着他、休伯特先生和布克大叔走出屋子来到前廊上坐下。休伯特先生甚至还没来得及再把鞋子脱掉,也没来得及请布克大叔把他的也脱了,索凤西芭小姐就从门里走了出来,托着一只托盘,上面搁着又是一杯甜酒。“得了,西贝,”休伯特先生说,“他才吃过饭。他现在不想喝。”可是索凤西芭小姐像是根本没听见他的话。她站在那里,那颗黄斑牙现在没有闪光,而是固定着,因为她这会儿没开口说话,只是把甜酒递给布克大叔,过了片刻才说她爸爸以前总是说再没有一位密西比[14]女士的纤手更能使一杯密西比甜酒喝起来更加怡人的了,布克大叔想不想看看她以前是怎样给爸爸添点甜味的呢?她举起酒杯抿了一小口,然后端还给布克大叔,这一回布克大叔接下了。他再次把一只脚往后退了退,喝下了那杯甜酒,说若是休伯特先生打算躺下休息的话,他也可以睡一会儿,因为从各种情况看来,托梅的图尔是决心让他们有一番漫长、艰苦的追逐的,除非休伯特先生的那些狗表现特别出色,与往常大不一样。
休伯特先生和布克大叔进到宅子里去了。小麦卡斯林过了不多会儿也站起来,绕到后院,等他们起床。他一抬头就看见托梅的图尔的脑袋在巷子围栏的上方移动。可是等他穿过院子去拦截时,托梅的图尔连跑都没跑。他蹲在一丛灌木后面,观察着宅子,眼光从灌木丛边上朝后门与楼上的窗子看去,他发出声音,不能确切地算是耳语,却也不是大声嚷嚷:“他们这会儿在干啥?”
“他们这会儿在打盹儿,”麦卡斯林说,“不过你别太高兴了;他们起床后要放狗来逮你呢。”
“哈,”托梅的图尔说,“你也别太高兴了。我现在有保护了。我只消做到在得到那句话之前别让老布克逮住我。”
“什么话?”麦卡斯林说,“谁发的话?是休伯特先生决心把你从布克大叔手里买下吗?”
“嗐,”托梅的图尔又说了,“我受到的保护可比休伯特先生自己得到的还多。”他站起身来,“我要跟你说一句话,你千万得记住:每逢你想做成一件事,管他是锄庄稼还是娶媳妇儿,让老娘们儿搀和进来准保没错。完了你坐下来等着就成,别的啥也不用干。你记住我这话好了。”
说完托梅的图尔就走了。过了一会儿,麦卡斯林又回到宅子跟前来。现在毫无动静,除了有鼾声从布克大叔和休伯特先生睡的房间里传出来,还有稍轻的鼾声从楼上房间里传出来。麦卡斯林走进泉房,学休伯特先生的样,坐下来把双脚浸在水里,因为这样可以快点凉快下来,追逐马上要开始了。果不其然,没多久休伯特先生和布克大叔就走出屋子来到后廊上,索凤西芭小姐紧跟在后面,手里端着那只甜酒托盘,只是这回布克大叔不等索凤西芭来得及添加甜味就赶紧把他那杯喝了,索凤西芭小姐关照他们要早点回来,因为对于沃维克,布克大叔所了解的仅仅是猎狗和黑奴,今天她既然把他请来了,她非得让他参观她的花园不可,那是休伯特先生和任谁都没有插过手的。“是的,小姐,”布克大叔说,“我只不过是要抓回我的黑小子。然后我们就得赶回去。”
四五个黑小子牵来那三匹马。猎狗仍然一对对的拴着等候在巷子里,但他们已经听到那喧闹声了,就跨上坐骑,顺着巷子朝黑人住处驰去,这时布克大叔竟已赶到狗群的前面去了。因此麦卡斯林根本不知道他们是在何时从何处轰出托梅的图尔来的,也不知道他是从哪所小木屋里冲出来的还是从别处跑出来的。布克大叔骑着黑约翰冲在最前头,他们都还没顾得上放狗出去便听见布克大叔吼道,“盯住[15]!我的天,他从躲藏处跑出来啦!”这时黑约翰的蹄子在地上叩击了四下,就跟开了四枪一样脆响,这是它在聚拢四只脚准备飞奔呢,紧接着它和布克大叔便翻过山头不见了,就像是越过了这世界的地角天边似的。休伯特先生也吼起来了:“盯住!放狗呀!”于是猎狗纷纷朝山脊拥去,刚好赶上看见托梅的图尔冲过平地,即将进入树林,于是狗群又飞也似的冲下山头,在平地上疾奔。它们仅仅伸出舌头吠叫了一次,等簇拥到托梅的图尔身边时,它们看来像是要跳上去舔他脸似的,这时连托梅的图尔也放慢了步子,他和那群狗是走着一起进入树林的,那模样就像是猎完兔子一块儿回家。等大伙儿进入树林追上布克大叔,不论是托梅的图尔还是那群狗连影儿都不见了,只看到老杰克,那是大约半个小时之后了,拴在一丛灌木上,身上系着托梅的图尔的外衣,当作鞍子,地上摊着差不多半蒲式耳休伯特先生的燕麦,老杰克早就吃饱,连拿鼻子去吸起再喷回去的兴趣都没了。这算是哪门子追捕呀。
“然而咱们能在晚上逮住他,”休伯特先生说,“咱们给他设下圈套。咱们在半夜左右让黑小子们和猎狗在谭尼屋子四周布下包围圈,准保手到擒来。”
“今晚,不行,”布克大叔说,“天黑时,我、卡斯和那黑小子三个该在回家半路上才行。难道你手下的黑小子里没有那种能追踪那些猎犬的小杂种狗吗?”
“那还不得傻瓜似的在树林里兜上大半夜?”休伯特先生说,“我可以跟你打赌,赌五百元,你啥也不用干,只消天黑后走到谭尼小屋门口,喊上一声,就能把他逮住了。”
“五百元?”布克大叔说,“打就打!因为不管是我还是他天黑时谁也不会上谭尼家附近去的。五百块钱!”他和休伯特先生相互轻蔑地瞪视对方。
“打定了!”休伯特先生说。
于是他们等着,让休伯特先生派一个黑小子骑上老杰克回宅子去,大约半小时后那黑小子回来了,带来一只一丁点儿大的短尾巴小黑狗以及又一瓶威士忌。接着黑小子驱动坐骑来到布克大叔跟前,递给他一样包在纸里的东西。“那是什么?”布克大叔说。
“是给您的,”那黑鬼说。布克大叔便把它接过来打开。原来是方才系在索凤西芭小姐脖子上的那根红缎带,布克大叔骑在黑约翰背上,捏着缎带,仿佛那是条水蝮蛇,只不过他不打算让任何人看出他害怕这东西,他对着黑小子急捷地眨动眼睛。接着就停止了眨眼。
“什么意思?”他说。
“她就让带来给您,”那黑鬼说,“她说让您‘成功’。”
“她说什么来着?”布克大叔说。
“我也不懂,老爷,”黑小子说,“她光说‘成功’。”
“哦,”布克大叔说。后来小狗找到了那群猎狗。他们在距离相当远处就听到了它们的声音。这时太阳眼看就要下山,它们不是在跟踪嗅迹,而是在发出狗群想从什么地方出来的那种喧闹声。他们也发现那是什么地方了。那是地里的一间十平方英尺大存放棉花的小屋子,离休伯特先生家大约两英里,所有十一条狗全给关在里面,门用一块厚木板揳得死死的。那黑小子把门弄开,他们眼看狗群像开锅的粥似的扑出来,休伯特先生稳坐在马背上,瞧着布克大叔的脖颈。
“唷,唷,”休伯特先生说,“反正这样很有意思。现在你又可以使唤它们了。看来它们跟你的黑小子没什么冤仇,而他跟狗群也处得不错。”
“冤仇是不够深,”布克大叔说,“我是说双方都是如此。我还是得依靠那只小杂种狗。”
“那也好。”休伯特先生说。接着说,“嗨,菲留斯[16],走吧。咱们吃晚饭去吧。我告诉你,你想逮住那黑小子唯一要做的就是——”
“五百块钱,”布克大叔说。
“什么?”休伯特先生说。他和布克大叔相互盯看着。他们现在已不是在怒目而视了。他们也不是在互相打趣。他们是在初起的薄暮里坐在马背上,相互对看,仅仅是眨了几下眼。“什么五百块钱?”休伯特先生说,“是赌你不可能今天半夜在谭尼的小屋里逮住那黑小子吗?”
“是赌今天半夜我跟那黑小子除了我自己那所之外都不会走近任何别的房子。”
“五百块钱,”休伯特先生说,“就这么定了。”
“定了。”布克大叔说。
“定了。”休伯特先生说。
“定了。”布克大叔说。
于是休伯特先生带了那群猎狗和几个黑小子回去了。而他麦卡斯林和布克大叔还有那个带来小杂种狗的黑小子继续前进,那黑小子一手牵着老杰克,另一只手捏着系小狗的皮带(那是一段磨旧的犁绳)。这时布克大叔让小狗闻闻托梅的图尔的外套;那只小狗好像这会儿才第一次明白他们要找的是什么,他们本该把套在它脖子上的皮条解开,骑马追随在它的后面,可是不早不晚,宅子那边的黑孩子吹响了招呼用晚餐的猎狐号角,他们便不敢那样做了。
接下去天空全黑了。这以后——孩子不知道究竟过了多久,也不清楚他们在什么地方,离宅子有多远,只知道那是块良田,天黑了已有一阵子,而他们还在往前走,布克大叔时不时弯下身让那小狗再闻闻托梅的图尔的外套,而自己则端起威士忌瓶子再呷上一口——他们发现托梅的图尔又绕回来了,正在兜一个大圈子往大宅子走去。“我的天,咱们算是找到他了,”布克大叔说,“他想缩进洞去呢。咱们抄近道回宅子去,赶在他缩进窝之前截住他。”因此他们让那黑人放开小狗,让他骑上老杰克跟踪图尔,而孩子和布克大叔则策马朝休伯特先生家奔去,只在山冈上停留片刻,让马儿喘口气,同时谛听小狗在沟底叫唤的声音,托梅的图尔还在那儿兜圈子呢。
可是他们压根儿没逮住他。他们来到漆黑的黑人村;他们可以看见休伯特先生宅子里灯光仍然亮着,有人再次吹响了猎狐号角,那肯定不是什么小孩吹的,而他从未听到过有谁把猎狐号吹得这样气急败坏的,他和布克大叔便分开,守在谭尼小屋下的斜坡上。接着他们听到了那小狗叫起来了,不是在搜寻嗅迹,而是在狂吠,约摸在一英里以外,接着那黑人发出了高声吆喝的声音,他们便知道小狗又失去嗅迹了。那是在沟边出纰漏的。他们在堤岸上来回搜寻了一个多小时,仍未能把托梅的图尔乱七八糟的嗅迹理出个头绪来。最后连布克大叔也不抱希望了,他们开始朝大宅赶回去,那只小狗现在也上了坐骑,就趴在黑小子身前的骡背上。他们正来到通向黑人村的巷道上;他们顺着屋脊能看见休伯特先生的大宅如今已一片漆黑,这时,小狗突然叫了一声,从老杰克背上跃下,一落地就急急奔跑,每蹦一下就叫一声,布克大叔也下了马,而且不等孩子双脚完全退出铁镫就一把将他从小马背上拽下,两人也奔跑起来,一直跑过好几座黑黑的小屋,朝小狗蹿去的那座跑去。“咱们找到他了!”布克大叔说,“快绕到后面去。别喊;就给我抄起根棍子朝后门猛敲,声音要响。”
事后,布克大叔承认是他自己不好,他竟忘掉了即便是小小孩也该明白的事理:但凡惊动一个黑鬼时千万别站在他面前或是背后,而是要永远站在他的一边。布克大叔居然忘了这档子事。他对准前门而且就站在门口,还有那小狗梗在他前面,只要新吸进一口气就像叫救火和救命似的叫;他说他光知道小狗尖叫一声,转了个回旋,托梅的图尔便已在狗的身后了。布克大叔说他都没看见门是怎么开的;那只小狗仅仅尖叫了一声,便从他腿缝里钻过去,接着托梅的图尔飞跑着从他身上跨过。他甚至都没有颠跳一下;他撞倒了布克大叔,没有停止奔跑,便在布克大叔着地前扶住了他,他托住布克一只胳膊,把他拉起来,仍然没停下,把他往前拖了总有十英尺,一边嘴巴里说,“留神这儿哟,老布克。留神这儿哟,老布克。”然后才把他扔下,兀自往前跑。到这时,他们连小狗的叫唤也完全听不见了。
布克大叔倒没有受伤;就只是托梅的图尔把他四脚朝天撂倒在地时一下子气儿回不过来。不过他后面兜里揣着个威士忌酒瓶,他省下最后一口原本想在逮住托梅的图尔时喝的,所以他不愿动弹,非得先弄清楚那摊湿的仅仅是威士忌而不是血。因此布克大叔稍稍转向一侧,松开身子,让孩子跪在他背后把碎玻璃从他兜里掏出来。接着他们朝大宅子赶去。他们是步行去的。那黑小子牵着马赶了上来,不过谁也不提让布克大叔再坐上去。他们现在根本听不见小狗的声音了。“他跑得很快,不错,”布克大叔说,“可是就算是他,我也不信能赶上那杂种狗,我的天,今儿晚上真是够瞧的呀。”
“咱们明天准能逮住他。”孩子说。
“明天,去你的吧,”布克大叔说,“明天咱们已经回到家了。休伯特·布钱普或是那黑鬼,不管是谁吧,只要把脚踩进我的地,我就要让上头以非法侵入和流浪罪把他们逮捕。”
宅子里一片漆黑。他们能听见休伯特先生此时鼾声大作,就像是在一门心思对着房子练习竞走。可是他们听不见楼上有任何声响,即使进入了黑黢黢的门厅,来到了楼梯底下。“看来她的卧室是在后面,”布克大叔说,“在那儿,她不用起床也能对着楼下的厨房吆喝。再说,家里来客人时,未婚的女士一定会锁上房门的。”因此布克大叔就在楼梯最低一级处坐下来,孩子便跪下来帮布克大叔脱下马靴。接着他也脱了自己的,并把靴子贴墙根放好,他和布克大叔便登上楼梯,摸黑来到二楼的过厅。这里也是黑黢黢的,还是听不到什么声响,除了楼底下休伯特先生的鼾声,于是他们一路摸黑朝前楼走去,直到摸到一扇门。他们听不见门里有什么声音,布克大叔试着转了一下门把,门儿开了。“行了,”布克大叔悄没声地说,“轻点儿。”他们这时稍稍能看出一点儿了,也仅能看出床和蚊帐的轮廓。布克大叔卸下背带,解开裤子的纽扣,来到床边,小心翼翼地往床沿坐下去,想松快松快,孩子再次跪下,帮布克大叔把裤子拉下来,他正脱自己的裤子时,布克大叔撩起蚊帐,抬起双脚,就翻身上床。这时,索凤西芭小姐在床的另一边坐了起来,发出了第一下尖叫声。
* * *
[1] 这里的“他”已不是艾萨克,而是麦卡斯林·爱德蒙兹,下同。本故事发生在1859年,当时他9岁。下文常用“孩子”来指他。
[2] 因为图尔是托梅跟艾萨克的祖父卡洛瑟斯老爷养的私生子。
[3] 如作为陪伴者的休伯特不在,未婚的索凤西芭小姐的名誉将受到损害,布克便不得不与之结婚。因此,他们非得把想摆脱妹妹的休伯特追住不可。
[4] 应是麦卡斯林庄园里的一个黑种仆人。
[5] 打猎用语,原文为“stole away”,意思是催促猎狗紧跟住猎物的嗅迹。
[6] 这前后用的都是猎人追捕猎物的语言。“撵上树”即逼进死角之意。
[7] 据注家泰勒女士说,这种美国南方的沼泽鹰在冬季总是掠过野草飞捕猎物。故此福克纳以之比喻布克大叔胯下的那匹黑马。
[8] 用糖水、波旁威士忌和冰兑成的一种饮料。
[9] 一种猎狐犬,因约翰·沃克参与育种而得名。
[10] 这是当时美国南方绅士正式鞠躬的一种姿势:在把头低下去的同时右脚向后退十八英寸左右。
[11] 参见英国诗人托·格雷(1716—1771)的《墓园挽歌》中的诗句:“世界上多少花吐艳而无人知晓,/把芳香白白的散发给荒凉的空气。”
[12] 此处的“雄”,原文为“buck”,与“布克”谐音,休伯特是接住妹妹的话头在打趣。
[13] 英语俗语中有“疯得像只大黄蜂”(mad as a hornet)之说。休伯特是在继续逗弄布克。
[14] 密西西比的简称,这里有学小儿语故作娇态之意。
[15] 原文为“gone away”,意同前面的“stole away”,亦是招呼猎狗的惯用语。
[16] 布克大叔教名梯奥菲留斯的简称。
3
第二天午饭前那孩子回到家里时真是快筋疲力尽了。他累得不想吃饭,虽然布蒂大叔一直等着要大家先吃饭;他方才待在小马背上直想打盹,简直无法再走一英里了。事实上,他准是一边对布蒂大叔说话一边就已经睡着了,因为等他再醒过来早已是黄昏了,他正躺在颠簸不已的大车底的干草上,布蒂大叔则坐在自己头顶的赶车座上,那模样就跟他往常骑在马背上或是坐在厨房炉灶前一把摇椅里做饭时一模一样,他手里拿着鞭子,就跟平时拿把勺子或叉子搅动食物尝味道时一模一样。布蒂大叔用湿麻袋包住面包、熟肉和一瓶酸奶,准备让他醒过来时吃。在眼看黑下来的暮色里,他坐在大车里吃着。他们准是很快就动身的,因为他们已来到离休伯特先生家不到两英里处了。布蒂大叔等他吃完。然后说,“再跟我说一遍。”于是他又说了一遍:他和布克大叔如何终于找到了一间空房间,布克大叔就坐在床沿上说,“噢天哪,卡斯。噢天哪,卡斯,”这时他们听到休伯特先生上楼的声音,看见烛光从过道上照过来,接着休伯特先生走进房来,穿着睡衣,走过来把蜡烛放在桌子上,站在床前盯看着布克大叔。
“嗐,菲留斯,”他说,“她终于把你逮住了。”
“这是意外事件,”布克大叔说,“我向上帝起誓——”
“哈,”休伯特先生说,“不见得吧。这话你跟她说去。”
“我说了,”布克大叔说,“我已经跟她说了嘛。我向上帝起誓——”
“那当然,”休伯特先生说,“不过你听呀。”他们听了一分钟。那孩子倒是早就在听她的吼叫了。她不像刚开始时那么吵得吓人;不过声音一直是持续稳定的。“你要不要回进房间去再跟她说这是次偶然事件,你完全没有不好的用意,希望她能原谅并把一切都忘掉?那好吧。”
“什么好吧?”布克大叔说。
“回进去再跟她说呀。”休伯特先生说。布克大叔盯着休伯特先生看了足足有一分钟。他迅速地眨动眼睛。
“那么我回出来后怎么跟你说呢?”他说。
“跟我?”休伯特先生说,“我的看法是根本不是你所说的这么回事。你不也会这么认为的吗?”
布克大叔盯看着休伯特先生。他又迅速地眨动起眼睛来。接着他又停住了。“等一等,”他说,“你要讲道理嘛。就算是我真的闯进了一位女士的卧室,甚至是索凤西芭小姐的卧室;为了把问题说得更清楚些,就算是除了她世界上再没别的女人而我闯进她房间就是为了想跟她睡觉,难道我会带上个九岁的男孩吗?”
“我也正是要讲道理,”休伯特先生说,“你是自觉自愿进入大熊出没的地区的。好吧;你是个成年人,你明知道前面是大熊出没的地方,你还知道退路就跟你知道进去的路一样,而且进与退都是可以由你自己选择的。可是不。你一定要钻进熊洞去躺在熊的身边。至于你知道或是不知道熊在不在洞里那是无关紧要的。因此要说你能从熊洞里逃出来连爪痕都没留下一处,我信了才怪哩,那我不成了个十足的大傻瓜了。说到底,既然好不容易有了个机会,我自然也想过几天自由自在的太平日子。是的,老兄啊。她可逮着你了,菲留斯,这你也明白。你参加了一次艰苦的赛跑,你跑得挺快,可就是闯进了母鸡窝,这样的错误犯上一回也就满够了。”
“是啊。”布克大叔说。他深深吸了口气又把气儿慢慢地、轻轻地吐出来。不过你还是能听到出气声。“呣,”他说,“那我看我只好碰碰运气啰。”
“你本来就是在碰运气嘛,”休伯特先生说,“你回宅子里来就是来碰运气的。”这时他也停住了。接着他眨动眼睛,不过只眨了大约六下。完了他也停住话头,盯住布克大叔瞧了足足有一分多钟。“碰什么运气?”他说。
“那五百块钱呀。”布克大叔说。
“什么五百块钱?”休伯特先生说。他和布克大叔相互盯视着。现在是休伯特先生再次眨动眼睛然后再次停下来了。“我原以为你说过是在谭尼的小屋里找到他的。”
“正是这样,”布克大叔说,“你和我打的赌是我会在那儿抓住他。即使有十个我这样的人站在那扇门的前面,我们也是逮不住他的。”休伯特先生对着布克大叔眨眼,一下下很慢,也很稳定。
“这么说你还打算让我为那个愚蠢的赌负责。”他说。
“你当初也是在碰碰运气嘛。”布克大叔说。休伯特先生朝布克大叔眨眨眼睛。接着他停住了。然后他走过去从桌上拿起蜡烛,走了出去。两人坐在床沿上瞧着烛光顺着过道照过去,并听见休伯特先生下楼的脚步声。过了一会儿,他们又开始见到烛光,并听见休伯特先生重新上楼的脚步声。接着休伯特先生走进房间,来到桌子前,把蜡烛放下,并在边上放下一叠纸牌。
“玩一盘,”他说,“暗扑克[1]。你洗牌,我切,这孩子发牌。五百块钱对西贝。咱们也可一锤子把这黑小子的问题给解决了。要是你赢,你买下谭尼;我赢,我买下你那黑小伙儿。两人价钱都一样:三百块。”
“赢什么?”布克大叔说,“赢家买下黑奴?”
“是西贝,笨蛋!”休伯特先生说,“是西贝!咱们坐到半夜争吵还为别的什么?牌比输的一方把西贝拿去,还得把黑奴买下。”
“这样吧,”布克大叔说,“我就把那死丫头买下,这档蠢事别的全都一笔勾销。”
“哈,”休伯特先生又说,“这正是你平生一本正经干的第一等蠢事啊。不行。你说过你要碰运气,现在就让你来碰。它就在这里,就在这张桌子上,正等着你哪。”
于是布克大叔便把牌洗了,休伯特先生切了牌。接着孩子拿起那摞牌,依次发牌,直到布克大叔和休伯特先生都有了五张。接着布克大叔久久瞪视着自己手里的牌,然后说要两张,于是孩子给了他两张,休伯特先生却朝手里的牌倏地看了一眼,便说要一张,于是孩子给了他一张,这时休伯特先生把他的垫牌甩在布克大叔扔掉的两张牌上,把新拿的牌插到手里的一副牌中,把牌展开,又倏地看了一眼,便把牌合上,看着布克大叔,说:“怎么样?对你那三张有帮助吗?”
“没有。”布克大叔说。
“呣,对我可有。”休伯特先生说。他把牌往桌面上一甩,使牌面朝上一张张摊开在布克大叔的面前,那是三张老k和两张5[2],然后说,“老天,布克·麦卡斯林,你算是撞见丧门星了。”
“就这些吗?”布蒂大叔说。这时时间已晚,太阳快下山了;他们再赶十五分钟就能抵达休伯特先生家了。
“是的,您哪。”孩子说,接着又说了下面的情况:布克大叔如何在天刚亮时把他叫醒,接着他从一扇窗户里爬出去,找到那匹小马,就离开了那儿,而布克大叔还说要是在这期间他们把他逼得太紧,他也要顺着水落管爬下去,躲在树林里,直到布蒂大叔来到。
“哈,”布蒂大叔说,“托梅的图尔是在那儿吗?”
“是的,您哪,”孩子说,“我去牵小马的时候,他正等在马厩里呢。他说,‘他们还没弄妥吗?’”
“那你说什么了?”布蒂大叔说。
“我说,‘布克大叔像是已经给弄妥了。可是布蒂大叔还没来呢。’”
“哈。”布蒂大叔说。
这就是大致的情况。他们来到那所大宅。也许布克大叔正在观望着他们,不过如果是的话,他却根本没露面,没从树林里走出来。也没见到哪儿有索凤西芭小姐的影子,因此至少是布克大叔还没有完全屈服;至少他还未向她求婚。于是那孩子、布蒂大叔和休伯特先生一起用晚餐,接着他们从厨房走进房间,清了清桌子,仅仅在上面留下那盏灯和那副纸牌。这以后的情况就跟昨晚一模一样,不同的仅仅是布蒂大叔没系领带,休伯特先生穿的是正式的衣服而不是睡衣,桌子上放的是一盏有罩子的灯而不是一支蜡烛,休伯特先生坐在桌子的一头,手里拿着那摞牌,用大拇指翻动纸牌边缘,盯视着布蒂大叔。接着他把牌边拍拍齐,把这摞牌放在桌子中央的灯下,叠起胳膊支在桌子边缘上,身子稍稍前倾,盯视着布蒂大叔,而布蒂大叔坐在桌子的另一头,双手放在膝上,上上下下都是灰色的,就像块古老的灰色岩石或是长满灰色苔藓的树桩,纹丝不动,长着白发的头颅圆圆的,跟布克大叔的一样,只是他不像布克大叔那样爱眨眼,身躯也比布克大叔厚实些,好像是因为老坐着盯看在煮的饭菜,又好像他烹煮的食物使他比应分的厚重一点儿,而他做饭所用的原料,面粉之类啦,也使他全身都变得灰扑扑的很不惹眼。
“开始之前来点儿甜酒怎么样?”休伯特先生说。
“我是不喝酒的。”布蒂大叔说。
“好吧,”休伯特先生说,“我早知道菲留斯之所以显得有人情味,除了他的娘娘腔之外,还有别的原因。不过没关系。”他眼睛朝布蒂大叔眨了两回,“拿布克·麦卡斯林来赌我答应过的作索凤西芭结婚陪嫁的土地与黑奴。要是我赢了你,菲留斯把西贝娶了,没陪嫁。要是你赢了我,你把菲留斯带走。不过菲留斯买谭尼欠我的三百块钱还得给我。没错吧?”
“没错。”布蒂大叔说。
“来四明一暗的,”休伯特先生说,“就一盘。你洗牌,我切牌,这孩子发牌。”
“不行,”布蒂大叔说,“不要卡斯。他太小了。我不想让他搀和到任何赌博里来。”
“哈,”休伯特先生说,“不是说跟阿摩蒂乌斯·麦卡斯林玩牌不算是赌博吗。不过没关系。”他仍然在瞧着布蒂大叔;他说话时连头都没扭过去:“上后门口去喊一声。把第一个应声的活物带来,管他是牲口、骡子还是人,只要会发十张牌就行。”
于是那孩子走到后门口。可是他根本不用喊,因为托梅的图尔就蹲在门外墙根下呢,于是他们回进餐厅,休伯特先生仍然交叉双臂坐在桌子他那头,布蒂大叔双手放在膝上坐在另一头,那摞纸牌面朝下放在他们之间的灯下面。孩子和托梅的图尔进来时,那两个人连眼皮都没抬。“洗牌吧。”休伯特先生说。布蒂大叔洗了牌,把牌放回到灯下,两只手也放回到自己膝上,接着休伯特先生切了牌,又把胳膊交叉起来搁在桌沿上。“发牌吧。”他说。他或是布蒂大叔仍然是谁都不把眼皮抬起来。他们就那样坐着,这时托梅的图尔那双马鞍色的手伸到灯光下,拿起纸牌开始发牌,他给了休伯特先生一张面朝下的,给了布蒂大叔一张面朝下的,给了休伯特先生一张明的,那是张老k,还给了布蒂大叔一张明的,那是张6。
“布克·麦卡斯林赌西贝的嫁妆,”休伯特先生说,“发牌。”于是那只手发给休伯特先生一张牌,那是张小3,又给布蒂大叔一张牌,那是张小2。休伯特先生抬起眼来看看布蒂大叔。布蒂大叔用指关节在桌上敲了一下[3]。
“发牌。”休伯特先生说。于是那只手发给休伯特先生一张牌,那又是张小3,又给布蒂大叔一张牌,那是张4。休伯特先生瞧了瞧布蒂大叔的牌。然后他看看布蒂大叔,布蒂大叔又用指关节在桌子上敲了一下。
“发牌。”休伯特先生说,那只手发给他一张爱斯,发给布蒂大叔一张5,这时休伯特先生就那样静静地坐着。足足有一分钟,他不看任何东西,也一动不动;他光是坐在那里,盯看着布蒂大叔自洗牌以来头一回把一只手伸到桌面上,掀起他那张面朝下的牌的一只角,对它看了一眼,然后又把手放回到膝上。“你先加注吧。”休伯特先生说。
“我拿那两个黑奴跟你赌。”布蒂大叔说。他也一动不动。他坐在那儿,姿势就跟他坐在大车里、马背上或是待在那把摇椅上做菜时一模一样。
“赌什么呢?”休伯特先生说。
“赌梯奥菲留斯为买谭尼欠你的三百块钱,加上你和梯奥菲留斯说好要为托梅的图尔花的那三百块。”布蒂大叔说。
“哈。”休伯特先生说,不过这一回声音一点儿也不高,甚至也不是短促的。然后又说,“哈。哈。哈。”同样不是高声的。然后他说,“好。”接着又说,“好,好。”接着又说,“咱们先等一分钟。要是我赢,你把西贝带走,没有嫁妆也没有那两个黑奴,我就再不欠菲留斯任何东西。要是你赢——”
“——那么梯奥菲留斯便自由了。可你还欠他买托梅的图尔那三百块钱。”布蒂大叔说。
“那是倘若我决定‘跟’[4]你的话,”休伯特先生说,“如果我不跟呢,那就菲留斯什么都不欠我,我也不欠菲留斯什么,除非我收下那个黑小子,那是我多年来就跟你也跟他一直在解释我这里实在不需要的。我们就重新回到这件蠢事一开始的那个局面,除了那一点之外。因此结果造成的形势是:要就是我得白白送掉一个黑奴,要就是冒买进一个的风险,而这个你已承认在你家里是养不住的。”这时他停住了话头。约摸有一分钟,似乎他和布蒂大叔都睡着了。接着休伯特先生拿起他那张脸朝下的纸牌,把它翻过来。又是一张3,休伯特先生就坐在那儿,不朝任何地方看,他的手指在桌子上叩击出一个鼓点子,慢慢地,很稳定,也不太响。“呣,”他说,“你需要一张小3,但拢共只有四张,而我手里已经有了三张。你光是洗牌。接着我切了牌。倘若我跟你,我就非得买下那个黑鬼不可。是谁发这些牌的呢,阿摩蒂乌斯?”不过他并不等别人回答。他伸过手去把灯罩弄斜一些,光线顺着托梅的图尔的胳膊往上移动,这胳膊应该是黑色的,但是也不算太白,移动到他星期天穿的衬衫上,那应该是雪白的,但是现在也不太白了,每回他逃跑都穿这件衬衫,正如布克大叔每回去抓他都要系上领带一样,而光线最后落到他的脸上;休伯特先生就坐在那儿,捏住了灯罩,盯看着托梅的图尔。接着他把灯罩放回去,拿起他的牌,把它们翻成脸朝下,把牌往桌子中间一推。“我派司了,阿摩蒂乌斯。”[5]他说。
* * *
[1] 这种牌戏原文系“draw”,为“draw poker”的简称,玩法是每人发五张暗牌,下注后可要求换发手中不需要的牌,一般不超过三张。然后比大小。北京人俗称“拉耗子”。
[2] 这是所谓“满堂红”。
[3] 意思是催促发牌,好把牌戏进行下去。
[4] 扑克术语,意为对方下注后自己也下同样的注,然后双方摊牌以决胜负。
[5] 1957年,福克纳在一次回答提问者时说:“托梅的图尔希望得到自由,因此他把适当的牌发给适当的人,而休伯特先生是明白这一点的。”(《福克纳在大学里》,第7页)休伯特手里有三张“3”,布蒂那张暗牌倘若是“3”,那就是一副顺子,要比休伯特的牌大。因此,休伯特认输了。这样,布克就不必与索凤西芭结婚,而且还将谭尼赢去与图尔成亲。不过,从福克纳的《熊》等作品可以看出,索凤西芭还是与布克结了婚,而且生下艾克。关于这一点,克林思·布鲁克斯在他的《威廉·福克纳浅介》(耶鲁大学出版社,1983)里是这样说的:“我有一次问福克纳先生,布克大叔后来还是与索凤西芭小姐结了婚,还生下一个孩子,亦即艾萨克·麦卡斯林,这件事是如何发生的呢。布克大叔刚从索凤西芭小姐的掌心里被解救出来,在这样幸免于难之后布克大叔肯定是更加警惕与神经紧张的呀。福克纳解释说,他始终没顾得上写出布克大叔是怎样终于被俘获的。”(见该书第133页)
4
这孩子仍然太疲倦,直想睡,难以骑马,因此这回他、布蒂大叔还有谭尼三个全坐在大车里,让托梅的图尔骑在老杰克背上牵着小马。天亮刚过,他们回到家中,这一次布蒂大叔都没来得及动手做早饭,那只狐狸也没能从柳条筐里钻出来,因为那些狗就在这房间里。老摩西干脆钻进柳条筐要跟狐狸待在一起,因此它们都从后面那头钻了出去。那是说,狐狸钻出去了,因为布蒂大叔开门进去时,老摩西脖子上仍然套着大半只筐,还是布蒂大叔帮摩西把筐从它身上踢开的呢。索赛才迈开步子穿过前廊绕房子跑了一圈,他们就能听到狐狸顺着披屋柱子蹿上屋顶时那些爪子的搔刮声了——这场赛跑够精彩的,只是结束得太快,那棵树晃动得太厉害了。
“你这算是哪门子规矩,”布蒂大叔说,“把那骚东西跟这些狗全关在同一个房间里?”
“就别操心狐狸的事了,”布克大叔说,“快去做早饭吧。我都觉得离开家足足有一个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