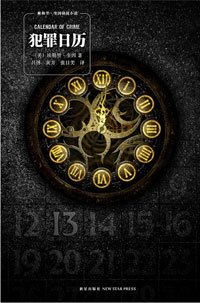早上,他妻子过来替他取出体温计,然后拿到窗边照了照。
“多少?”
还没等她回答,他就猜到情况应该比昨天更糟糕,他感觉头疼得特别厉害。
“三十六度五。”
“你确定?”
“你自己看。”
他信她。体温居然低于正常温度,并且自己也没有感冒,这让他觉得有点丢人。但是,他的鼻炎又犯了,鼻子红通通的,眼珠子显得更加明亮。
“你最好还是卧床休息一天,这样才能根治感冒。所以你今天还是别出去了。刚好今晚上勒迪克夫妇俩会过来。”
今天是周四,每个周四马里耶特·勒迪克和阿蒂尔·勒迪克都会来他们家吃晚饭,然后再一起玩会儿纸牌。
外面天阴沉沉的,但也没下雨。平纹细布窗帘很透,透过窗帘,马路上的车辆行人一览无余,只是都是被雾霭笼罩着,有些模糊。街头艺人流动马车的车顶上湿漉漉的,晨露欲滴,像是抹上了一层光泽。一缕缕轻烟从马车上面的烟囱中缓缓飘出,一群小孩坐在马车的步阶上吃饭,大部分孩子都顶着一头乱糟糟的头发,身上的衣服也破破烂烂,比身体大好几号。
夜里,艾蒂安不停地流汗,整个床上都迷漫着他的汗味儿,所以凌晨三点左右,路易丝逼着他去换了件睡袍。早晨看着旁边忙着梳洗的妻子,他偷偷地深吸了一口气。他从没把这个习惯告诉他妻子,也没告诉任何人,这个秘密只有他一个人知道:他喜欢自己汗液的气味。
还记得一个夏天的早上,那时候他还很小,五六岁的样子,他闻着自己手背上刚流过汗后湿热的皮肤散发出来的气味,立马就喜欢上了。他正准备再用力吮吸一次时,母亲发现了,诧异地看着他,说:
“你在做什么?”
母亲一脸的严肃吓到了他,出于本能,他撒了个谎:
“没什么。我舔一下手,因为我好难受。”
“手不干净。”她说道。
后来,开始学习基督教教理时,他确信母亲所说的“不干净”并不是指身体上的不干净,他那天的行为,在圣洁的信徒看来就是一种罪恶。
“你要洗澡吗?”路易丝问道。
她刚洗完澡,浴缸里的洗澡水还没放。他也不反感用她洗过的洗澡水泡澡。煤气热水器反应很慢,并且使用时总会发出嗡嗡的轰鸣声,他听了很难受。
“我觉得得洗个澡。”
“我让费尔南德过来换一下床单。”
路易丝下楼时刚好透过窗户看到泰奥先生出现在地铁口,随即路易丝就帮他把后门打开,然后仓库管理员也很快到了,把店子正面的百叶窗撑了起来。商店和整个城市一样,迎来了新的一天。费尔南德推着吸尘器在公寓里忙个不停,附近的家庭主妇也都骑着用来运蔬菜和水果的自行车沿着勒皮克街转悠着。
浴室里,艾蒂安全身赤裸,站在镜子前面照了又照,觉得自己还是很瘦。他几乎能看出胸前肋骨的轮廓。皮肤变白了,白得有点不健康。他拿起剃须刀开始刮胡子,但因为要擤鼻涕不得不停下来好几次。
他再度睡下后,费尔南德还没忙完,她在床周围又忙了一会儿。有时候他会在心里暗暗思考她会怎么想他和路易丝呢?他俩就生活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窗户内外同样的装潢,并且除了勒迪克,他们几乎不和任何人往来。为了不让自己又胡思乱想,他翻开大仲马的书,想要重新找回阅读的兴趣。
翻了几页之后,他的脑海突然闪现一个想法,让他觉得特别难过,以前看这本书可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二十年后》里面的人物延续了《三个火枪手》里面的身份,只是在《三个火枪手》中他们都才二十多岁。现在大仲马把他们写成一群老头,至少是一群历经沧桑的男人。他们的年纪和他差不多。
每一次楼下的电话铃声响起,他都会竖起耳朵认真地听。
“是的,佩尔先生。您的订单已经打包好了。今天上午我就给你送过去,保证万无一失。”
她每次都不会直呼对方的名字,所以他只能根据他们的对话试着去猜测。
弗朗索瓦到了这个年纪还没有自己的裁缝,还得打电话问妹妹裁缝的地址,这不是很奇怪吗?路易丝肯定已经打过电话到对方家里去了。这个点,她丈夫应该在家。两家人闹翻了这么久,突然接到这样一个电话,他也肯定会大吃一惊。
突然间,他很想再写几张纸条,藏到法布尔的那本书里面。他觉得这样就可以摆脱内心偶尔冒出来的不可告人的想法的纠缠,他每次想起都吓得冒一身冷汗。还记得小时候在里昂,他家附近的一条街上有一个人特别令人印象深刻,他特别干净,这份整洁他从没在父亲身上见过。那人高高瘦瘦,瘦得只剩下一个骨架子,那时候他觉得这个男人很老,但应该和他现在的年龄差不多。他下巴上留着一撮尖尖的山羊胡子,手上一直拄着一根黑色的拐杖。他应该没有工作,因为随时都能见到他像个木偶似的从那里经过,眼睛直直地盯着前方,不对任何人讲话,也不向任何人打招呼,看到一群小孩子在人行道上玩耍就果断停下脚步转身往回走。
他曾听父母说:
“他精神有点问题。”
他母亲还说:
“他妻子真可怜!丈夫还在,却像守着活寡一样。”
变成这样子,整天神经兮兮的,他自己也不想。这一想法倒是让他有点后怕,就像之前他说过一个词,让他母亲很是震惊一样。其实他不完全是在胡思乱想。如果真的什么也没有,那为什么特恩斯街的医生要建议他记下每次犯病的情况呢?为什么他觉得自己最近几个月消瘦了不少呢?为什么他总是觉得困乏,并且一点胃口也没有,上个楼梯也要喘半天?他才刚满四十岁,医生说他身体的各个器官都非常健康啊!
他有点力不从心,感觉事情已经超出了他的理解范围。这时候楼下来了好几个顾客,于是他悄悄起身,把夹在《昆虫世界》里面的那页纸抽出来,但是却不知道有什么重要的信息需要补充,于是就仅仅明确了一下日期,在“星期二”旁边写下“九月二十三日”。很可能今天什么事也不会发生。前两天不也一点情况都没有嘛。
他妻子并不知道他已经起来了。他再次回到床边,听到她对送货员让·路易说:
“我再重复一遍,东西就在仓库左边的角落。”她的语气很不耐烦。
“没有,夫人。”
“前天我还在那里见过。”
“但是我已经仔细找过了。”
“跟我来。我指给你看。教教你以后别老是一副自以为是的样子。”他开始在脑子里想象他们的一举一动,他觉得自己这个想法似乎有些荒谬。在他的想象中,他们首先走到商店的最里面,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然后跨过通往院子的门,继而穿过院子。
仓库里堆满货物,那里以前是一个马厩,门很宽,可以通过一辆车。门扇很厚,左边那扇门上还有一个很小的门。
仓库里面弥漫着一股纸箱和胶水的气味,一进门就得把电灯打开,灯泡上面布满灰尘,悬挂在一根电线下面。
他完全没想到,夏尔先生今天并没有去庆祝他孙女的洗礼。他就在楼下。艾蒂安听到了他的声音。为什么他妻子要亲自去仓库而不是让夏尔先生陪让·路易去呢?
他努力回想让·路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在这里工作的。一般来说,仆人只能在一家工作两三个月,但送货员却至少可以干上一年。他们刚来时可能还是小男孩儿,路易丝和他们都是以你相称。接着他们慢慢长大,下巴上开始出现胡须,变成了真正的男人,于是他们换到另一个地方工作。让·路易来这里应该已经有半年了。他是隔壁那栋楼门房的儿子。过去,路易丝看着他母亲怀孕,看着他出生,看着他坐在门口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艾蒂安过来后,常见他在马路边上的垒道上和同学们一起玩耍。
他觉得这不可能,但是那天余下来的时间里他有好多次想到这件事。
中午,他妻子上楼来吃饭时,他的两条手帕都湿了,眼皮也眨个不停。
“你不觉得困吗?”
“不觉得。”
“房间里太热了。我觉得最好还是把窗户开一点点缝。”
“随你。”
外面的空气灌进来,还有那突然变得清晰的嘈杂声,他一点儿也没觉得欣喜,反而觉得越发没有安全感,没有一点隐私可言。
上午他还在思索费尔南德会怎么想他。此刻他吃着饭,不停地打量着妻子,心里思忖别的男人会怎么想她呢?她见过很多男人,客户、代理商。的确,她比他见的人要多,尽管她从没有离开过商店。
他说不上来她算不算漂亮。他也从没思考过这个问题。在此之前,他觉得这个问题没有任何的意义。她是他妻子。他们彼此相依,两个人已经融为一体。在巴黎这样的大城市,只有两个人,也就是勒迪克夫妇俩,可以分享他们的私生活,还是一个星期一次。别人会觉得很惊讶吧?
除了这一家人,以及仆人、水管工、油漆工、安装玻璃门窗的人,真的想不出还有什么人曾经被邀请到他们家里来过。
晚上,当然是天气很好时,他们俩就会出去在附近转悠几圈,散散步,呼吸呼吸外面的空气,和路上随处可见的遛狗人一样悠闲自在。周日他们俩也会出门看看电影,夏天偶尔去乡下。但更多的时候,他们对外面的欢乐无动于衷,只是迫不及待地回到家里,关上门,享受房中秘事。
路易丝漂不漂亮一点也不重要,因为她只是他性生活上的伴侣。
知道别的男人怎么看她又有什么意义呢?
对他而言,她的每一个举动,甚至她裙子上的每一个褶皱,都是一个信号,无形之中说明了很多问题。
时常有一些代理商过来向他们推销产品,她认识了这些人,会不会还受到他们的赞美?她倚靠在柜台上,胸前的两座巨峰轻垂在桌面上时,会不会有炽热的目光和气息朝她侵袭而去?
如果真有这种目光,她肯定早就发现了。
有人追求她吗?他从不知道。或许还有某个人,胆子更大,向她提过那方面的要求?
但是她从没向他提及过,也从没有向他暗示过别的男人的态度。
难道她已经四十六岁了,他就可以安心了吗?他倒希望她长得丑点,至少是别人觉得她丑,她最好不能撩起别人的情欲。
三点左右,一阵扑鼻的香味飘进来,他知道厨房里正在炖野兔肉。每个星期四,路易丝都会上来好多次,看看厨房里什么情况,因为她不放心费尔南德。
是这样吗?他觉得他妻子比往常更加心不在焉了。
“我觉得你只需要穿件睡衣就可以了。”
“我更愿意穿得整齐点儿。”
“随你吧!”
他还是很谨慎。他不愿意穿着睡衣和勒迪克一家人一起吃晚餐。他很早就起来更衣,因为他一点儿也不想看书。他在房间里转来转去,不知所措。他们本可以有一个客厅的,因为家里还有一个闲置的房间,父母健在时那是路易丝的卧室。那个房间里的家具还在,只是已经被拆得零零散散,靠着最里面的墙堆放着。慢慢地,房间里面积攒了越来越多的商品,都是没卖出去的存货,下面没有多余的地方堆放,只能搬上来。
他们不需要客厅。他们在餐厅里面摆了两个活动扶手椅,所以如果不在卧室,他们一般就会待在餐厅。
集市上的音乐重新响起,但是一点也不热闹,只有两三个电动碰碰车孤零零地转动着,一个身穿白色羊毛套衫的男子独自坐在跷跷板上,在空中旋转。
灯光从厨房的门缝中穿过,艾蒂安觉得自己形单影只,差点儿冲下去,看看有没有其他人存在。
有时候,他会站在铁楼梯上面,一副傲然神气的姿态,认真听下面的情况。有时候,他会突然无缘无故的焦躁异常,有点神经质,甚至怀疑自己根本没生病。他还记得里昂的一个邻居,突然就一命呜呼,悄无声息地倒在餐厅里一张桌子前面,当时他妻子刚在厨房做好晚餐。妻子端着一钵汤回到餐厅时,一不留神,绊到他躺在地板上的庞大身躯。
他卧室的闹钟和商店的挂钟相差五分钟。下面现在是六点差十分。商店里稀稀疏疏的客人,一个接一个走到收银台,等待结账。
此时此刻他觉得时间仿佛变慢了,每一秒都相当漫长。他站在那里,感受着下午商店打烊时蜗牛式的节奏。路易丝终于朝楼梯这边走过来时,他立马踮着脚尖回到扶手椅上,生怕被她发现自己那一脸期待的表情。
等会儿,勒迪克一家人要过来,但她也没有特意去换身衣服,只是和平常一样,洗了手脸,然后抹了点粉,在脖子上喷了点香水。
“让·路易去仓库找什么?”
他满以为自己什么也不会问。但是他错了。不过妻子出奇的冷静,看上去不曾有一丝震惊,也没有转过身来看他。但是他肯定她的确吃了一惊。
“你听到了?”
她知道在房间里可以一清二楚地听到她在收银台那儿说的话。
“去找波特曼商行订的账本。”她接着说,“他硬说那些账本不在那儿。”
“我知道。”
“货肯定就在那里,都已经包装好了,地址就写在标签上。只是夏尔先生把纸箱放那上面了,让·路易没想到他要找的东西就被压在纸箱下面。”
费尔南德摆好餐桌,正准备把开胃酒放在餐盘里面端过来。路易丝在厨房和餐厅之间来回走动,从碗橱里面拿出一瓶味美思酒,还开了几瓶波尔多。
“你姐姐后来没联系你?”
“没有。她为什么要联系我?”
“我哪知道。我想既然你们已经言归于好,她应该给你打个电话。”
“并不能说偶然遇到一次,我们就和好如初了。”
他真不应该多嘴问这个问题。有时候,就像现在这样,他做的全是不应该做的事,不想生气却又怒气冲天。
“你还没测体温?”
“没有。”
“那现在测吧!”
他刚把体温计从嘴里取出来,门铃响了,勒迪克已经到了门外。三十六度七,他并没有发烧。但体温低于正常。
费尔南德去开门。路易丝走过去,马里耶特的一阵笑声立刻传来。
“我之前跟你说什么来着,亚瑟?”
随即她故意用很尖的声音解释道:
“我和阿蒂尔打赌我们今天会吃兔肉。”
“为什么?”
“因为现在正是吃兔肉的时候。每年九月份,你都会为我们至少做一次兔肉吃。”
“你不喜欢?”
“我超爱。”
两个女人拥抱了一下。马里耶特也习惯和艾蒂安行贴面礼,两边脸颊各一下,但她个子很矮,每次行贴面礼都得踮起脚尖。
“感冒了吗,你?”
对她而言,所有事情都可以成为快乐的理由。她没有站在原地,边说边往里走。她矮矮胖胖,比路易丝胖多了,身上肉嘟嘟的,就像被充了气一样。路易丝之前拿她开过一次玩笑:
“她不是走的,而是滚的。”
阿瑟则是平静地走进来,没有说一句话,已经很薄的嘴唇上依旧挂着那抹永恒的微笑。他朝艾蒂安眨了眨眼,算是打了招呼。
“怎么样?”
可以说,他们从没有离开过蒙马利特。马里耶特出生在勒皮克街鱼市场,那个鱼市场依然还在,人们都去那里买鱼,但是她父母已经不卖鱼了。
还是少女时,路易丝就和她一起玩耍,上同一所学校,之后又去了同一个修道院。
实际上,周六一起晚餐的传统在艾蒂安结婚之前就已经存在,所以阿蒂尔比艾蒂安更早来这里。
“味美思酒?”
马里耶特的丈夫继续说道:
“黑加仑!”
与此同时,艾蒂安发现两个女人正在用眼神交流着什么。马里耶特看着路易丝,像是在问她问题。艾蒂安觉得妻子微微摇了一下头,不仔细看真的难以察觉,并且妻子那表情似乎在说:
“别担心。”
突然之间,他的脸变得通红,为了掩饰,他把手帕从口袋里拿出来。现在他不能胡思乱想,否则肯定会失态。
“很严重?”阿蒂尔问他道。他那种轻蔑的口吻,总让人感觉他在嘲笑所有人。
这种感冒很容易传染。他指缝间夹着一根烟,嘴里不停地吞云吐雾。他已经不年轻了。看上去至少有四十八九,但实际上他一点儿也不像成熟男人,很可能永远也做不了成熟男人。
“为你们的健康干杯,孩子们!”路易丝说道。
作为回应,阿蒂尔肯定会说:
“也为我自己的健康干杯!”
每个人手上端着酒杯,相互敬酒。突然,艾蒂安又不经意间看到两个女人正在眼神交流。费尔南德走过来时,路易丝立马问她:
“一起吃,费尔南德?”
“我等会儿吃,夫人。”
忽然大家都不做声了。艾蒂安如果会画画,过后肯定会将刚才的场景完完整整地重现。他又瞟了一眼面前的三个人,或者说四个,如果把背对着他们正朝厨房走去的女仆也算进来的话。
餐厅简单质朴,中央挂着一个吊灯,照亮整个餐厅,吊灯由一个古老的滑轮改造而成,灯泡就安置在滑轮里面。浅黄色的微弱灯光洒下来。桌布也是黄色的。没有一个人坐着。阿蒂尔满头棕发,手里端着酒杯,背靠碗橱,身后就是一堆花花绿绿的彩釉陶盘。
路易丝穿着黑色的裙子,艾蒂安很喜欢她穿这条裙子,因为裙子后面包得很紧,可以把她臀部的曲线完美地凸显出来。她喝了一口酒之后,就把酒杯放到备餐桌上。而矮矮墩墩、满头金发的马里耶特则身穿绿色长裙,眼睛正盯着路易丝。
大家默默站着,突然路易丝打破沉寂,艾蒂安感觉她是迫不得已:
“到我的房间里去,我给你看点东西。”
艾蒂安站在那里没动。他一只手端着酒杯,另一只手握着手帕。他感觉脑子里嗡嗡作响,傻傻地看着她们朝门边走去,心里默默祈祷,希望路易丝能顺手把门关上。
突然他身后传来一个声音,似乎是巴黎郊区的口音,那副玩世不恭的语气一如既往:
“老板娘是有什么秘密想要向马里耶特坦白啊。”
艾蒂安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一时无语,眼睛却一直盯着那扇门,很快就听到门后窸窸窣窣的交谈声。厨房里传来餐具磕磕碰碰的声音,别人家的音乐也随风飘进来。一切都显得太不真实,他觉得这一刻其实并不存在。
最真实的估计还是他自己的声音,他觉得听到了自己的声音,还有电话那端马里耶特的声音。
“您会告诉她?”
“当然。”
他觉得她在微笑,可能是在嘲笑他。但不管怎样,他倒是觉得很有趣,觉得特别兴奋。
“什么时候?”
“我等会儿给她打电话。”
“为什么不马上就打?”
“因为我还得穿衣服,我现在什么也没穿。”
这句话也没引起他的任何遐想。因为马里耶特以及她的身体对他没有任何吸引力。
“五分钟之后?”
“十分钟吧。”
“我可以十五分钟之后给您电话。”
那是在勒皮克街和克利希大道拐角处的一个酒吧里,从酒吧走出来,可以隐隐约约看到文具店的正面。正值春天,阳光明媚。但是酒吧里蚊子很多,嗡嗡嗡叫个不停。
他不耐烦地抽动了一下鼻孔,然后朝只穿了一件衬衣的那位老板挥了挥手,老板看着他,一脸茫然。
“跟以前一样!”
他穿着一套全新西装,前一天在大百货街上买的,嘴里叼着一根烟,神情有点紧张,眼睛盯着墙上的大挂钟,挂钟的刻度盘周围装饰了很多小花。小酒吧里面充斥着一股酒精的气味。外面停了一辆货车,上面载满樱桃。家庭主妇们在街上大声交谈着。
那年他二十四岁。可岁月一刻不曾停留,听着手表发条滴答滴答地响,他满心焦虑。
一杯开胃酒下肚他还觉得不够,又喝了一杯,喝完立马觉得头有点晕,眼前一阵晃动,生活似乎一下子变得更有情调,从他面前经过的人,老板蓝色的围裙,马路上的嘈杂声,酒杯碰在一起发出的清脆声,各种各样的气味,还有他自己,在镜子里是一副紧张、极度渴望成功的样子,所有的一切交织成一支辉煌的协奏曲,如太阳的光芒一样光彩夺目,又宛如铙钹的鸣响般清澈。
他用手将柜子上的杯子往前一推,柜子包着一层锡皮,上面还有水迹。
“再来一杯?”服务员问道。
谁的声音不重要,从哪儿来的也无所谓,是不是老板满口的勃艮第口音问的也无关紧要。他只觉得一切太美好了。
“再来一杯!还有筹码。”
他似乎听到电话那头铃声响起。
“喂!是我。”
她笑了。
“您觉得我会不知道您想要怎样!”
“然后呢?”
“当然是愿意。”
“什么时候?”
“今天下午。她不确定具体几点。”
“我理解。”
“总之,今天下午三点以后。”
“她没说其他什么?”
“她只说她会去。”
他好想尖叫一声,好想回勒皮克街的房间收拾一番,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他可不能继续在这儿喝酒,喝上三个小时,他需要足够冷静。另外,他还有好多事情要做。比如买花,或者也可以买点水果。或者收拾一下房间,将那些不开心的事通通抛到一边。
“我得付多少钱?”
所有的满足,所有的喜悦,无一不从他的言语中显露出来。三个穿着白色工作衫的粉刷工都不说话了,放下酒杯,呆呆地看着他。
对面有两个很大的橱窗,昏暗中可以看到收银台旁边的一张面孔,黑色的头发盖在上面,脸上有一片乳白色的污迹。
那年他二十四岁。
两天前,为了能有更多时间和她在一起,他搬了家,在勒皮克街美日酒店订了一间房。
“不舒服吗?”
他向勒迪克打了个手势,让他别太担心,然后努力微微张嘴,将杯子里的酒一口喝干。
有那么一瞬间,他觉得那张脸不再属于他,表情坚硬,一点儿也看不出刚才他身上发生了什么事。就连那眼神,说不上迟钝,但相当呆滞,读不出任何信息。
“你又感觉到了什么?”
应该是这一变化太过于明显,就连阿蒂尔都注意到了。并且更让人好奇的是,一向喜欢拿所有事情开玩笑的他,突然变得一脸正经。
“发生了什么事?”
他来不及思考,更来不及掩饰,而是立马放下酒杯,把手放到胸前。
“胸口一阵疼痛。”他说得很小声。
“心脏?”
“估计是。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这声音好像不是从他嘴里发出来的,而是出自一个垂死的人之口。他将目光从门口移过来。
“你希望想我叫一下你妻子吗?”
“不用。什么也别告诉她。”
阿蒂尔以前就知道他的事情?他从没担心过这个问题。以前他和马里耶特通电话的事阿蒂尔应该知道。马里耶特对他什么都不隐瞒。
“你到底感觉怎么样?”
“说不上来。很快就没事了。”
事实上,他并没有什么疼痛。他倒是想真的大病一场。以他现在的健康状况,让他们相信自己生病也不是一件难事。他只要顺其自然,装作支撑不住快要晕倒的样子,俨然一副没有了生气、对万事漠不关心的表情。接着,他们就会打电话给马雷斯科医生,让他赶紧过来诊断。
勒迪克默默地看着他,看起来一无所知。可能他是真的完全不知情。
“已经没事了。”
“喝口水。”
他差点儿将一满杯味美思酒一干而尽,想要把所有伸手可拿到的东西都吞进肚子,就是为了能够喝醉,什么都不用想。活到现在,他就遇到过一次这种情况。他第一次喝醉才二十二岁,还不认识路易丝。第二天,他都以为自己死过一回了。
“你想要我把窗户打开吗?”
“不用了。关键是什么也别对她们讲。”
厨房的门先开了。费尔南德惊讶地问了一句:
“夫人在哪儿?”
他抬了抬下巴,示意卧室的方向。
“晚餐准备好了。我现在就上浓汤?”
他妻子和马里耶特出来了,路易丝还是一如既往的镇定,然后有些疑惑地看着女仆。马里耶特看起来倒是比之前更开心,更轻松。
“我是想问一下,现在可以上浓汤了吗?”
“当然可以。”
她突然转过身看了丈夫一眼,随即皱了皱眉。
“不舒服吗?”
“没什么。”
“你没觉得哪里不舒服?”
“已经没事了。”
“又犯了?”
“应该不是。只是一阵头晕。可能是因为那杯味美思。”
为什么马里耶特要用那种眼神看着她丈夫?或许他能让她感到放心。但她很快便有些慌张。
“我们开始吃饭吧。”路易丝说道,整个人一副心神不宁的样子,目光不停地扫向艾蒂安。
那目光特别严肃,她不会随随便便担心,那目光中也根本就没有担心,而是像一个女人要审视眼前的问题时才有的严肃而冷静的神情。
她一个问题也没提,也没问他到底感觉如何,只是默默地观察每一个小细节,像平常一样给他盛汤。
“你还是再去躺会儿,可能会好些?”马里耶特建议说。
路易丝立马回答:
“不用。”
仿佛她清楚再躺会儿也无济于事。
“如果是我,”阿蒂尔开了句玩笑,想要打破沉默,“感觉到有点感冒迹象,我就会喝掉一瓶朗姆酒,然后对马里耶特说……”
阿蒂尔的话没说完,艾蒂安觉得他的话没有一点意义,他还是机械地吃着饭,看着他们,仿佛以前从没见过他们。
晚餐在这种氛围中继续着,他说不出自己吃了什么。他只觉得周围的空气形成了一个密集的黄色气流层,他们四个人都被包裹在里面,就像一幅古老油画里的人物。
他感觉到妻子时不时投来目光,费尔南德穿着浅蓝色工作衫、围着白色围裙,不停地走来走去。现在他不能胡思乱想。就算想也办不到。在大伙儿面前,一点可能性也没有。
过后,可能是明天,也可能其他时候,他可以一点一点地整理思绪,一点一点地再现真实的画面。可能需要晚一些。因为这感觉太可怕了。
他问过自己许多次,是不是现在还不是时候避免所有的这一切。那个时候,看着桌子对面的路易丝,尽管勒迪克夫妇都在,但他还是很想将手伸过去,握住路易丝的手,坚守两人之间的约定,继续他们的生活,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真的很难做到吗?他们不是保守秘密十五年了吗?
“我们俩一起对抗她们两个女人?”勒迪克之前就提到过勃洛特牌游戏,现在又提出这个建议。
艾蒂安闻到了葡萄渣的气味,同以前的周四一样,他们今天喝的也是勃艮第葡萄酒。费尔南德撤走餐具,他们四个都站了起来。女仆收拾完餐桌后,在桌子上铺了一张绿色的毛毡。
“如果我们俩一起斗男人,我们早赢了!”马里耶特边往脸上擦粉边说。
她还瞟了艾蒂安一眼,说道:
“你现在的表情就和橱窗里的模特一样。”
的确,他也意识到了。他觉得让他嘴角微微上翘,露一个笑容,真的是比登天还难。此时此刻,路易丝焦虑的目光还一直停留在他身上。
难道她看出来艾蒂安很害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