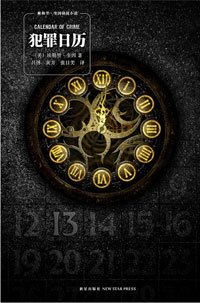阿蒂尔·勒迪克提了个建议,但也没抱太大的希望:
“我们再来最后一把,五百分?”
马里耶特已经起身,扯了一下裙子里面的内衣,对他做了一个罢了的手势,说道:
“今晚算了。艾蒂安累了。”
两个男人赢了。勒迪克每次都会赢,不管他的搭档是谁。他可是朱诺路附近各个餐馆的常客,一年大部分的时间泡在那里玩勃洛特牌。
他经常向别人这样介绍自己,同时灰色的瞳孔里散发出一缕笑意:
“阿蒂尔·勒迪克,法国人,四十五岁,打过预防针,第十八次勃洛特锦标赛冠军。”
之前有一年,他真的拿过勃洛特锦标赛的冠军,在蒙马特的各个咖啡馆里引发了一场热议。
艾蒂安从没向他吐露过心声,当然对方也不会和他交心。勒迪克尽管老是喜欢开玩笑,但从来不把火往自己身上引。
他父亲是昂古莱姆市的一个公证员或者诉讼代理人,他小时候就被父亲送到巴黎学法律。在学校待了两三年之后,他想像那些自编自唱的艺人一样,去蒙马特高地的小酒馆碰碰运气。
他不喜欢别人谈及他的那一段岁月。因为好长一段时间内,他和家里人关系闹得很僵,饥寒交迫地在外漂泊了很久,始终不肯承认自己真的一无是处。
那时候他已经和马里耶特在一起了,还是少女的马里耶特为了追随他离开父母。直到好些年之后,夫妻俩终于要结婚时,她的父母才原谅他们,后来互相经常走动。
马里耶特会时不时提起那段艰难的日子,当时生活困难到只能在垃圾桶里面翻吃的,并且经常没有地方住,就在火车站的候车大厅里面过夜,背靠着背相互取暖。说到这些时,她满脸洋溢着幸福。
阿蒂尔起初在一家报社策划广告,那家报社现在早就不在了。他发现自己在绘画方面倒是有点天赋,于是带着马里耶特搬到圣心教堂附近的一间画室住了下来,但是到最后什么也没成。现在他对绘画还抱有幻想吗?他尝试了无数个职业之后,误打误撞进了一家保险公司,当起保险代理人,还逛起了蒙马特的咖啡馆。
刚开始马里耶特就只是在家里炖炖粥做做饭。后来她在朱诺路上开了一个女式帽子店,慢慢地生意越来越好,到了忙季还得雇四五个临时工。
她从没骂过丈夫,也从没想过改变他的性格或者生活习惯。她就喜欢他本来的样子。他每次过马路时,看着妻子将手挽在自己胳膊上,努力让步伐合上他的节奏,他就觉得特别满足。
阿蒂尔没想到的是,艾蒂安一整个晚上没一次失误。他慢慢地融入游戏里面,尽管并不非常着迷,也没有花太多心思,因为这只是他打发时间的一种方式,就像在牙医的等候室里,脑子一片空白,什么也不想,等着时间一点一点流逝。别人叫到他名字时他一脸惊愕。
路易丝平时总是特别冷静,临危不乱,这次却分了好几次心。马里耶特。
她们在卧室里时发生了什么事?她们有什么事这么迫不及待地想要悄悄告诉对方?
再过几分钟,勒迪克夫妇就得走了。告别的话已经说出口,路易丝把纸牌放回抽屉,马里耶特去拿外套,她丈夫伸了伸懒腰,点燃一支烟。
很快房间里就只将剩下路易丝和艾蒂安两个人。其中一个人会走过去把门闩拴上,然后两个人一起进房间,集市上的灯光投射在房间的墙壁上,波浪般前仆后继。
他突然感觉一阵恐惧。或许应该挽留一下朋友。他清楚什么也没发生过,也不会发生什么。他们两个人将在同一个房间里,互相窥伺着对方。
“下个星期四见!”马里耶特欢欣鼓舞地说道,“艾蒂安,保重身体哦!”
他嘴角浮现一丝笑意,像极了阿蒂尔·勒迪克向别人介绍自己是勃洛特冠军时的那副嘴脸。下一个星期四,他感觉特别奇怪!下个星期他们还来吗?他们的聚会还能一个星期接一个星期定期举行吗?
还得等多久?
最让他吃惊,最让他感动的是,勒迪克握住他手时使出的力量。两个女人背对着他们站在门口。阿蒂尔并没有像平时一样礼节性地握一握手,而是加重手腕的力度,握好几秒钟,像是在传递什么信息,但是眼睛却并没有看他。
什么信息?难道他也知道?还是他一直都知道?
“星期四见。”阿蒂尔终于说话了。
随后,他对着路易丝,用一种戏弄般的语气说:
“晚安,老板娘!”
楼梯上微弱的光仅够看清阶梯,旁边的升降梯正在往上升,两边的墙壁已经历经三十多年,房主从没重新粉刷过,现在就像老教堂的墙壁一样暗淡无光。
“晚安。”路易丝回应一句。
“晚安。”
两位客人走了。片刻之后,他们拉了一下门绳。门开了,他们走了出去,夜晚的空气好清新,沁人心脾,集市上的灯光和噪音一股脑儿涌过来将他们淹没在其中。马里耶特的手摸索着丈夫的胳膊,挂在上面,而这边,楼层之间的平台上,艾蒂安和路易丝站在公寓大敞着的门前,一直目送着他们。
勒迪克夫妇会在路上说些什么呢?他们会走到西拉诺酒馆的露台上坐下来再最后喝上一杯,看着远处旋转木马上嬉闹的女孩,聊着今晚的聚餐吗?
“你回去吗?”路易丝轻声地问他。
他觉得她的这句话说得有点奇怪,于是瞟了她一眼,想知道既然现在就剩下他们俩了,她心里在想什么。
他跟着她进了屋,来到餐厅里,睡觉之前她得把酒放回碗柜,用过的杯子也得拿到厨房里先清洗一下,不然明早上起来,满屋子都会是酒气。
以往,她也是这样,同样的动作,同样漠然的表情,但是他确信今天她真的有些不同。交流仿佛被切断了,不仅仅是他们俩之间,就连他们和那些无生命的物体之间的联系也不存在了,并且她还丝毫没有想要修复这种联系的意思。
“我们去睡觉?”
她的嗓音和以前不一样。不一会儿,他们走进卧室,她随手转了一下开关,他一直站在她身后,但她没有看到他。艾蒂安觉得她微微打了一个寒战,像是被吓到了。
如果说她一进门就把灯打开,好摆脱这让人觉得神秘而诡异的黑暗,意味着什么,那她脱衣服之前先把头发散开就更说明点什么了。
昨夜,他们已经做过。
他们今天还会做吗?
他觉得当着她的面脱衣服很尴尬,所以换睡袍时转过身去了。他走到浴室里,想把浴室的门关上,但却不敢关死。他出来时轻轻推了一下,门敞开一大半。
“你不用测一下体温?”
“不用。”
“你好像已经不发烧了。”
“可能。”
“感冒怎么样了?”
“感觉好多了。”
“今天玩牌时你基本上没怎么擤鼻涕。”
的确。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整个晚上他都没有换手帕。鼻炎似乎好了很多,后颈也不那么僵硬了。
艾蒂安一从浴室里面出来,她就进去了。艾蒂安努力不去看她。一听到水冲在妻子身上的声音,他觉得浑身不自在,总是回忆那些亲密的画面。
“我关灯了?”
“随你。”
就在她转动开关准备关灯时,他突然产生一个主意。
“我觉得我最好还是服一粒安眠药。”
他们俩都几乎不吃那个东西,除了有一次牙疼得厉害,可能还是因为喝了太多的咖啡,他们才吃过一次。
“你觉得你会睡不着?”
她没有坚持,而是又去了一次浴室,出来时手上拿了一颗白色的药片,还有一杯水。她穿着睡衣站在床边他躺下的那一侧,他只能看到她的下半截身影,紧紧地靠着他。她弯腰时,睡衣上的丝质布料刚好从他脸上拂过。
他此刻有欲望?他自己也搞不清楚。他用手肘将自己撑起来,握住杯子,喝了一口之后才抬起头。妻子俯视着他,表情一如既往的平静,但是却有一些不同寻常的凝重。
灯关了,她爬上床,理了理被子然后躺下来,而他屏住呼吸,等待着,不知道她还会不会和以前一样。他感觉到妻子有一丝的犹豫,随即还是靠过来,直到脸快要贴在一起。然后他闻到妻子嘴里特殊的气味:
“晚安,艾蒂安。”
她的双唇凑了过来,自然而然碰了一下。没有躲避,也没有进一步的举动。
“晚安,路易丝。”
各自睡在自己的那一侧,过了一会儿之后,他们总是习惯再小声地重复一遍:
“晚安,路易丝。”
“晚安,艾蒂安。”
他还是说了,话一出口,顿时觉得胸口一阵抽搐,像是被勒了一下。她也给了回应。但是立马,房间里就一点儿声音也没有,安静得让人窒息。
他久久不能入睡,眼睛睁得大大的,盯着窗户,外面的灯光透过窗户射进来。他在心里纳闷,刚才吃的安眠药怎么一点儿效果也没有。他不想思考。时候不到。他还没有准备好。他知道,一旦开始思考就没法停下来,并且过程将艰难而漫长。
他不停地对自己重复着那些没有任何意义的话,就像小时候一想到惩罚了他的母亲,嘴里也絮絮叨叨地念叨:
“难以相信她怎么这么恶毒。很快她就会意识到自己做了什么,会为此而后悔,会为此而伤心。”
今天晚上,他也在自言自语:
“怎么会这样!”
外面一片喧嚣,有人坐在电动车上你追我赶,撞来撞去,玩得不亦乐乎。也有人从人行道走过,心平气和地谈论着生意。
路易丝也没有睡着。艾蒂安很确定她也没有睡着。或许她也是眼睛圆睁,看着外面的灯光投射在浴室门上的倒影。
他听不到路易丝的呼吸声,也感受不到一丝动静。她就那样一动不动地躺着。一会儿之后,艾蒂安都想碰一下她,好确认她还活着。
但是他不敢。
艾蒂安不恨她,眼神中不带任何的敌意。艾蒂安真的不能问她一下吗?或许他是真的没必要问得太清楚。黑暗笼罩着他们,他只想在一片漆黑中轻轻地说一句:
“告诉我,路易丝,是真的吗?”
她会明白的,这一点他很确信。只是,她不可能回答:
“是真的。”
如果他问了,又会发生什么事呢?没有答案。她不会告诉他。这个问题本身就毫无意义。
她肯定也特别急切地想问他:
“你明白吗?”
仅仅这么想一想,他就已经满头大汗。当然他肯定也没法儿回答。
他热得不行,和前夜一样汗流浃背,从头湿到脚。嘴中突然产生一股异味,应该是安眠药的味道。
为什么阿蒂尔·勒迪克要那么用力地握他的手?为了鼓励他?阿蒂尔知道该怎么办?又或者阿蒂尔的用意很简单,只是想要表达一下对他的同情?
或许他最好还是和勒迪克聊一下。但是他从没对任何人吐露心声。实际上,到现在他才意识到,他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朋友。在学校时就这样。成年后,服兵役之前,在里昂一家银行工作时也这样。他父母从来没弄清楚过他脑子里在想什么。
他没有朋友,不仅如此,其他年轻人所说的情人,他也不曾有过。
他大部分的同学都会一连好几个星期甚至好几个月和同一个女孩儿约会,以证明他们喜欢这个女孩。至少在他眼中,从言行看,他们还真的像是坠入了爱河。
为什么这种事不会发生在他身上呢?他也尝试过好多次。他也带女孩儿去电影院,去罗纳河边,去乡下。他笨拙地在她们身上抚摸。但是,随后他肯定还说了不少他本不想说的话。
他看到了她们的缺陷,知道她们的小秘密。对于她们,他产生的更多的是同情,而不是占为己有的欲望。
欲望强烈到让他难以忍受时,他就会去找妓女搭讪,并且每次都是在同一个路口,找同一个人,只要看他一眼,对方就明白他想干什么。
他从没有和一个关系亲密的女朋友手挽手散步,从没有因为一个玩笑而爆笑。服完兵役后他就来到巴黎,到了晚上经常一个人在街上游荡好长时间。每一次看到窗帘后面一对对情侣亲热的身影,他就万箭穿心般痛苦。
路易丝微微动了一下,动作轻得几乎无法察觉。随后艾蒂安打了一个哆嗦,心生一丝希望,尽管知道他现在没什么好期望的了。妻子应该也在仔细听他的呼吸声。她也一样不幸吗?还是她在同情他?
这十六年里,艾蒂安常常偷偷看着她,问题到了嘴边但最终未能问出口。他相信妻子肯定知道他有问题想弄清楚,只是妻子没有勇气面对这个问题。
他们是如此需要对方!难道她不清楚这一点?
被子下,他的双腿变得沉重。身体有点麻木。浮现在脑海中的已经不再是那些想法,而是一些模糊的画面。
比如一个在这个房间里睡了很久的男人的样子。当然不是在同一张床上,他和路易丝结婚之前,路易丝买了一套全新家具,旧家具早已被她送到拍卖市场。
瞬间后,他又看到妻子站在收银台旁,眼睛死死地盯着铁楼梯的上面,留心上面的一举一动。她用一种冷漠的商人语气对他说:
“如果您想从这里过……”
他真的相信仓库保管员当时什么也没发现?平常保管员都在外面整理货柜上的商品。有时候她不得已把他打发到仓库去拿点什么东西。但是她不能每次都把他打发走。
商店最里面有一个柜子,从泰奥先生的透明打印室也看不到那个角落。她朝那个角落走去,臀部的曲线还是那样优美,后颈还是那样白皙圆润,一头乌黑秀丽的长发倾泻而下。
她回头看了一眼,想要确认铁楼梯正好夹在他们和一直坐着的夏尔先生之间,同时她还瞟了一眼外面的橱窗。
随后,她迅速将手挽在他的脖子上,就像马里耶特挽起丈夫的手臂一样自然,双唇也随之凑过来,和他的嘴唇黏在一起。
但他们很快就打住了。
“我想给您看一款文件夹,我猜您肯定很感兴趣。”
上面的男人听到了吗?他也正窥伺着店子里的一切动响吗?
她在他耳边喘着气:
“明天上午九点左右我会想办法溜出去。”
他回了一句:
“希望不要太晚。”
坐在勒皮克街酒店房间的床边,他左顾右盼,等了又等。而为了能去和他幽会,路易丝可是绞尽脑汁。
那个时候,商店已经由她全权管理了。但有时候她会借口女仆做事她不放心,上午亲自出去买东西。勒皮克街上熙熙攘攘,全是去载东西的小货车。家庭主妇们蜂拥而至,上的上,下的下,俨然街上的两股洪流。酒店的仆人正在整理房间,大部分房间依然房门紧掩。
经常,路易丝都得从水桶和扫帚上跨过去。
她一进门先送上第一个吻,随后立马从他怀里挣脱开,开始脱外面的裙子,脱内衣,迫不及待想要将自己曼妙的身躯赤裸裸地展现在他面前。
“爱我吗?”
“爱。”
“幸福吗?”
即便仅仅只有十分钟时间,她也会把衣服脱得光光,眼睛里闪烁着无尽的喜悦和骄傲。
“你待会儿会经过商店?”
“是的。”
“大概几点?”
那时候他还是东南区文具店的代理人。巴黎的总经销商把他派到右岸地区。他一天上午在外出差,进了克利希大道的这家商店,手上提着一个很重的公文包,表现得异常的谦卑和礼貌,像个乞讨者。
他还记得,他首先打招呼的是一个穿着麦麸色罩衫的男人,因为商店前面有一个很醒目的名字,所以他就向那人问了一句:
“比拉尔德先生?”
回答他的是夏尔先生。
“我去叫一下老板娘。”
他朝透明的打印室走去,一个穿着黑色长裙的年轻女人正在和一个员工讲话。
他们第一次相见,她就是在那个打印室里,透过玻璃窗瞥见他。他站在外面,看到她嘴唇一直在动,那是她正在和仓库管理员交待什么事情。
“加坦夫人马上就过来。”
这是他第一任丈夫——纪尧姆·加坦的姓。
那一天上午天很热。正值七月。市政洒水车慢慢地从马路上驶过。商店的大门大开着。
她和老泰奥讲完话,朝他这边走过来。他把头上草帽揭下来,放在一叠文件上。从打印室到收银台的那段路很长,因为商店特别深。他注视着她一路走来,目不斜视。
“请您见谅……”路易丝走到他身边时,他结结巴巴地说道。
因为什么?他说不出来。他脑子一阵混乱,只是隐隐约约觉得她注意到了自己。
“我是东南区文具店的新任代理人,和您已经合作很久了。”
他们没有就座,而是肩并肩站在柜台前面,艾蒂安把样品一一摆在柜台上,路易丝的手放在柜台上。路易丝离他很近,他仿佛都能感受到她身上散发出来的热气。
“您什么时候再过来?”
“下个星期的这个时候,如果您的订单没问题的话。”
她只是简单地应了一声:
“您下周过来吧!”
她边说边把手伸过去,深情地看着他。
“你看起来真的特别年轻、动人!”艾蒂安后来对她说。
他第二次拜访时,处理完订单的事,路易丝邀请他到楼上喝一杯。
“每次接见特别重要的供应商,都会请他上去喝一杯,是这样吗?”
这是他第一次爬上铁楼梯,爬到楼梯顶端时,他非常吃惊地发现楼梯直接通向卧室。
“很抱歉我把您带到这里来,但是从这里走比从大楼入口走更方便。”
旁边只有一个围着围裙的女仆,但他并没有看清她长什么样子。
“拿两个杯子过来,朱莉。”路易丝对她说。
然后路易丝又转向他:
“您是想喝点开胃酒还是一杯水就够了?”
“随您,您喝什么我就什么。”
餐厅的窗户敞开着,外面的凉爽空气时不时灌进来,和室内的燥热的空气有如对流。
他一直不清楚她是不是故意把他带上楼来的,也不清楚这种事情有没有发生在其他代理人身上。这个问题他从没敢问她。
十六年之后,他还会想起味美思的味道,那杯酒的颜色还历历在目。路易丝端起酒杯喝酒,他发现一滴玫瑰红葡萄酒挂在她的嘴唇上,垂垂欲滴。
“您结婚了吗,洛梅尔先生?”
“还没呢,夫人。”
“您很年轻,不是吗?”
“我今年二十四岁。”
那个时候,他还不知道她多大。其实她刚满三十。
“您来巴黎很久了?”
他的嘴唇微微颤抖了一下,还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他就回了一句自己都不知道是什么的话,然后他伸手再去拿杯子,手却不小心碰到她的手指。随即手指相扣,掌心渗满汗水。目光相遇,突然间,她已经依偎在他怀中,他也不知道是被自己一把搂过来的,还是她主动扑过来的。
为什么那一吻之后,他似乎看到她双眸中泪光闪闪。
他觉得自己终于也等到了这一刻。火热的身体紧紧地贴在他身上,让他无法放手,他已经不想再失去她。
他们狂热地缠绵,都没有注意到楼下电话响起,夏尔先生在楼梯角落叫道:
“夫人,您在上面吗?是拉波切尔商铺老板找您。”
他们先后下楼,走在狭窄的楼梯上,艾蒂安有些恍惚。
此刻他躺在自己床上,他在哭泣,在默默地流泪,一点呻吟的声音也没有。
“你睡了吗?”路易丝终于吭了一声。
他不是故意不回答的。他真的有点没反应过来,已经分不出现实与梦境,二者像是被什么东西隔着,很厚,用手去摸却是摸不出那是什么。
之后他经常来克利希大道,但是路易丝因为个人原因,不能每次都把他叫上楼。于是他们就想到了商店最深处的那个黑暗的角落,当然还得当夏尔先生在楼梯另一边某个看不到这个角落的地方才行。
他们第一次见面后一个月,他要了她,就在楼上卧室的床上,暴力地、接近痛苦地要了她。两个人都像失去了理智,然后互相看着对方,不清楚对方眼中流露出来的是恶意还是爱慕。
路易丝恨他吗,对她失望了吗?接下来那个星期,每次给她电话,她都是很冷漠地回复一两句,爱理不理。
每天,他都要从商店前面经过很多次,但是不敢进去。有一天上午,她出来给他开了门。
她也会经常想起这段经历吗?
一次,仅此一次,他见到了她丈夫。那时正值秋天。他看到一个肥胖的男人,四十来岁,棕褐色的胡须,站在柜台前。他穿着一件米色大衣,头上戴着一顶帽子,咋一看,他还以为这是个客人。
她给他们俩做了简单介绍。
“我丈夫,东南区文具店的代理人洛梅尔先生。”
“幸会。”
她还是一如既往的淡定。
“一般都是我丈夫负责客户,”之后她向他解释道,“父亲去世之后,我就和他结婚了,那时候我才十七岁,对生意上的事一窍不通。”
他恳求她出来见面,只有他们两个人,于是他们决定在勒皮克街附近租一间房。那时候,他在离北部火车站不远的拉斐特街上租了一个带家具的房间。
“我们最好还是不要经常在店子里见面。你最好也不要直接给我打电话,因为不一定每次都是我接电话。”
她向他提起马里耶特,从此马里耶特便充当他们的传声筒。
“我们一起上学。她是我唯一的朋友。所以她知道了也没关系。”
于是他和这个未曾谋面的女人通过电话建立了联系,维护着共同的秘密。
“又是您!”一听到他的声音她就尖叫起来,“我不是跟您说了吗?她没回复。”
“求您了,别拿我开玩笑。”
“那好,请放心,年轻人。如果您放乖点,再过两三个小时她就会去找您。您去老地方等她就可以了。”
他真想赶紧辞掉东南区文具商代理人的工作,然后找一份夜间工作,专门在菜市场运菜,这样他就能时常和她约会了。
勒皮克街的那个房间很普通,卫生状况令人担忧,但是路易丝完全不在乎。他在客户那儿待了好长时间,然后一忙完就急匆匆跑过来,生怕错过一点点和她在一起的时间。
圣诞节过后,新年未到,路易丝对他宣布:
“下个星期,我会给你一个特大惊喜。”
他苦苦哀求她告诉自己是什么惊喜,最后她还是屈服了。
“我一个住在拉罗谢勒的嫂子病危,应该是没救了。如果她死了,我丈夫就得去参加葬礼。”
嫂子去世,他们终于有了两晚宝贵的时间,可以单独在一起,在酒店的一个小房间里快活了两夜。
最后一天早上,路易丝边穿衣服,边看着他,眼神比往常更加严肃。
“你觉得你是真的爱我?”
“千真万确。”
“爱到愿意和我共度此生?”
他觉得,这是再明显不过的事情了。
“好好想想。不用马上做出回答。”
“但是……”
“下次我过来时,你就要坦白告诉我,你愿不愿意娶我。”
她走了,连告别吻都没有。接下来三天,他每次给马里耶特打电话,对方都会毫无怜悯之心地告诉他:
“她今天没空,我可怜的朋友。”
“为什么?”
“我怎么知道?可能她丈夫感冒了得在家休息?”
“真是这样?”
“这只是个猜测而已。要不然就是她自己不想见你……”
等到他们再见面时,天已经很冷了,那天上午九点半,屋里的灯光像天空一样亮白。一年四季在外做生意的女商贩们把取暖用的火盆端出来,双手放在上面取暖。
路易丝没有立马冲过去抱住他,而是停在门口,面无表情,轻声说道:
“你下定决心了吗?”
“你很清楚我只想娶你。”
“你真会娶我?”
她平静地甩了一下手,从他怀里挣脱出来。
“当然是真的。我爱你。我会尽我的全力爱你,用我……”
“过来。不是,不是这样。”
路易丝紧紧地拥抱着他,抱了好长时间,直到他都觉得有点喘不过气来。
“你想做什么?”感觉到她想要往后退,他开始有点担忧。
“我要离开。”
“但是……”
“不是今天。近段时间都不要去找我。”
她终于还是睡着了吗?她和我一样,也在浮想联翩吗?
集市上的音乐终于停了。马路上的脚步声越来越少,但是却越来越清晰。
“我曾经这样问过他,问他是不是一直把我当傻子。”外面传来一个含糊不清的声音,显然是一个醉得晕乎乎的人说的。
“他怎么回答?”
两人的声音向着布朗什广场的方向,越来越低,渐渐消失。
一个星期之后,路易丝回来了,他感觉什么东西不一样了。也有可能是他对她的态度有些误解。她变得更加冷静,更加深思熟虑,但是两人之间的激情越来越火热。
难道是因为他们俩现在就已经把对方当成丈夫和妻子了吗?
“你保证你以后都不会抛弃我?”
他向她保证,正要说点什么,她立马打断他。
“你不会觉得我人老珠黄了?”
春天走了,夏天又来。一天下午,他走进商店,他还清楚地记得,那天集市上繁华一片,生意如火如荼。每个月他都会这样正式到那里去一次,以东南区文具店代理人的身份,正式出现在她的商店里。
她站在收银台后面给了他一个眼神,但是他却没有立刻反应过来。他反而还在抱怨,为什么她不带自己去商店里面的那个角落。
“我正在处理一个订单。”
的确。她当着他的面很快把工作处理完,然后指着楼上。
当她领着他走到门口,他喘了口气:
“你丈夫呢?”
她只是点头示意了一下。
“病了?”
同样的动作。然后,她提高嗓门叫道:
“再见,洛梅尔先生。希望发货不要太慢。”
整个晚上,他都处于不明不白的状态。他迫不及待地想要问她,他有好多好多问题要问。他给马里耶特打电话,而对方回答说:
“您最好还是耐心等一等,亲爱的朋友。”
“她丈夫病了吗?”
“您知道了?”
一阵沉默,随后他吞吞吐吐地说道:
“严重吗?”
而她,只是平淡地回了一句,仿佛非常不想聊到这个问题:
“估计是。”
接下来的半个月,他就只见到路易丝两次。第一次,她刚进来就走了,像一阵风一样。
“我得马上回去。我出来只是找医生拿药方。”
他想开口说点什么,却立刻被她制止。
“不要说!现在什么也别说。”
走到门口,她才转身问了一句,语气近乎冷漠:
“你爱我吗?”
接下来的一次见面她也问了同样的问题,两人相拥在一起,肌肤相触,她激情似火地挑逗他,仿佛想要将他吃掉。
“如果有一天你不打算再爱我了……”
一天早上,他走到克利希大道的拐弯处时,被眼前的景象吓了一跳。文具店的百叶窗全部紧闭,门口却贴着一张讣告。门房站在门口,正和两个邻居细声交谈,可能是在解释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一下子慌了神,不知所措,随便上了一辆公交车,完全忘记了自己本来是要去哪里。
和客户会面时,他一直坐立不安,有如置身于冰冻的浓雾中,无所适从。后来他经过好几个酒吧,都想进去给马里耶特打个电话。
他要说什么呢?
中午他去了一趟酒店,想去看看有没有给他的留言。什么也没有。晚上,还是什么也没有,他在床上躺了一整晚,眼睛一直盯着天花板。
又过了三天,他还是没有路易丝的一点消息,也没有和马里耶特联系。到了下葬的那天上午,他去了布朗什广场,偷偷站在一个报亭后面的角落里,远处的门上面挂着黑色篷布,门前的空地上围着一簇簇的人群。
他看到棺材被抬了出来。路易丝就站在旁边,全身黑色的丧服,脸上戴着一块面纱,在一个矮矮胖胖的女人和一个似乎浑身不自在的男人的陪同下,上了最前面的一辆汽车。
那正是马里耶特和她丈夫,那时候他们和他还不认识彼此。
下午四点,他终于在拐角的一家酒吧拨通电话。天阴沉沉的。房间里的灯全亮着。商店的百叶窗还是紧掩,但是楼层之间的窗户那儿散发出灯光。
公寓里电话响起,他的心在怦怦直跳。好像过去了很久,电话才通,是马里耶特的声音:
“可以让路易丝接一下电话吗?”
“我去看看。”
马里耶特像是没有听出他的声音。他隐约听到电话那头两人窃窃私语的声音。随后有人拿起电话。
“是你吗?”路易丝问道。
“是我。”
他一下子哑口无言,不知道该说什么,也忘了自己打电话的目的。随即,他傻乎乎地说了一句:
“你怎么样?”
“很好。”
一阵沉默。这样的沉默让他有种错觉,像是电话已经被挂断。但马上,他又听到路易丝焦急的声音:
“你呢?”
“我想见你,迫切地想见你。”
“真的?”
“真的。”
她迟疑了一下,不过最终也没有让他马上过来。丧礼后马里耶特和阿蒂尔应该一直在陪着她。
“你能等到明天吗?”
“如果你觉得这样更好的话。”
“我是这么觉得。明天给我电话。”
突然,他觉得安眠药开始发挥功效,全身越来越麻木。他仿佛听到了一个非常微弱的声音,好像刚刚从她嘴里说出来的:
“现在,你可以了。”
他一阵抽搐,紧紧地攥着手指,克制着不要发出任何声响。
路易丝轻轻碰了一下他的后背,看他是不是真的熟睡了,而他继续保持纹丝不动,装作全然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