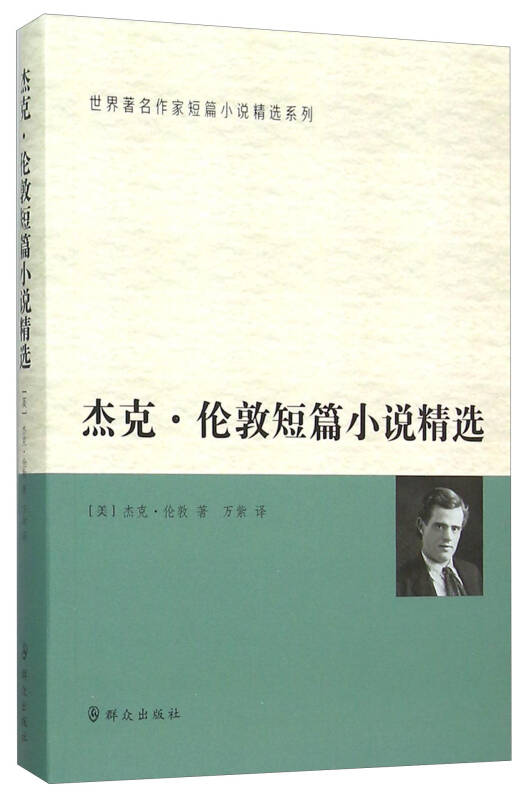那个老姑娘小小的,直直地坐在椅子上,惊愕地听着警长的声音,他的声音有些颤抖,她还从没有听到过他发出这种声音。事实上,麦格雷不是在跟她说话,而是在和电话那头一个看不到的人讲话。
“不,克罗米埃先生,我没有给媒体发布任何消息,也没有以内阁先生们的名义邀请任何记者或摄影师来。至于您的第二个问题,我还没有任何新消息要告诉您,也没有任何想法,就像您说的,如果有什么发现,我会马上向预审法院汇报……”
他看到雅格特用生气的目光朝让维耶的方向看去。她好像把让维耶当成了警长没有控制住自己愤怒的见证人。她的嘴角带着一丝浅笑,有点像是在对那个探员说:
“好吧,您的老板……”
麦格雷把同伴拉到走廊里。
“我去一下那个公证员家。你继续问她问题,别逼得太紧,温柔点,你懂我的意思。或许你会比我更有可能让她上钩。”
这是真的。如果他早上就预想到要跟这么一个固执的老女人打交道,他会带上年轻的拉普安特,而不是让维耶。在整个司法警察局,就数拉普安特最会和中年女性打交道。有一个中年女人还曾摇摇头对他说:
“我很奇怪一个像您这样有家教的年轻男人怎么会做这种工作……”
她又补充说道:
“我肯定您会因此受苦的。”
警长重新来到街上,记者们都去附近的一家小酒馆里放松了,只留下一个记者在那里值班。
“兄弟,没有什么新消息……不用跟着我……”
他没有走很远的路。找上一个相关人员也没走很远。好像所有跟这件事情有关的人都住得很近,好像整个巴黎就只有这几条贵族阶级的街道。
公证员家在威尔塞克赛尔街,和多米尼克街上的那栋房子属于同一时期,同一风格,也有一个能过马车的大门,一个铺着红地毯的宽敞楼梯,还有一个电梯,上下时应该没有噪音。他没有坐电梯,因为公证员的事务所在二楼。双开门上面的两个黄铜把手擦得很亮,就像写着字的牌子一样,请客人不必敲门直接进去。
“如果出现在我面前的又是一个老人……”
他非常吃惊地看到一群办事员中有个漂亮的三十多岁的年轻女人。
“您好。我找奥博内公证员。”
办公室里有点太安静了,有点严肃,但是他们没有让他等着,几乎马上就有人把他带到一个宽敞的房间里。在那里,一个差不多四十五岁的男人站起来迎接他。
“我是麦格雷警长……我来找您是有关您的一个客户,圣伊莱尔伯爵……”
对方微笑着跟他说:
“这样的话就不关我事了。他是我父亲的客户。我去看看这会儿他有没有时间……”
奥博内先生的儿子去了另一个房间,在那里待了一会儿。
“请这边走,麦格雷先生……”
这次警长面对的仍然是一个千真万确的老人,对方身体已经不太好了。老奥博内深深地坐在一个椅背很高的扶手椅里,眼皮不停地眨着,有点像一个刚刚从小憩里被喊醒的男人那般惊慌失措。
“请说话声音大一点……”他儿子出去时建议道。
奥博内公证员原来应该很胖。他还留下一些丰腴,但是身体很软,到处都是皱纹。一只脚穿着皮鞋,另一只脚由于脚踝肿了,穿着一只毡毛拖鞋。
“我猜您来是要跟我谈我那可怜的朋友?”
他说话也很轻柔,说出来的音节如同黏稠的液体。他是用提问的方式开始他们之间谈话的。
“您知道,圣伊莱尔和我是在斯坦尼斯拉斯认识的……有多少年了?请稍等……我今年七十七岁……所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已经认识六十年了……他打算从事外交行业……而我的梦想是成为索米尔军校的骑术教官……那个时代还有一些马……会骑马的人不是自然而然就会骑的……我这一生都没有机会骑马,您知道吗?这一切都是因为我是独生子,要继承父亲的事务所……”
麦格雷没有问他他爸爸以前是不是也住在这栋房子里。
“从读高中以来,圣伊莱尔就是一个活泼的人,但是像他这样的人很少,他对指甲都很讲究……”
“我猜他交过遗嘱给您吧?”
“他的外甥小马泽龙刚才问了我相同的问题。我请他放心……”“是外甥继承他所有的遗产吗?”
“不是所有的。对于这份遗嘱,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是我修改的。”“很久之前改的吗?”
“最后一次修改是十几年前。”
“和之前的遗嘱有什么不一样吗?”
“只是一些细节不同。鉴于所有相关的人都必须在场,我没有告诉他外甥。”
“相关人都有谁呢?”
“大体上讲,阿兰·马泽龙继承了多米尼克街的那栋房子和一些财产,这笔财产数额不是很大。管家雅格特·拉里厄享有一份终身年金,可以保证她安享晚年。至于那些家具、摆设、油画还有私人物品,圣伊莱尔把它们遗赠给一位老朋友……”
“是伊莎贝尔·德v……”
“我看出来您已经知道了。”
“您认识她吗?”
“很熟悉。我和她的丈夫更熟,他是我的顾客。”
知道这两个男人选择同一个公证员麦格雷很吃惊。
“他们不怕在您的事务所碰上吗?”
“这样的事从来没有发生过。他们很有可能没想到这一点,我也想过这会不会让他们很尴尬。您看,他们已经,就算不是朋友,至少也相互尊重,因为他们两个都是守信用的人,另外,也是有风度的人……”
这些话像是从过去冒出来的一样!实际上,麦格雷已经很久没有听到过“守信用的人”这个词了。
坐在椅子里的老公证员产生一个转瞬即逝的想法,偷偷地笑了。
“是的,有风度的人!”他狡黠地重复了一遍,“可以说,他们在某个领域还有相同的品味……现在他们都去世了,我觉得告诉您这个,不算是泄露职业秘密,更何况您应该也是个保守秘密的人……圣伊莱尔是我的老朋友,他会把自己放荡不羁的经历告诉我……将近一年的时间里,他和王子享用同一个情妇,一个漂亮的姑娘,胸部很丰满,在布勒瓦尔街的一家杂志社工作,我忘记是哪家了……他们都不知道……每个人都觉得情妇只属于自己……”
老人用轻佻的眼神看了看麦格雷。
“这两个人懂得生活……我已经很多年都不管事务所的事情了,我的长子代替了我的位置……但是我每天都会下楼去我的办公室,继续帮助老客户……”
“圣伊莱尔有朋友吗?”
“我刚刚跟您说的客户有些就是他的朋友。在这个年纪,我们看着人们一个接一个死去。我想到最后,我是他看望的最后一个人吧。他的腿脚很灵活,每天还去散步。他有时候上来看我,就坐在您现在坐的地方……”
“你们都聊些什么?”
“当然是聊我们那个时代,尤其是在斯坦尼斯拉斯认识的那些人。我现在还能给您讲出大部分人的名字。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从事伟大的职业,很令人惊讶。我们的一个同学,不是最聪明的,已经多次当选委员会主席了,我都记不清多少次了,直到去年才去世。另外一个进了法兰西学院,是将军军衔……”
“圣伊莱尔有敌人吗?”
“他怎么会有敌人呢?在整个职业生涯中,他没有推翻过任何人,现在这种事情太常见了。他的职位都是他耐着性子等到的。他也从来没想过靠回忆录挣钱,所以销量才会那么差……”
“v那一方面呢?”
公证员惊讶地看着他。
“我跟您说过王子了。他当然知道,也知道圣伊莱尔会遵守诺言。如果不是为了全世界,我敢肯定,阿尔芒已经受到瓦雷纳街的接待,并且可能已经成为那里的座上宾。”
“他的儿子也知道吗?”
“绝对知道。”
“他是怎样的人呢?”
“我认为他跟他父亲不是很像。我真的不太了解他。他看上去很爱待在家里,在我们那个时代,取一个像他这样沉重的名字很让人费解。他对上流社会的生活不感兴趣。很少在巴黎看到他。他全年的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诺曼底,和他的妻子、孩子一起照料农场和马……”
“您最近见过他吗?”
“明天会看到他,还有他的母亲,因为要宣布遗嘱,因此,我很有可能要在同一天要处理两起遗产。”
“今天下午王妃没有给您打电话吗?”
“还没有。如果她看了报纸,或者有人告诉了她这个消息,她可能会跟我联系。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有人会杀害我的老朋友。如果这不是发生在他家里,而是在别的地方,我会发誓说凶手肯定认错人了。
“我猜雅格特·拉里厄是他的情妇?”
“不能说是这个词。您要知道,圣伊莱尔从没有跟我谈论过这件事。但是我了解他。雅格特年轻时,我也认识她,她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姑娘。而阿尔芒很少试都不试,就让一个漂亮女孩子从他手边溜走。如果您能明白的话,他这件事情做得很唯美。这是有可能的,而且时机……”
“雅格特没有家人吗?”
“我不认识她的家人。如果她有兄弟姐妹的话,很大可能都已经去世很久了。”
“谢谢您……”
“我猜您很着急?您知道,不管怎样,我都很乐意帮助您。您也像个守信用的人,希望您能抓住那个犯罪的恶棍。”
麦格雷觉得自己深陷在过去,深陷在一个好像已经消失的世界里。他再次回到朝气蓬勃的巴黎街头时,迷路了一般,有些女人穿着紧身裤去买东西,有些酒吧里的家具是镀铜的,有些车在红灯前停下。
他朝雅各布街走去,他没有坐车。他来到商店门口,百叶窗拉了下来,他看到一张黑色框的卡片,上面写着:
因家中有人去世,暂停营业
他按了好几次门铃,没有响应。他走到对面的人行道上看看二楼的窗户。窗户是开着的,但是没有声音。一个黄铜色头发的女人,胸部丰满又柔软,从一个画廊的黑暗处跳了出来。
“您要找马泽龙先生?他不在家。快正午的时候,我看到他把百叶窗关上,然后走了。”
她不知道马泽龙去哪里了。
“这个男人不太平易近人……”
麦格雷当然要去拜访伊莎贝尔·德v,但是想到这次拜访他就心情激动。他希望能往后推推,先多了解些情况。
他很少会对什么人感到这么不知所措。根据《柳叶刀》的专业说法,一个精神病医生,一个教师或者一个小说家,可以更好更直接地了解那些从上个世纪跑出来的人吗?
只有一件事情是确定的:阿尔芒·德·圣伊莱尔伯爵,一个心地善良而温和的老年人,用公证员的话说,一个守信用的人,在他家里,被一个自己信任的人杀害了……
这起无耻的意外犯罪,这起让人摸不着头脑的犯罪是不合情理的。首先什么东西都没有丢,其次第一颗子弹近距离射向他之前,这个前大使正平静地坐在办公桌后面。
也许他自己给来访者开了门,也许那个人有公寓的钥匙。不过雅格特确认说只有两把钥匙,一把是她的,另一把是伯爵自己的。
麦格雷的脑子里充满困惑,他走进一家酒吧,要了一杯啤酒,然后走进电话亭。
“莫尔斯,是您吗?您眼下有物件清单吗?请看一下上面有没有提到一把钥匙……对,是大门的钥匙……怎么样?是吗?在哪里找到的?在他的裤子口袋里?谢谢……还没有进展吗?不,我待会儿就回去……如果您要联系我,请打给让维耶,他在多米尼克街……”
他们在死者的口袋里发现了两把钥匙中的一把,而雅格特拿着她的那一把,当天早上麦格雷和外交部的人跟着她进公寓,是她开的门。
人们不会杀害一动不动的人。盗窃排除了,还剩下什么?老人们之间的情感犯罪?或者是利益纠葛的悲剧?
雅格特·拉里厄得到了一份终身年金,远远超过她所需要的,公证员确信地说。
外甥继承了那栋大楼和他大部分的财产。
至于伊莎贝尔,她的丈夫才刚去世,很难想象她会想到这一点……
不!没有一种解释令人满意,而凯多塞那边,又斩钉截铁地排除了任何政治动机。
“去彭普街!”他对年轻的出租车司机说。
“好的,警长先生!”
他已经很久没有因为被认出来而觉得得意了。门房把他带到六楼,那里有一个小小的棕色头发的女人,非常漂亮。她先微微打开门看了看,然后才请麦格雷进入一个阳光普照的房间。
“请原谅,这里很乱……我正忙着给女儿做裙子……”
她穿着一条黑色丝绸紧身裤,丰满的臀部凸显出来。
“我想您来找我是因为那起杀人案吧,我不知道您想从我这里知道些什么。”
“您的孩子们没有住在这里吗?”
“我的大女儿在英国学英语。她住在一户人家里,通过工作换食宿,小女儿工作了。我在给她……”
她指了指桌上一块轻盈的彩色的布,她正用它来裁剪裙子。
“我猜您已经见过我丈夫了?”
“是的。”
“他反应如何?”
“您有很久没和他碰面了吗?”
“快三年了。”
“那和圣伊莱尔伯爵呢?”
“他最后一次来这里,是圣诞节前几天。他给两个女儿带来了礼物。他从来都不会漏掉礼物。甚至他在国外任职时,那时她们还是小孩子,他都不会忘记圣诞节,给她们寄来一些小东西。所以他们有各个国家的玩偶。您可以在她们的卧室看到。”
她不到四十岁,看上去相当迷人。
“报纸上写的是真的吗?他被暗杀了?”
“请跟我说说您的丈夫。”
她的脸马上黯淡下来。
“您想让我跟您说什么?”
“你们是因为爱而结婚的吗?如果我没有搞错,他比您大很多。”
“只比我大十岁。他从来没像过年轻人。”
“您爱过他吗?”
“我不知道。我和爸爸相依为命,他是一个尖酸刻薄的人。他觉得自己是一个被埋没了的伟大艺术家,却要靠修画为生。我在林荫大道街的一家超市上班。后来遇到了阿兰。您口渴吗?”
“谢谢。我刚刚喝了一杯啤酒。请继续……”
“或许是他那神秘的表情吸引了我。他不像其他人,他很少讲话,但说的话都很有意思。我们结婚了,很快就有了一个女儿……”
“你们住在雅各布街吗?”
“是的,我喜欢那条街,也喜欢我们二楼的小公寓。那个时候,如果我没记错,圣伊莱尔伯爵还是驻华盛顿大使。他有一次休假,来看我们,然后在圣多米尼克街接待了我们。我对他的印象很深刻。”
“他和您丈夫的关系怎么样?”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他对所有人都表现得很友好。他知道我是他外甥的妻子时,看上去很吃惊。”
“为什么?”
“很久之后我才搞明白,但还不是很确定。他应该比我想象的更了解阿兰,不管怎样,在那个时候,比我更……”
她停下了,好像在担心刚刚说过的话。
“我不想给您一种印象,我是因为现在跟丈夫分开了,怨恨他才这么说的。再说了,是我选择离开的。”
“他没有尽量挽留您吗?”
这里的家具都很现代化,墙壁很明亮。他瞥了一眼白色的厨房,井井有条。一些习以为常的噪声从街上传来,而近处的布洛涅森林的绿色铺排开来。
“我猜想您不是怀疑阿兰吧?”
“坦白说,我还没有怀疑任何人,但是我也不会漏掉任何猜测。”“我确定您走错方向了。在我看来,阿兰是一个不幸福的人,他以前从来都没有适应,也永远都不会适应生活。我离开爸爸是因为他是一个尖酸刻薄的人,可是我又嫁给了一个比他更加尖酸刻薄的人,这不让人感到惊讶吗?久而久之,我意识到了这一点。总之,我从来没有看到他满意过,我在想他有没有笑过。
“他什么都担心,担心身体、生意,担心别人怎么看他,担心邻居和客人的目光……他觉得,所有的人,恨他。
“这很难解释。请不要嘲笑我下面要跟您说的话。我跟他生活在一起时,总是觉得可以听到他从早到晚想着一个令他烦恼的想法,就像闹钟的滴答声一样。他静静地走来走去,突然间看着我,仿佛一直能看到我的内心深处,我不可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他还是面容惨白吗?”
“是的,惨白。”
“我遇到他时他就已经这样了,在乡下是这样,在海边是这样。好像是人造的惨白……
“看上去没什么。但和他没办法交流……那么多年,我们睡在一张床上,有时候我醒来看着他,感觉他就像个陌生人。
“他很残酷……”
她试图纠正这个词。
“我或许有点夸张了。他觉得自己很公正,尽全力显得很公正。这是一种怪癖。他对琐事很公正,这就是我提到残酷这个词的原因。我们有了孩子以后,我发现了这一点。他用看我和其他人的眼神看她们,一种赤裸裸的冷漠。如果她们做了一件小蠢事,我会尽力地维护她们。
“‘阿兰,在她们这个年纪……’
“‘没有任何理由让她们养成弄虚作假的习惯。’
“这是他最喜欢用的一个词。弄虚作假!小小的弄虚作假!小小的弄虚作假!
“他把这种不妥协带到日常生活的琐碎小事里。
“‘你为什么买鱼?’
“我试图去解释……
“‘我说的是牛肉。’
“‘我买东西时……’
“他固执地重复道:‘我说的是牛肉,你不能买鱼肉。’”
她再次住口。
“我是不是说的太多了?我没有说什么蠢话吧?”
“请继续。”
“我说完了。几年以后,我明白了美国人所谓的精神上的残忍是什么意思,也明白了为什么在美国这会成为导致离婚的一个原因。有些教师不用提高嗓门,就可以让教室里笼罩着一种恐惧。
“和阿兰在一起,两个女儿和我都快要窒息了,就算看到他离开家去办公室也不会觉得有一丝放松。他就在下面,在我们脚下,从早到晚,每天要上来十次,用冰冷的眼神注意着我们的一举一动。
“我做什么都要跟他汇报。我出门时,他必须知道我的行程,然后质问我都跟哪些人说话,说了什么,以及别人是怎么回答我的……”
“您骗过他吗?”
她没有生气。在麦格雷看来,她还试图微笑,带着一种满意,甚至是某种贪婪,但她控制住了。
“您为什么问我这个?他跟您谈论过我吗?”
“没有。”
“我跟他生活在一起时,没有做过值得他指责的事情。”
“是谁使您决定离开的?”
“我受不了了。我快要喘不过气来了,我跟您说,我也想让两个女儿在一种更宽松的氛围里成长。”
“没有什么私人的原因,促使您投奔自由吗?”
“或许有。”
“您的两个女儿知道吗?”
“我没有向她们隐瞒我有一个朋友,她们也很支持我。”
“他跟你们住在一起吗?”
“我去他家里见他。他和妻子离婚了,和我年纪差不多,他跟他妻子在一起,不比我和我丈夫在一起幸福,我们好像刚好互补。”
“他住在这个街区吗?”
“也在这栋楼里,比我们低两层。他是医生。您可以看到他门上挂的牌子。如果有一天阿兰同意离婚,我打算结婚,但是我怀疑这件事不会发生。他非常笃信天主教,但这更像是传统,而非信仰。”
“您的丈夫生活很宽裕吗?”
“时好时坏吧。我离开他时,他给我了一笔微薄的津贴,是给孩子们的,这是应该的。接下来的几个月,他都履行了承诺。后来就推迟了。最后,他什么都不给了,借口说她们都已经长大了,可以养活自己了。但这件事不至于把他变成杀人凶手,不是吗?”
“您知道他舅舅的情妇吗?”
“您是说伊莎贝尔吗?”
“您知道v王子星期天上午去世了吗,今天下葬?”
“我在报纸上看到了。”
“您觉得,如果圣伊莱尔还活着,会娶王妃吗?”
“肯定会。他一生都希望他们有一天可以结婚。他谈论伊莎贝尔就像谈论陌生人,就像谈论几乎超自然的生物,我很感动。但是这个男人接受现实,有时候有点太……”
这一次,她很坦诚地笑了出来。
“很久以前的一天,我去见他,不记得是为了什么了,我一直想挣脱他的手,但是很难。他没有感到很尴尬。在他眼里,这很正常……”
“您丈夫知道吗?”
她耸了耸肩膀。
“当然不知道。”
“他嫉妒吗?”
“按照他自己的方式嫉妒。我们很少联系,您应该明白的意思,这种联系很冷淡,甚至是机械的。他指责的不是我被另外一个男人吸引,而是我犯了一个错误,一个原罪,一种背叛,他认为这种行为是不干净的。如果我说的太多了像是指责他的话,请原谅我,事实并非如此。您发现了,我并没有把自己变得比过去更好。我很久都没有过做女人的感觉了,我利用……”
她的嘴唇肉肉的,眼睛里泛着光。连续几分钟,她的两腿不停地交叉又放下来。
“您真的不想喝点东西吗?”
“再次感谢您。我该走了。”
“我想这些只有我们两个知道吧?”
麦格雷冲她笑了笑,朝门口走去。在门口,她向麦格雷伸出胖乎乎的温暖的手。
“我继续缝制我女儿的裙子。”她小声说,像很勉强一样。
就这样,他还是超脱了老人圈子一会儿。离开彭普街的公寓以后,他又回到街上,听着街上的声音,闻着街上的气味,一点都不感到惊讶。
他很快就拦到一辆出租车去多米尼克街。在走进那栋大楼之前,他还先去喝了一杯啤酒,在马泽龙夫人家里,他拒绝喝东西。在酒吧里,他和一些部委及大出版社的司机擦肩而过。
那个记者还待在原来的地方。
“您看到了,我并没有跟踪您。您可不可以告诉我您去见谁了?”
“那个公证员。”
“他告诉您新消息了吗?”
“没有。”
“还没有线索吗?”
“没有。”
“您确定这不是一起政治案件吗?”
“好像不是。”
那个穿制服的警员也在那里。麦格雷在电梯房旁边敲了敲门。让维耶来给他开门,没有穿西装,雅格特没有在办公室。
“你对她做了什么?你让她出去了?”
“没有。她接了一个电话以后就想出去,硬说家里面没什么吃的了。”
“她现在在哪里?”
“在她的房间里。她在休息。”
“你说的是什么电话?”
“您走了半个小时后,电话响了,是我接的。在电话那端,我听到一个女人的声音,很虚弱的声音。
“‘请问是哪位?’她在电话那头问道。
“我没有回答,反问道:
“‘您是哪位?’
“‘我想找一下拉里厄小姐。’
“‘您是谁?’
“她沉默了一阵,然后说:‘我是v王妃。’
“正在这时,雅格特看着我,好像知道是谁打来的。
“‘我把电话给她。’
“我把听筒递给她,她马上就说:
“‘是我,王妃夫人……是的……我很想去,但是这些先生不允许我出门……公寓里有很多警察,带着各种仪器……他们已经连续问了我几个小时问题,就连现在还有一位探员在听我说话……’”
让维耶补充说:
“她好像很看不起我。然后,她又听电话。
“‘是……是,王妃夫人……是……我明白了……我不知道……不……是……我试试看……我也很想……谢谢,王妃夫人……’”
“她后来说什么了?”
“什么都没说。她重新坐到椅子上。沉默了一刻钟之后,她勉强小声说:
“‘我想您不会让我出去的吧?就算家里没有任何吃的了,就算我到现在还没吃饭?’
“‘待会儿会有人处理这个问题的。’
“‘就算这样,我觉得我们两个这样面对面待着也没事可做,我想去休息。你允许吗?’
“自那以后到现在,她都待在房间里。把门从里面反锁了。”
“没有任何人来吗?”
“没有。有几通电话,一通是美国一家通讯社打来的,还有几通是外省的几家报纸打来的……”
“你从雅格特身上什么都没问出来?”
“我问了她几个几乎没有恶意的问题,希望能取得她的信任。她只是用一种讥讽的口吻说:‘年轻人,不要班门弄斧了。如果您的老板知道我跟您说悄悄话……’”
“外交部没有打电话来吗?”
“没有。只有预审法官打来过。”
“他想见我吗?”
“他说您有进展的话要给他打电话。他已经见过阿兰·马泽龙了。”
“你没有说吧?”
“我一直保密到最后。后来这个外甥自己发现了,抱怨说您没有经过他的允许就看了圣伊莱尔的私人信件。他以遗嘱执行人的身份,要求查封公寓,直到宣读遗嘱为止。”
“法官怎么回复他?”
“让他找您。”
“马泽龙没有再回来吗?”
“没有。或许还在路上,因为我刚刚接到这通电话。您认为他会回来吗?”
麦格雷犹豫一会儿,最后从他那里拿过一个电话号码簿,找到要找的那个电话,然后站着,表情很凝重,拨通电话。
“您好,是v王子的宾馆吗?我想找一下v王妃……我是司法警察局的麦格雷警长……好的,我等着……”
房间里有一种不同寻常的寂静,让维耶屏住呼吸看着老板。几分钟过去了。
“不,我没有离开……谢谢……喂……是的,夫人,我是麦格雷警长……”
这不是他平常的声音,他感觉到了一种情感,就像小时候跟圣菲亚克尔伯爵夫人说话时一样。
“我在想或许您想我主动联系您,不是为了告诉您一些细节……是的……是的……等您愿意时……那么我一个小时之后会出现在瓦雷纳街……”
这两个男人静静地看着对方。麦格雷最后叹了一口气。
“你最好留在这里,”他最后说,“打电话给卢卡,让他给你派个人,最好是托伦斯。那个老女人想走就让她走,但你们两个人中要有一个人跟着她。”
他还有一个小时。为了恢复耐心,他从挂着绿色窗帘的图书室里拿出一个信盒。
“昨天,在隆尚,在雅格特身上,我感觉到了您,您由此可知我有多么爱您了。您怀里抱着一个红棕色头发的漂亮女孩子,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