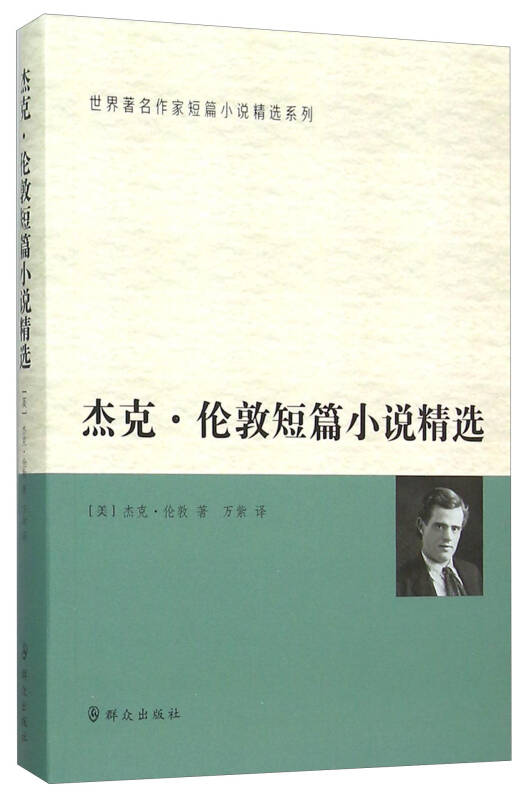麦格雷没想到会找到一家闻上去仍然有着丧礼气味的房子,那种气味和收入微薄的家庭甚至小资产阶级家庭举办丧礼时的气味一样。
“喝这个,卡特琳,”在去教堂和墓地之前,会有人这样对寡妇说,“你需要鼓起勇气。”
她边哭边喝。男人们在外面喝酒,然后又回到屋子里。
也许上午银色的纱幔装饰过门廊,但应该很早之前就被取下来了,前院已经恢复到和往常一样,一半阴暗,一半阳光,一个穿制服的司机在清洗一辆黑色长车,有三辆车停在台阶下面,其中一辆是大越野,车身是黄色的。
这栋房子和爱丽舍宫一样宽敞,麦格雷这才想起来这里就是v宾馆,是经常举行舞会和慈善拍卖会的地方。
他走上台阶,推开那扇玻璃门,独自站在一个铺着大理石的大厅里。几扇双开门在他左右两侧敞开着。他透过门看到豪华的客厅,那里陈列的东西,很可能就是别人跟他说过的古钱币和鼻烟盒,和博物馆里的一样。
他应不应该走向其中一扇门,登上通向二楼的两段楼梯呢?他犹豫了,这时宾馆的一个侍者不知从哪里出来,悄悄走近他,拿过他手中的帽子,没有问他的名字就小声说道:
“这边请。”
麦格雷跟着向导走上楼梯,来到二楼,穿过另一个客厅是一个长长的房间,应该是画室。
他没有等很久。侍者微微打开一扇门,悄声说:
“麦格雷警长来了。”
他穿过的那个漂亮的小客厅不是面向前院的,而是面向一个花园。几棵树上都有小鸟,枝叶擦过那两扇开着的窗户。
有个人从椅子上站起来,他过了一会儿才明白,她就是那个自己要见的人,伊莎贝尔王妃。他的惊讶应该是太明显了,因为王妃边走向他边说:
“您觉得我会是另外一个样子,是不是?”
他不敢回答是。他没有说话,很惊讶。首先,即使她穿着黑色衣服,也不像是在服丧,他说不上来这是为什么。她的眼睛不红。看上去没有被击垮。
她比照片上矮一些,但是,譬如说跟雅格特比较,她并没有因为岁月而衰老。他没有时间分析她的容貌。晚些时候再说。现在,他开始下意识地录音。
让他最吃惊的是,他看到的是一个矮胖的女人,脸颊鼓鼓的,很光滑,身上胖乎乎。在圣伊莱尔卧室里的那张照片上,一身王妃裙勉勉强强勾勒出她的髋部,而现在,她的髋部变得跟一个护士的髋部一样大了。
他们身处其中的这间漂亮的小客厅,是不是她最常待的地方呢?墙上挂着老旧的壁毯。地板闪闪发光,每一件家具都摆放得井井有条,麦格雷莫名地想起他以前拜访过的一位当修女的姑妈的修道院。
“请坐。”
她指了指一个镀金扶手椅,跟这把扶手椅比起来,他更喜欢普通的椅子,他害怕使脆弱的椅腿发出断裂的声音。
“我首先想到的是去那里,”王妃边坐下边向他坦白,“但是我已经知道他不在了。他的尸体被带到尸体解剖处了,是吗?”
她没有因为别人提到的那些词和画面感到害怕。她的面庞很安详,几乎带着微笑,这也使麦格雷想起修道院,想起那些修女特有的安详,她们看上去从来没有过过自己的生活。
“我坚持再见他最后一次。这一点我待会儿再跟您说。我现在首先想知道他有没有很痛苦。请坦白告诉我。”
“请放心,夫人。圣伊莱尔伯爵是被一枪毙命的。”
“是在办公室里吗?”
“是的。”
“坐着?”
“是的。他当时似乎正在修改校样。”
她闭上眼睛,好像是在给这幅画面一点时间出现在她的脑海里,麦格雷鼓起勇气,开始提问。
“您去过圣多米尼克街吗?”
“只去过一次,很久之前,在雅格特的帮助下。我选了一个确定他不在的时间。想要看一下他的生活环境,想象他在不同的房间里。”
她想起一件事。
“这么说,您还没有看那些信?”
他犹豫了一下,决定承认事实。
“我看了,但不是所有的……”
“它们放在那个镀金铁丝网图书室里吗?”
他点点头。
“我料到您已经看了。我不怪您。我知道这是您的工作。”
“您是怎么知道他去世了的?”
“通过我的儿媳。我儿子菲利普和妻儿从诺曼底来参加葬礼。刚才,从墓地里回来以后,我的儿媳就看起了一份仆人们经常放在桌子上的报纸。”
“您的儿媳知道吗?”
她看着他,流露出一种近乎天真的惊讶。如果她不是王妃,麦格雷会以为她可能在演戏。
“知道什么?”
“您和伯爵的关系。”
她的笑容也是修女的笑容。
“当然。她怎么可能不知道呢?我们从来都不遮遮掩掩。我们之间没什么龌龊。阿尔芒是我很亲密的朋友……”
“您的儿子认识他吗?”
“我的儿子也是什么都知道。他还是孩子时,我有时候就会从远处把阿尔芒指给他看。我想第一次是在奥特伊……”
“您的儿子从来没有去看过他?”
她很有逻辑地回答,她总是很有逻辑:
“去干什么啊?”
鸟儿们在树上嬉戏鸣叫,一阵令人舒服的清凉从花园里传来。
“您想来杯茶吗?”
住在帕斯街的阿兰·马泽龙的妻子请他喝啤酒。在这里,王妃请他喝茶。
“不用了。谢谢。”
“麦格雷先生,请告诉我您所知道的一切。您看,五十年来,我已经习惯想象和他生活在一起。他还是大使时,我去过他生活的城市,我跟雅格特达成协议,可以去他住的房子里看一眼。他是什么时候去世的?”
“据我们所知,在夜里十一点到十二点之间。”
“他还没有准备睡觉。”
“您怎么知道?”
“因为在回卧室之前,他总是会给我写几个词以结束他每天写给我的信。他每天上午都会用相同的开头开始写信:‘你好,伊西……’
“好像如果命运允许我们俩生活在一起,他醒来时就能看到我一样。然后白天他继续写,在信中告诉我他都做了些什么。到了晚上,他的最后几个词也是不变的:‘晚安,美丽的伊西……’”
她困惑地笑了笑。
“真不好意思,我一直重复那个让您发笑的词。对他来说,我还一直是那个二十岁的伊莎贝尔。”
“他后来见过您。”
“是的,从远处。所以他知道我已经变成一个老女人了,但是,对他来说,现在没有过去感觉真实。您能明白吗?我也不明白。他没有变。现在请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请告诉我一切,不要试图照顾我的感受。您知道,一个人活到我这个年纪,是很坚强的。凶手进来了。是谁?怎么杀死他的?”
“有人进到寓所里,我们在办公室和寓所里没有找到任何武器。雅格特确定她快九点钟时就把门锁上了,和每天一样,插上插销和锁链,所以我们只得相信是圣伊莱尔伯爵自己打开门迎接来访者的。您知道他有晚上会见客人的习惯吗?”
“从来没有。他退休以后变得墨守成规,他的时间安排基本上是固定的。我可以给您看看他最近几年写的信……您会发现信的第一句话总是:
你好,伊西。跟每天早晨一样,我跟你说早上好,因为新的一天开始了,而我,也要开始我单调的一天了……
“他是这样称呼他那设定好的日子的,容不下任何意外的人或事。
“至少我收到了昨天晚上的信……不!每天早上,都是雅格特去买牛角面包时把信寄出来的。如果今天她已经寄了信,她会打电话跟我说的……”
“您觉得她怎么样?”
“她对阿尔芒和我很忠心。阿尔芒在瑞士摔断胳膊时,雅格特写下他口述的信。后来他做手术时,也是她每天写信告诉我情况。”
“您不觉得她嫉妒您吗?”
她又笑了,这种笑让麦格雷难以适应。她那么镇定、安详,使他很吃惊,尽管他料想到这次会面或多或少会有些戏剧性。
这里的死亡和其他地方的死亡似乎意义不一样,伊莎贝尔毫无障碍地生活着,一点都不害怕,好像这是人生中一个正常的阶段。
“她是有些嫉妒,但就像狗嫉妒自己的主人。”
他犹豫着要不要再提一些问题,要不要再聊某些话题,是她用一种让人无法生气的简洁方式把这些问题和话题摆在桌面上的。
“如果说她之前有过另一种嫉妒,那是对他的其他情人,而不是对我。”
“您觉得她也是他的一个情人吗?”
“肯定是。”
“他在信中跟您提到过?”
“他对我毫无隐瞒,甚至是男人犹豫要不要跟妻子坦白的那种可耻的事情。譬如,几年前,他在给我写的信中提到:‘……今天,雅格特很烦躁。今天晚上,我想我应该让她高兴一下……’”
她像是在捉弄满脸吃惊的麦格雷。
“您很惊讶吗?但是这很正常啊!”
“您也不嫉妒吗?”
“关于这一点,不嫉妒。我唯一害怕的是,他遇到一个足以取代我在他心目中地位的女人。警长,请继续跟我说。那么你们对于这个来访者一无所知?”
“除了他用的是一把大口径手枪,很有可能是一把七点六五毫米口径的自动手枪。”
“击中了阿尔芒的哪个部位?”
“头部。法医断定说他当场毙命。他滑到椅脚旁边的地毯上。后来凶手又开了三枪。”
“既然他已经死了,为什么还要开枪?”
“我们也不知道。凶手惊慌失措?狂怒到失去理智?很难马上回答这些问题。在重罪法庭上,人们经常指控屡次伤害受害人的残暴凶手,譬如多次用刀捅受害人。但是根据我的经验以及我同事的经验,会这么做的几乎都是害羞胆小的人——我不敢说是敏感的人。他们惊慌,拒绝看到受害人痛苦,失去了理智……”
“您认为这件事也是这样吗?”
“除非涉及报复或者一种由来已久的仇恨,但这种情况很少见。”
他开始在这位夫人面前感到放松,这个女人什么都讲,又什么都听得进去。
“但与这种推断矛盾的是,接下来凶手又想到把弹壳捡起来。这些弹壳应该散落在房间里,弹壳与弹壳之间离得很远。他一个都没忘,也没有忘记不留下一丝指纹。听了您跟我说了你们和雅格特的关系之后,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那天早上,雅格特发现尸体以后,似乎没有想到跟您打电话,也没有去警察局,而是去了外交部。”
“我想关于这一点,我可以跟您解释一下。我丈夫一过世,电话几乎不停地响。一些我们几乎不认识的人想要知道关于葬礼的信息,或者是想要对我表示安慰。我的儿子很生气,就决定把电话线拔了。”
“所以,或许雅格特尝试过给您打电话?”
“很有可能。另外她之所以没有亲自来通知我,是因为她知道葬礼这天会很难接近我。”
“您不认识圣伊莱尔伯爵的敌人吗?”
“一个都不认识。”
“在给您的信里,他提到过外甥吗?”
“您见过阿兰了?”
“今天上午见的。”
“他说什么?”
“什么都没说。他去见了奥博内先生。明天就要宣读遗嘱了,公证人应该会联系您的,因为您必须到场。”
“我知道。”
“您知道遗嘱的内容吗?”
“阿尔芒坚持要把家具和私人物品留给我,目的是如果他比我先去世,我还可以有点做过他妻子的感觉。”
“您接受这份遗赠吗?”
“这是他的意愿,不是吗?我的遗愿也是这样。如果他没有去世,丧期一结束,我就会成为圣伊莱尔伯爵夫人。这是我们早就约定好的。”
“您的丈夫知道这个计划吗?”
“当然知道。”
“您的儿子和儿媳也知道吗?”
“不仅是他们,我们的朋友也都知道。我再重复一遍,我们没有什么好隐瞒的。现在,由于我要继续保留的那个名字,我不得不生活在这栋大房子里,不能像我梦寐以求的那样,搬到圣多米尼克街。阿尔芒的房子不会比这里差。我可能不会活很长时间了,尽管这样,我还是想住在他家里,您懂的,就像他的遗孀一样。”
麦格雷产生了一种自己很不适应的感觉。他几乎被这个和他见过的所有女人都不一样的女人征服了。不仅仅是被她,也被她和圣伊莱尔创造并且一起经历的传奇征服了。
乍一看,这就像一个童话故事或者动人的爱情故事一样荒唐。
在这里,在她面前,他突然发现自己相信了。他有了他们看和感知的方式,有点像在他姑妈的修道院里,他踮着脚尖走路,低声说话,满怀虔敬和恭敬。
接下来,他突然用另一种目光看着这个女人,巴黎警察总署警员的眼光,他非常愤慨。
他们是不是在耍他啊?这些人,包括雅格特、阿兰·马泽龙、他穿着紧身裤的妻子、伊莎贝尔,还有公证员奥博内,他们是不是都没有说实话?
有一个死人,一具如假包换的尸体,头颅大开,腹部大开。这表明这个杀人凶手不是第一次进到前大使家的混蛋,然后近距离地杀害他,而大使自己没有怀疑他,也没有反抗。
多年以来,麦格雷明白,一个人没有动机,没有一个足够强的动机,是不会杀人的。就算凶手是疯子,但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是生活在受害者周边的人。
总带着点侵略性怀疑的雅格特是不是疯了?那个被妻子指控有精神暴力倾向的马泽龙是不是疯了?伊莎贝尔是不是失去理智了?
每一次他这么想时,都准备好了要改变态度,提出一些残酷的问题,为了使这种会传染的温柔溶解。
而每一次,王妃一个吃惊或天真的眼神,或者狡黠的眼神,都会使他心软,使他羞愧。
“总之,您想不到任何人会想杀死圣伊莱尔吗?”
“肯定没有。您和我一样清楚遗嘱的大致内容。”
“如果是阿兰·马泽龙需要钱呢?”
“如果他需要钱,他舅舅会给他钱,不管怎样,他原本就打算把财产留给外甥。”
“马泽龙知道吗?”
“应该知道。我的丈夫死了,阿尔芒和我会结婚,这是真的,但是我没有同意我的家人继承他的遗产。”
“雅格特呢?”
“她不知道自己以后的日子得到了保障。”
“她也不知道您想要去圣多米尼克街生活?”
“她知道,并且为此感到很高兴。”
麦格雷身上有种东西在抗拒着。所有这些都是假的,讲不通。
“您的儿子呢?”
她很惊讶,等着麦格雷说出具体的想法。见麦格雷不再说话,她反问道:
“我儿子跟这件事情有什么关系?”
“我不知道。我在查。他今后是家族的继承人。”
“就算阿尔芒活着,他也还是继承人。”
当然!但是,他不会觉得妈妈再嫁圣伊莱尔是一种委屈下嫁吗?
“昨天晚上,您儿子在这里吗?”
“没有。他跟妻儿下榻在旺多姆广场的一家宾馆,他们来巴黎时习惯住在那里。”
麦格雷皱皱眉,看看墙壁,好像是在通过墙壁估量瓦雷纳街这栋大楼的面积。难道没有好多空房间吗?没有空余的套房吗?
“您是想说,自从他结婚以来,就再也没有在这里住过吗?”
“首先,他很少来巴黎,来了也不会待很久,因为他恐惧上流社会的生活。”
“他的妻子也这样?”
“是的。他们刚结婚时家里有他们的公寓。然后他们有了孩子,一个,两个,三个……”
“他们有几个孩子?”
“六个。最大的二十岁,最小的七岁。我可能会使您感到反感,但是我没法跟孩子生活在一起。认为所有女人生来都是做妈妈的这种说法是错的。我生了菲利普,因为那是我的义务。我按照我应该做的那样去照顾他。几年以后,一听到房子里的哭声和跑来跑去的声音,我就会受不了。我的儿子知道这一点。他妻子也知道。”
“他们不怨您吗?”
“他们接受真实的我,接受我的错误和荒谬。”
“昨天晚上您一个人在家吗?”
“和仆人们一起,还有两个修女,她们是来停尸房里守夜的。戈热神父,我的思想导师和老朋友,一直待到十点钟。”
“您刚才跟我说您的儿子和儿媳现在在家。”
“他们等着跟我道别,至少是儿媳和孩子们在等着和我们道别。您应该已经看到他们的车在院子里了。他们要回诺曼底,只有我的儿子不回去,他明天要陪我去公证员家。”
“您允许我跟您的儿子简短见一面吗?”
“为什么不可以呢?我料到您会提出这个要求。我原以为您会想要见见他们一家人,所以我要求儿媳推迟出发时间。”
就这么简单吗?抑或这是一个挑战?麦格雷又想到那个英国医生的理论:一个老师可以比麦格雷更直接地分辨出真相吗?
在这些人面前,他尽力做出警察的样子,但却比从前更谦卑、更心软。
“这边请。”
她领着他穿过画廊,一只手在一个门把手上停了一会儿,门后面传来一些声音。
她打开门,简单地说道:
“这是麦格雷警长……”
在宽敞的房间里,警长首先看到一个男孩子在吃蛋糕,然后是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女孩正低声向妈妈求某样东西。
妈妈是一个高大的金黄色头发女人,四十多岁,皮肤很粉嫩,让人想起彩色画或者明信片里健壮的荷兰女人。
一个十三岁的男孩子趴在窗户上往外看。王妃刚才讲了很多,麦格雷正在一片一片地保存着这些画面,不久之后就可以把它们像一个拼图一样拼好了。
“这是弗雷德里克,老大……”
这是个年轻的高个子男人,和他妈妈一样,有着金黄色的头发。他轻轻地斜一下身子,没有伸出手来。
“他也想从事外交行业。”
还有一个十五岁的女儿和一个十二三岁的男孩子。
“菲利普没在这里吗?”
“他下楼去看看车子准备好了没有。”
生活好像暂停了,就像在火车站的候车厅里。
“请走这边,麦格雷先生。”
他们沿着另外一条走廊走到尽头时,碰到一个高大的男人,此人厌烦地看着他们走来。
“菲利普,我在找您。麦格雷警长想跟您简单谈谈。您想在哪里接待他?”
菲利普伸出手,似乎有点心不在焉,但这么近地看到一位警察,他又很好奇。
“哪里都行。就这里吧。”
他推开一扇门,那是一间挂着红色纱幔的办公室,墙上挂着一些逝去长辈的画像。
“我走了,麦格雷先生。恳请您有什么进展一定通知我。等他的遗体送到圣多米尼克街,请告诉我一声。”
她消失了,轻轻的,好像没存在过一般。
这间办公室是谁的?很有可能谁的都不是,因为没有任何东西能表明有人曾经在这里工作过。菲利普·德v指着一个座位,然后递给麦格雷一盒烟。
“不用了,谢谢。”
“您不抽烟吗?”
“只抽烟斗。”
“我通常也是。但是在这栋房子里不行。我妈妈害怕那个。”
他的声音里有一种厌倦,或者不耐烦。
“我猜您是想跟我聊聊圣伊莱尔?”
“您知道他昨天夜里被杀害了吗?”
“我夫人刚才告诉我了。承认吧,这是一个奇怪的巧合。”
“您是想说他的死可能和您父亲的死有关系吗?”
“我不知道。关于死因,报纸上只字未提。我猜不可能是自杀吧?”
“您为什么这么问?伯爵有理由自杀吗?”
“我不知道,我们无法知道别人脑子里在想些什么。”
“您认识他吗?”
“我还是孩子时,妈妈把他指给我看过。后来我自己也碰到过他。”
“你们说过话吗?”
“从来没有。”
“您怨恨他吗?”
“我为什么要恨他?”
他看上去对麦格雷这些问题也由衷地感到吃惊。他看上去也像个守信用的男人,没有隐瞒什么。
“我母亲一生都对他抱有一种神秘的爱,对此,我们并不生气。此外,我父亲是第一个采取同情态度、并置之一笑的人。”
“您什么时候从诺曼底来到巴黎的?”
“星期天下午。上周父亲发生事故以后,我一个人来过,然后又走了,因为他那几天看上去没有生命危险。星期日母亲打电话告诉我他因尿毒症发作去世时,我很吃惊。”
“您和家人一起来的吗?”
“不是。我夫人和孩子是周一到的。当然了,老大除外,他是师范学院的寄宿生。”
“您妈妈跟您说起过圣伊莱尔吗?”
“您想说什么?”
“我的问题也许很可笑。她有没有在某个特定的时刻跟您说过她会嫁给伯爵?”
“她不需要跟我说这个。我很早以前就知道了,如果我父亲比她先去世,他们就会结婚。”
“您从来没有参加过您父亲的社交活动吗?”
这个问题好像突然击中了他,他想了想才回答。
“我想我明白您的想法了。您在杂志上看到过我父亲和母亲的照片,也许是在某个国家的宫廷里,也许是在王室的一场盛大婚礼或订婚仪式上。当然,我十八岁到二十五岁之间参加过一些这样的活动。我说的是大概二十五岁时。后来,我结婚了,住在乡下。我母亲有没有跟您说过我是在格里尼翁农业学校毕业的?父亲把他在诺曼底的一处房产给了我,我就和家人生活在那里。您是想知道这个吗?”
“您没有任何怀疑吗?”
“圣伊莱尔被杀这件事吗?”
麦格雷觉得对方的嘴唇稍稍颤抖了一下,但是他不敢确定。
“不,不能说有怀疑。”
“但是您还是想到了什么吧?”
“想法还不成熟,我宁愿不跟您说。”
“您有没有想到一个人,他的生活可能会因为您父亲的死而改变?”
菲利普·德v抬起眼睛,之前他的眼睛低下了一会儿。
“我承认想到过这一点,但是我不能停在这个想法里。我听说很多关于雅格特和她的忠诚……”
他看上去对这场谈话很不满意。
“我不想给您添麻烦。但是我得跟家人道别,我希望他们能在深夜之前到家。”
“您会在巴黎待上几天吗?”
“待到明天晚上。”
“您住在旺多姆广场?”
“我母亲告诉您的?”
“是的。职责所在,我再问您最后一个问题,请您不要感到不安。我也不得已问了您母亲同样的问题。”
“我猜是问我昨天晚上在哪里吧?几点钟啊?”
“晚上十点到十二点。”
“这段时间可不短。让我想一下!我在和母亲吃饭。”
“您一个人和她一起吗?”
“是的。我快九点半时离开的,那时戈热神父来了,我不太喜欢他。我回到宾馆,回到我夫人和孩子身边。”
一阵沉默。菲利普·德v直直地看着前方,犹豫着,表情很窘迫。
“后来我好像又去香榭丽舍大道……”
“直到午夜吗?”
“不是。”
这一次,他看着对面的麦格雷,流露出一种羞愧的微笑。
“鉴于我最近的服丧,在您看来这可能很奇怪。这是我的一个习惯。在日内斯杜,我的知名度太高了,我不允许自己冒一点点险,我甚至都没有想到这个念头。是因为我年轻时期的记忆吗?我每次到巴黎,都习惯和一个年轻女人一起度过一两个小时。但我坚信这件事情不属于明天,坚持认为我的生活不会因此变得复杂,我只是……”
他做了一个空荡荡的动作。
“她住在香榭丽舍大道吗?”麦格雷问道。
“我没有告诉过我太太这件事情,她不会明白的。对她而言,超脱某个世界之外……”
“您太太结婚前叫什么名字?”
“伊雷娜·德马尔尚日……如果这对您有用的话,我可以详细告诉您,昨天晚上陪我的是一个棕色头发女人,不是很高,穿着一件浅绿色的裙子,胸下面有一颗美人痣。我想是左边吧,不确定了。”
“您去她家了吗?”
“她把我带到了贝里街的一家宾馆,我猜她住在那里,因为衣橱里有很多衣服,浴室里也有很多私人物品。”
麦格雷笑了笑。
“很抱歉耽误您这么久,很感谢您的耐心。”
“我这里您放心了吗?请这边走!我得让您一个人走下楼梯了,因为我急着……”
菲利普看了看手表,伸出手来。
“祝您好运!”
在前院里,司机正在一辆长型轿车旁边等着,车子的发动机已经启动,发出几乎难以察觉的轰鸣声。
五分钟后,麦格雷已经完全沉浸在一家酒吧厚重的气氛里,他点了一杯啤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