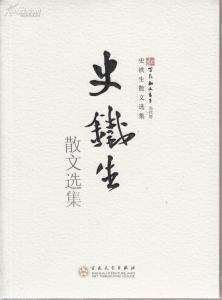第八部分
只过了三天,是十六日的中午,太陽红得像个油盆子,男人们都还在地里干活,突然村里冒了烟。这烟先如龙一样翻滚,后来一刮风,半空里就盖了一面黑布。白河说:这谁家的瞎婆娘烧啥哩?便传来拴劳媳妇尖锥锥的喊着房着火房着火了!拴劳的媳妇早晨起来捅一只鸡的屁股,发觉有软蛋的,可中午了到鸡窝去看却没有蛋,再抓了鸡捅屁股, 里边的蛋也没了,就在巷里骂是谁把她家的鸡引去下了蛋。骂着骂着,闻到呛味,扭头一看,邢轱辘家起了火,火苗子从后窗冒出来,像一堆胳膊在招摇,赶紧叫邢 轱辘,叫不应,到前门去叫,前门锁着,才跑到村口喊起来了。地里人听到喊声,都往村里跑,跑得最快的是邢轱辘东隔壁的龚仁有,龚仁有一到家,邢轱辘家的火 已经烧到房顶,他忙把被子褥子在尿窖子里蘸湿了,搭梯子就苫在自家的檐头。而随后来的人要救火,屋顶上的瓦咯乍咯乍地烧炸了,檩条开始往下掉,拿桶提水去 泼,越泼火越大,樊喜成还在喊:铲土压!铲了土压!屋顶就垮下来。
火烧当日穷,邢轱辘在村里借了一间旧房住下,拴劳把当时从李长夏家装出来的麦给了一麻袋,就着手调查这火是怎么烧的。马生认定这是阶级敌人在破坏。 那么,阶级敌人就是地主了,查每一户地主中午都在干啥。去了李长夏家,李长夏还在炕上,病得屙呀尿呀都不晓得,他媳妇到河里给他洗铺在身下的垫子,洗的时 候龚仁有的老婆也在河里洗衣裳,龚仁有的老婆证明李长夏两口子不可能去放火。查王财东家,王财东和玉镯都没下地,玉镯说她在家里纺棉花,一中午没出门,王 财东伤风感冒了,她是做了一碗胡辣汤,喝过就在炕上蒙被子捂汗着。查张高桂老婆,张高桂老婆那日回了娘家。马生一分析,二返身又去王财东家,说:是你放的 火!王财东说:我咋能放火?马生说:你不老实!王财东说:老实着呀。马生说:刚才到你家,你说你伤风感冒了,鼻涕流下来,这已经半天了,你鼻涕还在嘴唇 上,你这是故意不擦要证明伤风感冒了。哼,越是要证明自己,越说明你心虚!白土就说:他确实伤风感冒了一直在炕上睡着。马生说:你咋知道的?白土说:我给 他家挖猪圈里粪,我知道。马生说:你还给地主家干活?白土说:他病着,猪圈里粪多得埋了猪腿,我来帮帮。马生说:你滚,给贫农丢人!
白土当长工的时候一直住在王财东家前院的一间草棚里,后来分到了王财东家后院的两间房,但白土有些不好意思,不去住,给玉镯说:我还是住草棚吧。玉 镯说:那两间房已经不是我家的了,是你的,你住吧,住你的。王财东还自动封了中堂的后门,又在后院墙上重开了门,让白土单独出入。白土是收拾了那两间房, 坐在屋里搓身上的垢甲,搓出绿豆大一疙瘩丢在地上,再搓绿豆大一疙瘩丢在地上,太陽从屋檐下的斜窗射下光柱,有无数的东西在那光柱里游动,就感觉是在做梦。以后的日子,他每天仍到王财东家来一次,一声不吭地干这干那,玉镯不让他干,他说不干不干,走出院子了却又回来挖起猪圈里的粪来。也就在第三次终于挖完了粪要走时,马生他们又来追查火灾的事,骂了他一顿, 把病着的王财东硬拉到农会院子里去了。
王财东到天黑没有回来,玉镯急得在家里坐不住,她去河里提水,只提了半桶,摇摇晃晃走不稳,水就扑洒了一路。碰着拴劳的娘,拴劳娘说:你自己提水呀?!她听出来这是在讥笑她,她不敢看拴劳娘的眼睛,低头就走,走过了又回了身,说:啊姐,你说我那人没事吧?拴劳娘说:他放火了咋能没事?她说:他没放火,他真的没放火。拴劳娘说: 没放火能把他叫去农会?!她不再问了,回到院里坐在门槛上发瓷。村里有了牛叫,也有了狗咬,后来是白河的小儿子跑来,拿了个萝卜,洗都没洗在吃着。她说: 我给你剥剥皮。小儿说:你家有没有柿饼?她说:不多了,我给你取两个。小儿说:取三个!你给我取三个了我才给你说话呀。她给了三个柿饼,小儿说:马生让我 给你传话哩,晚上给你男人送饭去。她赶紧拉住小儿,说:咋晚上还不回来?小儿嘴里嚼着柿饼,调不过舌头,始终没再回答又跑走了。
玉镯还是做了生姜拌汤送去,可她去了很快又提了饭罐回来,直脚到两间房那儿呜呜地哭。她给白土说,她说她只能给白土说,说她去送饭的时候,他们在打 她男人哩,吊在木梁上用劈柴打,打得劈柴上都是血,她去了才放下绳来。她说男人原本脑子不好了,挨了打人显得更瓜了,见了她不说话,也不吃饭,马生就让她 把饭罐提走了。说马生还叫她回家取被子,话狠得很,今天不交待今晚不回去,十天半月不交待那就死在这里。但白土给玉镯出不了主意,也不会说宽心话,只是唉 唉叹气,在屋子里来回转。
第二天,徐副县长带着检查组到了老城村。检查组原本是检查土改工作的,但老城村发生了火灾,就听取拴劳和马生汇报火灾的事。检查组里有个叫王甲由的 人,以前当过教师,他亲自审问了王财东,觉得事情有些蹊跷,又到火灾现场去察看,他的分析是火从后窗的布帘烧起的,而布帘又是马生家门框上的镜子折射了陽光引发的。王甲由的结论大家都不相信,但王甲由说他学过这方面的知识,并当场把镜子支在太陽下 照着一堆棉花,两个小时后棉花真的冒烟燃起来。这一下,王财东清白了,拴劳让王财东回家去,王财东却不走了,说:说我放的火,关我哩打我哩,现在查明了, 又咋处理放火的人?马生骂道:你在说我?王财东说:是你家门上的镜子照的。马生说:镜子也是从地主家分来的!徐副县长发话了,说:让你走你就走,就这点事 你不服气,那分你家地分你家房产你是不是更怀恨在心?!拴劳就推着王财东走出院子,说:你来的时候还伤风感冒着,现在不是病好了吗?回去,回去!顺手把院 门关了。
※※※
火灾虽然不是王财东放的,但徐副县长从火灾这件事提醒着拴劳和马生:分了地主的土地房屋和家产,地主肯定怀恨在心,伺机要破坏土改的。他列举了城关 镇一户地主在水井里投毒,东川镇一户地主在他家屋梁上记录了谁分了他多少地谁分了他多少房,桃花峪乡一户地主在分过他家的地里又偷偷埋界石,吴家川乡一户 地主三口人吊死在农会的院门上,南溪乡三户地主联合了在一个晚上杀害了农会主任。拴劳和马生就以巩固老城村土改成果,严防地主分子反攻的由头对王财东,张 高桂老婆,李长夏进行了几场批斗。
首先批斗的还是王财东。那个晚上,农会办公室的院子里点了三盏灯,灯盏子有碗大,灯芯子也指头粗。灯芯子是燃一阵就得往出拨一点,这任务交给了白河 的小儿子。马生布置的第一个发言的是白土。白土说:我不会说话。马生说:说不了话,你上去扇他耳光子!白土说:熟人我下不了手。马生骂白土是稀泥抹不上 墙,说:下不了手?你现在就去叫王家芳,让他提前到会场!白土去了王财东家,王财东被打后,腿疼得立不起身,白土二返身回来给马生说王家芳腿疼得走不动, 是不是批斗会改日开?马生说:这是请客呀?!他走不动,拖都要把他拖来!白土就和白菜的男人用筐子把王财东抬到会场。抬时,玉镯把被子垫在筐子里,白土要 抬杠子前头,他嘴上没说,想着是抬杠子前头了就可以不看王财东。批斗开始后,顶替白土发言的是北城门口的一个妇女,她愤怒地说王家芳家里饭吃得好,二三月 大家都没啥下锅了,王家芳家的门前老有鸡蛋皮皮。吃鸡蛋你就吃鸡蛋嘛,故意把鸡蛋皮倒在那里馋别人?!还有,王家芳夏天里穿绸褂子,冬天里穿四件衣裳,还 在外边套一个羊皮袄,戴绒线的地瓜皮帽子。一次王家芳热了,卸了帽子,帽壳里还藏了钱呀,几十张的钱,也没给大家分一张,客气话都没有。没说两句就呼起口 号:打倒地主!打倒旧社会!她一呼口号,全场都呼口号,白河的小儿子也兴头来了,喊,他门牙是豁豁,一喊就漏气,又离得灯近,灯芯子就扑闪,院子里忽明忽 暗。白土训道:你个碎仔喊啥哩,把灯管好!但第二个发言的却就是个孩子,他爹是中农王三水,他说王家芳家有一棵桃树,王家芳从来不让他去摘桃子,他曾经摘 过一次,刚爬上树王家芳就骂,还提了棍撵过来,吓得他从树上掉下来。可是后来王家芳让他上树去摘桃子,还说你多摘些了给毛蛋。白河的小儿子听到了,说:你 没给我桃!王三水的儿子说:我没给你桃是我给你送去的半路上桃子揣在怀里,桃毛痒得不行,我回家擦桃毛,擦了桃毛吃起来把你忘了。有人就笑起来,连王财东 都笑了。马生就呵斥不要笑,全场重新安静下来,王三水的儿子说:后来,我才知道王家芳让我上树摘桃子,是他知道要分他家的地呀房呀树呀,他这是要拉拢我! 第三个发言批斗的是刘巴子,刘巴子批王家芳曾经把穿过的一件旧袄给了他,是看不起穷人么,他让我给他家割麦,五黄六月,太陽把我能晒死,麦芒钻在衣服里能 把我扎死,他让白土给我送的啥饭呀?!白土可以作证。白土说给你送的是纯麦的捞面,人家在家吃的是麦和豆子搅在一起磨出的杂面。刘巴子说:就送了一碗,一 碗饭够谁吃,塞牙缝呀!白土说:那是我在半路上偷吃了一碗,我嫌你懒,一晌午只割了一畦麦。马生就说:白土你说的啥话?不会说就甭吭声!刘巴子继续说:我 肚子饥呀,我捋着麦穗子把揉出的麦粒往嘴里嚼,嚼,能渴死,没水喝,狗日的地主不给我提水喝!一股风吹进来,把毛蛋管着的油灯吹灭了,院子里一片黑,谁咕囔了一句:水拿河盛着哩,懒么。
每隔十天半月,三户地主都得去农会院子里被批斗,王财东的腿伤越来越重,连箩筐都坐不了,还是卸下门扇抬了去,人也看上去像个傻瓜,像抬着一只猪, 猪还哼哼,他不言传,闭了眼睛。马生说这是抗拒批斗哩,玉镯拿艾卷燃着让他吸,还掐了竹篾儿支着他的眼皮子。一次,又是通知第二天开批斗会,玉镯就让王财 东好好睡一觉,可王财东睡醒后说他做了一个梦,梦到海了,海尽是水。玉镯听人说梦到水是见财哩,王财东说:日子过倒灶了还见财?见棺材!玉镯赶紧捂他的 嘴,不让说晦气话,还呸呸呸朝空中唾几口。但梦的事毕竟让玉镯心情要比往日好,而产生了能为王财东去求情的念头,她便在晚上去了马生家。马生说:他是地 主,他怎么能不去?玉镯说:他病得实在起不来,要是不让他去了,我感恩不尽啊!马生说:你咋感恩?玉镯就跪下磕头。马生说:磕什么头?把玉镯往起拉,手却 到了玉镯怀里。玉镯捂怀,马生又使劲拉扯她的裤带,她的裤带是用麻丝编的,马生说:地主的媳妇系这好的裤带!猛地一拽,裤带还是没扯下来,却把裤腰撕开了,就势压在地上,说:你要让我进去,明日他就免了会。
第二天,是没有人通知去开批斗会。玉镯烧了一锅艾叶水,把自己身子洗了又洗,然后坐在猪圈墙上看猪在圈里拱着粪土,王财东在炕上喊她,她都没听见,后来王财东用力敲炕沿板,她揉揉眼, 进去了说:你想吃啥?我去集市上买些肠子,给你做辣汤肥肠。可仅仅五天,又通知要开批斗会,玉镯对来人说:你让马副主任来。马生背着手来了。玉镯问:怎么 还开批斗会?马生说:这一顿饱了,下一顿又饥了,吃饭吃不厌烦。玉镯说:你再抬抬手让家芳过去么。马生说:我这心里过不去你么,过五次我估计就能放下了。 王财东在里屋的炕上躺着,马生把玉镯就又压在了外屋的织布机上,用织出的布把玉镯的胳膊绑住干事。王财东爬到炕沿要下来,又下不来,一下子跌到炕下的尿桶 里,头朝下,在尿里溺死了。
※※※
检查组离开老城村的时候,徐副县长让我跟他们一块回乡政府,他说他要回报我吃些好饭。乡政府的饭果然不错,每天中午都是白菜豆腐汤两个蒸馍,再炒一 盘回锅肉或者韭菜鸡蛋,隔两三天了还有一顿辣汤肥肠。徐副县长有一条被单,底色是黄的,上边又印有大大小小的黑色圆点,像是豹纹,晚上睡觉就盖着。他告诉 我,这被单是匡三送他的,匡三从县兵役局调往军分区的前一个月,匡三邀他去家喝酒,因为喝得多了,晚上他们睡在一个房间,匡三就盖着这条被单。匡三不盖这 条被单匡三就是一个人,瘦小的人,可匡三盖着这条被单睡着了,他就猛然睁眼看见匡三是一只豹子。因此他离开时匡三说:这屋子里你看上什么了,我就送你什 么。他就索要了这条被单。徐副县长给我说得神神秘秘,但我晚上故意没睡实,半夜里看徐副县长,徐副县长在睡时把被单裹得紧紧的,而他一睡着,被单就蹬开 了,掉在地上,他还是他,一只眼瞎着,一只眼睁着,鼾声像是在吼。后来,老城村的白土到乡政府找到我,请我能去给王财东唱一场陰歌,我已经答应了,徐副县长不让我去,他说:你咋没政治头脑!我说:啥是政治头脑?他说: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了,你给地主唱什么陰歌,让地主托生了再当地主,那革命不是白干了?我说:地主托生了是地主,共产党就有个批斗的事干了嘛!他有些生气,说:你给我贫嘴?!我也便认真了,再不和他戏谑,当着生人面就恭恭敬敬叫着他是副县长。当检查组最后离开乡政府时,我也便拿着徐副县长的一个便条去了县文工团。
※※※
王财东是草草地埋葬了的,过了头七,玉镯的脑子里总觉得钻了一只蜂,嗡嗡地响,时不时拿手拍太陽穴,见人就絮絮叨叨,说家芳是梦见一海的水,他就让 尿溺死了,原来尿也是水。先是听者脸上给她苦愁着,其实她的话从未入耳,后来看到她就躲,她便遇见牛给牛说,碰见树给树说,她家门前的树叶子枯黄,不到半 年树都干死了。到了夏天,她丢三落四得厉害,要到打麦场上的麦草垛上撕些麦草回来做饭呀,走到打麦场上了,吆了一声麻雀,便忘了她来要干啥,而从地里摘了 个南瓜回去。要么,几天都不出门,用白粉涂她的那双白鞋,落上灰尘就涂,粘上一粒麻雀粪也涂,穿上涂了白粉的白鞋在屋里走,问着家芳你说好看不?白土从地 里回来,都要捎一担土的,把土垫在玉镯家的猪圈里,他听见玉镯在堂屋里说话,以为来了客,进去看时,她一个人在屋里走。白土就可怜了她,再去集市上,拿自 家的黄豆换了一只黑毛狗让她养了,想给她有个伴。玉镯有了狗,却每天拉了狗去倒流河给狗洗毛,她说她要把黑狗洗成白狗。
白土还背了一篓红薯到集市上去卖,卖给了一家饭馆,回到家里重新算账,觉得是少给了他一角钱,二返身又要去讨。出了村碰着有人赶牛车也去集市的,他 要人家把他捎上,人家说这得掏捎脚钱,他说不给你钱,我地里有豆角,给你摘豆角。那人竟然在他地里摘了一筐豆角。白土要回来了一角钱后,村里人说:为了一 角钱你让人家拿了你一元钱的豆角?他说:摘多少豆角我愿意,欠我的钱得讨呀!大家就议论:啥人配啥人,白土和玉镯两个脑子都不清白,撮合他们成个家吧。
这年冬天,拴劳承头,几个人一商量,要白土接玉镯住到他家去,或者白土把枕头拿到玉镯的炕上来。话说给白土,白土不同意。拴劳说:给你个媳妇你不同 意?白土说:同意。拴劳说:那你就和玉镯过活么。白土说:玉镯是地主婆呀。当时马生也在,马生说:把地主婆睡了你就算革命翻身了!白土没有接玉镯到他的屋 里,打通了玉镯家的堂屋后门,封了他自己后院墙上的门,又恢复了王家以前的模样。他对玉镯说:你是我媳妇了。玉镯说:你是我媳妇了。他说:说错了,不是 你,是我是你媳妇了。他给玉镯梳头,给玉镯捉身上的虱子,问玉镯:还有啥活吗?到了晚上,玉镯要吃水烟,玉镯吃惯了水烟,白土就给她点火。吃毕了烟,玉镯 睡觉前要洗一洗,端了水盆在卧屋里,她让白土出去,白土就站在卧屋外,心里说:睡觉呀还洗啥的?等他回到卧屋,玉镯已经睡下了,白土摸摸索索才爬上炕,坐在玉镯的旁边,他不敢干那事,看着玉镯白胖白胖的,怕弄破了她。后半夜了也睡下,一睡下白土就睡死了,像一摊泥。
白土就这么一天一天地过活着,但不知什么时候起,他在半夜起来小便,迷迷糊糊从炕上下来,去屋角的尿桶里尿了,再迷迷糊糊爬上炕去睡,好像看到过炕 下多着鞋, 天亮了要下地干活,却看到炕下的鞋就是一双玉镯的布鞋,还有一双他的草鞋。他有些疑惑,以为是在做梦,还是自己半夜里没有看清。这样的事发生过三次四次, 就在他又一天半夜里起来小便,窗外有月亮,朦朦胧胧中再看到炕下多了一双鞋,是一双胶底鞋,他就摸索着寻火柴,嘶地划了一根,似乎看到从炕上爬起个黑影, 而火柴燃尽了,屋子里一片黑,比没划火柴前更黑,窗子的一扇打开着,低头看炕下的那双胶皮鞋也没了。白土终于明白有人晚上偷偷进了他家,还偷上了炕,怨自 己睡得死没有觉察。白土感到了奇耻大辱,气得把头往炕沿上磕。可这事他不能声张,他要查查这是谁,发誓要报复这人。天明后,他在窗外查看了脚印,果然是胶 底鞋印,于是留神着村里谁穿了胶底鞋。村里穿胶底鞋的有五个,三个男的,两个女的,女的排除掉,而三个男的一个是会计,会计是跛子,走路踏出的脚印左边深 右边浅,一个是西城门口米家的儿子,这儿子个头小,鞋也小,另一个就是马生了。证实了是马生,白土犯了难,他不知该怎么报复,也不敢去报复,只好将倒坍的 院墙重新修好,还在院墙头上用泥巴压了一层野枣刺,再是把窗子钉好,多热的天也不开。还有,他夜里不敢睡死了,贴着玉镯睡,后来抱着玉镯,玉镯没有反应, 他大胆了,能整夜抱着睡。那只狗一直拴在后院里,现在拴到院门口,只要狗一叫,白土就起来拿了杠子,大声说:谁?谁?!直到狗不再叫。
白天里,马生动不动就来了,来了脸拉得长长的,不是让白土去河滩地的渠上查看流水,就是说又要开会呀。白土都应承着,却和玉镯一块去查看水渠,一块 去开会。玉镯迅速地发肿,人越来越瓷,你问她话了,她可以说一句,不问她了,她永不吭声,再到后来了出门就寻着回家。白土不能干什么都带着她,把她留在家 里又不放心,白土就在一次去赶集市时,背着编草鞋的耙子和玉镯走了,还有那黑狗,就再没有回老城村。
※※※书旗小说网,<a href="http://www.bookqi.com/">http://www.bookqi.com/</a>
村里人没有去找白土,白河也没有找,只是白土和玉镯养的猪、鸡他接管了自己养,还拿走了地窖里的土豆红薯,意外地发现了一个罐子,罐子里装着土蜂 蜜,也给媳妇提回来。媳妇病得久了,又添了哮喘,每天坐在炕上喉咙里像装了风箱。白河和二儿子经管地里的活,白石的媳妇在家料理着猪鸡,三顿饭给婆婆端到 炕上。白河的媳妇想让小儿子到炕上和她说说话,小儿子去谋着吃一勺土蜂蜜就离开了,只是白河的小尾巴。白河说:唉,毛蛋不爱到他娘跟前去,他娘可能快死呀。果然不出一月,白河的媳妇一口气上不来就憋死了。做娘的 一死,白石的媳妇就不待见毛蛋。一天,白河去县城办事,家里只有白石媳妇、二儿子和毛蛋,当嫂子的做了包谷糁煮面条,舀饭时毛蛋趴在灶沿上说:给我舀稠 些。嫂子说:我下锅给你捞呀?!毛蛋致了气,饭端上来,桌子上放着一盘炝好的葱花,他全拨到自己碗里,嫂子说:葱花里盐重。毛蛋端起碗就摔在地上。二哥一 看,就打,还让他在院子里跪了,双手举块洗衣板在头上。这当儿村里一个老汉进来借筛子,说:呀,白河不在,你们整人家尾巴呀?!毛蛋一看有人为他说话,把 洗衣板一扔,顺门跑了,就坐到西城门洞等他爹回来。白河回来了,毛蛋就告诉,白河说:就三个人吃饭哩,你要捞一碗干的,别人喝汤呀?但拉着毛蛋一进院子, 白河的脸就黑了。家里矛盾一多,白河觉得毛蛋在家生活不好,就给白石说让毛蛋到乡政府跑个小脚路去。白河说:他能干啥呀?白河说:我八岁就给县汇元堂当伙计哩。白石安排了毛蛋去乡小学敲钟,每月管待吃喝还发八元钱的补贴。
拴劳的媳妇依旧打骂着养女。以前打骂,翠翠都是顶嘴,后来慢慢大了,打骂她不吭声,却出门到倒流河对面的豁口去一坐一天,或者去逛集市,半夜里悄悄 回来。气得拴劳媳妇说:还回来干啥,有本事就不回来!一天,翠翠在地里锄草,说好晌午饭让弟弟送来,可已经过了晌午,饭还没有送来,饿得头晕,回到家里却 见养母和弟弟吃饭,养母说:让你弟吃了就给你送饭呀,你咋回来了?翠翠进厨房拿了一个馍,说:我再锄去!出了门,没去地里,而跑到乡小学找毛蛋。拴劳媳妇 得知翠翠去白河小儿子那里去,把翠翠抓回来,又去白河家指责白河不管教小儿子,年纪小小的勾引了翠翠。气得白河中了一次风,自此嘴歪着,腿脚不稳,走路得 拄棍,还要扶墙。
毛蛋回来看望他爹,村里人问:你咋把翠翠勾引去学校的?他说:她自己来的。又问:你们干那事了?他说:没有!急得眼都红了。村里人认为毛蛋还是童子身,或许他还不会干那事。但毛蛋临走时给嫂子和二哥说,要把爹孝敬好,每天必须给爹吃两颗荷包蛋,荷包蛋的钱由他出。
翠翠抓回来后被拴劳媳妇打了一顿,把头发都给剃了,样子不男不女。有人对拴劳说:孩子大了,不能那样待啊!拴劳说:唉。一脸苦愁。拴劳的媳妇这是村 里人都知道的,但媳妇做事这么过分而拴劳还不管,村里人就不明白这是啥原因。翠翠并没有安生,又跑了出去,这回拴劳媳妇没有去抓,放话说任她在外死呀活 呀,全当就没这个孽种。但她和拴劳在家里闹,抓拴劳脸,抓出了五道血印子。出来和马生到农会办公室去,马生把帽子往墙上的木橛子上挂,说:来,你也把脸皮 挂上。
冬至那天早晨,白河躺在炕上,儿媳在给他煮荷包蛋。白河说:拣颗大的给我煮,煮一颗。儿媳说:咋煮一颗了?白河说:给我毛蛋省些钱。邢轱辘却跑来说:快起来,快起来!白河说:我站不起身么。邢轱辘说:给你说个事你就能站起来蹦哩!邢轱辘说乡政府来人把拴劳五花大绑了!白河是从炕上坐起来,但还是走不了路。邢轱辘就背了白河往农会院子去,还没到,就见在巷口拴劳果然被绑着往村外去,马生从他口兜里掏印章。拴劳一拉走,马生散布的情况是翠翠在乡政府告状,说拴劳四年前强奸过她。而在乡政府一审问,拴劳把啥都承认了,就没有再回村,从乡政府送到县城坐了牢。
※※※
开过年的四月,樱花开得像雪一样,白石突然到县文工团来找我,提了一袋菌子。我这才知道他从乡政府已经调到县城,在商业局当局长了。我说:哎呀,我 还没给你恭贺的,你倒给我送礼?!白石就哈哈笑,嘴里有了一颗金牙。那时候,嘴里能有金牙那是一种贵气,我不晓得他是在门牙上包了一层金皮还是把门牙直接 拔了重新安装的整颗金牙。他说:这是马生送你的!我说:马生?他说:你不记得啦,老城村的马生呀!你得去老城村给他唱一场的。我说:马生死了?他说:他咋 能死,命硬得很,只克别人死。我说:在他手里是死了不少人哩。那让我去给谁唱陰歌呀?他说:马生要结婚呀,村里要闹一场陽歌,马生嫌城关镇陽歌队的那些人声都不好,说你能唱陰歌就能唱陽歌,一定请你去一趟的。县城关镇是有支陽歌队的,正月十五元宵节我也曾看过他们的表演,成百人的队伍都穿着彩衣,打着红伞,有伞头有文武身子有丑角在土场子上唱神歌、扭花步,然后绕转起不同的阵形,如五梅花,霸王鼎,双背弓,卷席筒,八角楼,蛇盘蛋。可是,他们闹的是陽歌,是给活人唱的,要活着的人活得更旺,更出彩,而我唱的是陰歌,为亡人唱的,要亡人的灵魂安妥,我怎么能去呢?我表示了我去不成,却说:这光棍终于有个自己的女人啦!新娘是 哪儿的?白石说:哈,一对旧家具!我说:娶的是二婚?白石说:拴劳你认识,拴劳的媳妇你可能不熟悉,是拴劳的媳妇。拴劳的媳妇我怎能不熟悉呢,但我怎么也 想不到马生是娶了拴劳的媳妇。这世事真是千变万化!我仍关心着老城村的事,问起白石他爹白河和他叔白土,问起白菜和玉镯,以及李长夏刘巴子龚仁有还有那个 邢轱辘。老城村的话题让我们几乎说了一个晌午,直到起了风,飞来的樱花瓣在地上铺了一层,他才离开的。离开的时候他却低声问我是不是和军分区司令熟?我说 军分区司令是大官,我见都没见过。他说:你哄我了,我听说过在解放前你帮过匡三。我说:你是说匡三?他调到军分区了?!是匡三司令?!他说:什么时候你领 我去拜会一下司令?我说:领可以,不知道他认不认我。
但后来白石并没有再找我,我听说了他是端午节的第二天就拜会了匡三司令,领他去的是徐副县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