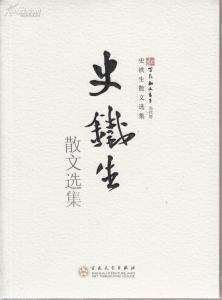第六部分
检查组在乡政府召开了一次各村寨农会主任汇报会,老城村原本是拴劳去的,拴劳那天正好上了火,满嘴都起了疮,马生便参加了。会上,乡政府附近的几个 村都讲了他们的情况,大致是土改工作基本完成,但不约而同地出现了新的问题,即分了地主的土地房屋牲口农具和大件家具后,村里的富农反倒成了土地最多的人 家,而中农又不如了贫农。他们就提出能不能也分富农的土地房屋牲口农具和大件家具?或者,不论阶级成分把所有的土地房屋牲口农具大件家具统统收起来,再按 人头平均分?白石就强调土改是有政策条文的,政策条文上怎么写,我们就怎么去执行,不能遗漏也不能突破,所以只能是在阶级成分上动两头,固中间,把地主的 分给贫农,而富农不能分,中农更不能分。马生是坐在会场后一排的右边,他一直看着主席台上的徐副县长,觉得徐副县长右眼瞎着,一定是看不到左边,他就捅了捅身边的刘山,刘山是涝池村的农会主任,他说:你是不是共产党?刘山说:四七年我就入党啦。马生说:共产党不是共产吗,咋就不让按人头平均分?刘山说:国民党当年诬蔑共产党 共产共妻,你是不是也想着给你分谁家的老婆呀?!马生嗤嗤地笑。白石却点名马生笑什么,你汇报汇报老城村的情况。马生站了起来,刘山低声说:别说二话!马 生回了句:我知道。却就大声说:我恨哩!白石吓了一跳,扭头看徐副县长,徐副县长说:你恨哩…你恨谁哩?马生说:我恨我们老城村!白石说:老城村怎么啦? 马生说:老城村穷么。我刚才听几个村寨的介绍了,田王村有四户地主,一户是二百亩地,一户是一百八十亩,另外两户也都是一百四五十亩。李家寨有五户地主, 两岔堡有三户地主,人家的地全是一百多亩。东川村的地主竟然是三百亩地。老城村最大的地主是多少呢,也就是六十六亩。白石说:不要比较这个,你只说土改情 况。马生说:政策上规定动两头固中间,可老城村穷,矛盾又复杂,土改任务我们还没有完成。白石有些不高兴,说:还没完成?老城村不能拖全乡的后腿啊!马生 说:我抓紧,会抓紧。白石就说:一定要抓紧,检查组会到老城村去检查的。
马生一回到村,把会上的事说给拴劳,拴劳说:咱已经任务完成了,你咋能说还没完成,自己给自己脸上抹黑?马生说:别的村地主都是二三百亩,土地一 分,贫农就分到十四五亩,咱却仅仅是七亩,现在两个富农一户三十亩,一户二十五亩,那不是打倒了两户地主,又出现两户地主?拴劳说:你这啥意思?马生说: 土改是让穷人翻身的,到最后富农还是比贫农多出一二十亩地?拴劳说:政策上是不能分富农的呀。马生说:咱不分富农,可以把富农改定为地主,那不就分地啦? 拴劳说:富农是咱算出来的呀。马生说:肉在咱案子上还不是由咱切呀剁呀?!两人就商量了,先是决定把李长夏刘三川都定为地主,后又考虑没有富农也不行,那 就改定李长夏为地主。而且得快定快分,赶在检查组来之前把生米做成熟饭。
老城村有木匠,也有泥瓦匠,而既是木匠又是泥瓦匠的只有李长夏。李长夏的本事大,但脾性狂,同样的一句话从别人嘴里出来是一个味儿,从他嘴里出来就 让人听着不舒服。土改一开始定成分,他没了解情况,一看好几户有手艺的人如木匠、泥瓦匠、席匠、石匠的都是中农,他说我家成分不要和他们一样,要定就定富 农,富农这名字好听。后来知道了定成分是咋回事了,又给他家定了富农,虽然心里不高兴,但他家地多,剥削多,也没了办法。而当白河分到了王财东家的方桌, 在巷里说这是老城村最好的桌子,他还拉了白河到他家去看他家桌子,说:王财东的这是核桃木的,我这是楠木,你知道楠木吗?现在,要把李长夏定为地主,马生 在村民会上讲了话,他说老城村的地主指标应该是三个,先指标完成了两个,还缺一个,那就得从富农里往上递增。贫农们一听,就计算着李长夏家三十亩地,留下 十亩,那每家便能再分一亩半多的地了,于是全场叫好,还呼了一阵:共产党万岁!那天李长夏也在场,当时骂了一句:娘的!但字还没骂出来,人就晕倒在地。他老婆给他掐人中,掐醒来扶了回家,他挪不动步,说:我腿呢,我没腿了!老婆把他背了回去。会上的人都说李长夏多张狂的人,一遇到事也是一摊泥么。
李长夏回家后就睡下了,第二天脸全成了绿色。以前是张高桂哭,现在是李长夏哭。王财东和玉镯在家里吃饭,玉镯说:你多吃一碗。现在咱又多了个垫背 的,还有啥想不通的,好好吃饭!王财东说:咱盖房时长夏一直帮忙,这个时候了你该去给宽宽心。玉镯说:他家就那么些地也定了地主,我去了他老婆会不会以为 我是去看笑话的?王财东说:一条绳上的蚂蚱了谁笑话谁?!玉镯去了,不知道说什么好,反倒是李长夏老婆抱住了玉镯,鼻涕眼泪把玉镯的怀襟都弄湿了,玉镯就 也陪着流眼泪。拴劳马生领着人在地里栽了界石,再来家拉牛搬家具,李长夏腿瘫得还是下不了炕,只在炕上骂。马生就吼:你地主在骂谁?你骂吧,骂一句多装一 升麦!就往麻袋里装麦子,装了两麻袋。李长夏老婆赶紧进了卧屋,劝李长夏不敢骂。搬走了两个板柜,三个八斗瓮,四个箱子,一台织布机,一辆牛拉车,五根檩 木,还有那张楠木桌子,四把椅子。拉牛时,牛长声叫,李长夏对玉镯说:你把牛拉来让我看一眼。玉镯去给拉牛的人求情,牛被拉到卧屋,李长夏把牛全身都摸了 一遍,最后拍着牛头说:你去吧,谁分了你,你让谁上坡滚坡,下河溺河,不得好死!马生听到了,冲进来说:你说啥,你说啥?!李长夏说:马生,你家那房,是 你爹求我去做的木工,工钱我只要了一半,你这白眼狼这么害我,我后悔当初没在你家屋梁上做个手脚!马生啪地扇了李长夏一个耳光,说:你以为你没做手脚吗, 你肯定做了,才使我家日子过倒灶了!再扇一个耳光,李长夏就昏过去了。玉镯说:马生,他没说啥,他哪儿有做手脚的本事,做手脚都是写个咒语夹在卯缝里,他 不识字,他哪儿能写咒语,他要有那本事,该给自己屋梁上弄个好处,家产也不至于被分的。马生说:你来这儿干啥,地主和地主串通呀?!一脚踢过去,没踢着, 玉镯顺门逃走了。
李长夏的家产,马生分得了一个箱子,一个罗汉床,临走时,看见墙上有个镜子,摘下来揣在怀里。
马生把镜子挂在他家的门框上,镜子就能照到前边邢轱辘家的后窗上。分了地后,邢轱辘还是出去赌博,他媳妇劝过吵过都不顶用,索性自己也在村里和一伙妇女码花花纸牌。她们玩纸牌不押钱,每人来都端一升豆面,输过十把牌了,豆面就归赢家,自己拿个空升子回去。邢轱辘赌博没迟没早,回来常是媳妇不在家,猪在圈里哼哼着,鸡把蛋下在了麦草堆里,他就立在门口死狼声地喊:喂——死到哪儿去了,冰锅冷灶的?!旁人取笑说:懒婆娘休 了去!邢轱辘倒笑了,说:她离了我咋活呀?旁人说:怕是你离不了她!这两口子都是能在炕上折腾,确实是谁也离不了谁。马生忙了一天,晚上回来,一进巷口就 听见邢轱辘在屋里骂媳妇,骂得啥脏话都有,走到后窗外了,却传来啪啪啪的肉声。马生知道这是邢轱辘和媳妇又干那事,手在拍媳妇的屁股了。便猫下腰还要听,听着听着两口子又吵骂了起来。马生回到家里,一时啥也心慌得做不成,就把拿到的李长夏家的那个镜子挂在了自家门框上,镜子里果然就有了邢轱辘家的后窗,窗里的炕上邢轱辘在拿鞋抽打媳妇的光屁股,屁股白得像个大白石头。
从此,马生一回到家总要站在门下看一会儿镜子,镜子里的邢轱辘家后窗没装木扇板,就那么个大格子框,也不糊纸,吊个布帘子。这布帘子常拉开着,那媳 妇就睡在炕上,喜欢把两条腿举起来,可能也是他们嫌太光亮了吧,帘子有时就又拉合了。镜子里只剩下印花布帘,马生就咽口唾沫,闷在屋里转来转去。
马生这时候就出去到那些贫农家去吹牛了。吹到分地,他总要说在分李长夏家的地时,拴劳是怕这怕那,而他就硬下手,哈,分了不是就分了吗?!那些贫农就给他拿吃喝,说拴劳太软,干农会的事就得刀子残火哩!马生说:拴劳最近好像家里有什么事,身体不好么。那些贫农说:身体不好了,你就应该当正的嘛!马生嘿嘿地笑,说:正的副的都一样。
拴劳确实是自立春后和媳妇有些合不来,经常脸上有血印子,明明是被指甲抓过的,他说是让树梢子挂的,但时不时就捂个肚子,承认着得了胃病。当他找到 马生要记账时,马生说:我不识字,账本子还是你装上好,我能吃能跑的,我给咱把印章拿上,你说在哪儿按,我就在哪儿按!拴劳却说:这啥意思?马生说:你身体不好,还不是为你好?拴劳说:你甭给我想点子,我是胃不好,口兜里装着胃药也装着花招呀!
这一天,马生从巷子里走,腰带松了下来,一头吊在腿前,他突然想到这吊着的是他那东西,嘴里就哼哼着:腰里缠三匝,地上拖丈八,半空里撵着老鸦!抬 头就往天上看。邢轱辘媳妇提了一副羊肠子要去河里洗,碰上了,说:看啥哩?马生说:看天哩。邢轱辘媳妇说:看天哩?马生说:看能么能上天去!邢轱辘媳妇 说:我用簸箕一扇就上去了!马生说:是不是?在邢轱辘媳妇屁股上捏了一把。邢轱辘媳妇没理会,说:再给大家分些东西么?马生说:多分了让你们受活呀?!手 又到怀里去。这回邢轱辘媳妇把羊肠子甩过来,打中了马生的脸,拧身走开了。马生缓了半天神,说:你以为你是白菜?!没想巷口里正走过白菜,一闪就不见了, 进巷来的却是张高桂老婆。马生说:白菜又去寺里啦?张高桂老婆不理他。马生说:你个地主婆,不理我?张高桂老婆说:地主婆不敢理你么。马生说:是白菜去寺 里啦?张高桂老婆说:我怎么能知道她去哪儿?马生说:她顶了印花帕帕。张高桂老婆说:哦,再过两天是庙会呀。马生说:娘的,和尚又发财呀!
骂过了和尚发财,马生突然想到寺里不是有二十亩地吗,怎么就没收回呢?于是,马生就在这个中午再次去了铁佛寺。
还在寺前,马生就看见了白菜和一些妇女在打扫寺前的场子,他没有前去搭话,背了手就在那块地里用脚步丈量起来。和尚是首先发现了他,跑过来说:马 生,马生!马生说:我是农会的!和尚说:噢,马农会,你在寻啥东西?马生说:我量地哩。和尚说:量地哩?马生说:量量看能收回多少亩。和尚说:这地是寺产 呀。马生说:一切土地归农会啊,你这一块是二十二亩吧,寺后那块是多少?和尚说:这我得找拴劳说去,他当主任哩,怎么政策又变啦?!马生说:你不是有佛 吗,还可再问问佛!
马生又继续用脚步量地,他以为和尚回到寺里要给那些妇女讲的,那些妇女也会来地里问他的话了,可是,妇女们没有来。当他迈着脚步到了地的那头,就没意思再迈着脚步丈量过来。地头上有一个土洞,查看了洞口的蹄爪印,知道是一个獾洞,就给自己找个事儿,捉起獾来。捉獾得用柴禾在洞口生火,烟熏进去獾就出来了。他找了些柴禾在熏,天慢慢黑下来,那些妇女陆续回村了,路过地畔,还是没有理会他。但马生在回村的妇女中,始终没有见到白菜。
马生提着一只獾回到村,直直地往白菜家去。白菜的男人在院子里举石锁子。这男人脑子简单,身体却好,喜欢使槍弄棍的,举了几十下石锁子,又趴在地上俯卧撑。马生站在院门口,说:下边又没有女的你晃啥哩?那男的不撑了,说:你寻我?马生说:你吃獾呀不?那男人说:你咋舍得给我吃?马生把獾扔过去,说:白菜呢?那男人说:中午就回娘家了。马生说:是吗,那我后半晌咋看到她在寺里?那男人说:啊。声音不大,却提了棍顺门就走。马生说:你?那男人说:我去寺里!马生说:你这脾气,咋搁不住事呢?别打人啊!
※※※
马生叮咛着别打人,他回到家里,就等着打人的消息。
这白菜怀不上孩子,去铁佛寺烧过香,就结识了和尚,隔三岔五往寺里去,甚至和尚还来过她家,带了一包香灰让白菜和她男人冲了水喝。但后来村里就有了 说法,说白菜去寺里怀里揣过一瓶酒,和尚怎么能喝酒呢?又说白菜头上的印花帕帕是和尚给的。这些话当然没人给白菜的男人提说,但白菜从此不同她男人睡觉, 她男人就起了疑心。男人说:你求孩子哩,不和我睡觉哪能有孩子?白菜说:佛会赐的。男人说:佛会赐的?!我可告诉你,你敢给我戴绿帽子,我就卸你的腿!当 马生说了白菜在寺里的话,那男子就觉得白菜骗了他,又从马生说话的神气里听出马生是在嘲笑他,一时恼火,提了棍赶去寺里要看个究竟。到了寺里,寺门关着, 咚里咚咣敲了半天,和尚才出来开了门,他劈头喝问:是不是白菜在寺里?和尚说:没,没没没呀!他说:没有你牙花子乱叩?便往里走。和尚倒提高了声音说:白 菜就是没在寺里呀!他说:你喊那么大声是报信不成?!看了大殿,大殿里没有,进了禅房,禅房里也没有。和尚说:你到厨房厕所再去看,哪里有?他偏不去厨房 厕所,就坐在禅房的床沿,这床支得很高,床单子垂在地面,突然闻到了一股桂花油的香味,白菜的头发上搽的就是桂花油,他说:白菜肯定在,你把她藏哪儿了? 和尚说:没有,真的没有。他气得一把拽掉床单,没想床下竟然还有一床,白菜就在里边蜷着。他一拳把和尚的鼻梁打得陷下去,又在身上撂了三棍,采着白菜头发 回了村子。
在村口碰着了一个媳妇也常去寺里的男人,那男人又把这事说给另外几个香客的男人,他们各自在家打着媳妇,逼问与和尚有没有那事。打得猛,这些媳妇都承认了。于是这些男人在后半夜再去了寺里,把和尚一顿饱打。一个说:给他一口气,别让咱背上人命案。白菜的男人却不住手,竟把和尚的裤子撕开,说:长了个啥东西爱的!拿起剪子要铰。和尚爹呀娘呀地求饶,他们不铰了,却给了个碗,让和尚自己弄出精水来,要求限天亮能弄出一碗就饶了他。和尚在那里弄起来,他们就在寺里翻寻,能拿的东西都往怀里揣,揣不了的全砸烂。到了天明过来看和尚,碗里的精水只盖了碗底,和尚趴在地上。白菜的男人说:就这点本事还糟蹋别人的媳妇?!踢了和尚一脚,踢得和尚翻过身来,和尚却已经死了。
和尚一死,这些男人散开就走,白菜的男人说:谁走就是谁打死的!他们又回来商量对策,最后把和尚拉到寺前地里,刨个坑埋了。然后回村给拴劳汇报,说 和尚先在寺里要糟蹋白菜,白菜不从逃了出来,他们的确是去了寺里要教训和尚的,但一到寺里,和尚畏罪上吊了。拴劳吃了一惊,说:死啦?他们说:死啦。拴劳 说:你们没打他?他们说:人都死了打他也不会疼,没打。拴劳说:尸体呢?他们说:埋了。他没亲没故的,不埋让臭在寺里?拴劳就去找马生,给马生说:爷呀, 老城村摊上事啦!马生说:是打了人啦?拴劳说:你咋知道是打了人了?马生说:瞧你这神色,那还不是打人啦。拴劳就说了铁佛寺的事,马生一时愣了,噢噢了几 声,却笑起来,说:也好,也好,二十亩寺产就收回来了!拴劳说:这是人命啊!马生说:咱对外说和尚云游去了不就得了?!拴劳说:这成?马生说:成!拴劳 说:我心里还是慌的,那你就去收地分地吧。
二十亩二分地再分给十三户贫农,每户一亩三分。为了便于耕种,马生决定如果谁肯把分到的河滩地退出换寺前的地,一亩可以兑两亩。结果,他自己得了十 二亩寺前地,又动员白菜的男人和白土各兑到剩下的一个三亩一个七亩。这些地在和尚手里时已经犁过,现在只需要用铁齿耙耙一遍。耙地时,马生在,白菜的男人 在,白菜也在。马生耙到埋和尚的地方,埋的坑浅,铁齿就把和尚的天灵盖耙开了。马生喊白菜:你来看这是啥?白菜一看,瘫得坐在地上,自后人就傻了,不再说 话,除了吃饭,嘴都张着,往外流哈喇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