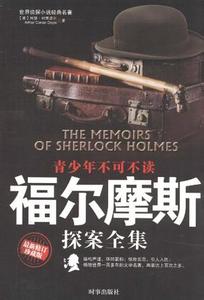第34章
不难相信这个故事使我受到异常的影响,但我对于当时自己那种心烦意乱的状况却无法形容。我对这个故事显得很吃惊,问了她无数具体细节,我发现她无所不知。最后我开始了解这个家庭的处境,那个老妇——我指自己母亲——是如何死的,如何留下财产的。因母亲曾十分认真地向我保证过她死时会为我做点什么,留下一些财产,这样如果我还活着,就应该以某种方式来取它,而不会受到儿子——我哥哥和以前的丈夫——的阻止。她说她并不确切知道财产是如何安排的,但听说我母亲留下一笔钱,以她的种植园作为支付方式,以便在得知女儿的消息时能对她作些补偿,无论她在英国还是其它地方。这笔被信托的财产现留在那个做儿子的手里,就是我们看见与他父亲一起的人。
这个消息对我太好了,不可小看,你可以肯定它让我思绪万千——我想着应该采取什么办法,怎样让自己与亲人相认,或者是否应该与他们相认。
对于现在所面临的困惑我自己实在无力解决,也不知道该如何办。我一日夜心情沉重,既睡不着觉又无法交流,被丈夫觉察到了,他不明白我为啥会痛苦,极力让我高兴,但毫无用处。他不断让我告诉他遇到啥烦恼,我迟迟不说,最后在他再三要求下我才不得不编造了一个显然也并不假的故事。我说我感到烦恼的是自己发现我们必须迁到别处去住,改变定居的计划,因我发现如果住在那儿我就会被认出来。由于母亲已去世,有几个亲戚来到了我们现在住的那片地方,我要么会让他们知道我——处于我目前的境况从很多方面看都不适合——要么迁移。我不知如何是好,所以感到忧愁。
他对此表示同意,认为我们现在处于这样的境况让任何人知道都是绝不恰当的,因此他说只要我觉得合适,他愿意迁到该国的任何地方或甚至任何其它地方。可现在我又遇到另外的问题,即假如我迁到另一个殖民地,就再无法对母亲留下的东西进行应有的查询了。再者,我简直无法想到把自己前一个婚姻的秘密泄露给现在这个丈夫,那段故事是经不起讲述的,我也不知道讲了会有啥后果。并且,这个地方的所有人也必然会知道我是谁,以及我现在的处境如何。
这种困惑持续了很久,让我丈夫极度不安,他认为我对他不坦率,没有让他了解我的所有苦恼。他经常说很想知道自己做了什么让我不信任他,不管什么事情,尤其是如果事情令人十分悲哀痛苦的话。的确应该在一切事情上都要信任他,因为男人从妻子那里最应该得到的就是信任。然而我又不知如何把此事向他坦白。可如果不把自己的事对任何人有所倾谈,那么我的一精一神负担就会过于沉重。无论人们怎样乐于说我们女人不能够保守秘密——不管是女人的秘密还是男人的——凡重大的秘密,我们都应该有一个密友、一个知心朋友倾谈其中的欢乐或痛苦,无论情况如何,否则我们的一精一神负担就会倍增,也许会变得难以承受。这一点我请人们去予以证实。
正因为如此,男人和女人们,甚至那些在其它方面出类拔萃的男人们,才经常发现自己在这方面很软弱,无法独自承受心中的欢乐或痛苦,不得不把它们泄露出来——即使仅仅为了发泄一下自己的感情,让伴随而来的一精一神压力得到解脱。这绝非愚蠢的标志,而是事情发展的自然结果。这样的人,如果对此种压力继续抗争下去,也必定会在睡梦中把秘密泄露出来,无论这个秘密具有怎样致命的一性一质,也不管被泄露给的人是谁。自然所必需的事有时会对犯下重大罪恶——特别是暗杀——的人心里产生强烈影响,使他们非要把此事透露出来不可,尽管结果必然会让他们自己遭受毁灭。瞧,虽然神圣的法官的确应该为得到那一切发现和忏悔感到荣耀,但之所以取得那些非同寻常的效果,必定也是上帝通常借助自然之手,充分利用了相同的自然因素所致。
我长期与罪行和罪犯打交道,可以对此举出几个相当典型的例子。我被关在新门监狱时,认识一个被称作“夜蝇”的人。我从那时起也不知道他们用这个词指什么,但他是个被默许可以每天晚上出去的人,这时他便会玩一弄诡计,让被称为“捉贼者”的诚实的人次日去发现他的诡计,然后归还前一夜偷到的东西,并因此获得奖赏。这个家伙必定会在睡梦中把自己的整个行为说出来——他采取的每一步,偷到的东西,在哪里偷到的,就好象他醒着时所讲的那么肯定。所以他被放出监狱之后,不得不把自己锁起来,或者被他的老板起来,这样谁也听不到他说话。但另一方面,假如让他把一切详细情况都讲出来,把四处去所取得的成功充分告诉任何朋友、同伙或老板——我可以这样称他们——那么一切都会变得正常,他也会像其他人一样安然入睡。
由于这样发表关于我生活的故事在于让人看到其中所包含的应有寓意,让每个读者获得启发、告诫、警示和改进,所以我希望别认为上述一事毫无必要地偏离了正题——因为有些人对于自己或他人心中的重大秘密是非讲出来不可的。
在这种负担的压迫下,我对于上述处境感到苦恼,唯一的安慰是我尽可能让丈夫了解一些情况,我认为它们会使他相信我们有必要考虑在世上别的地方定居的事。下一个我们所面临的需要考虑的是,我们应该去哪里的英国殖民地定居。丈夫对于这个地方完全陌生,对一些地方的位置甚至没有一点地理知识。而我直至写到这儿时也不知道“地理”一词的意思,只从长期与来往于那里的人们的谈话中有了一般知识。我明白:马里兰、宾夕法尼亚、东泽西和西泽西、纽约、新英格兰都在弗吉尼亚北部,所以它们的气候都更寒冷,,我因此也不喜欢。因我天生喜欢暖和的天气,现在上了年纪,我就更不想到寒冷的地方去了。我便想到去卡罗莱纳,它是英国在美洲大陆上最南边的殖民地。我打算去那儿,更因为我可以在适当的时候,随时轻易能回来过问母亲的财产并要求得到它们。
这样决定之后,我便向丈夫提出离开此地,把我们的财产搬到卡罗莱纳去,我们决心在那儿定居。因丈夫很同意我的第一个看法,即留在我们这儿根本不恰当;我让他确信别人会知道我们的事,而其余的情况我则对他隐瞒着。
但此时我又发现一个困难。那个主要的问题仍然让我感到心情沉重,我无法想到离开这里而又不以某种方式对母亲为我做了什么这样一件大事查询一下。我也难以想到在离开的时候,不让自己过去的丈夫(哥哥)或我的孩子(他儿子)知道,我只是愿意这样做时完全对现在这个丈夫隐瞒,或者对他们隐瞒我有现在这个丈夫。
我对于该如何办想了无数的办法。本来我很乐意让丈夫先到卡罗莱纳去,然后自己再着手办事,但这是不行的,没有我他就不愿意走;他对那里和怎样在任何地方定居都不熟悉。于是我想我们两人先离开,待定居好后我再回到弗吉尼亚,可我知道即使那时他也不愿意和我分开,把他一个人留下。事情明摆着:他天生是个绅士般的人,不仅不熟悉情况而且也有一种惰一性一,待我们真的定居下来后,他会宁愿带着槍钻到林子里去——那儿的人把这叫做打猎,是印第安人通常要做的。瞧,他宁愿那样也不照料一下种植园里的一般活儿。
因此这些就是无法克服的困难,我不知如何处理。我强烈地感到要把自己的情况透露给原来的丈夫,这种感觉难以阻挡,尤其因为我想到假如他活着时我不那样做,也许以后根本没法让儿子相信我真的是同一个人,我就是他母亲。那样我不仅会失去亲人的帮助和安慰,而且会失去母亲给我留下的任何东西。另一方面,我认为让他们知道自己目前的处境绝不恰当,无论涉及到我有一个丈夫的事还是我被作为囚犯带到这里的情况——从两方面考虑我都绝对有必要迁离这儿,以后再从另一个地方、以另一种身份回来。
怀着这些考虑,我继续对丈夫说我们绝对有必要离开波托马克河,因在这儿我们会很快被人们知道,而假如到世上任何别的地方去,我们就可以像任何一个家庭那样带着好名声去那儿种植。由于当地居民总是喜欢带着财产的家庭到他们当中去种植,所以我们肯定会受到欢迎,根本不会把自己的处境泄露出去。
我还告诉他自己在这里有几个亲戚——我现在不敢与他们相认,因他们不久便会知道我到这里来的原因,让我的情况暴露无遗——所以我有理由相信已故的母亲在这里给我留下了什么,也许数量不少,我很值得花时间去查询一下。可是要这样做也必然会公开暴露我们的情况,除非我们离开这里;然后不管在哪里定居我都可以再回来,好象是来看望我的哥哥和侄子们,与他们相认,并查询一下属于我的东西,受到尊敬,同时获得公正的对待。而假如我现在这样做,便只会遇到麻烦,比如强行去得到自己的东西,并遭遭遇诅咒、反抗和各种侮辱,而这也许是他不忍看到的。假如不得不提出合法的证据,以证明我真是她的女儿,我也许会措手不及,只好到英国去求助,最终有可能失败,得不到自己的财物。凭着这些理由,丈夫至此又知道了所需要的整个秘密,我们便决定离开,到另一个殖民地去寻找定居处,而一开始就把卡罗莱纳选定了。
为此我们着手了解去卡罗莱纳的船只,很快便得知在河湾的另一边——如人们所说——即在马里兰,有一艘满载大米和其它货物的船从卡罗莱纳驶来,并将返回那里。得到这个消息后我们租了一只单桅帆船装运货物,仿佛要与波托马克河永别一般,带着自己所有的东西向马里兰驶去。
这是一次漫长难受的航行,我丈夫说比他从英国来这里的整个航行还糟糕,因天气恶劣,河水汹涌,船小又不方便。在沿波托马克河驶了足足100海里时,我们来到一个被叫做威斯特摩兰郡的地点。这条河迄今是弗吉尼亚最大的河流,我听说也是世上流入另一河流而非直接进入海里的最大河流;在穿越它的过程中我们遇到了恶劣天气,时时面临极大危险,因虽然人们只把它叫做一条河,但它经常都极其广阔,以致我们来到河中间时一连数里格都看不见河岸。接着我们穿越切莎皮克大湾,它就是波托马克河涌一入的地点,有近30海里宽,这样我们的航行足足有200海里,而载着我们所有财产的船只又是如此简陋拙劣。假如不幸遇到意外,我们最终会多么悲惨啊——比如失去财物,只留得一命,在一个荒凉陌生的地方被弄得赤身一裸一体,一贫如洗,在整个附近没有一个朋友或熟人。一想到这我就感到十分恐惧,即便在危险过去之后。
唔,经过5天的航行后我们来到被称为“菲力点”的地方,发现去卡罗莱纳的船已装载好于3天前离开。这让人失望,然而我是不会为任何事气馁的,对丈夫说既然去不了卡罗莱纳,而我们到达的这个地方又肥沃有益,我们不妨看看能否在这儿找到改变处境的办法,如果他喜欢的话我们也可在此定居。
我们立即上了岸,可是发现这里没有任何供生活或储藏东西的方便条件。不过我们在这儿遇到一个相当诚实的基督教贵格会教徒,他指点说我们可以去东边约60英里远的一个地方,就是说在这河湾的入口附近。他说他就住在那里,我们可在那儿安顿下来,要么开始种植,要么等找到另一个更便利的地方再去种植。他很热情地邀请我们去,我们就同意了,这个贵格会教徒也与一道同行。
我们在这儿买了两个仆人,即一个坐一艘利物浦的船刚上岸的英国女仆和一个黑人男仆——对于所有打算在那儿定居的人这些都是绝对必需的。这个诚实的贵格会教徒对我们很有帮助,待到达他所建议的地点时,他为我们找了一间贮藏货物的便利的仓库,以及我们和仆人的住处。大约两个月后,在他的指点下我们从当地政一府那里买下一大片土地,以便建立自己的种植园。这样就把去卡罗莱纳的念头完全搁在一边,因在这儿我们受到相当不错的欢迎并了有方便的住处,直到我们能够把事情准备好,让足够的土地得到治理,还有了建造房屋所需要的材料。这一切都在那个贵格会教徒的指点下办成,所以一年下来我们让近50英亩土地得到整治,一部分圈为私有,有的种上烟叶,虽然不多。另外我们有了园圃和谷物地,足以让仆人也有蔬菜和面包吃。
此时我极力说服丈夫让我回到河湾那边去打听一下朋友们。他现在更愿意一些,因除了从他们所说的打猎中消遣外——他很喜欢打猎——他自己手头还有足够的事要做。的确我们两人经常对视着,有时真感到无比快乐,这是由于我们想到现在的处境远远比过去好了,不但比在新门监狱时好,而且也比我们从事那种邪恶勾当期间最顺利的时候还好。
我们目前的情况非常不错。我们用35英镑现金从殖民地的业主那里买到土地,只要我们活着时就有一个足够大的种植园;至于孩子,我如今已不可能再有了。
而我们的好运并没就此结束。如上所述,我穿过河湾去了我的哥哥——曾经是丈夫——住的地方。不过我没有到先前那个村子,而是沿波托马克河东面被叫做拉帕汉诺克河的大河驶去,这样到达了他那个巨大的种植园背面,然后从一片可以通航的流入拉帕汉诺克河的小湾来到离他的种植园很近的地方。
这时我已完全下定决心直截了当地去找哥哥(丈夫)并告诉他我是谁。只是我不知道他会有什么样的心情,或者说我这样鲁莽地去拜访他会使他有多么生气,我便决定先给他写一封信让他知道我是谁,告诉他我不是凭着过去那种关系——我希望他已经把它忘了——来找他麻烦的,而是作为一个妹妹来向哥哥寻求帮助,因母亲去世时曾给我留下一些财产,我相信他在此事上会公正地对待我,特别是考虑到我千里迢迢来寻求得到它。
我在信中对于他儿子说了一些非常温和亲切的话,我说他知道孩子也是我的,由于我嫁给他也正如他娶我一样没有罪——我们当时谁都不知道彼此是亲戚——所以我希望他能满足我看一下自己唯一的孩子的强烈渴望,也让孩子看到一个年老体弱的母亲对他怀着怎样深厚的感情,而我在他心里从来没有什么印象。
我确实相信他收到这封信后会马上把它拿给儿子看,知道他的视力很不好,无法看清。可结果还要好些,由于视力差,他便让儿子拆开所有给他寄来的信;在我的信差把信送去时老先生不在家里或到别处去了,所以信就直接交到我儿子手里,他打开信并读了其中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