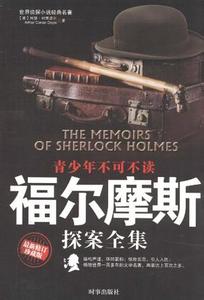第35章
一会儿后他把信差叫进去,问让送这封信的人在哪里。信差告诉了地址,大约有7英里远,于是他让信差等等,让人准备好一匹马,带上两个仆人跟着信差到我这里来了。请任何人判断一下吧,信差回来对我说老先生不在家,但他的儿子与自己一起来了,这时我感到多么惊愕啊!我简直给惊呆了,不知道会是和平还是战争,也不知如何是好。然而我只有短暂的思考时间,儿子就在信差后面,此刻他走进我的住处,在门口问信差什么。我听不清楚,猜想大概在问派他去的女士是谁?因信差说:“在那儿,先生。”听见这话他径直朝我走来,吻我,把我抱在怀里,激动万分地与我拥抱,以致说不出话来;但我能感觉到他像一个只能无声地哭泣的孩子那样胸口起伏着,颤一动着。
我发现(这并不困难)他不是作为陌生人而是作为儿子来到母亲身边————确实是一个从不知道自己母亲是啥模样的儿子,我心中的喜悦无法表达或形容。一句话,我们母子俩俯在彼此身上哭了很久,最后他先开口说话。“亲一爱一的母亲,”他说,“你仍然活着?我根本没想到会亲眼看见你。”至于我,我好长时间什么也说不出来。
我们两个恢复一点平静并能够谈话后,他把情况告诉了我。他说他没把我的信给父亲看,也没说什么;一奶一奶一留给我的东西在他手里,他会公正地对待我,让我完全称心如意;至于父亲,他已年老体弱,身心都不好,极其烦躁易怒,几乎成了瞎子,什么都不能做。对于这样一件难办的事他怀疑是否应了解一下该如何行动,所以他就亲自来了,既是为了满足自己见到我的愿望——他对此无法克制——又是为了让我知道情况后,由我自己决定是否与他父亲相认。
这真是处理得非常谨慎明智,让我发现儿子已成了一个有理一性一的男人,用不着我指点了。我说我并不吃惊他父亲成了他所说的那个样子,因为在我离开时他的大脑就受了点影响,而他的烦躁主要由于我在知道他是我哥哥后,不愿听从劝告仍与他作为夫妻一起生活。我说他比我更了解父亲的现状,所以该怎么办我乐意听他的意见;对于见他父亲的事我并不在乎,既然已先见到了他——他已把最好的消息带给我,即他的一奶一奶一把留给我的东西托付给了他,他现在已知道我是谁,我便毫不怀疑他会照自己说的那样公正地对待我。然后我又问母亲去世多久了,在哪里去世的,并讲了这个家庭的许多详细情况,使他对于我的的确确就是他母亲的事没有了丝毫怀疑。
儿子接着问我住在哪里,情况怎样。我说我在河湾的马里兰那一边有个特别的朋友,我就住在他的种植园里,那个朋友与我坐同一艘船从英国来;至于在河湾那边他住的地方,我并没有属于自己的住处。他说如果愿意我可以同他回家一起生活,直到死去,而父亲谁也不知道,绝不会猜到我是谁。我考虑片刻,说虽然离开他去别处生活实在让我非常不安,但我也不能认为同他生活在一座房子里,总是面对着那个曾给我平静的生活带来巨大打击的可怜人,会是世上最让人愉快的事。尽管我会很高兴有他(我儿子)作伴或者尽可能离他近一些,但我却无法想到住在那座房子里自己还必须保持克制,害怕会在谈话中把自己暴露。在同作为我儿子的他的谈话中,我必然会畅所欲言,而这就会使整个事情被暴露,那无论如何都是不利的。
他承认我说得对。“不过,亲一爱一的一妈一妈一,”他说,“你要尽量离我近一些。”于是他让我骑到马背上,把我带到与他自己的种植园相邻的另一个种植园,,让我在这儿受到最好的款待——即使在他家里也只能这么好了。他把我留下后便回去,说次日再来谈谈那件主要的事情。他一开始就叫我姑母,拿了一些钱给那儿的人——他们好象是他的佃户——让他们对我尽量尊重。他离开大约两小时后,便派来一个女仆和一个黑人男仆侍候我,我的晚饭也准备好了。这样我仿佛来到一个新世界,几乎开始想到要是根本没把兰开夏郡的那个丈夫从英国带来才好呢。
然而这个愿望也并非出于真心,因我像一开始那个非常一爱一自己兰开夏郡的丈夫,作为一个男人他是最值得享有这种一爱一的。而我这里只是顺便说说。
次日差不多在我刚起床后儿子就又来看我。谈过一会儿话,他先取出一只鹿皮袋给我,里面装有55块西班牙皮斯托尔,说是给我的从英国来的费用;虽然他不应该打听,但他应该想到我身上没有带多少钱,人们通常都不会带很多钱到那个地方来。接着他拿出一奶一奶一的遗嘱念给我听,由此表明她把约克河岸的一个种植园以及园里的仆人和牲畜都留给了我及我的继承人(假如我有孩子),并把它们托付我的这个儿子,让他一旦得知我的消息后就交付给我;如果我没有继承人,那么我通过立遗嘱把财产留给谁都行;不过她把种植园的收入留给了该儿子,直至得到我的消息;如果我已不在人世,那么财产归他和他的继承人所有。
这个种植园虽然在另一个地方,但他说他并没有出租,而是交给一个雇工头儿管理,因为他自己管理着附近父亲的种植园,只是每年过去照料三四次。我问他觉得那个种植园能值多少,他说假如我拿去出租他每年可以给我约60镑,但假如我要靠种植它为生,它的价值会多得多,他认为我每年能有约150镑的收入。但鉴于我可能要么在河湾那边定居,要么想回英国去,他便说如果我让他做管家,他会像管理自己的种植园一样好好照理它,并相信他应该能每年给我送来价值约100镑的烟叶,有时会更多。
这些就是我所得到的无比奇异的消息,也是我以前从没有经历过的事情。我的心也的确更加庄重地(我想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庄重)仰望着上帝之手,满怀感激之情——是上帝之手为我创造了这样的奇迹,而我自己也许是被允许在世上生存下去的邪恶的最大奇迹。我必须另外注意到的是,不仅在这一次,甚至在所有其它让我感激的场合,当我意识到上帝对我那么仁慈,而我却一直以邪恶的行为回报他,此时我过去的邪恶和令人憎恨的生活就显得可怕无比,我对于它也憎恶到极点,并以此自责。
不过我把这些想法留给读者去加以提升吧,毫无疑问你们会看到其中的原因;我则继续讲述事实。儿子待我那么亲切,为我提出多么好的建议,使我在听他谈话时几乎泪流不止。的确,我只是在略为平静一点后才能和他说几句,不过最后我奇迹般地能够表达自己的意思了,说我很高兴把留给我的东西交到自己儿子手里,至于继承权的事,我在世上除他外没别的孩子,如果结婚也已过了生育的年龄。因此我希望他起草一份文件,我会在上面签字,同意我去世后所有财产都归他和他的继承人。同时我微笑着问他为啥到现在还是个单身汉。他很快温和地回答说,弗吉尼亚并不产生很多的妻子,既然我谈到回英国去,不妨从伦敦给他找一个妻子来。
这便是我们第一天谈话的主要内容,也是我有生以来遇到过的最快乐的一天,它使我得到了最为真实的满足。这以后他每天都来看我,大部分时间陪着我,并把我带到他的几个朋友家,让我受到极为尊重的款待。我还有几次去他自己家里吃饭,他总是注意不让半死的父亲在近旁,以免我们彼此看见。我送给他一件礼物,那是我最值钱的东西——一只金表——我说自己箱子里有两只,在他第三次来看我时我碰巧带着一只,就给了他。我说自己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可以赠送,不过希望他为了我时而吻一下这只表。顺便说说,我的确没告诉他这是我在伦敦的聚会所里从一位女士身上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