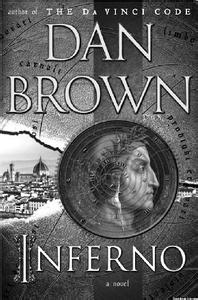在那昏暗、静寂的火车站上,两个特工人员把总统从轿车里扶出来,搀他站稳了脚步。他的个子高出他们许多,穿了一件天鹅绒领子的大衣,头上那顶灰色的宽檐软帽拉得很低,被凛冽的寒风吹得呼扇着。他一只手抓着个特工人员的胳膊,另一只手拄着手杖,一瘸一拐地朝有栏杆的斜坡踱去。走到跟前,他戴上手套,一路上颠着双腿,把自己拖上了列车殿后一节的车厢。站在若干码之外的维克多-亨利可以望到他那宽阔的肩膀在大衣下面起伏着。一个高身材、帽子上插了一支摇摇晃晃的棕色翎毛的女人手里拿着一张迎风抖动的纸跑过来,碰了维克多-亨利的胳膊一下。“上校,你上总统这个车厢。”
走上斜坡,帕格才明白总统为什么戴上手套:那钢制的栏杆很凉,把他手上的皮肤都粘住了。一个侍役领着维克多-亨利走过餐具室。这里,另一个侍役正用做鸡尾酒的震荡器哗嘟哗嘟地摇着冰。“先生,您呆在这儿。等您做好准备,总统就请您过去陪他。”
这是一辆普通的普尔曼卧车隔出的一个房间,强烈的火车气味也和一般车厢一样。绿色的椅套上满是尘埃,也破旧了。维克多-亨利把大衣和帽子挂在一个小套间里,拢了拢头发,剔了一下指缝,又用软纸在他那双擦得锃亮的皮鞋上轻轻揩了揩。火车开始慢慢滑行,既不震动,也没有声响。
“坐下,坐下,帕格,”总统坐在一张安乐椅上向他招手。
“你喝什么?有威士忌加柠檬,因为哈利整晚上都喝它。可是咱们配点什么都可以。”
“总统先生,威士忌加柠檬就好得很。谢谢您。”
哈利-霍普金斯懒洋洋地坐在绿沙发上说:“你好,上校!”
按说生病的是罗斯福,其实,两个人比起来霍普金斯的样子更难看:消瘦,胸部凹陷,肤色发灰。总统的脸色是红润的——也许在发烧,他那眼眶发黑的眼睛炯炯有神,潇洒的红色蝴蝶结和他那宽大面庞上的快活、轻松的神情很相称。坐在椅子上,他体格魁梧,虽然从裤管上可以看出他的腿可怜地只剩下了骨头。帕格心里忽然闪过一个念头:华盛顿和林肯也都是个子高得非凡的。
“帕格,你对于诗怎么样?”总统那种有教养的口音这个海军军官听了总感觉有些不自然。“你可知道有一首诗最后的两句是:‘没有我不肯坐的火车,也不管它往哪里开。’1啊,这就是我眼下的感觉。仅仅上了这辆火车就使我觉得好了一倍。”总统把手背放在嘴上,粗声咳了一下。“哦,算好了九成吧——假如这是条轮船,那就会是一倍啦。”
1引自美国女诗人米莱(1892-1950)的诗集《旅行》第三节。
“先生,我也更喜欢坐船。”
“怎么,你以前抱怨的话又出来了,水兵?”
“没有,先生,真的没有。我很高兴在作战计划处。”
“是吗?那么我听了很高兴。自然,我丝毫也不知道你跟那些英国伙伴在搞些什么名堂。”
“先生,我明白这一点。”
总统逗趣地把眉毛挑了挑,接着说下去:“我连一点点影子也不知道。昨天国防部长收到了你起草的那个东西,等它蹦回到勃纳-沃克勋爵手里时,他会看到上边修改的地方象是我的笔迹。那也只不过是偶然相象。”
“我记住这一点。”
“一定要记住。你记得,在转交的那封信第一页上,有一句是这么开头的:‘当美国参战的时候’。一个和我的手迹一模一样的人把那个十分可怕的字句划掉了,改成‘万一美国被迫参战的时候’。这个改动不大,可是十分重要!”这时,侍役送来饮料。总统拿了一高脚杯桔子水。“大夫的命令:大量大量的果子汁。哈利,那东西你带来了吗?”
“在这儿哪,总统先生。”
“那么,咱们就动手研究吧。我想吃顿快餐,然后想法睡它一会儿。帕格,你在火车上睡得好吗?”
“睡得好,先生,只要能把车里的温度调节好。不过一般要末热得烤人,要末冷得可以结冰。”总统把头朝后一仰。“哈,哈,听我告诉你一个国家机密:美国总统也遇上了同样的麻烦。他们正在替我建造一辆特殊的钢甲车。我已经告诉他们:别的我不在乎,但是暖气设备一定得灵!哈利,咱们叫快餐吧。”他看了一下表。“帕格,你饿吗?我饿啦。我再告诉你一个国家机密:白宫的伙食大有改善的余地。告诉他们我要鲟鱼和鸡蛋。我想吃鲟鱼和鸡蛋已经想了好几天啦。”霍普金斯到前边去了。
就帕格所知,总统这个车厢是一辆正规的普尔曼游览车改装成一间起居室的样子。他本以为总统的车会更神气些。罗斯福一只胳膊肘靠在椅子的扶手上,另一只放在膝盖上,以宁静、豪迈的神情朝车窗外望着。“我确实觉得一分钟比一分钟好。你们没法设想我是多么喜欢摆脱那个电话。你的孩子们怎样?一个在海军里开飞机,还有一个是个年轻的潜艇军官。”
维克多-亨利知道总统喜欢炫耀他的记性,可这仍然使他很吃惊,很感动。“他们都很好,先生,可是您怎么会记得?”
总统带着有点孩子气的得意神气说:“啊,帕格,一个搞政治的就得学习大象的美德:学它的记性好,学它的皮厚,自然,还得学它那条长而什么都要嗅嗅的鼻子。哈哈哈!”
霍普金斯回来又坐到沙发上了,累得腰都弯了下来。他打开公事包的拉链,然后交给亨利上校一份三页长的文件,上面还附着一张深色的复制品。“你看看这个。”
帕格读第一页时带着怀疑,然后转入惊异——这时,火车的轮子正徐缓地发出咔噔咔噔的声音。他把文件一页一页地看完之后,就望望霍普金斯,又望望总统,不想先开口。拿在他手里的是陆军情报方面得到的一份惊人的德国作战命令的摘要,是德国陆军里一批反纳粹的陆军军官有意偷偷塞给美国驻柏林大使馆的一个职员的。帕格对这个人很熟悉,但是他完全没料到这个人会起传递情报的作用。弗兰克林-罗斯福说:“你认为是真的吗?”
“哦,先生,从第一页那个影印的东西来看,倒确实和我见到过的德国军事文件很相象。标题很象,字体、分段等等都很象。”
“内容呢?”
“如果是真的话,那么,总统先生,这可是在情报方面一个难以置信的突破。”
总统笑了笑,疲惫地表现出对一个下级人员的天真想法的宽容。“如果这两个字是语言里最难解的字眼。”霍普金斯沙哑地说:“在你看来,这内容象是真的吗?”
“我说不上,先生。我对俄国地理没那么熟悉。”
“咱们陆军方面的人觉得它似真似假,”霍普金斯说。“上校,干吗会有人伪造象这样一个令人大吃一惊的文件——一份完整的入侵苏联的作战命令,包括那么大量的细节?”
帕格思考了一下,小心翼翼地说:“哦,先生,也许是希望用这方法来刺激苏联,让它动员起来,从而挑起两个战场的战争。那样的话,德国军队也许会推翻或杀掉希特勒。另外,也可能是德国情报人员故意玩的一个花招,来试探咱们和俄国人究竟接近到什么程度。种种可能性都有。”
“麻烦就在这里,”总统打了个哈欠说。“咱们的驻俄大使要求我们务必不要把它转达给俄国人。他说,莫斯科已经到处是这类东西。俄国人认定这些都是从英国情报方面来的,为了在斯大林和希特勒之间制造麻烦,以便把德国人从英国背上转移开。”总统吃力地咳了差不多一分钟。他朝椅背上仰了仰,喘过一口气来,从车窗里望着火车正在经过的一个小镇上的街灯。忽然,他的样子显得厌烦了。
哈利-霍普金斯朝前弯了弯身子,把酒杯在双手之间平衡着。“目前存在着一个要不要把这个文件交给这里驻华盛顿的俄国大使的问题,帕格,有什么看法吗?”
帕格犹豫了。这样一个政治性问题超出了他所能掌握的范围。罗斯福总统带着些不耐烦的神情说:“帕格,说呀。”
“我赞成交给他。”
“为什么?”霍普金斯说。
“交给他有什么可损失的,先生?假若是真的话,在咱们和俄国佬的关系上就大大赢得一分。如果是假的话,那又能怎么样?反正他们不会比现在更不信任咱们。”
哈利-霍普金斯脸上的疲惫紧张在一副温暖和蔼的笑容中消失了。“我认为这是个十分精明的回答,”他说。“因为这也正是我对自己所说的。”他把文件从帕格手里拿了过来,又放回公事包里,拉上拉链。
“鲟鱼和鸡蛋做好了吗?”弗兰克林-罗斯福说,“我已经等不及啦。”
“总统先生,我看一下去。”霍普金斯马上站了起来。帕格在那狭窄的床位上躺了一个来小时,辗转不能成寐。车厢里一下热得叫他出汗,一下又冷得可以结冰,他怎么拨弄那个调节器也不中用。最后他索性让它冷下去了,因为他在冷空气里睡得还比较好一些。火车缓慢、匀称的运动也开始催他入睡。
梆,梆。“先生,总统想找您谈谈。您要穿件浴衣吧,先生?总统嘱咐说,不必穿整齐了,就到他房间去。”
“谢谢。我有浴衣。”帕格瑟缩地从他冰冷的房间来到总统这间过暖的寝室。弗兰克林-罗斯福那张著名的大下巴的脸、那副夹鼻眼镜和那杆轻快自如的烟嘴,衬着一条蓝色睡裤、一件沾上咖啡斑点的灰运动衫和累垮了的庞大身材,看上去十分奇特。总统稀薄的头发是蓬乱的,他的眼睛是朦胧的。把他的特有风格和总统的尊严剥掉之后,他就和许多躺在床上的老人一个样:羸弱、衰颓而且忧郁。寝室里有一股药味。这景象使维克多-亨利感到十分不安,因为总统看来是那样虚弱,那样病容满面,那样无足轻重。同时,也因为罗斯福只比他大上七八岁,可是看来已经老态龙钟了。蓝色的毯子上面堆了一叠文件。他正用铅笔在手里拿着的一张上批着什么。
“帕格,我打扰你的美梦了吧?”
“一点也没有,先生。”
“坐一会儿,老伙计。”总统用两个指头把眼镜摘了下来,使劲按摩一下他的眼睛。随着火车在一道颠簸不平的铁轨上咔噔作响,床畔的几只瓶子也碰得叮当乱响。“哎呀,我眼睛真疼。”他说。“你眼睛疼吗?什么办法也不灵。每逢这个鼻窦炎一发作,眼睛总是疼得更厉害。”他把文件夹起来,撂在毯子上。“帕格,我曾经答应自己要做一件事——要是能找到时间的话——那就是,把仅仅一天之内送到我这里处理的事务写成一份备忘录。随便挑哪一天,任何二十四小时中间,你看了会大吃一惊。”他在文件上轻轻拍了拍。“那会成为对历史的一个很有价值的间接阐明,你说会不?就拿今天晚上我所处理的这个烂摊子来说。看来维希法国将要和希特勒订全面的联盟。是用停止供应他们粮食、把他们活活饿死进行威胁呢?——这是英国人的建议;还是向他们提供更多的粮食,笼络他们去顶住希特勒呢?——这是咱们大使的想法。可是当咱们向法国人提供更多粮食的时候,德国人就干脆吞下更多的法国人自己生产的粮食。你看怎么办好?……再看这个。”他拿起一份夹起的文件。“日本外长正在跟希特勒会晤。这你从报上已经看到了。他们想搞些什么名堂?咱们是把亚洲舰队从马尼拉调到新加坡,使他们在入侵法属和荷属东印度之前有所顾忌呢?——这是英国人的想法;还是为了慎重起见,干脆把太平洋舰队全撤回来,撤到西海岸?——这是海军作战部长所想做的。我倒想顺便听听你对这个问题的意见。另外,还有个一触即发的问题——亚速尔群岛。咱们要不要在希特勒入侵葡萄牙夺取它们之前先下手拿过来?或者,咱们要是先下手会不会反而迫使希特勒入侵葡萄牙?”
总统继续轻轻弹着其他文件,就好象它们是肉铺或杂货店里的帐单似的。“啊,对了,《选拔兵役法案》。这方面情况很糟。这是史汀生打来的报告。国会原来授权的法案在几个月内就要满期了。现在又得为这个开始一场新的立法斗争。可是紧接着《租借法案》这个战役,国会不会再有心情来延长征兵的期限了。如果他们不延长,军事上咱们就将处于无能为力的状态——这是摩根韬的看法。财政部想迫使我去冻结德国、意大利在美国所有的投资,但是国务院不同意,咱们在他们两国的投资数额是他们在咱们这里的四倍——又是摩根韬。英国人同意把他们在这里的投资全部卖掉,把他们手里所有的美元给我们,摩根韬已经告诉国会他们要这样做,可是如今英国人又裹足不前了。这类事情还有的是。老伙计,这只是一天工作中间的一部分。一个历史学家一定会对这样的横断面感到兴趣,会不?我曾叫人查了一下威尔逊和林肯的档案,他们从来也没有处理过这么多事务。我终归有一天要把这份备忘录写出来。”
罗斯福咳得很厉害,时间很长。他闭上眼睛,蜷缩一下,一只手放在背后。在东摇西晃的火车里,这个姿势使他失去平衡,庞大的身子眼看要象只倾斜了的木桶似的翻倒了。维克多-亨利赶快奔过去扶稳了他的肩头,可是总统长而有力的胳膊抵住了床边。“谢谢,帕格,这列火车每小时原定不应超过三十五英里。他们在一点点加快呢。”他搓了搓背。“我一咳嗽,就刀扎似的疼。可是麦克因台大夫告诉我说准是伤了筋,也就是说,不是胸膜炎。眼下我实在不能得一场胸膜炎。我最好再吃点那个咳嗽药。请你递给我那把汤匙和那个装着红药的瓶子。谢谢你,老伙计。”总统吃了一汤匙药,作了个鬼脸。象所有夜总会里模仿的那样把他的大脑袋朝一边歪去。罗斯福用他那双充血的眼睛锐利地盯了海军上校一眼。
“帕格,德国潜艇用他们新的狼群战术不断地往西边扩张。目前他们炸沉的数量正在超出咱们的造船厂和英国造船厂联合起来建造新船的能力。你想必已经留心到这一点了。”
“先生,这情况我在我们的会议上已听到过不少了。”
“你相信英国人所说的炸沉的吨数吗?”
“我相信,先生。”
“我也相信。《租借法案》一通过,咱们马上就给地们运送大量物资。可是那批物资只能运到英国,可绝不能运到大洋底下去。这是极其重要的。”
罗斯福提到《租借法案》时口气那么随便,使维克多-亨利大吃一惊。他和英国人一样,正为参议院里的激烈辩论捏一把汗。“先生,您认为《租借法案》会通过吗?”
“哦,这个法案会通过的,”总统漫不经心地说。“可是以后呢?目前有七十条船正在那里等着装货,帕格。这批货就是不能让德国潜艇打沉。英国人需要这批物资。他们更需要看到这批货物到达而鼓起斗志。问题是如何把它们送到冰岛那么远——从那里,英国人自己就能护航了。可是从这里到冰岛,他们没办法。他们的护航线已经不能拉得再长了。那么,咱们怎么办?”
维克多-亨利在总统用询问的目光逼视下,心里忐忑不安地说:“先生,那只有护航。”总统阴郁地摇了摇头。“帕格,你知道在目前一提到护航,下文会是什么。”
在《租借法案》的斗争中,护航这个问题是辩论得最激烈的。拉古秋集团大声叫嚷倘若通过了《租借法案》,战争贩子们下一步势必要求对载着物资的船只提供护航,而护航就意味着立即和德国开战。总统在公开场合所坚持的是美国不改变在大西洋上“中立巡逻”政策,不护航。
罗斯福严峻、红晕的脸上露出皱纹,已为帕格越来越熟悉的那种狡猾、顽皮的神情又出现了。“不过,我正在考虑。比方说,咱们派一个驱逐舰分遣队出去演习怎么样?你明白,不是去护航。完全不是护航。只不过是演习一下护航的程序——也可以说是专业演习。海军经常要演习,不是吗?这是你的本行。那么,假定这批演习的驱逐舰看中了这批运输船,情愿和它们一道航行——你要明白,纯粹是为了演习,而且光是这么一趟。为了避免障碍和牵连,假定一切都做得丝毫不拘形式,不下书面命令,不留记录。你不认为德国潜艇看见有十六艘本逊级的美国驱逐舰在掩护那些运输船,他们会有些踌躇不前吗?”
“踌躇,是会的。可是,总统先生,以后会发生什么情况,那要看他们上级的训令啦。”
“他们早已得到了不许和咱们的军舰发生冲突的训令,”罗斯福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和神情都很冷酷,“那是显而易见的。”
维克多-亨利的脉搏跳得剧烈起来了。“先生,他们可从来也没遇到过咱们的驱逐舰在护航啊。假使一只潜艇开过来,发射一枚鱼雷呢?”
“我不相信会发生这种事,”罗斯福简慢地说。“在英国人接过护航之前,德国人甚至可能一直没发现那批运输船。北大西洋的气候目前恶劣极了。大部分德国潜艇仍然在冰岛的那一边。”他一边说,一边在烟嘴上插上一支烟。维克多-亨利赶紧用他的打火机给他点了火。“谢谢。这可违背了大夫的命令。可是我需要吸一支。帕格,我想办成这件事。我正在考虑,也许你跟着驱逐舰出海去处理这件事。”亨利上校强压下自己的震惊,说:“是,是,先生。”
“这很象上次转让飞机,那件事你办得很好。任何事全靠你用一种最镇定、不动声色、不冒失的方式去办。关键在于不留记录,特别是没有来龙去脉,只是悄悄地、万无一失地把那些船送到冰岛那么远。能做到吗?”海军上校弯着腰坐在那里望着总统也许有一分钟之久。
“能,先生。”
“知情人要限制到绝对最低额。我甚至跟哈利-霍普金斯也没谈过这件事。”
“先生,当然总得让斯塔克将军和金将军晓得。还有,司令官、支援部队和在战术上指挥这项掩护任务的长官。参加演习的其他人员只服从命令就是了。”
罗斯福笑了,喷出一口烟。“好!要是你能限制在三名将军一名军官之内,那就再好不过了。但是许多人员将要参加这次演习,会有些议论的。”
维克多-亨利无动于衷地说:“不会很多。”弗兰克林-罗斯福扬起他的浓眉。“总统先生,要是德国潜艇发动进攻,咱们怎么办?我同意这不大可能发生,可是万一发生了呢?”
罗斯福隔着缭绕的烟圈望着他。“咱们的赌注就押在它不会发生上头。”
“我明白,先生。”
“你要知道如果发生一场交战事件,那就会破坏全部设想,”总统说,“你也明白其他的含义。”
“是,先生。”
“好,现在告诉我,”总统用温和得多的神情说,“老实告诉我你对这个主意的看法。这是我自己想出来的。如果你认为不好,尽管说,可是要告诉我为什么不好。”
维克多-亨利弯了腰朝前坐着,胳膊肘支在膝盖上,用一个食指在另一只手上划着记号。“那么,先生——首先,正象您所说的,德国潜艇上的那些家伙也许根本看不到咱们。要是看见了,他们是会吃惊的。他们一定要通过无线电去请示。我们也许会碰上个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打了再说的家伙,但我看不一定会。我了解德国潜艇上的人。从职业上说,他们是优秀的军官。这是个得向希特勒请示的政策性决定。请示需要时间。总统先生,我认为这批船可以顺利通过。”
“好极啦。”
“可是只能灵一回。这是在政策上给他个出其不意。再来一回就太冒险了。”
罗斯福叹了口气,点着头。“正是这样。整个局势是太可怕了,非冒点儿险不可。英国人说,第二批大规模护航开始之前,他们的许多条被炸伤的驱逐舰就修好可以投入战斗了。咱们也正在赠给加拿大一些海岸巡逻快艇——帕格,这是不能外传的——以便他们协助堵上从这儿到冰岛之间的空隙。这第一批《租借法案》下的物资关系特别重大。”总统把散堆在毯子上的文件收拢一下。“请你把这些放进那个匣子里。”
维克多-亨利关上公文匣的时候,总统正用双臂支着身子舒舒坦坦地钻回毯子里。他打着哈欠说:“和英国人开的那些会怎么样了?”
“整个说来,十分好,总统先生。”
总统又打了个哈欠。“应该开始搞这种类型的联合参谋工作了,这是非常重要的。我对这件事很满意。”他咔的一下把床头的灯关掉了,只留下壁龛上微弱的灯光照着这间寝室。
“他们在新加坡问题上给了你一些麻烦,是不是?”
“先生,实际上我们已经把那个问题丢在一边了。没有解决的办法。”
“帕格,你可以把灯全关上,电钮就在门旁边。”
“是,先生。”
一盏蓝灯和总统的香烟头还在黑暗中发光。他在毯子里发出的声音显得疲倦,还象是半堵塞了似的。“这个问题还会时不时地碰到。他们自然是紧紧地抓住那个帝国不放,可是目前是要打败希特勒。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他们却始终咬定是一码事。那么——帕格,关于那个演习,咱们明天早晨再聊聊。”总统是带着讥讽和洋洋自得来使用这个巧妙字眼的。
“是,是。先生。”
“这趟海上旅行可以使你换换环境,你一定会很开心的。等你回来之后,我想请你、你的太太、你们一家吃顿便饭,安安静静地吃一顿家常便饭。罗斯福夫人时常谈起你。”
“谢谢您,总统先生。我感到十分荣幸。”
“晚安,老伙计。”
烟灰缸里的红烟头熄灭了。正当维克多-亨利伸手抓住门把手的时候,总统忽然说:“帕格,我身边一些最能干的人一直劝我宣战。他们说,战争是无法避免的了,只有宣战才能把人民团结起来,使他们全力以赴地为战争效劳。我估计你是同意他们的。”
海军上校考虑了一下,望着蓝光里那个魁梧的身影。“是的,总统先生,我同意。”
“打仗是件坏事,”总统说,“很坏的事。这个时刻也许即将到来,但目前还没有。在这期间,我只有继续被人称作战争贩子、胆小鬼、优柔寡断的人,全都合成一体了。我就是这样来挣我这份薪水的。好好休息一下吧,帕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