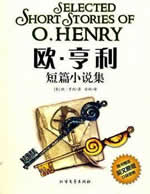《信仰和创伤》之一:牛虻有没有其他选择?
这是第四次面对《牛虻》——小说、大学英语课本、电影、话剧。不同的形式,不同的年龄。每一次的接触都有不同的感受。
虽然伏尼契夫人那忧伤和浪漫的结尾一样打动我的心灵,但我现在觉得“无论我活着,还是死了,我都是快乐的牛虻”这句话只能算一半正确——只有死去、而且是如此这般地死去,牛虻才能算是快乐的,至于他活着的快乐,那是一种符号。
我不想贬低暴力革命,但我对暴力革命的价值却持怀疑态度。尤其是暴力革命鼓吹者经常怀抱个人仇恨并且无限扩大化。所以,我觉得牛虻是一个病态的革命者。在“意大利的独立和自由”之后是对蒙坦里尼主教和上帝的痛恨。这种痛恨是因为曾经热爱,并且同样交织着热爱。
有的时候,人必须直面选择。牛虻选择为革命而死亡,蒙坦里尼主教选择上帝然后死于绝望。但是,人有时候却无法选择。琼玛能够选择什么?她最后的对生活的爱看样子都要被牛虻的那封信带走——马蒂尼能否安抚泪眼婆娑、悲痛欲绝的琼玛?话剧中的吉普赛少女希塔能够选择什么?遭受匈牙利奴役的意大利除了暴力革命,有没有其他选择?这些都是一个个问题。
因为年轻时的亚瑟是那么地信仰上帝、信仰蒙坦里尼,所以才会在受伤之后如此痛恨;因为年轻时候的琼玛是那么信仰革命,所以才会对“背叛”的亚瑟做出伤害之举;因为牛虻是那么地热爱蒙坦里尼主教,所以才会在受到欺骗之后始终耿耿于怀;因为牛虻依然爱着琼玛,所以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展示自己的创伤。
信仰和创伤,联系得如此紧密。
都说牛虻是坚强的,实际上他自己坦露过:“其实我的内心并不那么坚强。”正因为他面对琼玛是一次次的欲言又止、面对蒙坦里尼主教的真情流露,才使得牛虻的形象显得还算丰满。因为这些创伤,也才使得这个病态的革命者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值得同情。
所以我在心里依然忍不住想问一个问题:牛虻有没有其他选择?
当然,顺便也可以再问一下:蒙坦里尼主教有没有其他选择?
没有。
他们注定要互相伤害、然后在绝望和痛苦选择死亡。肉体的死亡是其次,年轻的亚瑟早已死去,沧桑的牛虻无论在出场之前还是出场之后都是为了复仇而活着。
而蒙坦里尼主教,并不像我们曾经认知的那么虚伪。暴力革命仇视非暴力革命,非暴力革命也不会容忍暴力革命。所以,他也别无选择。
越真挚的信仰,会让人越偏执。
革命和上帝,是两种不同形式的信仰。年轻的亚瑟企图同时保留两种信仰,是因为他没有被卷入到两种信仰的齿轮之间。那时候他还没有接纳暴力革命。而经历决定方向,放弃了对上帝的信仰、在皮鞭和暴力之下活过来的亚瑟,只能蜕变为尖刻而决绝的牛虻。但是,曾经拥有过两种信仰的亚瑟不会快乐——任何曾经改变过信仰的人都会遭受这种内心的折磨——我宁愿把牛虻临死前的叫喊“这一槍可不怎么高明”看成是一种革命符号——他终于可以彻底地选择一种信仰,并且为之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