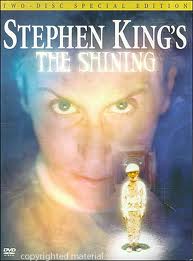我醒来的时候,嘴巴里臭烘烘的,脑袋也嗡嗡响,而且模模糊糊地意识到即将降临的灾难。似我的感觉却不错,相比而言。就在这时,一个令人愉快的声音说道:“感觉好点了吗?”
一个娇小的黑发女郎弯腰看着我。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可爱的小东西。虽然我还很虚弱,但已经恢复到足以欣赏这一切的程度了。她衣着非常古怪:紧身白短裤,一条几乎透明的东西紧裹在她的rx房上,一种类似金属盔甲的东西罩在脖子后面、肩膀上和脊椎骨上。
“好点了。”我承认说,做了个鬼脸。
“嘴里的味儿不好吧?”
“就像巴尔干国家的内阁会议。”
“喝了吧。”她递给我一杯东西;香料味很浓,还有点辣,但立刻冲走了嘴巴里的异味。“别,”她继续说道,“别咽下去。像小孩一样吐出来,我去给你拿点水。”
我照办了。
“我是多丽丝·马斯登,”她说,“你的日班护士。”
“很高兴认识你,多丽丝。”我说,饶有兴趣地盯着她看,“说说,为什么这副打扮?不是说我不喜欢这样,但你看上去就像连环漫画里的流浪者。”
她低头看了看自己,咯咯地笑了。“我觉得像个舞蹈演员。不过你会习惯的——我已经习惯了。”
“我已经习惯了。我喜欢这副打扮,不过为什么穿成这样?”
“老头子的命令。”
我又一次问为什么,然后我知道了原因,我又一次感到糟透了。我不再说话。
多丽丝说道:“吃点午饭吧。”她端起餐盘,坐在我的床边。
“我什么也不想吃。”
“张嘴,”她语气坚定地说,“要不我就揉进你的头发里。来吧!真乖。”
趁吞下几口饭的空隙,我费劲地说:“我感觉相当好。给我来点‘旋转’我就能站起来。”
“你不能服用兴备剂。”她直截了当地说,一边继续往我嘴里喂饭,“特种饮食,多休息,等会儿也许会给你一点安眠药。这都是老头子的命令。”
“我怎么了?”
“极度疲劳,饥饿,我…生中见过的第一例坏血病。还长了疥疮,生了虱子——不过疥疮已经治好了,虱子也杀灭了。现在你都知道了,如果你敢跟医生说是我告诉你的,我就当面说你撒谎。翻过身去。”
我翻过身,她开始给我换药。我好像浑身都长了疮;她用的药物有点刺痛,接下来的感觉是凉。我在思索她告诉我的情况,努力同忆我在主人控制之下是如何生活的。
“别哆嗦。”她说,“很痛吗?”
“我没事。”我告诉她。
我确实想停止哆嗦,平静地理清思绪。就我的记忆而言,在这期间,大概是三天的时间里,我水米未进。洗澡?让我想想——我根本没洗过澡!我每天都刮脸,还换上一件干净衬衣;但这是伪装的必要部分,而且主人也是知道的。
另外,根据我的记忆,自从我偷了那双鞋穿上之后,在老头子抓到我之前,那双鞋就从来没脱过——开始穿的时候,那鞋子很紧。
“我的脚现在是什么形状?”我问。
“别管闲事。”多丽丝说,“转过身来躺下。”
我喜欢护士;她们平和、朴实,而且非常宽容。我的夜班护士布里格斯小姐没有多丽丝那么令人垂涎;她长着一副患了黄疸性肝炎般的马脸——但对于她这样年纪的人来说,身材还不错。身体结实,保养得很好。她的那套音乐喜剧里的打扮和多丽丝的属于同类,可她却穿得一本正经,走起路来活像掷弹兵。而多丽丝走路的时候会轻轻扭动身子,真是赏心悦目。愿上帝保佑她。
我半夜醒来感到恐惧的时候,布里格斯小姐拒绝给我安眠药,但她却和我打起了扑克,赢了我半个月的薪水。我想从她那儿了解总统的情况,因为我想这段时间已经足够老头子行动了,或赢或输总会有个结果了,可她却守口如瓶。她甚至不承认自己知道任何关于寄生虫、飞碟和诸如此类的事情。尽管这是她穿着一套戏装坐在那里的唯一原因!
我问她当下有没有什么新闻,可她坚持说她最近一直忙着看电视剧。于是我让她把立体电视搬到我的房间,这样我就可以看新闻了。她说必须征求医生的意见,因为我在需要“静养”的名单上。
我问她我什么时候才能见到这个所谓的医生。她说她也不知道,因为医生最近很忙。
我们医院里住了多少病号?她说她确实记不清了。就在这时,叫她的铃声响了,她离开了,可能是去看另一个病号了。
我收拾了她。她离开后,我在下一副牌里做了手脚,让她拿了满把烂牌。再以后,我怎么也不肯和她打牌了。
后来我睡着了。叫醒我的是布里格斯小姐,她用冷冰冰、湿乎乎的洗脸巾抽我的脸。她把我安置好,准备吃早饭,随后多丽丝接了她的班,把早饭端给了我。这一次,我是自己吃的,我一边吃,一边想从她嘴里套出点消息——收获和我对付布里格斯小姐时一样。护士们总是把医院当成弱智儿童幼儿园。
早饭后,戴维森过来看我。“听说你在这儿。”他说。他只穿了短裤,其他什么也没穿,只有左臂缠着绷带。
“你听说的比我多多了。”我抱怨说,“你怎么了?”
“蜜蜂蜇了我。”
我不再提他的胳膊;如果他不愿意告诉我他是怎么受的伤,那是他的事。
我继续道:“老头子昨天来了,听了我的汇报就突然离开了。从那以后你见过他吗?”
“见过。”
“情况怎么样?”我问。
“还是说说你自己的情况吧。你怎么样?好了吗?那些负责心理分析的伙计们允许你重新接触机密了吗?”
“难道还会怀疑我不成?”
“你活下来了,这就是大疑问。可怜的贾维斯就没救过来。”
“啊?”我还没想过贾维斯的事,“他现在怎么样了?”
“不能说好。一直没有缓过来,昏迷不醒,第二天就死了——你离开的第二天。我是说你被他们抓住的第二天。没有明显的死因——就是死了。”戴维森打量了我一番,“你一定很坚强。”
我并没有感到自己很坚强。只觉得软弱的泪水又一次涌了出来。我眨了眨眼睛,把泪水挤回去。
戴维森假装没看见,继续和我说话:“你真该看看你溜走后所引起的大骚乱。老头子紧跟着你追出去,身上什么都没有,只有一把手枪,加上满脸凶相。他本可以抓住你。我敢打赌——却被警察抓住了,我们不得不把他从监狱里弄出来。”戴维森咧嘴笑了。
我自己也露出了些许笑容。老头子一身呱呱坠地的打扮,单枪匹马地去冲锋陷阵拯救世界——这种事,真是既英勇又傻气。“真遗撼,我没有看到。后来又怎么样了’”
戴维森小心谨慎地上下打量了我一番,然后说道:“等一下。”他出门离开了一小会儿,回来后说,“老头子说没关系。你想知道什么?”
“一切。昨天发生了什么情况?”
“那件事我在场,”他回答说,“于是我变成了这样。”他朝我晃了晃受伤的胳膊。“我算幸运的。”他接着说,“三名特工牺牲了。真是好一场轩然大波。”
“可怎么会这样?总统呢?他——”
多丽丝匆匆忙忙地进来了。“哦,你在这儿呢!”她对戴维森说,“跟你说了让你躺在床上。你现在该去摩西医院做修复手术了。救护车都等了十分钟了。”
他站起来,冲着她咧嘴笑了,还伸手在她脸上捏了一下。“我不到,宴会就开不了席。”
“好啦好啦,快点。”
“来了。”他和她一起走了出去。
我大声喊道:“嗨!总统怎么样了?”
戴维森停下来,扭头道:“哦,他?他没事——连划伤都没有。”他走了。
几分钟后,多丽丝怒气冲冲回来了。“病人!”她说,口气像骂人,“知道为什么把他们叫‘病人’吗?因为你必须有耐心才能忍受他们1。我至少在二十分钟以前就该给他打针了;可我直等到他进了救护车之后才能给他打。”
【1英语中总统是:president;病人是:patient;耐心是:patience。这三个单词发音相似。】
“为什么要打针?”
“他没有告诉你?”
“没有。”
“好吧……没理由不告诉你截肢,移植,左臂下半部分。”
“噢。”好吧,我想我不可能从戴维森那里听到事情的结局了,移植一截新的肢体是件大事,他们通常会把病人关上整整十天。
我在想老头子:昨天的大事之后,他还活着吗?当然,我提醒自己,戴维森和我说话之前曾经请示过他。
但这并不是说他没有受伤。我又开始套多丽丝的话。“老头子怎么样了?他也是病号吗?告诉我是不是违反了你们神圣的搪塞大法?”
“你的话太多了ll”她说。“该给你增加早上的营养了,你也该睡一会儿了。”她拿出一杯牛奶,就像变魔术。
“说,,姑娘,要不我把牛奶泼你脸上。”
“老头子?你是说部门的主任?”
“还能是谁?”
“他没有住院,至少没在这儿住院。”她颤抖了一下,做了个鬼脸,“我可不想让他在我这儿当病号。”
我同意她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