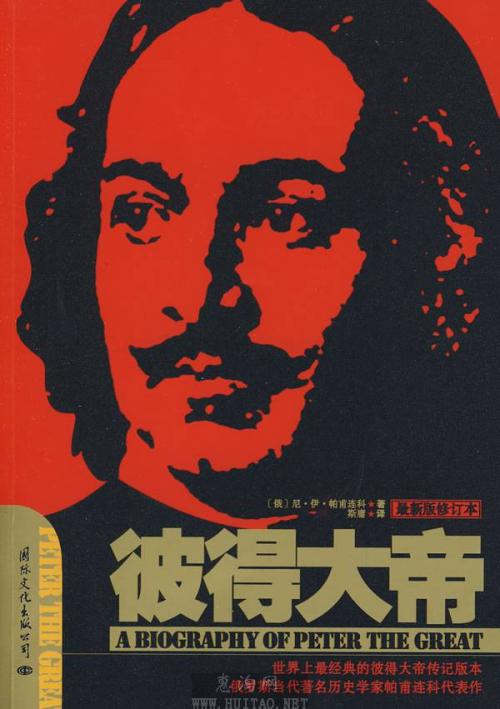搬到存信巷之后,父亲回家的次数愈来愈少了,他宁愿长年待在台北的武昌街十八号——当年立委的休闲俱乐部,和工友老李同住在一间陰暗的宿舍里。他的生活日益消沉,成天逃避在围棋里面,虽然隶属于一交一 通委员会,却总是拒绝发言质询。他不常回家的理由最主要是跟母亲不和,两人无法相处,连一个礼拜都嫌多。他们的心性不同,人生观不同,对人的态度不同,心理的需求不同。譬如父亲好面子,母亲实际;父亲被动,母亲主动;父亲寡言,母亲善道;父亲感性,母亲理性。然而在所有浮面的差异之下,潜藏的却是人性共通的恐惧、挣扎、渴望、失望、哀伤、逃避、自怜与嫉恨..
父亲好不容易从台北回来,母亲为了取悦他,总是费心地替他张罗牌搭子,当大家高高兴兴地正在玩牌时,站在父亲身后的母亲,看着看着就成了后座驾驶,开始指挥东指挥西的,忍不住还要骂上两句“笨死了”。父亲听着听着,突然忍不住了,站起身来满脸涨得通红,愤恨地撂了一句:“你聪明!你打好了!”然后转身就走了,当天便打道返回台北。我盼了半年好不容易把他盼了回来——还是干爹教我用激将法写信骂他“不回家就是老混蛋”,才把他激了回来——没想到两天就走了,这一去可能又是半年,我心里真是失望极了。
母亲在金钱上老是有恐慌感,看到别的立委都有本事赚外快,便说服父亲挂牌当律师。父亲不擅言辞,虽然挂了一胡一 大律师的招牌,不幸上法庭时口拙,无法替一人进行有效的辩护(说不定他心里想的是和解算了),因此律师的招牌不久就给砸了,母亲为了此事经常当外人的面说他无能。别说替一人辩护口拙,就连和母亲吵架,他也是挨了一百句才能回个一两句,骂完便赶紧夺门而出。有时他从台北领了薪俸回来走到半路碰上同事告急缺钱用,他就把信封里一半的钱给了那个人,回家只能一交一 给母亲一半的薪水当家用,患有金钱恐慌症的母亲病情因而日益严重。
小时候我是父母一之 间的夹心饼,起先是母亲在我身边叨念父亲的自卑与无能,长大一点换成父亲在我面前数落母亲的拜金与现实。我记得父亲爱看武侠小说,但又恐怕母亲笑他没出息读闲书,便躲在被窝里拿着手电筒偷看,喜欢和爸爸起腻的我也躲在里面和他一起偷看。父女二人像是做了坏事的小偷,紧张中带着莫明的兴奋。这时父亲好像在跟他同年龄的玩伴告状一般悄悄地对我说:“那个老达卜(上海话发音的“老太婆”)根本是金钱挂帅,她心里永远是金钱第一,她第二,别人第三。”听了这些话,我深深觉得他是如此的厌恶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