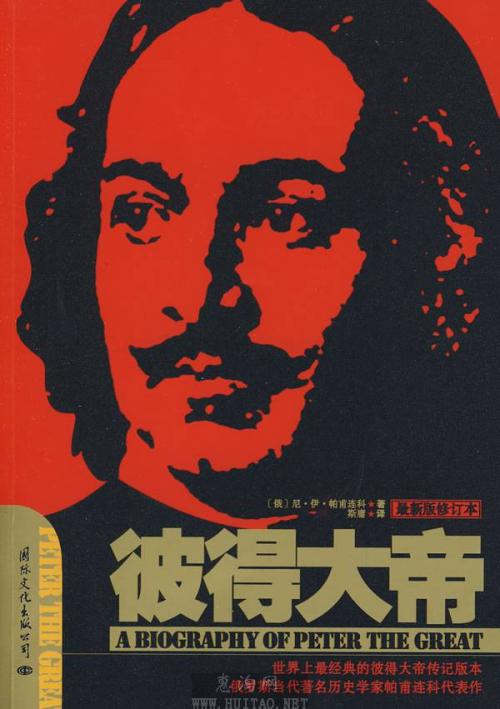我小时候确实有心理学所说的恋父情结,父亲一向是我的荣耀以及我同情的对象,母亲的强势与批判使得我一面倒地倾向于他。我无论在长相、气质和心性上都比较像父亲,而且父亲和我的关系又特别近,似乎不需要太多的言语便能直接地融合,母亲对这一点时常流露出妒意,从眼神就可以清楚地感觉到。上小学后母亲开始把对父亲的不满(其实是对自己的不满)迁怒到我身上,总嫌我和他一般无能、没用。她时常拿我最要好的朋友周中立与我相比,她总说中立能干、活泼、头脑清楚,我和她站在一块儿简直像个老实的小傻瓜。她日复一日地加重我头上的罪名,我虽然反弹但似乎愈来愈朝着她的精神暗示发展,后来我从心理学上完全印证了父母的指责终将一一实现。
父母欠缺觉察的教育方式形成了我许多人格上的矛盾。父亲一宠一 我、纵我,要星星月亮他都设法摘下来给我。上小学后我的钢笔起码有五十支,我喜欢圣诞卡片,爸爸一买就是一百张——他无法时常回来看我便转而以物质的形式补偿。从小到大他总共只打过我一回——他和朋友下棋眼看着就要赢了,我过去夺他的注意力,把他胜算在握的棋给毁了。他气得一巴掌托住我的屁一股使劲一推,把我从客厅的前端推到了后端,但地板很滑所以我毫发未伤。我心里笃定他不会真的伤我,拍拍屁一股笑嘻嘻地站起来就跑。
他在家的时候我是个满洲格格,他回台北之后我就成了灰姑娘。当时村子里的人耳语,盛传我是母亲抱来的养女。我听见了跑去质问妈妈,妈妈说他们存心不良 ,我是她打了几个月的安胎针才保住的亲生女儿,这才提起了乐老师与朱大夫的传奇故事。
一家三口的紧张关系只有一个人可以扮演润滑剂的角色,别人都起不了什么作用,这个人就是父亲姊姊的儿子,我的表哥——刘光夏。中国人常说“甥舅最有缘”,此话确实不假。爸爸的亲戚之中只有表哥到了台湾,母亲则一个都没有。表哥活泼、幽默,但也颇有个性。他长年教外国人华语,学生多半是外一交一 官。他时常和母亲聊起洋人世界的种种,我在旁边耳濡目染开始有了几分向往。表哥的感受力和滋养力都比一般男人强,譬如我刚出生的时候母亲不敢帮我洗澡,表哥却能一手包办。洁生出世后表哥立刻从夏威夷赶回来看我们。洁生喜欢哭闹没有人能治得了她,但一到表哥的手里不消多久就睡着了。表哥后来和专攻体育舞蹈的陈姊姊结婚,生下了小侄女璐璐和小侄儿老虎,他们的家就成了我的避难所及儿童乐园。
记得有一天夜里母亲和表哥在客厅里聊天,我觉得没趣,想到饭厅拿糖吃,但饭厅的灯没开,黑漆漆的令我有点害怕。我打岔要表哥帮我拿糖,妈妈嘲笑我既好吃又没胆儿。我的自尊心受了伤,气得壮起了胆跑到饭厅抓了一把糖,高声喊了一句大人平日随口即出的国骂之后,撒丫子就往外跑。母亲火冒三丈,拿着一根竹条跟在我后头追杀,两个人绕着存信巷不知跑了多少圈。后来我躲进一家人的后花园,母亲找不到我只好作罢。我听见她在我后头追杀的时候口里没停地喊着:“我今天非把你打死不可!”平日里我一跟她顶嘴,她也是对我又打又拧的,可都没那天晚上那么当真,所以我不敢回家了。
晚上11 点多一个人在巷子里没魂似的走着,排行老五的干哥哥骑着脚踏车经过时发现了我,得知事情的始末之后,他骑车载我回家准备向母亲赔罪了事。回家后我跪在母亲面前硬是不肯开口认错。表哥在一旁劝架,母亲好一阵子才软了下来,终究饶了我。第二天放学我对老李说:“我恨妈妈。”老李一脸惊骇,责备我怎么可以如此不孝。我得不到心理上的支持便径自走到竹林宣誓:长大之后一定要复仇雪耻。我想日后的叛逆以及与基督山李敖伯爵的因缘,大概就是这么一点一滴种下的吧。
另外一件令母亲恐惧的事,就是见到父亲烂醉如泥地回来,东倒西歪的完全失去了平日的压抑与克制。老李看到这种情境总是亦步亦趋地照料着父亲,我站在一旁揪着心,母亲则是吓得闪到了一边。老李示意要母亲过去扶爸爸,她说她最讨厌人没理性,爸爸是断掌,很可能一巴掌就把她打晕了。老李把爸爸扶到床 上,爸爸嘴里一直喊着:“因因哪!因因哪!”我凑上前去既难过又害怕地拉着他的手,他泪眼模糊地望着我哀号:“妈妈呀!妈妈!..”爸爸的哀号勾起了我心底最深的无助与同情,我含着眼泪束手无策地低头看着他吐了一脸盆的酒菜。
父亲长期不回家,母亲如果休战不打麻将,总是一根烟接着一根烟地抽个不停,或者焦躁不安地在客厅里来来回回地走着。她的不安和错综复杂的情绪严重地波及了我幼小易感的心。生活在一个欠缺沟通的家庭里,孩子只能窥见问题的一角,父母深埋的渴望、孤寂、幽怨与愤恨如同一座冰封千年的活火山,不知哪一天会爆发。妈妈在家时我的感觉就像坐在活火山口,心中充满着不祥,她迁怒的眼神也总是令我不寒而栗。我仍然清楚地记得她为我绑马尾头时为了避免头发很快就松开,往往过于实际地扎得太紧,我痛得发出“哎哟”的喊叫,她拿起梳子劈头就敲我的脑袋,我只好顶着一束紧绷的马尾去上学,离开她的视线时才敢稍微松绑。
日式的房子在冬日里门窗经常被吹得咻咻作响,爸爸人在台北,妈妈打牌去了,只剩下老李和我两个人在家,那种相倚相靠的孤独感总让我联想起当时私下流行的一首禁歌(因为某种政治因素而被禁了),歌词好像是:热红红的太陽往上爬呀,往上爬,爬上了白塔,照进我们的家,我们家里人两个呀,爷爷爱我,我爱他呀..
有一天我和母亲在街上走着,一位陌生男子迎面而来,母亲突然停下脚步过去拉住那名男子的手臂。我站在一旁看着他们一交一 谈时脸上浮现的表情,我猜想他们一定是多年不见的老友。他们谈完话之后过了几天母亲就带着我到那位叔叔家串门,母亲和他谈着谈着便开始哭诉自己守了多年活寡的难熬之苦,那位叔叔似乎相当同情母亲的遭遇。不久,那位叔叔便时常到家里来探望母亲。有一天我放学回家意外地发现他环腰抱着一脸笑意的母亲,母亲看见我立刻撇开他的手,表情十分尴尬。父亲从台北回来带我到包姑姑家聊天,我当着包姑姑的面把这件事告诉了父亲,父亲的反应颇为淡然。当时他和包姑姑到底讲了些什么话我已经记不得了,但自此之后那位叔叔和母亲就不再往来。我当着包姑姑的面向父亲告状的事令母亲对我更加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