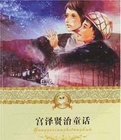费里斯比夫人是一个田鼠家庭的户主。她们一家住在农民菲茨吉本先生的菜园里。这儿是田鼠冬天理想的住处。每当食物短缺时,在树林和草原里生活太困难,田鼠们就迁移到这儿过冬。在这里,人们收割后遗留在松软土地上的一些豆荚、土豆、青豆和芦笋之类的食物,足够他们吃一阵子。
费里斯比夫人一家住在这里可真算走运。这住所是一大块水泥与炭灰混合做成的空心砖,略有损坏,里面有两个椭圆形的空洞。这块砖是有一年夏天被人丢在这儿的,后来被泥土埋住,只有一点儿砖角露出地面。这块砖完整的两面正好做屋顶和地板,里面两个空心成了两间房。费里斯比夫人和她的孩子们捡了树叶、干草、碎布、棉花、羽毛什么的铺在房间里,所以,冬天屋里干燥、温暖、舒适、房里有个隧道通到菜园的地面。洞口不大不小,能使一只田鼠进出还略有余地,而对猫的前爪略嫌窄小。这个隧道是个进出口,能通风,也可以使陽光射进起居室。卧室同起居室一样,也是椭圆形的,温暖但挺黝暗,即使是中午也显得光线不足。卧室和起居室之间隔断了,所以在砖后面挖了一条隧道,出入两室之间要绕着走这条隧道。
费里斯比夫人虽然是个寡妇(她的丈夫是前一年夏天逝世的),但她很能干。由于她肯干再加上运气好,全家四个孩子吃得不错,生活挺愉快。十二月是一年里最困难的月份,每年十二月到第二年三月天气寒冷,到了二月,豆角和青豆都被拣光了(鸟类也拣),芦笋根冻得象石头一样硬,土豆是冻了又化,化了又冻,上面沾着脏土,吃起来有股臭味。就在这种情况下,费里斯比夫人也想方设法把孩子们喂得饱饱的。
到了二月底的一天,费里斯比夫人最小的儿子蒂莫西生病了。那天早晨,天气干燥、晴朗、非常冷。费里斯比夫人同往常一样很早起床。她和孩子们一起睡在捡来的羽毛、绒毛、碎布上,就像睡在热乎乎的被窝里一样。
费里斯比夫人轻轻起来免得把孩子们吵醒,她悄悄过隧道进入起居室。起居室不像卧室那么暖和,但也不冷。从通道口射入了陽光,她知道太陽出来了。她看了看起居室旁的食品室,这是个用碎石围着的小洞,里面有足够三餐吃的食物,但她还是感到沮丧,因为这些都是他们这个月天天吃、顿顿吃的食物。她真希望能找到一小块绿色的莴苣,或是一个小蛋,或是尝点奶酪、玉米粉做的松饼。在不远的鸡房里倒是有不少见,但是对一只田鼠来说,鸡和鸡蛋都太大了。此外,在菜园和鸡房之间有一大片草地,上面长着高高的灌木和野草,那是猫的领地。
费里斯比夫人爬到通道口,先将须毛探出去,然后谨慎地观察四周。寒风刺骨,地面上和菜园角落里堆的枯叶上有一层厚厚的白雪。
费里斯比夫人跳过田地上的犁沟,来到篱笆边。她向右转,围着树丛的四周,用她那明亮的大眼睛想寻找小块的萝卜、冻着的防风草或是其他绿色的菜蔬。但是在这个季节,除了松树沙锅内的针状叶和冬青树叶外,找不到绿色的食物,而那绿叶子又不是田鼠或其他动物能吃的。她已经到了菜园最远的角落,在她的正前方,她看到了绿色的东西。就在篱笆旁树丛边有个树桩,树桩上有个洞,洞口旁的什么东西似乎有点像叶子。
费里斯比夫人顺利地穿过篱笆,但她靠近树桩上的洞口时却十分小心。如果洞口看起来挺深,里面很可能住着什么动物。她在离洞口大约一步远的地方停下来观察,侧耳倾听,什么声音也没有。但她已看清了那个绿东西是什么。其实近看,那是块棕绿色的玉米壳。这里怎么会有玉米壳?玉米地在场的另一端,在牧场旁边。费里斯比夫人向前跳近一点,然后小心翼翼地爬到洞口向洞内窥视。她那习惯在黑暗中看东西的眼睛发现了好东西——里面存放着过冬的食物,由于某种原因被忘掉或被遗弃的食物。
这是谁放的?是浣熊?不大可能,这里离溪水太远了。倒像是一只松鼠或是一只土拨鼠放在这儿的。她知道这两种动物在每年新玉米下来时不但尽量地放开肚皮吃,并且还有本事把玉米运走贮存起来。
不管是谁干的,为什么搞来了又放弃这食物呢?她终于想起来了,去年十一月时,就在这丛林附近,一声巨响把所有动物都吓得躲到自己的藏身之地——那是猎槍声,随着而来的是一种非常痛苦的声音,然后受难者再也不需要贮存食物了。
后来,费里斯比夫人一直不知道受难者是谁,更甭说他叫什么名字了。她不能为他哭泣——食物就是食物。这不是她想寻找的绿色莴苣,可是她和孩子们也非常喜欢玉米。在洞中有八个大玉米棒子,这对一个田鼠家庭来说可算是丰富的供应了。在玉米下面,她还看到一堆新鲜花生(这是场另一块地种的),一些山胡桃核仁,还有一堆发着香甜味的干蘑菇。
费里斯比夫人用她前爪和锋利的牙齿把玉米衣剥下,折成袋状,然后将玉米粒剥下后放在袋中,她轻快地跳跃着把玉米粒带回家中。吃过早饭,她可以带孩子们来再搬些玉米粒回去。
费里斯比夫人背靠着通道口,先将尾巴甩进通道,然后一面拖着玉米袋,一面高兴地喊着:
“孩子们,起床吧?看看我给你们早餐吃什么,你们一定会吃惊的!”
孩子们跑出来,激动地擦着眼睛,因为在冬季最寒冷的日子里,任何意外的食物都是罕见和令人欢乐的。老大特莉莎第一个出来,挤在她旁边的是弟弟马丁,他高大强壮,长着一身深色的皮毛,像他逝去的父亲那样英俊。妹妹辛西娅后出来,这个小巧玲珑的田鼠姑娘,毛色淡雅,长得漂亮。不过她不大文静,并且过分喜爱跳舞。
“在哪儿?”辛西娅问着:“在哪儿?什么东西要让我们吃惊?”
“蒂莫西呢?”费里斯比夫人问道。
“妈妈,”特莉莎忧虑地说,“他说他病了,起不来。”
“胡说。马丁,告诉你弟弟马上起床,不然没有早饭吃。”
马丁乖乖地跑进卧室,但一会儿就跑回来了。
“他说他很难受,他不想吃早饭,就是让他惊奇的美餐也不吃。我摸了摸他的脑门,热得烫手。”
“啊,天呀!”费里斯比夫人说,“看来他是真病倒了。”大家都知道蒂莫西经常自己觉得病了,而实际上又没病,“你们先吃吧,我进去看看怎么回事。”
费里斯比夫人把玉米衣的包打开,拿出玉米粒在桌上分成五份。餐桌是一块光滑的板子,搭在几块石头上。
“玉米!”马丁喊道,“哎呀,妈妈,您从哪儿弄来的?”
“吃吧!”费里斯比夫人说,“等会儿我带你们去瞧,那里还有好多呢。”然后,她转身消失在通往卧室的过道里。
“还有好多,”马丁同他的姊妹们坐下时说,“看来足够吃到搬家那天。”
“我也希望这样。”辛西娅问,“哪天搬家?”
“两周以后,”马丁用带有权威性的语调说,“也可能三周。”
“啊,马丁,你怎么会知道?”特莉莎不以为然地说。“要是天气还这么冷怎么办?再说,要是蒂莫西的病还没好怎么办?”可怕的现实由于无意中被点破,大家都感到忧虑,谁也不吭声了。辛西娅说:“特莉莎,你不该那么丧气。他的病会好的。他不过是感冒而已。”辛西娅把她那份玉米吃完了。其他孩子也各自吃完了自己的那份。
在卧室里,费里斯比夫人摸着蒂莫西的前额。他的前额确实很热,还有点汗。她摸摸他的脉,不禁吓了一跳。“肚子疼吗?”“不疼,妈妈。我不感觉疼,只是冷。我一坐起来就头发晕,喘不过气来。”
费里斯比夫人焦急地望着他的脸,她想看看他的舌头。但是房间很暗,她只能看见他面孔的轮廓。他是四个孩子中身体最弱的一个。他的面孔瘦长,像他的父亲和哥哥一样黝黑。他的眼睛又大又冰凉,当他说话时,眼睛里闪烁着智慧的光芒。费里斯比夫人知道,他是她的孩子中最聪明,最有头脑的一个,虽然她从未公开说过这点。但蒂莫西的体质最差,一旦有流感或是别的什么病流行时,蒂莫西总是第一个病倒,也是最后一个复原。也可能由于这个原因,他患有轻度的忧郁症。这次毫无疑问他是真的病倒了,费里斯比夫人摸了摸他的前额,断定他在发高烧,脉搏跳得很快。
“可怜的蒂莫西,躺下盖好。”费里斯比夫人将当毯子用的一些碎布盖在他身上。“等会儿我们在起居室给你铺张床,那里光线好。今天早晨我找到不少玉米,足够冬天吃的了,你想吃点吗?”
“不,谢谢您。我不饿,现在不想吃。”
蒂莫西闭上眼,几分钟后就睡着了,但睡得不安宁,不断地展转呻吟。
上午十点左右,费里斯比夫人,马丁和辛西娅到那棵树桩的洞里,搬回来了玉米、花生和蘑菇(他们没要山胡桃,因为太硬了,田鼠敲不开,而且要没完没了地嚼)。特莉莎留在家里照顾蒂莫西,他们把蒂莫西放在起居室临时搭的床上。中午,他们带着好多食物回家时,看见特莉莎正急得直掉眼泪。
蒂莫西的情况更坏了。他烧得两眼发直,呼吸困难,全身不断地颤抖。
特莉莎说:“啊,妈妈您回来太好了。蒂莫西在说胡话,喊着什么妖怪和猫。我跟他说话,他什么也听不见了。”
蒂莫西不只是听不见,也看不见了。他的眼睛虽然睁得大大的,却好象认不出眼前的东西。当妈妈同他说话时,他光瞪着她,似乎她也不存在。然后他哼哼着,好象想说什么,但又说不出来。
其他孩子都吓得发呆,最后马丁问道:
“妈妈,怎么啦?他出了什么事?”
“他病得很厉害,体温太高,已经昏迷了。没办法,我一定要去找老先生,蒂莫西需要吃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