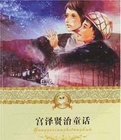《老先生》
老先生的住房在离农场较远的一面砖墙里。这面墙原在一所大农舍的地窖上面。多年前,这所大农舍被烧毁,现在没有人记得它过去的样子,也记不清谁曾住在里面。这个地窖至今还是个方形的深洞,旁边的断垣残壁挡住了风的侵袭,成了好些小动物的住所。夏天这里有蛇,对费里斯比夫人是个威胁,可是到冬天就没事了。
这是个漫长而艰苦的行程,并且挺冒险的,她得特别小心。其实,如果是平常的日子,要出这样的远门,费里斯比夫人不会这么晚了还动身的,她担心没等回家天就黑了。但情况很明显,蒂莫西不能等到第二天了。犹豫了几分钟,她说她得走了,随后就出了门。
如果费里斯比夫人能照直走(那是去老先生家的最短路线)。她这趟出门就容易多了。但这条路线靠近农舍和谷仓,那只猫不断地在那里蹓跶,所以她必须绕开,绕着场兜个大圈子,然后紧靠着树丛的边缘走。
费里斯比夫人像匹小马一样从容不迫地向前跳跃。她的动作轻捷,没有一点声音。她选择的落脚处是光秃的土地或是草皮,避免在枯叶上跳动。因为不管她多轻,跳在枯叶上也会窸窣作响。她还是时时刻刻警惕着——注意那木块、树根、石头以及其他能藏身的任何东西,以免从中钻出个比她个头大的、对她不友好的动物。虽然猫是个的头号敌人,但树林中也有其他动物追逐老鼠。
费里斯比夫人就是这样一面眼观四方、向前跳跃,一面心里惦着蒂莫西,并且希望老先生能治好他的病。
两个多小时以后,费里斯比夫人跳进了老先生住的砖墙。虽然她丈夫生前是老先生的好友,并且常来拜访他,可是她本人只在那年夏天来过一次,但现在她还很清楚地记得这个地方。这是树林中一块零星的开垦过的土地。很久以前,那时房子还没烧毁,房子周围是一大片草地。后来这块地长满了杂草、野果子和野花。夏天这里是个荒芜而美丽的地方,五颜六色的鲜花盛开争妍,空气中飘着黑浆果和紫苜蓿的花香味。这里也长着有毒的植物,比如一种有点像茄子的毒草和一种有毒的深色果实,到处都有蜜蜂在嗡嗡采蜜。
到了冬天,这里一片荒凉,鲜花和绿叶都已凋零,残存的枯枝上悬挂着干果实、豆荚,在风中沙沙作响。老先生就是从这里果实、根茎、枯花中拣出草药,提炼成药粉,靠这些药常能把病者从死亡线上挽救回来。
上次费里斯比夫人来这里也是为了蒂莫西,那时他还是个小仔,比一块小弹石人大不了多少。他同哥哥姐姐玩耍时,不知被什么有毒的昆虫咬了一口,其他孩子也不知道咬他的是什么,只看见他忽然缩成一团,瘫在那里,差不多都不能呼吸了。
那时候,费里斯比先生还活着。他们两口子轮流把蒂莫西背到老先生家里。那次出远门可真惨,提心吊胆的。当他们到达目的地时,曾担心蒂莫西已经死了。老先生检查了蒂莫西的身体,看了他的舌头,按了他的脉,在他脖子附近发现了一个小肿块。“蜘蛛叮的,”老先生说,“不是那种‘黑寡妇’蜘蛛,但也够厉害的。”他将像牛奶似的液体滴在蒂莫西的嘴里,然后把他扶起来使药汁进入喉咙,因为蒂莫西已经不能吞咽了。几分钟后,他的肌肉放松,能伸动四肢了。“他会好的,”老先生说,“但几小时内他还很虚弱。”
回家的路上费里斯比夫妇很愉快,到家后,其他孩子高兴地睁大眼睛瞧着蒂莫西活着回来了。费里斯比夫人一直认为蒂莫西的身体没复原,从那以后,他走路时,特别在疲倦时,两脚直发软。他长得不像他哥哥马丁那样高大强壮,可是他经常思考问题,这一点很像他父亲。
现在,费里斯比夫人来到老先生的房前——砖墙下面约两英尺处的一个洞,原来地板梁立在这里。费里斯比夫人踏过碎石铺的台阶下去,她敲了敲门,心里念叨着:“千万让他别出门!”可是,没有回应,老先生不在家,她就在他门口一条窄长的砖上坐下来等待。
半个钟头过去了,太陽逐渐西沉,费里斯比夫人听到上面有轻微的嚓嚓声,然后看见老先生回来了。他拿着个布袋子,里面装得鼓鼓的。老先生的皮毛是灰白色的,很有光泽。费里斯比夫人曾听说他原来的皮毛不是灰白色的,后来因为上了年纪才变浅的,是不是如此她也不清楚。老先生确实年事已高,但很有智谋,走路还很利落。
“老先生,我真高兴您回来了!”她说,“我想您不记得我了吧?我是费里斯比夫人。”
“我当然记得你。听到可怜的费里斯比先生去世的消息我很难受。你的小儿子——蒂莫西好吗?”
“就是因为他我才来这儿,他病得很厉害。”
“是吗?我曾担心他可能不像你的那几个孩子那么健壮。”
“我希望您能救他。”
“那当然,请进吧,我先把口袋放下。”
老先生的房子比一个鞋盒略大些,像一个隐士的住所。里面没有家具,一个角落里铺着被窝,一块砖当桌子,另一块砖由于当杵捣药,所以磨得很光滑。在一面墙下整整齐齐地摆着一堆堆他采来的药材:根茎、种子、枯叶、豆荚、树皮和枯萎的蘑菇……
老先生将口袋里的东西拿出来摆在墙根下,这是看来像是薄荷叶的一种植物,根茎纤维很多,深绿色的叶子上有粗粗的脉纹。
“这是海笠草,”老先生说,“它四季常青,可以做成春天服用的高级滋补品。很多人只用它的叶子,而我发现它的根部更有效用。”他将这草摆齐,又说:“当然你不是为这来的,小蒂莫西怎么不好?”
“他发高烧,已经昏迷。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温度多高?”
“他的前额摸着烫手,出汗,可他自己感到冻得发抖。”
“把他用毯子包起来。”
“我这么办了。”
“他的脉搏怎样?”
“脉搏很快,一下紧连一下。”
“他的舌头怎样?”
“舌苔都是紫色的。”
“呼吸怎样?”
“呼吸很快,胸部好象胀气。他说他喘不过气来。”
“他不咳嗽?”
“不。”
“他得了肺炎,”老先生说,“我开点药给他服,最要紧的是别着凉,必须卧床。”他从墙上凸出的一块石头上取下用白纸包得很整齐的三袋药粉。
“今天晚上先让他吃一袋,把粉在水里搅匀后给他喝,要是他还昏迷,捏住他的鼻子把药灌进喉咙。明天早晨吃第三袋,后天早晨再吃一袋。”
费里斯比夫人把药接过来,说:“他能好吗?”她简直不敢听回答。
“这次他会好的。明天体温会下降,后天等他吃完三袋药,体温就会正常。但这并不等于他完全恢复了健康,他的肺抵抗力很差,要是他受了一点凉,或是吸进了冷空气,那怕是过两天,肺炎还是要犯的,并且会更重。至少要精心调养三周,或是一个月才行。”
“以后怎么办?”
“以后也还要特别小心,当然,我们希望那时天气要暖和些了。”
这时太陽已经落到了树林西边高山后面去了。费里斯比夫人向老先生道谢,急着赶回家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