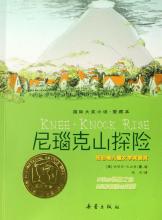我心里对爸爸说:“这没有用。”
可我还是得生一种病出来。感冒不成的话,我还可以拉肚子。
我们家是喝纯水的,因为爸爸说上海的自来水质量很差,要是不过滤,不烧开,喝了肯定会生病。
所以我用刷牙杯子接了满满一大杯自来水,一口气喝下去,喝了一嘴的漂白粉味道。
然后我抽了水箱,回我的房间里去。我想我会拉肚子的,照爸的说法,我肚子里这会儿有半肚子的细菌了。
我躺在床上,放平身体,这才觉得,今天这一天,真的好长啊。
这时,我肚子里咕噜一声响,我想,那是细菌已经各就各位了。我就等着肚子疼,,想起来我己经好久没拉肚子了,只能想起来从前我拉肚子的时候疼得坐在马桶上哭,可到底是怎么疼的,却已经忘记了。
我心里希望这次生病不要太疼,好心应该有好报。
等我再次醒来,已经半夜了。我的肚子一点也没有疼,也许这次自来水里的细菌正好不够。
我听听,那边屋里传来爸爸断断续续的打鼾声。他们这会儿是真的睡着了。
我起床,走出屋子。在客厅里,我望见月亮在爸爸妈妈的房间里撒了一地白光,爸爸侧着身体睡着了,妈妈也侧着身体睡着了,他们的姿势其实很像,可是他们却要离婚。
我在客厅餐桌的小抽屉里摸到空调的遥控器,把空凋“滴”的一声就打开了。里面的冷气马上吹过来。我把温度开到20度,很冷很冷,然后再到浴间去把头发冲湿了,落汤鸡一样地跑到空调的风口里吹。不一会儿,浑身就像冰棍一样凉,从头发上滴下来的水,可以说比冰还要凉。它沿着脖子流到背上,我整个后背就起了鸡皮疙瘩。
然后,我关空调,放好遥控器,听到我们家的钟在报时,是半夜三点。我还从来没有在这时候起来过呢。
离开客厅的时候,我到窗台那里去望了望街道,平时热热闹闹、车水马龙的南京西路,现在没有人,也没什么车,黑脸的警察也回家睡觉去了,红绿灯好像也不工作了,只剩下一个黄灯一闪一闪的,像什么人在眨眼睛。我想看看这时候会不会正巧让我看到一个小偷在偷东西,听说下半夜的时候小偷就起床来偷东西了。可我等了好一会儿,没有看到。
我回到床上再躺下去,头发湿湿的贴在头上,很不舒服。但我还是很快就睡着了。
再醒来的时候,天已经大亮。爸在听早新闻,播音员说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又打起来了,他们那里总是在打仗。我摸摸头,体温摸上去很可疑,摸摸肚子,也一点不疼,就像每一个普通的早上一样。想要生病,凭良心说,也不是容易的事。妈进来叫我起床,看到我正把手捂在额头上,倒吓了一跳。她扶着门框,说:“淼?”
我摸着额头说:“我就是试试是不是有点热。”
妈说:“这样怎么试得准?要用水银尺来量。”她转身就走了。
等妈拿着盛体温表的绿塑料盒进来时,后面跟着爸爸,妈把体温表放到我嘴里的时候,爸爸在旁边握住我的手,把我的脉。爸的手指洗得真干净,指甲雪白的,像听诊器一样准准地压在我的脉上,我假装无辜的样子,其实心里早早就泄了气,让我装病,可不是好主意,只能吓唬不是医生的家长。我和李雨辰都忘记了,不要说装病,就是真病,我爸爸也不怕,他就是干这个的,他怕什么。可见别的孩子一试就灵的招数,也不是每个人都合适的。
一分热度也没有,心跳也正常。
爸爸妈妈站在床头,四只眼睛望着我,他们好像有点手足无措似的,他们是想明白我想干什么。
我说:“我觉得头昏。”
妈说:“当然!你的头用得这么厉害,要是螺丝的话,早就磨没了。你就睡觉吧,好好养养。”
爸说: “起来活动活动,有时小孩子早上低血压。也会头昏,不要紧的。”
我只好起床来,一路洗脸,刷牙,叠被子,一路琢磨自己。我真的是头不昏眼不花,肚子里咕咕叫,那是饿了。也许病也有一个潜伏期,我得耐心。
可整整一上午,我都是好好的。最后连妈都松下一口气来,说:“你吓着我了呢,淼。”
我翻了一眼妈,没理她。自从他们跟我说了离婚的事,我们之间的关系就变得很奇怪,有点不能像平时那样说话了。爸坐在桌孑对面,看着我不说话。
我们三个人各自坐着,很奇怪,很别扭,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关系肯定和从前不同了,现在我不知道该怎么笑,怎么说话,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