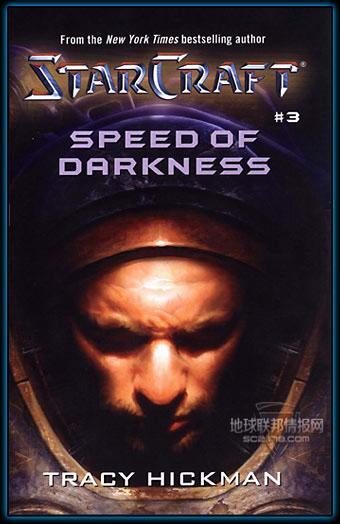诺羽.蓝本特的庄园位在偏远的地方,但藉由交通上的便利,它仍然可以快速地到达本世纪的大都市之一。哈兰非常熟悉这个都市,比任何居住在里头的市民都要来得清楚。从时空分区里,他对这个现实作过详细的观察,每隔它的十年访查过都市里的各个角落。
他能从空间和时间的观点来看待这座城市。他能将各个部件拼合起来,将它视为一个具有生命与成长力的有机体,当中包括它所遇到的灾难与复甦,它的喜乐与麻烦。现在,他要在这个城市的一般时间里待上整整一个星期,切身地体会它悠闲与活力的生活。
尤有甚者,他的初步探索要更加着重在“自由民”的身上,那些不住在城里,却对城市具有更大影响力的那群生活优渥的居民。
482世纪是几个贫富差距相当严重的世纪之一。社会学家有一条方程式来描述这种现象(哈兰曾经见过纸本,不过他在这个学门上只能懂得大概)。给定任何一个世纪,方程式可以用三种关系参数来运作,而在这482世纪中,这些关系参数正好接近于容许的极限值。哈兰曾一度见到社会学家摇头感叹,他们认为,如果再出现任何严重恶化的倾向,那就得进行一次现实变革。但在进行变革之前,“近身观察”是需要的。
然而必须说的是,贫富差距方程式却有它不够适宜的另一面。它意谓着该世纪存在着优闲阶级,而在往最好的方向来看,那将鼓励着精致文化的发展。只要位于阶级另一人们的生活不致于困苦到无以复加,只要优闲阶级在享受特权时不要忘记他们的社会责任,只要他们的文化不致于步入明显的自残病态,永恒时空总是倾向于忘掉贫富差距方程式的理想状态,仅仅作些无关大局的微调。
虽然与他的理念抵触,但哈兰也开始了解了这一点。通常,当他必须在一般时间里头过夜时,总是待在最贫穷地区的旅馆中,在那里他可以隐姓埋名,在那里陌生人毫不受人注意,在那里他现身的影响甚微,顶多只对现实的千丝万缕造成一些轻微的扰动。虽然,轻微扰动也可能超越临界点,并有效地干扰了现实的局面,所以即便是待在偏僻乡间的篱笆中过夜,对他也是一件非常不寻常的事。
更何况,在乡间篱笆里的夜里,偶尔还是会被农夫,流浪汉,甚至是野狗所惊扰。
但现在哈兰居然处于情况的另一个极端,安稳地睡在由场力铺设好的床上,那是由能量与物质精巧嵌合而成的材质所制成的,在这个社会中,只有居于经济状态最高层的人,才能够负担得起的这种精致床铺。在所有的一般时间里头,这种床在纯物质导向的世界中是十分罕见的,但在纯能量导向的世界里却又是相当普及的设计。无论如何,当他躺下时,床面将以他的身躯而重新塑模,当他静止时床面自动变得坚实,当他转身时床面也会柔顺地配合并缓和他的动作。
他勉强地承认,自己非常喜欢这种玩意儿,而且他也理解了永恒时空对每个时空分区的生活设计,要让永恒组员们生活在该世纪环境的中间水平,而不是考虑到舒适与否的程度。如此一来,他们才能接触到问题,并亲身“感觉”到这个世纪,而不致于由于太过认同,而屈从该时代的特性。
哈兰心想,在这里的第一晚,就生活在当地贵族的环境之中,实在太过奢侈了。
就在他入眠之际,他想到了诺羽。
他梦到自己坐在全时理事会里,双手威严地交握在胸前。他向下看着非常非常卑微的芬吉,恐惧地倾听对他的处分,宣判着将他派往遥远遥远的不知名未来世纪中,去作着终生的观察工作。宣布流放的字句出自哈兰之口,坐在他右手身边的则是诺羽.蓝本特。
起初他并未见到她,不过后来他的眼光却向一旁游移着,他的话语变得犹豫。
难道别人看不到她吗?全时理事会的其他成员们,眼睛全都向着前方望去,除了推瑟尔之外。
推瑟尔面向哈兰微笑,彷彿她并不在这里。
哈兰想命令她离开,不过他无法说出话来。他想用手臂推开她,但他的动作迟缓,她丝毫未动。她的身体冰冷。
芬吉开始大笑——笑得愈来愈大声——
——然后诺羽也开始大笑。
哈兰张开眼睛,迎向射入室内的阳光,然后惊恐地发现,那个女孩就正在他的眼前。过了一会儿,他才记起自己所在的地方。
她说道,“你一边呻吟,一边用手肘推着枕头。你作了什么恶梦吗?”
哈兰没有回答。
她说道,“你的浴池已经准备好了。还有你的衣服。我已经安排你加入我们今晚的聚会。待在永恒时空里这么久之后,返回我原来生活环境的感觉真奇怪。”
哈兰对她轻描淡写的态度感到不满。他说道,“我希望,妳应该没有告诉他们我的身份。”
“当然没有当然没有。”
当然没有!如果有需要的话,芬吉应该会对她施予精神上的轻微麻醉。无论如何,他可能不会想要这样作。毕竟,他已经对她作过“近身观察”了。
这种想法令他感到恼火。他说道,“我想要一个人独处。”
她疑惑地瞧了他好一阵子,然后便离开了。
哈兰闷闷不乐地按照这个时代的习惯,进行了晨间的洗浴和更衣。他从不期盼今晚的聚会有什么令人振奋的际遇。他会尽其所能地少开口,少作为,差不多就像一面墙壁而静静地站在那儿。他的功能不过是一对耳朵和一双眼睛。把这些感官和最后报告作出连结的则是他的内心,除此之外,其它多余的行动都没有必要。
这对他说来是相当平常的事,身为一位观察师,他事先不晓得要看什么。身为一位观察师,从新人训练时期就受到教导,对资料不能有先入为主的概念,也不能对引导出来的结论有任何预期。任何这方面的想法,无论自认有多么的忠实再现,都将无可避免地扭曲他的观点。
但在目前的情况之下,全然地保持客观是办不到的。哈兰强烈地怀疑,可能不会有任何值得观察的东西,因为他只不过在芬吉的游戏里头扮演一个角色。就在那与诺羽之间……他看着前方两呎处由反射器所投射出来的三维影像。这件482世纪的无缝连身服,显现出明亮的颜色,他觉得,这衣服让他看来相当滑稽。
在独自一人用完由机械仆人送来的早餐之后,诺羽.蓝本特急急忙忙地奔跑过来。
她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道,“现在已经是六月了,时空技师哈兰。”
哈兰粗声地说道,“在这里不准使用头衔。六月又如何?”
“但我是在二月进入了”——她迟疑了一下子——“那个那个地方,而那不过是一个月之前的事。”
哈兰皱着眉头。“现在是哪一年?”
“噢,年份没错。”
“妳确定吗?”
“我十分确定。是不是出了什么差错?”她有种令他感到恼怒的习惯,也就是谈话时会靠向对方愈来愈近,而且她在说话中常有些许的咬字含混情况(这点倒是该时代的特征,而非她个人的问题),使得她的话听来总是带有一丝童稚的气息。哈兰不会受到愚弄。他后退了几步。
“没有差错。因为现在比较合适,所以我们让妳回到这个时刻。事实上,在所谓妳离开的这段时间里,妳都一直在这里。”
“怎么可能?”她的表情看来更加疑惑。“我一点都记不得这段期间的事。难道还有第二个我我我我吗?”
哈兰完全没有耐心对她细细地解释。他如何能够让她了解到,每一回当他们对一般时间的干涉之中,都会无可避免地导致整个世纪中的生活,因而引起所谓的“微量变革”呢?就算是时空组员偶尔也会忘记微量变革(代号“c”)和可观变革(代号“c”),对现实都一样能够产生改变效应。
他说道,“永恒时空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别再问了。”他以资深计算师的态度骄傲说道,彷彿他们进入六月是由他所下的决定,好让这三个月的跳跃能够保持在微量变革的影响之下,而不会引发出任何可观变革的结果。
她说道,“但是,我的生命就少了三个月的时间,”
他叹了一口气,“妳在一般时间内的活动,与妳的生理年龄毫无关系。”
“那么,我究竟有没有?”
“有没有什么?”
“失掉三个月的时间啊?”
“时间之父啊,女人,我可以简单明白地告诉妳。妳的生命里没有少掉任何时间。妳不可能丢掉一分一秒!”
由于他的吼叫,使得她惊讶地后退一步,然后,她突然咯咯地笑着。她说道,“你说话的腔调太好玩了,特别是当你生气的时候。”
他皱起眉头。什么腔调?他在这个时空分区里所讲的语言和任何人一样。或许还更加标准。
愚蠢的女人!他发现自己正站在反射器之前,看着投射出来的影像,而影像也同时回盯着他,双眼之间显出深深的皱纹。
他舒缓了面容,心里想着︰我一点都不帅。我的眼睛太小,耳朵太突出,脸颊太宽。
他过去从未想过这个问题,但现在这个念头突然在他心中涌现︰如果帅一点的话该有多好。
在深夜里,趁着印象仍然清淅时,哈兰将收集到的对话作了一番记录。
如往常一样,他利用55世纪所制造的分子录音器。它的外型是单纯的几何圆柱状,长约四吋、外径半吋。它的颜色是低饱和度的深棕色,可以轻易地夹在袖口、口袋、衬里,端视穿着的服装形式为何,或者可以配合不同的材质,将它挂在腰带、钮扣或者手环上头。
无论怎么摆放,录音器是个拥有三个分子层结构的记录器,每一层的容量都能记忆大约两千万个字符,圆柱的一端连结着翻译器,非常有效地和哈兰的微型耳机产生共振而播放出来。
在圆柱的另一端,则是连到黏在他嘴边的场力驱动微型麦克风。这么一来,哈兰就能够一面听、一面说来作加以记录。
今晚那场一个小时的“聚会”中,里头的每个声音,现在都在他的耳里再次播放,随着聆听现场的重现,他也同时地透过麦克风作出发言,将这些注记录在第二层上。哈兰在第二层所录下来的内容,能与第一层的原音作出对准。他在第二层里描述到自己观察的印象,评估重要等级,并指出彼此之间的关连。最后,当他需要利用这支分子记录器来撰写报告时,他就不仅只有原来的录音,还能同时拥有亲身诠译的内容。
诺羽.蓝本特走了过来。她完全不作任何通知便径自进入。
哈兰心中一股气恼,于是拔下微型耳机和麦克风,挂回到记录器上,将它们置入工具包中,然后发出巨大声响而将它关上。
“你为什么对我生气?”诺羽问道。她的臂膀裸露,包覆着修长双腿的贴身裤管表面上,透出淡淡的冷色光辉。
“我没有生气。我对妳一点情绪都没有。”此时此刻,他觉得自己的话应该是完全真切的。
她说道,“你还在工作吗?你应该觉得累了。”
“如果妳还在这里,我就无法工作,”他没好气地回答。
“你的确的确在生我的气。你整个晚上没有和我说过一句话。”
“我尽可能不和任何人说话。我不是来这儿作演讲的。”他静待对方自动离开。
不过她却回应道。“我为你带了另一杯饮料过来。看得出你在会场上很喜欢,所以一杯是不够的。特别是你有工作要做。”
他注意到她身后的机械仆人,正平缓地受着力场牵引而滑了过来。
整个晚上他都吃得很少,仅仅从盘中拣取些许食材,而这些料理,在他过去的观察中全都作过报告,当时的他除了亲身测试而略微一尝之外,克制自己贪吃的食欲。不过违抗了自己的意志,他很喜欢这些料理。违抗了自己的意志,他特别喜欢这种淡绿色的发泡饮料(称不上是酒精,而是带有薄荷香味的一种特殊饮品)。在两个物理年之前,也就是在最近一回的现实变革之前,这种饮料还不曾存在于这个世纪里头。
他从机械仆人那儿接过了饮料,然后生硬地向诺羽点头道谢。侯卫东官场笔记
为什么一场与物理效应无关的现实变革,最后竟然能让一种新饮料发明出来呢?他不是计算师,所以他没有必要问自己这个问题。除此之外,就算是最精细复杂的计算,也无法消除所有不确定和随机的效应。如果真能作到这种程度,那就根本不需要观察师的存在了。
在整间屋子里只有两个人,诺羽和他。机械仆人在过去这廿年来,达到了普及的程度,而且在目前的这个现实中,还将会流行个将近十年,所以这栋屋子里头没有人类的仆役。
当然,只要女性在经济上的独立程度能够与男性相同,如果这个世纪的女性能够扮演好她们的母亲角色,而不是摒弃了自然分娩的行为,那么,482世纪的女性如此过着独立自主的生活,应该也没有任何的“不恰当”之处。
哈兰现在对这个世纪的表征,感觉自己在心情上已经比较能够释怀了。
女孩舒展着手肘,坐到他对面的沙发上。沙发下沈,彷彿要将她的身子整个地包覆起来。她把穿着的透明鞋子一脚踢开,在可曲挠的冷光裤管之下,她让自己的脚趾头一曲一伸,看来就好像是猫的手掌一般。
她甩甩头,让那只从她耳际向上箍扎住复杂发型的物品随之松脱。她的头发自然地流泄而下,在黑色发丝的对比之下,她的颈子与肩膀更加显得白皙。
她轻声问道,“你年纪多大?”
没有必要回答。这是私人问题,而且也不关她的事。他应该坚定又礼貌地回应道︰可以麻烦请妳离开,好让我能做好我的工作吗?不过他却发现自己口中说出︰“卅二岁。”当然,他指的是物理年龄。
她说道,“我比你小。我廿七岁。不过我想我不会一直比你年轻。我想我变成老太婆之后,你的外貌应该还是会和现在一样。你为什么决定要当卅二岁?你能不能随心所欲的更换年纪?你有没有想要变得更年轻一些?”
“妳在说什么?”哈兰抹着自己的额头,想要弄清楚对方的话。
她温柔地说道,“你能永远地活下去。你是个时空组员。”
这是个问句还是一句描述?他说道,“妳疯了。我们和任何人一样会变老和死去。”
她说道,“你可以告诉我。”她低沈的语气中充满诱惑。他过去总认为这种延续五万年的语言十分刺耳,但现在却令他感到动听。或者说,那仅仅不过是饱足之后,加上空气中的散布的香气,让他的敏锐听力变得迟钝?她说道,“你能够看遍一切时间,到达所有地方。我多么想要在永恒时空里工作呀。我等了好久,他们才让我进入。我原本以为他们会让我成为时空组员,但后来才发现那里只有男人。
有些人因为我是女人而不和我说话。你你你你就不和我说话。”
“我们都很忙,”哈兰含糊地说道,他试着让自己的拙劣反应,听起来不会那么明显。“我一直都很忙。”
“但为什么那里没有女的时空组员?”
哈兰不晓得该怎么回答。他能说什么?成为永恒时空里的一份子,必须符合两个条件,然后才能加以细细筛选。第一个条件,他们必须有充分的能力。其次,他们从一般时间被抽离出来之后,不能对现实产生任何危害。
现实!这是他在任何情况之下都不能提到的字眼。感到脑内一阵天旋地转,于是他闭上了眼睛。
他们遇见了多少身处一般时间之中优秀的人材,但却完全不能接触,因为将他带入了永恒时空,就代表着这个人在一般时间内,从来没有过婴儿的出生阶段,没有死亡的阶段,没有婚姻的阶段,也没有推动现实发展的事迹,而这正是全时理事会所不能容许的现实扭曲。
他能告诉她吗?当然不能。他能告诉她永恒时空从不认为女性拥有这种资格,出于某种他并不清楚的原因(计算师可能知道,但哈兰并不是计算师),她们从一般时间里抽离而出所造成的现实扭曲,比起男性多出了数十到上百倍的机率。
(所有这些想法一时杂乱地涌进他的脑中,带着失落的回旋,并产生另一种奇妙的感觉,几乎是奇特的影像,但并非全然地引发不悦。现在,诺羽面带微笑靠过身来。)她的话犹如一股激起涟漪的清风。“噢,你们这群时空组员,总是神秘兮兮的。你们一点都不告诉我。那么就让我成为你们的一份子吧。”
她的话已经不是单纯字词的集合,而是深深地直接渗入到他的内心。
他非常想要告诉她︰待在永恒时空里一点都不有趣,女士。我们整天工作!我们要从永恒时空启动的那一刻起,一路规划着所有时代的一切细节,直到地球死亡的那一刻为止。而且我们要从所有一切的可能之中,尝试规划出各种无穷尽的发生机率,并拣选出一条比较好的路径,决定我们可以采取的变革方式,作出最小的扭曲。然后在新的现实产生之后,我们再重新观察,再度作着同样的工作,永远进行着重覆的程序。自从24世纪由那位神秘人物,维科.玛兰松,发现了时间力场之后,然后直到27世纪开启了永恒时空,便产生了时空中的各种可能发展,并永远永远地产生下去……
他猛力地摇头,但脑中的晕眩丝毫未减,而在这纷杂混乱的思绪之中,他突然灵光一闪,但在下一秒中却又立刻消逝。
晕眩不断持续。他想要紧紧地控制,但又放开了。
是那杯薄荷香味的饮料吗?
诺羽更加靠近了,他视线里所看见的脸庞已经显得朦胧。他的脸颊可以感到对方头发的摩娑,也能感到她所吐气息的温热。他必须离开她,但——奇怪地,奇怪地——他觉得自己不想离开。
“如果我变成一个时空组员……”她的声音直接在他的耳边响起,虽然他能更清楚地听到自己的猛烈的心跳声。从她的湿润的双唇说道,“你不想要吗?”
他不知道她是什么意思,但这时他一点也不在意。他似乎身在火焰之中。他笨拙地伸出手来探索。她没有作出反抗,反倒与他的手纠合在一起。
一切就如梦幻般地发生了,彷彿是在看着别人的事。
这并不像他原先想象中的令人反感。起初,他觉得有些惊讶,但却一点也不感到恶心。
即使在事完之后,带着温柔的笑容的她倚靠在他的身上,他发现自己喜悦地伸出手来,轻轻抚摸她那已经湿透的头发。
在他的眼中,她已经变得完全不同。她不是一个女人,甚至不是一个个人。突然之间,以一种陌生与奇特的方式,她成了他自己的一部分。
时空计划书上从未提及这件事,然而哈兰一点也不感到内疚。只有想到芬吉,才会在他的心中激起一股情绪。称不上内疚。绝对不是。
那是一种满足感,或者说是胜利感!坐在床上的哈兰无法入眠。现在脑中的晕眩已经消退,但自从他成年以来,这还是首度与另一个女人共同躺在同一张床上,这件事实仍令他难以置信。
由于墙面与天花板的室内照明,已经调查并降低成微光模式,不过他还是可以模糊地看见她的身影,并听到她熟睡时的呼吸声。
只要伸出来便可以感受到她身子的温热与柔软,而他不敢这么作,深怕打断了她正在作着的好梦。她可能正梦着两人刚刚经历过的事,唤醒她似乎会同时打断她与他的现实关系。
在此之前,他似乎想到了某件奇怪与不寻常事情的片断……那是介于真实与虚幻之间的奇特念头。他想要重新抓住,但却没有办法。忽然之间,他认为重新抓住这些想法是相当重要的。虽然他无法回想起当中的所有细节,但他隐隐约约地知道,有那么一刻,他的确解开了某件事情。
他不能确定那是什么,但就在他半昏半醒之间,某种不属于人世间的洞察力,突然地在他心中甦醒过来。
他感到一股焦虑。为什么他还是记不起来?他曾获取了这些重要的概念。
此时,他先把身旁女孩的事情摆在一旁。他想道︰如果我再试着遵循这条思路……我当时想到了现实与永恒时空……没错,还有玛兰松和那个新人!他暂停了下来。为什么是那个新人?为什么是库柏?他先前应该没有想到过他。
但如果没有的话,为什么现在心中突然浮出布林斯里.薛瑞丹.库伯的身影?他深深地皱着眉头。它们彼此之间有什么关连?他究竟想要追查什么事?是什么让他确定确实有些事情值得去追查?
他感到一阵寒冷,因为这些问题在他心中曾经犹如一丝遥远地平线上的冒出的曙光,而且他应该要知道的。
他深吸了一口气,摒住呼吸。让它出来吧。
让它出来吧。
而在这夜阑人静之处,一个已经全然改变他人生的夜晚,一个让他再也享受不到比此更高喜悦的时刻,他发现了许多事件的阐明与解释。
他让念头发芽与成长,让它自行开花结果,直到他可以看到上百种谜团的简单答案——奇怪的谜团。
回到永恒时空之后,他会研究和调查这回事,但他心中却早已晓得,他触及了原本不该让他知道的骇人秘密。
一件影响永恒时空的大秘密!
【第五章译注与对照】
*自由民(perioeci、περοικοι)︰历史名词。该字源于古希腊斯巴达城邦里的阶级名称,地位介于“公民”和“农奴(helot)”之间;自由民具有人身自由,也能够拥有属于自己的财产和土地,但却不能拥有能够参与国家政治的“公民权”。
*反射器(reflector)︰半科幻名词。
*机械仆人(mekkano)︰科幻名词。
*分子录音器(molecularrecorder)︰科幻名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