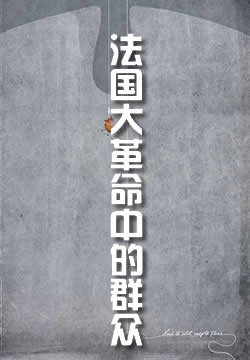这个女人走了很久,脚步变得更虚弱了。她使劲看着远方光秃秃的、在黑夜的半影中已模糊不清的道路。最后,她那向前挪动的脚步再也不成其为行走了,完全是在摇晃着。她打开一扇栅栏门,里面有一堆干草,她就在草堆下面坐了下来,立即便睡着了。
这个女人醒来时发现已是星月无光的深夜。厚厚的云层弥漫于空际,茫茫无边,遮住了整个天宇;卡斯特桥市镇上方有一道光环,衬映着漆黑的穹隆遥遥可见,再经周围的黑暗大力烘托,便越发显得明亮了。女人把目光转向这片微弱、柔和的辉耀。
“我能走到那儿就好了!”她说,“后天见他,老天爷保佑!也许那时候我早就进坟墓了。”
在远处的阴影深处,一座庄园住宅的钟报了时,敲响了一点,声音很细弱。午夜以后,钟的声音会显得不那么洪亮和悠扬,好像变成了纤弱的假声。
过了一会儿,一道亮光——两道亮光——从远处的阴影中冒出,而且越来越大。一辆马车沿公路驰来,驶过了栅门。里面可能载着一些出外就餐晚归的人。车上的一盏灯光向这个蜷缩着的女人身上一闪,清清楚楚地照出了她的脸。这张脸的底子是年轻的,表面却衰老了,总的轮廓柔韧,尚是孩子型,但眉眼口鼻这些较细致的部分已经开始变得棱角分明而且瘦削了。
这个步行人显然又下了狠心。她站了起来,朝四面看了看,好像很熟悉这条路,然后慢慢向前走去,仔细打量着这堵围栅。不一会儿,前面隐隐约约出现了一团白白的东西;原来是另一个里程碑。她伸出手指在碑面上摸了摸记号。
“还有两个!”她说。
她靠在石头上休息了一会儿,然后又振奋起来,继续上路。她坚强地支持了一小段距离,就又像刚才那样泄了气。这一次是在一个孤零零的小灌木丛旁边,里面有一堆白色木屑,撒在盖满树叶的地面上,这说明白天樵夫在这儿砍柴编过格子栏。现在,没有一丝窸窸声、没有一丝微风、没有一丝最微弱的树枝撞击声来陪她做伴了。这个女人从门上往里看了一眼,便推门走了进去。门边放着一排柴薪,有的已捆好,有的还没捆,还有一些大小不同的木桩。
这个徒步旅行者僵立在那儿,但这并不显得是先前的行动已经结束,而仅仅是暂停。这样过了几秒钟。她的姿势好像是在倾听外部有声音的世界,不然就是倾听想象中的心灵对话。如果仔细观察,便会看出有一些迹象表明她是在一心一意干着后面这件事。此外,后来发生的事情也表明,她是在运用自己的发明才能,学着聪明的贾凯·狄罗[1],代替人体四肢的自动装置的设计者,离奇古怪地搞起机械创造来。
借着卡斯特桥的晨曦,这个女人双手摸索着从柴堆里选出了两根棍子。棍子的下一段几乎是笔直的,有三四英尺长,上端分成y形丫杈。她坐了下来,掰去上面的细枝,拿着余下的部分又上了路。她把树杈分别夹在两腋下当拐杖,试走了几步,便战战兢兢地把全身重量都压在上面——她的重量是那么轻——摇摇摆摆地朝前走去。这个姑娘替自己做了一个物质帮手。
这副拐棍效果很好。现在,她的脚步轻轻踏着公路和木棍点着公路的声音,就是这个旅人发出的全部声音了。她已经走过上一块里程碑好一大段距离,若有所思地朝斜坡上面观望起来,好像在预期着下一个里程碑就要到了。那副拐棍虽然非常有用,但能力毕竟有限。机械只能转移劳动,却不能代替劳动,本来要花费的气力并没节省下来,只是改由身体和胳臂来使劲罢了。她力竭了,向前挪动得一下比一下虚弱,终于向旁边一摆,倒在了地上。
她躺在那儿,简直不像个人样儿。过了十几分钟,晨风沉闷地呼啸起来,掠过地面,把从昨天以来一直铺着不动的枯叶重新吹得到处滚。这个女人拼命转过身来跪着,然后站立起来,扶着一根拐杖稳住脚,试着迈了一步,又迈了第二步,第三步。这副拐杖现在只用作手杖了。她这样朝前走去,下了梅尔斯托克山,另一块里程碑就出现了,不久一道有铁条的围栏也出现在视野中。她摇摇晃晃地走到第一根柱子边,紧紧抓着柱子,到处张望。
现在已能看清卡斯特桥的一盏盏灯光了。天快要大亮了,车虽然不可能很快就有,但总有希望会碰上一辆的。她倾听着,除了一种凄厉得已登峰造极的声音——一只狐狸的嗥叫外,听不到任何有生命的东西发出的音响。这只狐狸每隔一分钟发出三声空洞的嗥叫,像丧钟般准确。
“不到一英里路了!”这个女人喃喃地说道,“不,还要远些。”她停了一下后继续说,“到市政厅是一英里,我落脚的地方在卡斯特桥的那一头,再走一英里多一点就到了!”过了一会儿,她又说道,“五六步是一码——可能得六步。我还得走一千七百码。一百乘六是六百,十七乘六百。噢,可怜可怜我吧,天哪!”
她扶着铁栏前进,先向前伸出一只手握住铁栏,然后伸出另一只,身体靠在铁栏上,拖曳下面的双脚往前挪动。
这个女人没有自言自语的习惯,但极度强烈的感情会减弱弱者的个性,正如它会增强强者的个性一样。她又用同样的声调说道:“我相信,往前走过五根柱子就到了,就不用再走了,鼓起劲来走过去吧。”
这就是下述这个原则的实际应用:半真半假的虚幻信念比根本没有信念好。
她走过了五根柱子,手扶着第五根。
“只要相信我急于要去的地方就在下一个的第五根那儿,我就会再走过五根。我能做到这一点。”
她又走过了五根。
“只要再过五根就到了。”
她又走过了五根。
“可是还有五根。”
她又走了过去。
“那座石桥就是我旅程的终点。”她说道,胡卢河上的石桥已经在望了。
她向石桥挪去,在挣扎中呼出的每一口气都散入空中似乎永远不会回来了。
“现在看看实际情况吧。”她一面说,一面坐了下来,“实际情况就是:我还有不到半英里远的路程。”她用自己一直都知道是虚假的东西来哄慰自己,使自己鼓起了劲头,走完了半英里路。要是作为整体,这样一段距离她是无力对付的。这个方法表明,凭某种神秘的直觉,这个女人了解到了一个似是而非的真理:无知也许比预知更强有力,目光短浅也许比高瞻远瞩更有效果,奋力一搏并不需要能囊括一切,而是需要有限度。
现在,这半英里路就像一个麻木不仁的毗瑟拿[2]一样挡在这个病弱、疲惫的女人面前,是她那个世界中冷漠无情的主宰。道路穿过杜诺坞荒地,两边都很开阔。她审视了一下这片宽广的空间,审视了一下灯光,又看了看自己,叹了一口气,就靠着桥上的护石躺了下来。
从来没有人像这个女人那样这么悲惨地运用过自己的智谋。一切可能帮助她孤零零一个人越过最后这段要命的八百码路程的办法、手段、策略和技巧,都在她那忙碌的脑子里盘算过了,也都由于不切实际而被放弃了。她想到了棍子、车轮、爬行——甚至滚动。后两个办法比挺着腰步行还要费劲。她再也想不出主意来了,绝望终于到来。
“不再走了!”她轻轻说着,闭上了眼睛。
桥那一面有一道阴影,从中好像脱离出一部分,孤零零地移动到了灰白色的公路上,静悄悄地朝这个躺着的女人挨过来。
她觉得有什么东西碰着了她的手,又柔软又温暖。她睁开眼睛,那东西又碰了碰她的脸,原来是一条狗在舔她的面颊。
这条狗是个硕大、肥壮而又安静的家伙,站在那儿黑乎乎的,身后衬映着低低的地平线,至少比她眼睛现在的位置高两英尺。究竟是条纽芬兰狗,是条獒犬,是条猎犬,还是别的什么犬,那就很难说了。那样子好像太奇异、太神秘了,普通名称所指的种类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能把它包括进去。由于不属于任何品种,它就成了犬类伟大气质的理想化身——犬类共同特征的一种概括。除去其隐秘和残酷的一面,黑夜的悲哀、肃穆和仁慈都在这个形影中得到了体现。黑暗使普通的小人物也有了诗歌的才能,甚至这个苦难中的女人也把自己的思想转化为形象了。
她从躺着的位置上仰视着这条狗,正像她以前站着仰视男人那样。这个和她一样无家可归的动物看见这个女人蠕动起来,就恭恭敬敬地往后退了一两步,后来发现她并不憎恶自己,就又舔了舔她的手。
她心里像闪电般起了一个念头。“或许我可以利用利用它——那就这样办吧!”
她朝卡斯特桥的方向指一指,狗好像理解错了:它朝那边跑去,后来发现她不能跟随,就转了回来,悲哀地号叫着。
这个女人的努力和发明才能已到了最后那种最悲惨、最奇特的地步,她急促地喘息着,弯腰曲背地站了起来,把两只小胳臂放在狗的肩膀上,身子紧紧靠在上面,喃喃地说了几句激励话。她在内心感到悲痛,却随着自己的声音愉快起来了。强者需要从弱者那儿获得鼓励,这就很奇怪了;而更奇怪的是,欢乐竟会从这种绝对的沮丧中得到那么有效的激发。她的朋友慢慢向前走着,她挪动着小碎步跟在旁边,身体一半的重量都压在这条狗身上。有时候她倒了下来,像原先直立着行走时从拐杖、从栏杆上倒了下来一样。狗现在已完全了解她的愿望和无力,遇到这种情形就痛苦得发狂。它要拖着她的衣服往前跑;她总是把它叫回来。现在可以看出,这个女人倾听着人的声音,不过是为了避开他们罢了。她不想让人发现她在公路上,不想让人知道她这种悲惨境况,显然是有目的的。
她们前进的速度不可避免地非常缓慢。来到镇头上后,她们就转向左边,走进一条荒芜的栗树林荫道森森的阴影中,卡斯特桥的灯火像从天上落下的金牛星宿一般照射在她们面前。她们就这样绕过了市镇,到达了目的地。
她急欲达到的这个靠着镇边的地方有一座如画的楼房。原先这只是一个装人的箱子,外壳是那么单薄,没有任何多余的东西,又是那么紧密地箍着那块供人住宿的空间,结果下面的狰狞面貌全都透过外壳显露出来了,就像透过裹尸布看见了死尸的形体一样。
后来,大自然好像生了气,就帮了它一把忙,长出一大片常春藤,把墙壁全都覆盖住,渐渐使这个地方显得像个修道院了。人们还发现,从这所房子的正面越过卡斯特桥镇上的烟囱望去,眼中的景色在全郡也算得是最壮观的一种,附近的一位伯爵有一次曾说过,他情愿放弃一年的租金,使自己家门口也具有住在这里面的人从他们家门口享受到的这片景色——住在这里面的人却很可能情愿放弃这片景色,以换取他那一年的租金呢。
这座石头建筑中心部分是主房,两侧是边房,顶上有几个细长的烟囱,像哨兵似的兀立着,现在正迎着徐徐的风发出悲哀的咯咯声。墙上开有一扇门,门边垂悬着一根金属丝,作为门铃的拉索。这个女人把身子尽量往上跪起来,勉强够着了门柄。她推了一推,身子往前一鞠就倒了下去,脸贴着前胸。
快到六点了,房子里有行动的声音了。对这个累瘫了的可怜的人儿来说,这所房子就是安息所。大门旁边的一扇小门开了,里面出现了一个男人。他看见了这堆喘着气的衣服,回去取了一盏灯,又走了出来。他再一次走进去,带来了两个女人。
这两个女人扶起这个趴在地上的身子,把她搀进门去,那个男人随即把门关上了。
“她是怎么到这儿来的?”一个女人说。
“天晓得。”另外那一个说。
“外面有一条狗,”这个精疲力竭的旅人喃喃地说道,“它到哪儿去了?是它帮助我到这儿来的。”
“我用石头把它打跑了。”那个男人说。
于是这只小小的队伍往前移动——男人在前面拿着灯,后面是那两个皮包骨的女人,中间架着那个软绵绵的小个儿。就这样,他们走进了房子,消失了。
* * *
[1] 贾凯·狄罗(1721—1790),瑞士机械学家。
[2] 毗瑟拿,印度教主神,喻不可抗拒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