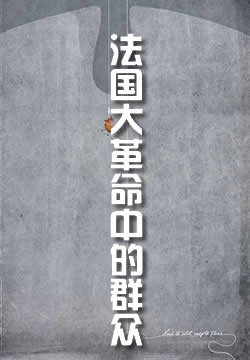古堡夜会 在蓝天的衬托之下,每向前跨进一步,古堡就显得更加雄浑高大,带着一副咄咄逼人的神气,强使人对它瞩目,并陷入沉思。目光固然可以转往另一个方向,可是决不会感觉不到它那沉重结实、赫然存在的威势。从古堡那边吹过来的飓风,径直穿过中间的平地迅速扑来,仿佛是它向这里呼出来的气息。由于流云的飘移浮动,悬岩绝壁的面貌也不断变换着它们的色彩和形状,原来笼罩在茫茫浓雾中的地方,豁然开朗大放光明,随后又依次化为令人黯然神伤的一片灰暗,这片灰暗逐渐扩展开来,把那些明亮耀眼的断崖峭壁又笼罩在阴暗之中。人们本以为这是万古如斯的景观,而实际上其中一切却都瞬息万变。
另一边是看不见的海洋地区,许多鸟儿从那里突然冲向天空,高悬在高地之顶,对这些早就习以为常的景色,无动于衷。在云层形成的茶色苍穹衬托之下,飞鸟的形体是白色的,它们飞掠的弧线说明,这是一群海鸥,由于预感到气候的压力,才飞向内地。鸟儿在古堡的后面飞升,流云又在鸟儿的后面升起,看来几乎就像是在用它那囊括一切的胸怀,抚慰那些升得最高的飞鸟。
这一硕大无朋的遗迹,从东面一英里的地方看去,整个轮廓清清楚楚,就像一座镶嵌的大理石雕塑。由于附带有那些突出部分,它的形状多种多样,从这附近看去,这些部分显出动物的小肉瘤、粉刺、骨节和臀部的种种模样。它的确很像远古时代一个巨大的多肢体动物——外形有点像乌贼之类——毫无生气地待在那儿,上面覆盖着一层薄薄的绿衣,把实体掩盖起来,只露出外表。这种油绿色植被形成的暗淡外衣,向下延伸,直达平地。多少世纪以来,犁锄一直试图往上爬,近一点,更近一点,想爬到碉堡的基座,可是总在接近基座之前就突然停下了。为了完成包围而屡次耕出的犁垅,显得清清楚楚,它们要冲上斜坡,却总在下面弯过去,以更陡的曲线向上爬,直到陡峭的山坡挡住它们,它们那一道道平行线,看来就像是波浪的条纹,在翻起来的时候突然停住了。具有这样一些特点的奇特地方,就是“美登”,意思是“大山堡”,据说它就是托勒密著作中的达尼姆[2],是杜若垂基人[3]的首府;它终于落入罗马的侵占之地,最后由于罗马人撤出不列颠而被遗弃。
黄昏过后是一个看不见月亮的黑夜,月亮没有放射光芒,但是也并非漆黑一片,只有一种暗淡而又四处漫延的微光,我安坐在一个离古堡一英里的小房子里,这时候从这儿已经看不见古堡了;然而,如同在白天一样,任何人只要一心想着它和它的伟大,它在过去时光那带有蛮荒粗野意味的伟大,这形体就在夜间薄雾后面坚持不懈地宣告它的存在,就仿佛它确实有声音在那样说似的。不仅如此,西南风[4]还径直从它的两侧吹过来,用水汽连续不断地滋润着夹在中间的这些已耕的平地。
专诚等待的午夜时分终于到了,于是遵照朋友白天向我提出的请求,向那座要塞走去。这是去赴一个约会。现在深夜降临,我倒有点后悔,不该前来践约。往那里去,一路上没有树篱[5],也没有树——不必说,是一片荒凉。这条路在一大片一大片显得更黑的休闲地里向前延伸,月光可以照出淡淡的像一条丝带似的路面。道路从碉堡附近通过,可是并没有直接通向它的正面。这个地方没有人住,所以也就没有人行小道。于是离开碎石铺砌的大路,另行择路前进。我跨进休闲地里,跄跄踉踉拖着沉重的脚步走过去。古堡逐渐从暗夜中显现出来,好像一个刚刚醒来的巨人,问我要在那里干什么。由于距离近,它现在显得十分庞大,一眼都看不到全貌了。那耕过的地,坡度越来越大,最后就到了尽头,接着,开始是长着青草的斜坡基座了,于是我向上攀登,直犯美登古堡。
作为王国[6]境内古代英国最大的建筑,无疑在白天能给人以深刻印象,而此时则使人印象更加深刻。我站定下来,花了几分钟的时间,从它那久远年代,想到它那巨大规模,又从它那巨大规模,想到它那孤寂处境,同它相距越来越近,不禁使人怦然心动,无限悲怆。暴风雨的风头迎面扑来,宣告今晚夜空的水汽游动得很低。我十分吃力才爬上那斜坡,风却闹着玩儿似地一跃而下,甚至在这样的月色之下,也可以从枯萎芦草的一起一伏,看出它吹过的路径——在这块高地的绝顶,除了苔藓以外也就只长这种草了。攀登了四分钟,终于上到了一处有利的地形。这还不过是外城的城头。紧靠内侧的斜坡并不太陡,如果小心翼翼,是可以滑下去的。我就这样下到了又潮湿又寒冷的阴暗沟底,并且看出,这条沟本身像是一条曲曲折折的小巷,宽度容得下一辆大马车走过,地上密密麻麻长着草本植物,沿着两道同样弯曲的土墙,向左右两边伸出去,通向黑暗的远处。这条沟的两侧都这样紧逼高耸的土墙,它们森严壁垒,无比沉重,使人感到一种实实在在的压力。现在的路是向上登堡垒的第二层,这第二层比第一层更陡更高,正如基督徒的同伴离开那样一座困难山一样。[7]向旁边拐过去本来是比较自然的趋向,可是通向内部的路却是向上攀登。当然有一座通向古堡的大门,可是很远,在另一边。比较聪明的办法当然可能是到那里去寻找入口。
不过,既然到了这里,我就攀登第二道斜坡。一撮撮草梗像是山的灰色胡须,在我俯向地面的脸旁摇曳。这些各种各类的草——酥油草、狗尾草、稞麦——枯死的穗头一磕一点、一抽一抖,好像地下有根绳子牵动着它们。不多的几丛蓟草发出口哨般的呼啸,甚至苔藓,在狂风的摧压下,也在以它那谦卑的方式碎语低言。
我突然明白,已经到达第二道防线的顶端,因为从一个新的方向,顺着一道瀑布式的曲线,吹过来一股逆风。这一阵阵奇特的大风,仿佛拨弄竖琴似地触动整个古堡,从整个营垒或者说城堡里引发出一种声音。这大风一阵阵扫过,要站稳脚跟都有点困难。我抬头向上看了一下,发觉天空比刚才更加阴沉,顷刻之间,就在眼前这股疾风过后,突然令人惊异地出现了一阵死一般的沉寂。我利用这个机会侧身滑下第二道壕沟的外崖,一到达沟底,就发现这暂时的沉寂不过是一场暴风雨的前奏。我刚刚在第二道城壕站定,暴风雨就开始了,最先是整个大气层都翻腾起来,像一个精疲力尽的壮汉重整旗鼓,再显神威时的一声长啸。现在从天空射到这个场景上来的光线,已经同虚无飘渺的磷光相差无几了。
狂风加快了速度,离开原来在开阔高地上的自然路线,取道城壕,长驱直入,在里面东奔西窜,身后还带着一阵急雨,随着急雨又袭来冰雹,成群结队的冰雹掠过壕沟,又滚,又跳,又蹦,又飞,噼噼啪啪冲下壕沟两边的斜坡,那样狼藉不堪,一派混沌。在倾盆大雨和飞溅冰雹轰击之下,两边的土坡好像都在颤抖,其实这也不过是色厄在敲打周坦国度[8]的巨人而已。不等到暴风雨多少停息一点,是不可能继续前进了,于是我就停在壕沟内侧的一个小岔口上,很可能两千年前正是在这个地方,曾经树立过一道路障;我就这样等待着情势发展。
可以听见暴风雨像步兵巡逻队似的,不时围着古堡一圈又一圈——每圈足有一英里——呼啸着飞掠过去。毫无疑问,当年的确有这样的队伍在这条路上通过,可是在最近这段时期,进到这里来的却只有羊群和牛群的队伍,在这里,如今有时还能够见到它们,惟有它们发出的声音和正在穿过峡谷沟壑的一阵阵风声,这两种强烈洪亮的声音才有相似之处。
原在意料之中的闪电把周围照亮了,从那些隐蔽的穹隆中——如果确有穹隆的话——发出一阵阵隆隆声,响彻整个古堡。闪电忽隐忽现,从前面提到过的有关军人的想象出发,闪电与战斗中刀光剑影简直相似得出奇。它具有昔日在这里挥舞过的古代兵器那种同样的黄铜色调。这种具有金属色泽的火焰,如此突如其来走进现场,就像一位展览会的主持人走了进来,翻开地图,揭开图表,打开展柜,仅在揭示以前还一直莫测高深地遮盖着的他那一学科的材料,就顿时全部改观了。悬岩峭壁和土阜圆丘那轮廓分明的形状,现在第一次清清楚楚地展现出来——毫无疑问,在那些土丘上,经常有长枪和盾牌弃置于地,而它们的那些主人则在阳光照耀之下,松开鞋子,张开大嘴,伸开胳臂,永世长眠了。同样也是第一次,当年占据古堡的人使用过的真正大门突然一闪,就在前面不远的地方。
在那里,一座几乎是直上直下的门脸矗立着,好像万夫难开,一道道护墙交叉重叠,宛如松松扣在一起的手指,而其中则有一条曲曲折折的小路——这种灵巧的构造,会使一个不明底细的人眼花缭乱,可是这种灵巧,即使是在那些还没有由于崩塌陷落而黯然失色的地方,现在也由于少数獾兔打出的几个洞穴而废毁了。当年的士兵一定在早晨走出这些大门去迎战韦帕辛[9]统帅下的罗马军团,晚上有些人不再返回,另一些人则带着他们的英雄业绩,鼓噪归来。可是也没有青史一页,也没有石碑一块来保存他们的英名伟业。
这天夜晚的听觉是多种多样的。我们几乎可以听到,岁月之流带着那些英雄业绩离开我们流向远方。在那个地点,那个门洞里,空中似乎飘荡着种种奇怪的发音;当年人们在那里进进出出的时候一定常常是笑语喧哗,群情振奋。还有一种无法消除的奇思妙想:它们就是人的声音;如果是,那么它们一定是至少十五个世纪以前人们谈话的时候振动空气产生的音波,滞留未逝。附近有个什么东西真在活动,吸引了注意力,使人不再对那个地方作只是渺茫的遐想。
闪电现在成了白色的,而且几乎连续不断,借着闪电不大强烈的光亮,我认出来,那是一个越来越高的小土堆。起初不过有一个人的拳头大小,后来达到一顶帽子的大小,然后下沉了一点儿,并且静止不动。原来不过是只鼹鼠在向上拱,它凭着某种本能,知道上边不会有人打扰它,才选择了这样一种天气在里面干活。随着细土一点点拱起来,拱起来,然后松松地落在一边,一些烧过的陶土碎片从土里边滚落出来,从前住在碉堡里的人使用的杯碗或其它容器,正是用陶土制成的。
暴风雨来得猛烈,去得也突然,也算是两相抵消了。刚才几乎是牢牢实实地陷身于云雾弥漫、冰雹轰击之中,更有雷鸣电闪,而此刻我发现自己脱掉了潮湿的衣衫,赤身露体,面对明月柔媚的顾盼,每一片带有水汽的草叶和宛如雾凇的苔藓表面,都有月光晶莹闪耀。
可是我还没有到达堡垒的内部,于是此时就来攀登那迟迟没有登上的第三道,也就是最后一道壕沟的内岸,它比前两道都陡峭。第一道是一个斜坡,可以缓步走上来,第二道可以蹒跚登上来,可是这第三道却要手脚并用了。爬到顶上,就有一件东西闯入眼帘,它是进入古堡区域之后,说明目前确实已经是到了十九世纪的第一个证据;这是立在一根杆子上的白色告示牌,借着西沉月亮的微光,刚刚能辨认出上面的字迹:
注意:——任何人如取走本土堡内之遗物、骸骨、砖瓦、石块、陶器或其它物品,或进行挖掘,一经发现,将依法予以检举起诉。
人到了这里就可以看得出来,现在脚下走过的地方和刚才的不一样:古罗马的断瓦残石虽然数量不多,但在草丛中仍然历历可见,足以证明这里确实曾有大厦矗立。在月光下,堡垒内部展现眼前,它如此宽敞,如此辽阔,仿佛真是一座山地高原,然而,它的范围却又全部在可以称作一座建筑的围墙之内。这是一个长久遭人进犯的残址;它的基石、柱础、门窗楣枋,甚至早在中世纪或现代历史开始之前就被搬运一空,用去建筑邻近的村落了。以前用来建造此地某个碉堡的石料,有许多现在都破开或凿小,成为周围远远近近的羊倌小房子壁炉架的一部分,这座异教祭坛的基石,也许垒成了附近某个村庄教堂的底层。
然而,这些内院和广场一概空空荡荡,它们只能作为牧场使用,这种情况却把残留的一切都保护起来,而这并非任何防御工事所能做到的。看不到留有任何人手可以攫取,气候可以侵蚀的东西,因此结果至少造成了亘古不变的大致轮廓,而这是其它任何条件都肯定无法达到的。
这座古堡建在这样一座孑然独立的山丘上,说明远古有那么一个智力超群的人物,能够透视遥远的未来,做出深思熟虑,高瞻远瞩的战略决策。这周围田野的天然形胜和它同这样一座堡垒结成浑然一体,在这座古堡的宏伟设计付诸实现之前,显然早已在他的心中反复推敲,成竹在胸了。“把它建在这儿!”——不是在那边那个山丘上,也不是在后面那个山梁上,而是在超越一切、无与伦比的这个优胜的地点——说出这句话的是什么人呢?他究竟是柏尔吉族[10]或是杜若垂基族的一个伟大人物,还是不列颠联合部落[11]哪个萍踪浪迹的能工巧匠,这一定会永远是一个不解之谜;不可能知道他的模样,或是他的相貌,他把脚在地上砰地跺了一下,说“把它建在这儿”,那时候他说的是哪种语言,也不可能知道了。
古堡连最里面的一层也是那样宽阔,一个人粗略看上一眼,只会有一种仿佛站在一个微风习习的开阔高地之上的感觉;然而置身其中,孤独之感不禁油然而生,而一旦想到:深更半夜在这里面逗留的人,同任何亲朋同类都为这三道同心的土墙所隔断,而且想到:假使有个人遭到鬼魂追逐,从这里发出惨绝人寰的号叫,即使有谁听见了,也决不会想要在这样一个黑夜里攀登这几道土墙,那么孤苦伶仃之感就会更加沉重了。我走到一个中央的小丘或者说讲坛,这里是整个建筑的绝顶和主轴。如果是在白天,从这里举目四望,那一定几乎是无边无际。在这座隆起的高地、高台或检阅台上,一些竖琴大概拨出过优美的音调,对英勇、力量和残酷表示过祝贺,对威严、迷信、爱情、生和死表示过庆祝,而对于单纯的仁爱,则也许从未表示过庆贺。国王或者首脑,也一定曾经多次把他那锐利的目光,转向今日在远处依然可见的伊斯宁大路[12]这一条古道,守望着那些或是为了增援或是为了进攻而逐渐逼进的武装部队。
突然,一个声音叫出我的名字,使我大吃一惊。由这个地方而生的怀古幽情和思今遐想,一直使我茫然若失,竟然忘记了,这个小丘正是我前面谈到的那个约会的地点。我转过身来,看见了我那位朋友。他站在那儿,手里提着一盏带有遮光罩的提灯,肩上扛着一把锹和一把轻便鹤嘴锄。他见我真地来了,表示出高兴和惊讶。我告诉他还没变天以前,我就动身了。
恶劣天气,一团黢黑或者困难重重,对他来说好像都毫无关系,毫无意义,因为他整个身心都沉浸在他自己的深切意向中了。他请我拿着提灯,陪着他走。我拿过提灯,走在他的身边。他约摸六十岁,小小个子,老式的灰白络腮胡修剪成一对扫面包屑用的刷子模样。他全身穿着黑色绒面呢的衣服——此刻不如说是黑褐色,因为他从脚上直到那顶低顶帽子的顶上,都沾满了泥浆。他并没有注意到这些,除了他要做的事情以外,他什么都感觉不到,他为了他那件事热情洋溢,连眼睛里都闪着光亮,就像是山猫的眼睛,而且使他动作灵活,完全同运动员一样。
“在夜里这个时候,没有人来打扰我们!”他高兴得要命,咯咯大笑起来。
我们向后走了不远,发现了一个拐角,比周围的草地高出一点,在周围这一堆不成形状的东西中间,现出方方的模样。他告诉我,如果要有的话,这里就是国王原来的宫室所在的地方。后来经过三个月的测量和计算,他的这个结论得到了确证。
他现在让我揭开提灯的遮光罩,我照办了,于是灯光便照射在湿漉漉的草地上。我终于识破了他的行径,我说,我守约前来,根本没有想到,他在这样一个不同寻常的时刻和我会面,除了在这个古堡中一边漫步一边冥想以外,他还打算做别的事情。我问他,既然有了切切实实的目标,他为什么刚才还要顾虑打扰不打扰,而且不挑选白天的时间呢?他不动声色地指了指他那把锹,然后告诉我,他的目的是要挖掘,随后又皱着眉头对那边那个反衬在天空下显得萧瑟憔悴的告示牌点了一下头。我问他,作为一个专业的而且远近闻名的考古家,有学位有地位,而且这样干又得受严厉的处罚,那么他为什么不去获取必要的批准呢?他按捺不住高兴,又咯咯大笑起来,并且说:“因为他们一向总是不肯通融!”
他说着立刻就挖起草皮来,等他拿起鹤嘴锄接着干的时候,又向我保证,处罚也罢,不处罚也罢,老实人也罢,强盗也罢,他反正相信一件事:天亮以前没有人会来打搅我们的工作。
我记得曾经听说过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因为热衷某种特别的科学、艺术或嗜好,丧失了道德感,而这种道德感本来是可以限制他们,使他们不至于沉湎其中达到非法程度的;我猜想,此时此地终于有了一个这样的实例。他现在或许在推测我的思路,因为他站了起来,郑重其事地声称,在这件事情上,他的意图是明明白白无可非议的;这就是发掘,研究,证实某种理论,或者放弃这种理论,然后重新掩埋起来。他的意思是说,不拿走任何东西——哪怕是一粒沙子。他说,他认为这不是什么十恶不赦的罪过。我问他,这真是对我作出的诺言吗?他重复我的话说,这是一个诺言。然后又接着挖起来。我在这件活儿上要出的力,就是让灯光老是照着他挖的那个洞。挖到约摸一英尺深的时候,他显得更加小心翼翼,并且说,不管东西是多是少,都不会离地面很深;这种东西从来都不是很深的。过了几秒钟,鹤嘴锄锄尖“咔哒”一声碰上一种像是石头的东西。他把这件工具抽回来,仿佛它已经刨进一个人的躯体里似地动情。他拿起锹,小心翼翼地铲土,很快就露出了一块同祭坛一样平平的地面。他的眼睛中又一闪一闪地发起亮来,他抓了几把草,把那块地面擦干净,最后又用他自己的手绢儿擦了擦。他把我手中的提灯一下抓过去,让它紧靠着地面,这时灯光照出了一整幅镶嵌画——由一块块色彩斑斓、图案精美的细致方砖铺砌起来的地面,一件不惜手艺,不惜时间,不惜气力制作出来的作品。他大叫一声,说他早就知道,这不仅是一座凯尔特人[13]的堡垒,而且也是一座古罗马人的堡垒;很可能凯尔特人原来不过建造了一个大致的轮廓,罗马人占领后加以改建,才使它成为眼前这种堂皇壮丽的建筑。
我问他,如果是古罗马人的,那又怎样呢?
照他看来,那就大有讲究了。这证明在这场重大争论中,大家全都错了,而只有他一个人是对的!他要继续挖掘,问我能等等吗?
我同意了——虽然不大情愿,不过他并没有注意到我不情愿。他在紧靠洞口的旁边,又抡起他那些工具。这位有学问,有地位,受人尊敬的学者,干起活来就像一个壮工一样熟练。有时他跪下来用双手刨挖,好像兔子打洞,他那身老式的绒面呢衣服蹭到洞口的地方,沾上了湿土。他不断地低声自言自语,说这次发现是多么重要,多么了不起!他取出了一件东西,用同样原始的办法——用湿草把它擦洗了一遍,原来是一个半透明的瓶子,艳如彩虹。看到这个彩瓶,我的朋友不禁大为感伤地沉吟起来,他一点一点继续向前仔细搜寻,又发现了一件武器。说来真是奇怪,我们只不过剥离了现代沉积的一层外壳,竟然就看到了一个古老的世界。最后发掘出一具骷髅,相当完整,他把它摆在草上,一根骨头对一根骨头,原封不动。
我的朋友告诉我,这个人一定是战死在这儿的,因为这里并不是埋葬死人的地方。他又转向那道壕沟,又挖又摸,后来从一个角落里掏出一个沉重的东西——一个四五英寸高的小像。我们像以前那样把它擦干净。这是一尊雕像,大概是金像,或者更有可能是镀金铜像——显然是尊墨丘利[14]神像,头上戴着带边帽,也就是那个有翅膀的帽子,墨丘利神通常都戴那样的帽子。更仔细察看一下,发现做工精美细致,而且因为保存在石灰质的土中,所以每一根线条都和它刚刚离开制作它的能工巧匠手中的时候一样崭新。
我们看来好像站在古罗马城镇的广场上,而不是站在威塞克斯的一座山丘上。我们聚精会神注视古罗马帝国——甚至这个遥远的地方都曾经是它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真正宝贵的遗物,根本没有注意当今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直到后来暴风雨又突然重新袭来,才提醒了我们。我抬头观望,看见乌云形成一个巨大的灭烛器[15],从这个城池堡垒上空压下来,好像落在内城的边缘上,把月亮阻隔在外面,我把背转过去朝向暴风,仍然把灯光向洞里照。我的同伴在继续挖掘,对周围的一切无动于衷。他现在生活在两千年前,看不见当前的一切东西,把它们全都视做幻梦。直到最后,他精疲力竭地在我身边站起来,环视周围,看着他所做的一切。提灯的光线越过内槽,照在摊放在对面的那具高大的骷髅上,倾盆大雨把骸骨冲刷得又干净又光滑,额头、颧骨和骷髅上的三十二颗牙齿,在烛光下闪着微光。
这场暴风雨和刚才一样,也是雨骤风狂,雹雨交加,而且也同刚才一样,突然停止。我们没有再挖。我这位朋友说,已经足够了——他已经证明了他的论点。他回过头去,准备把那堆骨头放进沟槽里掩埋起来。可是他刚一碰,那些骨头立刻成了碎块,空气风化使它们解体了,他只得扫起那些碎块。他计划中的下一个行动则更加困难,可是他执行了。那些珍宝又分别埋进它们原来的小洞里:它们并不是我们的。每放一样东西都好像使他感到一阵刺痛,有一瞬间,我似乎看见,他把手插进他上衣的口袋里去了。
“我们一定得把它们全部都重新埋进去。”我说。
“哦,是的,”他大义凛然地说,“我在擦手。”
堡垒统帅府第那片镶嵌地板的绝美花砖,再次沉入黑暗之中;那条沟槽也填平了,湿土平展地铺在上面。他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用的就是他曾经把刚才那具骷髅和铺地花砖擦拭干净的那条手绢儿。然后我们就朝城堡的东门走去。
我们到达开口处的时候,黎明突然展现在面前,它随着乌云逐渐消散,逐渐稀薄,姗姗而来,很快地我们全身都沐浴在粉红色的一片光明之中。他回家的路和我的不同,我们就在古堡外面那个斜坡下面分道扬镳。
我一边快步走着好使身体暖和起来,一边寻思着我那位行为古怪的朋友,心里不禁向自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他真地把那个镀金的墨丘利神像,和其它一些珍宝一起,又放进去了吗?看来他好像放进去了;可是我证明不了这件事。无论怎样,他很可能是言行一致的吧。
我自言自语着,这件奇遇也就这样结束了。
可是还有一件事要说一说,那是七年以后的事了。我那位朋友去世的时候留下一批动产,其中有一件精心保存的镀金小铜像——墨丘利神像,上面标着“罗马衰败时期”。它何时为他所有,未附记录加以说明。神像遗赠卡斯特桥博物馆。
(1885)
* * *
[1] 此即美登堡,在多切斯特西南二英里,为英国现存最大古代土堡,面积逾一百英亩,有两道城墙环绕,有些地方更有三道,城墙高六十英尺。
[2] 公元前二世纪古希腊天文学家、地理学家托勒密,在《地理》一书中论及罗马统治下的不列颠时总提到这一城市。
[3] 杜若垂基人为撒克逊人到达前在不列颠西南部地区生活的土著部落,首府在今多切斯特或附近。
[4] 在英国,西南风来自大西洋,是湿润的海洋风。
[5] 英国乡间道路两旁和农家周围多种植灌木,形成篱墙。
[6] 指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7] 英国散文作家j·班扬(1628—1688)的《天路历程》,叙述一个基督徒及其同伴受传播福音的人的指引,离开“毁灭之城”前往“天国之城”。途中历经艰险,包括翻越困难山。
[8] 色厄为北欧神话中的雷神,周坦为北欧神话中的巨人族。
[9] 韦帕辛为罗马皇帝(公元70—79年在位),继位前曾在克劳狄麾下任将军,参加远征。此次远征使不列颠于公元43年沦为罗马帝国之一省。
[10] 柏尔吉族为罗马人征服不列颠以前的当地土著民族。
[11] 不列颠联合部落为罗马人征服不列颠以前的当地部落。
[12] 伊斯宁大路是罗马帝国占领不列颠时修建的大道,北起诺福克,南达海岸。
[13] 凯尔特人为英国古代居民,撒克逊人迁居不列颠后,被迫退居北部和西南部的威尔斯、苏格兰、爱尔兰等地。
[14] 据罗马神话,墨丘利为诸神的信使,工匠和盗贼等的保护神。
[15] 指灭烛器的圆锥形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