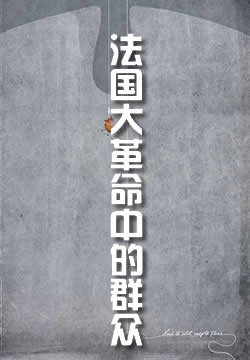“谈到什么展览会呀,世界博览会呀,诸如此类的事儿,”那位老先生说,“哪怕拐过街角就可以看它十个八个的,可现今我也不会去了。要在我这个脑袋瓜里留下一点儿印象,从过去到将来,也就惟有那破天荒第一遭儿,那是它们所有展览的老祖宗,眼下说,也就是老一辈时候的事儿啦——伦敦海德公园一八五一年的大展览。年轻的一辈人,谁也没法儿理解,它在我们大伙心里搅起的那股新鲜劲儿,那时候,我们个个都年富力强。一个正儿八经的字眼儿,居然都成了纪念那个场合的一个形容词儿啦。那时候有了什么‘展览’帽呀,‘展览’荡剃刀布呀,‘展览’表呀;不光这一些,甚至于还有‘展览’天气,‘展览’美酒、爱人、婴儿、老婆。
“说起南威塞克斯,那一年在好多方面都成了历史上了不起的分界线,或者飞跃线,那时候发生了许多事情,大家都可以把它们叫做时代的高峰。就像地质上的‘断层’一样,在我们眼面前,古代的和现代的都突然实打实地连在一起,在咱们国家这块地方,自从‘征服’[1]以来,大概从来没有哪一年发生过这样的事儿。”
老者的这一番话引起我们谈到各种不同的人物,那个时代在我们这些狭小、和平的土地上生活过,行动过的一些上上下下,高低贵贱的人。其中有三个人,他们那些稀奇古怪的小小故事,有些地方同大展览零零散散有些关系,可是比起住在那些穷乡僻壤斯蒂克福、麦斯托克和爱敦的其他任何人,那关系就要多得多啦。这三个人里面最突出的要数瓦特·欧拉摩尔——这是不是他的真名,姑且不论——咱们这伙人里面那些年岁大的,对他是很熟悉的。
据说,他是一个在外表上很能讨女人欢心的男人——在这方面简直无与伦比,别的不大明显。对于男人,他没有什么吸引力,有时候甚至还有点儿拒人于千里之外。他实际上是个乐师、花花公子和社交帮闲。他是个只说不干的兽医,在麦斯托克村住过一段时间,究竟从哪儿来,谁也说不上;然而有些人说,他第一次在这附近露面,是在绿山集市的一次表演会上拉提琴。
很多体面村民妒忌他,因为他对天真烂漫的少女有一种魅力——这种魅力有时候似乎有那么一点点不可思议和令人着魔的味道。从个人来说,他并不引人不快,可是相当缺乏英国味儿。他的皮肤是很深的橄榄色,满头浓密深暗的头发,黏糊糊的——擦上一种谁也不知道的油膏,就更加黏糊糊的了,他刚刚来到一个舞会上的时候,这种油膏让他身上闻起来有“童心爱”(青蒿)浸在灯油里的气味。他偶尔也有鬈发,两层鬈发几乎完全横着绕在他的头上。可是这种鬈发有时又看不见了,所以可以肯定,那根本不是天生的。有些女孩子原来爱他,后来一下变得恨他了,就给他取了一个绰号:“墩布”,因为他的头发密密麻麻,长得很长,全都披到肩膀上,时间一久,这个绰号就慢慢一点点地传开了。
他拉提琴,这可能和他具有迷人的本领大有关系,说句公道话,他拉琴很有属于他个人绝无仅有的特色,就像巡回传教士那样的。他拉出来的音调让人马上就能相信:“墩布”之所以没有成为第二个帕格尼尼,原因完全在于疏懒成性,不愿勤学苦练。
他拉琴的时候老是闭着眼睛,根本不看乐谱,好像是在随心所欲让琴自由地奏出乡下人从来没有听见过的如诉如泣的乐段。他创造种种方式表达央告乞求的感情,其中具有某种婉转如簧的特色,仿佛门柱也几乎为之心痛欲绝。他能让本教区任何一个敏于感受音乐的小儿,听到他拉的一支古老舞曲,几分钟之内就突然痛哭起来,他拉这些曲子的时候差不多完全沉醉其中,这些古老舞曲有上个世纪的乡村捷格舞曲[2]、瑞乐舞曲[3]和“心爱的快步舞曲”。它们的一些残缺不全的片断流传下来,甚至直到现在都还在新式的方舞[4]和飞旋舞[5]中影影绰绰地出现,不过没有名字而已,能够把它们辨认出来的,只有那些喜欢刨根问底的人,或者早年曾经和瓦特·欧拉摩尔这号人搅在一起的那些老古板和长期难得一见的人物。
他出名的时候稍稍晚于老麦斯托克合唱乐队,这个乐队是由杜威兄弟、梅鲁和其他一些人组成的,事实上,在那些威名远播的音乐家解散而且不再承担教职以前,他还没有崭露头角。他们衷心热爱谨严精确的作风,所以看不起这位新派人物的风格。提奥菲利斯·杜威(车马行卢本的弟弟)总是说,那种演奏缺乏“精华”——没有弓法,没有完整性——完全是异想天开。大概真是这样。然而十分明显,“墩布”有生以来从来没有拉过教堂音乐的一个曲子。他从来没有在麦斯托克教堂的楼座上坐过一次,其他的人则在那里协同演奏赞美诗达成百上千次之多,而且他完全可能从来没有进过教堂。他演奏的节目全都是魔鬼的调门。“他不会演奏《老曲第一百》[6],就像他不会演奏那种黄铜蛇形管一样,”那个车马行老板常常会这样说。(在麦斯托克,人家认为黄铜蛇形管是特别难以吹奏的乐器。)
“墩布”偶尔也能对一些成年人产生上面说过的那种使人感动的效果,特别是对那些脆弱敏感的年轻女人。卡琳·埃斯彭特就是这样一个人。虽然她遇见“墩布”·欧拉摩尔以前就已经订婚了,可在她们中间她却是受影响最大的,他那不知不觉使人丧魂失魄的旋律,使她感到不安,不,使她确实感到痛苦,终于受到伤害。她是一个漂亮姑娘,一副惹人见怜的模样,拙于言词,她同女伴们在一起,主要的缺点就是常常喜欢闹点别扭。那时她还没有住在“墩布”所住的麦斯托克教区,而是住在几英里之外的斯蒂克福,那在河的下游。
她是如何认识他,如何听到他拉琴,而且究竟是在什么地方,说真的,谁也不知道,但是大家的说法是这样的:事情要不是在那年春天开始的,就是在那年春天发展的,那是一天傍晚,她经过下麦斯托克,偶然在他家附近的桥上停下来休息,无精打采地靠在桥栏杆上。“墩布”这时正照例站在门口的台阶上,在他那把提琴的e弦上用三十二分音符和六十四分音符为来往过路的人编织出神不知鬼不觉的罗网,看着围在他身边的小孩子们泪流满面则哈哈大笑。卡琳假装在聚精会神地欣赏桥下流水的涟漪,而实际上她却是在侧耳倾听,这一点他是知道的。不久她心上的痛苦同时又加上了狂热的希望,想在无穷无尽的舞蹈迷阵中轻盈起舞。为了摆脱这种令人神魂颠倒的魅力,她决心继续朝前走,虽然这就必须在他拉琴的时候从他前面走过去。她偷偷地对那个拉琴的看了一眼,觉得放下心来,因为他双眼紧闭,一心一意在拉琴,于是她放心大胆地迈步走去。但是靠近一点儿之后,她的脚步就畏缩起来了,她每走一步都踏着节拍越来越颤颤巍巍,后来几乎就像是一路在跳舞了。她走到他正对面的时候,又朝他看了一眼,忽然看到他有一只眼睛睁着,嘲弄地盯着她,仿佛在笑她那种动情的样子。她离开那所房子已经很远,脚步才不再不由自主地跳跶;一连几个小时,卡琳都挣脱不了这种奇怪的着迷劲儿。
从那天以后,附近不论什么时候举行舞会,若是“墩布”·欧拉摩尔去当琴师伴奏,卡琳只要能够弄到请帖,她都想方设法去参加,虽然这样有时要步行几英里;因为在斯蒂克福,他并不像在别处那样经常演奏。
证明他对她具有影响的其它一些证据,也是非常奇特的,这得要一位神经病医生才能充分说明。她常常在晚上天黑以后安安静静地坐在她父亲——教区执事——的房子里,这所房子位于斯蒂克福村街道中部,在下麦斯托克与摩尔福之间一段东西向的大道上,两地相距五英里。在这里,她父亲、姐姐与前面实际已经提过的那个年轻人正闲聊。这个年轻人一心一意讨好她,并不知道她已经着了魔的事。突然她从壁炉边的座位上跳起来,仿佛受到了电击,疯癫一般朝着天花板往上跳,然后大哭起来,泪流满面。大概要过半个钟头,她才像平常一样恢复平静。她父亲知道她这种歇斯底里的毛病,对他这个小女儿的怪脾气,总是特别担心,害怕是一种癫痫病发作的症候。她姐姐朱莉亚则不然。朱莉亚已经发现了这种情况的原因。在卡琳往上跳的前一刹那,外面有一个男子沿着大道走过去,他的脚步声从烟道传来,只有特别精细敏感的耳朵,在壁炉旁边僻静的地方才能听见。卡琳一直在等待那脚步声,而正是那阵脚步声,才是她情不自禁跳跃的原由。这位姑娘知道,过路人就是“墩布”·欧拉摩尔,可是他走这条路并不是来拜访她;他去看的是另一个女人,他提到过那是他的未婚妻,她住在摩尔福,还要朝前走两英里。有一次,而且仅仅只有那一次,卡琳怎么也憋不住,终于开口了;那时刚好只有她姐姐一个人在场。“哦—哎—哟!”她大叫起来。“他是去看她,而不是来看我!”
为琴师说句公道话,他开头对这个性格易感的姑娘并没有想得很多,或者和她谈得很多。但是不久他就发现了她的秘密,忍禁不住要和她那太容易受到伤害的心来一段穿插演出,作为他在摩尔福那边比较认真求爱的正戏中的插曲。这两个人变得熟极了,虽然都是偷偷摸摸的。在斯蒂克福,他们的恋情,除了她姐姐和她情人内德·希普克若夫特知道以外,几乎没有任何一个人知道。她父亲不赞成她对内德冷淡,她姐姐也希望她能打消这种神经过敏的热情,不要迷恋几乎谁都对他一无所知的那个男人。可是最终的结果却是:那位果断纯朴的求婚者爱德华[7]明白了他的追求实际上越来越没有希望,他是一个体体面面的技工,地位比那个挂名兽医“墩布”牢靠得多。在他离开她之前,他直截了当对她提出了最后一个问题:她是否愿意说到做到嫁给他,要么马上结婚,要么从此分手。这件事儿,除了她给他一个否定的答复以外,不会有任何别的指望。虽然她父亲站在他这边,她姐姐也站在他这边,可是他拉不了琴,没法儿像“墩布”那样把你的灵魂像蜘蛛丝一样从你的身体里抽出来,最后让你觉得仿佛旋花草一样软弱无力,渴望找到什么东西可以攀附在上面得到支持。的确,希普克若夫特根本没有一只音乐的耳朵,唱两个音都唱不准,更不用说演奏了。
他本来就等着而且确实也从她那儿得到了那个答复:不行(尽管起初还有点希望)。这就使内德的生活开始了一个新起点。他用一种哀痛恳求的声调对她说,他决心不再缠着她让她为难,她再也不用因为远远在街道上或小巷里看到他的形影而感到苦恼。他离开了那个地方,他的路很自然是通向伦敦。
那时通往南威塞克斯的铁路还正在修建之中,没有通车运行,希普克若夫特同以前许多比他地位优裕的人一样,步行六天到达首都。手艺人用步行的办法走到雇用劳动力的巨大中心去,从记不清的时候起直到那时,大家都习以为常;而现在却成为历史陈迹了,他就是那种手艺人中最后的一批。
在伦敦,他依靠他这个行当循规蹈矩地过日子,干活儿。他比许多人都更走运,由于他不图私利,乐于助人,从一开头就受到欢迎。以后接连四年,他从来没有找不到活儿干。按照现代意识来说,他既没有上升,也没有下降;作为一个工人,他有所改善,但是他的社会地位,却丝毫没有变动。他对卡琳的爱情,他硬是保持噤口不谈。毫无疑问,他常常想念她,可他老是忙着,而且在斯蒂克福也没有什么亲戚,所以与那个地区不打任何交道,也没有表示过要回去的愿望。在兰贝斯[8]他那个安静的住处,干完了活儿以后,他以女人那种灵巧麻利劲儿,自己做饭,补袜子后跟,逐渐使自己显出像是要打一辈子光棍的样子。由于这种行为,人们当然就有正当理由说,时间并没能把小卡琳·埃斯彭特的形象从他的心里抹去,而这种理由可能有一部分是对的,但也有一种猜想,认为他的性格本身就是不大看重从异性的侍候中求得安慰。
他住在伦敦当技工,到了第四年正好是前面说到的海德公园博览会的那一年。他每天都在当时世界上还无与伦比的那个巨大玻璃房子[9]的建筑工地上干活儿,那是在各国之间和各行各业之间怀有伟大希望和展开巨大活动的一个时代。希普克若夫特虽然是以一种微不足道的方式成了这场运动中的一个中心人物,他还是勤勤恳恳,外表显得很平静。然而对他来说,这一年也注定要出现种种惊人的事情,因为那座建筑已经准备就绪,开幕前的忙碌也成为过去,开幕仪式大家也都亲眼见着了,人们从世界各地蜂拥而来。这时,他收到了卡琳的一封信,在这之前,他同斯蒂克福之间连续四年一直音讯杳然。
她告诉她过去的情人,为了弄清他的地址而碰到的困难,然后提到了促使她写信的事情。她的字迹模糊不清,说明她的手发抖。她用她擅长的最为巧妙的办法说出来,她四年前拒绝他,该是多么愚蠢。她头脑糊涂顽固不化,从此以后就多次给她带来悲伤,而最近更是如此。至于欧拉摩尔先生,则早已离开此地远走他乡,几乎同内德一样久,而她根本不知道他在哪里。如果内德再向她求婚,她会高兴嫁给他,而且要做他温柔娇小的妻子,一直到她离开人世。
如果我们可以从结果来判断,得知这个消息一定会有一股温情流过他的全身。毫无疑问,他依然爱她,即使还不到把其它任何幸福都置之度外的程度。这是从他的卡琳那儿来的,正是她,这些年来对他宛如死去一般,而现在又像从前一样复活了。这本身就是一件令人愉快、令人心满意足的事。内德已经逐渐屈从于,或者说满足于他自己那孤独的命运,所以他对任何事情都表示不出多少的欢欣。然而,某种专心致志的热情透露出:她承认对他满怀信心,这件事多么深刻地激动着他。他按照他那深思熟虑、有条不紊的方式,在当天,第二天,第三天都没回信。他得“好好想一想”。等到他真正回信了,他的回答里有大量严谨周密的推理,又夹杂着明确无误的脉脉温情;不过那种脉脉温情本身就足以透露出,他对她那种直言不讳的坦诚很为高兴;她以前曾经在他心中得到的安全碇泊所,即使不是一贯都很牢靠,也是可以恢复如初的。
他的信中夹杂着不多的几个略带挖苦的字眼儿,他写的时候嘴唇诙谐地抽动起来。他告诉她,她要是这个时候来,一切都是很好的。他想要她,那么她为什么不来得到他呢?她毫无疑问已经了解到,他还没有结婚,但是假定他的感情已经寄托在另外一个人身上了呢?她应当请求他宽恕,然而,他并不是那种能够对她忘怀的人,但是想想他一直受到怎样的对待,他受了多大的痛苦,她就不可能指望他到斯蒂克福去接她了。可是如果她愿意来找他,说她觉得对不起他,那才公平合理;那么,好吧,他知道从本质上看,她还是个多么善良可爱的小女人,他会娶她的。他还添了一句,说请她来找他,比起他第一次离开斯蒂克福,或者比起几个月以前,都要容易多了;因为新修的通向南威塞克斯的铁路,现在已经通车,而且为了博览会,还刚刚开始运行设计精巧、令人惊叹的特别列车,叫做游览列车;所以她一个人不必费力就可以到这里来。
她回信说,她对他热了一阵又冷了下来,而他对她却那么慷慨大度,他真是太好了;说她虽然对这么远的旅行感到害怕,她还从来没有坐过火车,只是远远看见过一列火车驶过,可还是衷心接受他的提议;而且确实对他感到歉疚,并且请求他宽恕,要努力永远做一个好妻子,补偿已经失去的时间。
剩下的关于何时何地等等细节很快就说定了,卡琳通知他,为了便于他在人群中认出她来,她要穿上“我那件绣花紫丁香色的新棉布长袍”,而内德则愉快地回答说,她到达以后第二天早晨结完婚,他就花一天时间带她去博览会。就在那年夏季的一天,中午刚过不久,他就按照约定从他干活儿的地方出来,匆匆忙忙赶到滑铁卢车站去接她。那天就像英国六月天偶尔会有的那样,又湿又冷,可是他在蒙蒙细雨中等在月台上的时候,他身体内部灼热起来,好像又有了某种东西,可以为之生活了。
“游览列车”在旅行历史上是一个崭新的起点,当时在威塞克斯线上,而且很可能在任何地方,都还是一种新鲜事儿。一群群的人涌到沿线所有的车站,来看那么长的一列火车驶过去,甚至在那些享受不到它所提供的便利条件的地方,人们也是如此。在早期蒸汽火车处于实验阶段的时代,低等乘客的座位是在敞篷车皮里,没有任何遮风挡雨的防护措施;下午潮湿的天气渐渐开始,停在伦敦终点站的那列火车上,坐在这种车皮里的可怜乘客,由于长途旅行而处于可怜巴巴的境地,个个脸色发青,脖子僵直,打着喷嚏,浑身被雨淋透,冷彻骨髓,许多男人连帽子也没戴;事实上,他们正像整夜颠簸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坐在敞篷小船里的乘客,而不是在内陆寻求乐趣的旅游者。女人们多少还可以掀起长袍的裙子包在头上,可是这样一来屁股又没有了遮拦,他们或多或少全都处于狼狈不堪的困境。
火车开进车站之后,男男女女忙着下车,吵吵嚷嚷,推推搡搡,内德·希普克若夫特的眼睛立刻就搜寻到了那个小巧苗条的身影,和原来说的一样,穿着绣花紫丁香花色的衣服。她露出担惊害怕的微笑,走到他跟前来——虽然因为长时间的风吹雨打而全身潮湿,面容憔悴,直打哆嗦,可是依然俊俏可爱。
“哦,内德!”她激动地说,“我——我——”他把她抱在怀里,吻了她,而她这时却突然哭了起来,泪如雨下。
“你身上都湿了,我亲爱的小可怜儿!我希望你不要着凉。”他说。他看看她身边各式各样的包裹,注意到她用手牵着一个刚刚学步的孩子——约摸三岁大小的一个女孩儿——她的头巾同别的旅客一样粘糊糊的,柔嫩的脸蛋也同别的旅客一样发青。
“这是谁——是你认识的什么人?”内德好奇地问。
“是的,内德,她是我的。”
“你的?”
“是的——我自己的。”
“你自己的孩子?”
“是的!”
“可是,谁是她父亲?”
“你向我求婚过后我找的那个年轻人。”
“嗯——上帝——”
“内德,我在信里没有提,因为,你知道,多不好解释呀!我想,等我们见了面,我可以告诉你,她是怎么生下来的,比写信好得多!内德,我希望你原谅这一次吧,不要责骂我,你看,我走了多么、多么远才到呀!”
“我断定,这指的是‘墩布’·欧拉摩尔先生!”希普克若夫特说,他因为吃惊倒退了一两码,隔着这段距离,他脸色苍白地盯着她们俩。
卡琳喘着气。“可是他已经走了好几年啦!”她恳求说,“而且我以前从来没有找过哪个年轻人!我该多么倒霉呀,他第一次诱骗我,我就上当了,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咱们那儿有些女孩子还不是什么事都继续照样干吗!”
内德仍然沉默不语,心里在琢磨。
“亲爱的内德,你会宽恕我吧?”她又说了一句,干脆就呜呜哭起来了,“我毕竟还没有骗上你,因为——因为如果你愿意,你还可以再把我们打发回去;不过这有好几百英里,又这么湿,马上就要天黑了,而且我一文钱也没有!”
“见鬼啦!我可怎么办?”希普克若夫特苦恼地呻吟道。
再也没有比这一对无依无靠的母女俩更可怜的景象了。阴雨天她们站在这个高大、凄凉、满是泥泞的月台上,不时有一阵细雨吹到屋顶下面淋到她们身上。她们大清早动身离开斯蒂克福的时候身上穿的漂亮衣服,现在都弄得一塌糊涂,完全湿透了,她们脸上显得疲惫不堪,眼睛里充满怕他的神情;看上去孩子也像是在想,她也做了什么错事儿,吓得一声不吭,后来眼泪汪汪,泪水沿着她胖乎乎的脸蛋流下来。
“怎么回事?我的小姑娘?”内德死死板板地问她。
“我要回家!”她说话的声音好像是心里再也憋不住的样子,“我的脚指头冷,我再也吃不到黄油面包啦!”
“真不知道,面对这一切,我该说些什么!”内德说,他转过身子,低着头走了几步,自己的眼睛里也是潮乎乎的;然后又直瞪瞪地望着她们。孩子困难地喘着粗气,一声不响地流着眼泪。
“想要点儿黄油面包吗,你?”他装出一副生硬无情的样子问道。
“是——是——的!”
“好吧,俺敢说,俺能给你弄一点儿!自然,你一定是想要一点儿的。你呢,卡琳,也想要一点儿吧?”
“我确实觉得有点儿饿,不过我可以忍过去。”她小声说。
“谁都不应该那么干,”然后他粗声粗气地说,“好啦,走吧!”他一边抱起那个孩子,一边又说下去,“无论如何,我想,你们今天晚上得住在这儿!不然,你们怎么办?俺给你们弄点儿茶和吃的;至于这件事情,我相信我不知道要说些什么!这是出站的路。”
他们什么也没说,一起来到内德的住处。那地方并不远,到了家他把她们的衣服烤干,让她们舒服一点儿,并且把茶准备好了,她们满怀感激地坐下。他突然发现自己成了这现成的一家之长,而这个现成的家使他这间小屋平添了一种温暖安适之感,使他自己成了父辈。过了一会儿,他就转向孩子,吻了她现在已经红喷喷的脸蛋儿,然后带着沉思渴望的眼睛看了看卡琳,也吻了她。
“你跑了这一大段路来这儿,就是要和我团聚,”他声音低沉地说,“我不明白,我怎么能这么老远又把你打发回去。可是你必须信任我,卡琳,并且表现出你对我真正相信。好啦,你现在觉得好一点儿了吗,我亲爱的小女子?”
孩子兴高采烈地点了点头,可是她的嘴却一直没有停过。
“内德,我来,就是真正相信你,而且我要永远如此!”
就这样,他虽然没有肯定同意宽恕她,还是勉勉强强地默默接受了上天给他安排的命运。在他们结婚的那一天(婚礼并没有像他原来打算的那样快,因为在教堂预告结婚后要等一段时间),他们从教堂回来以后,他就像他原来答应过的那样,带她去博览会。在一个家具陈列馆里,他们站在一面大镜子旁边,卡琳吓了一跳,因为镜子里照出一个人的身影,和“墩布”·欧拉摩尔一模一样——一模一样到了那种地步,除去是那个艺术家本人照在镜子里之外,简直不可能相信是另外什么人。可是等到内德、卡琳和孩子绕过挡住他们没法直接看到他本人的种种东西之后,却根本看不到“墩布”。他当时是不是真的在伦敦,一直都是个不解之谜,而且卡琳总是竭力否认这种说法:她之所以乐于到这个城市里来会内德,是由于有一种流言,说是“墩布”也到那里去了。要怀疑她的这种否认,也没有任何合理的根据。
那一年飞逝而过,博览会闭幕了,成了往事。公园里遮了六个月的树木,又显露出来,受风吹雨打,草地也重现绿茵了。内德看得出来,卡琳成了非常好的妻子和伴侣,虽然她已经使自己在他眼里所谓的贱了。可是在这方面,她也像另外的家庭用品,一把贱茶壶一样,常常能比一把贵茶壶沏出更好的茶来。一年秋天,希普克若夫特觉得他自己没有多少活儿可干了,而且到冬天景况会更差。他们两个都是在农村里土生土长的,所以都以为,他们会乐意重返他们那自然的环境中去生活。两个人就这样决定了:离开在伦敦那个幽禁他们的住所,到内德的老家附近去找活儿干,他的妻子和她的女儿,则在他寻找工作和住房的时候,暂时和卡琳的父亲住在一起。
卡琳和内德一起旅行,回到她两三年前在沉默和阴暗中离开的那块地方,一路上她那容易激动的娇小身躯洋溢着阵阵得意的情绪。一位满面春风的伦敦主妇,带着清清楚楚的伦敦口音,回到她曾经遭人白眼的地方,这本身就是这个世界上并非天天得见的一种凯旋荣归。
火车不在离斯蒂克福最近的那个路边小站停车,这三口儿坐车坐到了卡斯特桥。在这座郡城里,大家原来都知道内德,所以他想,这是一次好机会,可以在这里的一些作坊里初步打听一下是否有活儿可干。卡琳和她小女儿由于长途旅行觉得很冷,又看到地上是干的,而且天色还只刚刚接近黄昏,月亮正要升起,所以就步行往斯蒂克福去,留下内德让他随后快步赶上来,到中途某一所房子,就是谁都知道的那个旅店去接她。
女人和孩子沿着那条记得很熟的路十分轻快地走着,可是越走越乏。在三英里长的这段路上,她们走过了粗心威廉池塘,花区尽头儿旁边那个熟悉的路标,快要走到爱敦荒原山麓路边那家孤零零的静女客店了,从那以后这家客店已经废弃了许多年。卡琳正往上走的时候,忽然听到一些声音,原来那天下午在那个地点附近举行育肥食用家畜拍卖,她想,孩子和她都一样最好休息一下,于是就进去了。
客人和顾客很多,一直挤到过道里来了,刚进大门,她以前见过的一个男人正走过来,手里拿着一个喝酒的杯子和一个盛酒的缸子,朝倚在墙上的一个朋友走去,可是看见她了,就走过来大献殷勤,要请她喝一杯酒,这是热乎乎的金酒和啤酒混合酒,他倒了满满一杯,接着说:“一点儿不错,这就是原来那个小卡琳·埃斯彭特呀——到斯蒂克福去?”
她答复说是的,虽然她并不是恰好需要这种饮料,不过既然已经端上来,她还是把它喝了,于是请她喝酒的那个人又请她再进里边去坐坐。她一进了屋子,就发觉所有在场的人都紧靠墙边坐着,只有一把椅子空着,她也照样坐下了。接着就是说明他们的情况。“墩布”站在对面墙角里,用松香擦他的提琴弓,看上去和以前完全一样。大家把屋子中间的人请走了,准备跳舞,他们就要重新开始跳了。她戴了一块面纱挡风,所以以为他认不出她来,也不可能猜出孩子是谁;她发觉自己在他面前能够十分平静——以她在伦敦的生活教给她的庄重态度自制自持,感到又惊讶,又高兴。她还没喝完杯中的酒,跳舞就开始了。跳舞的人分成两行,音乐响起来,舞步开始了。
对卡琳来说,事情起了变化。她内心的战栗又复活了,手抖得很厉害,简直没法儿把酒杯放下。让这个伦敦主妇战栗的不是这场舞,也不是跳舞的人,而是那把提琴拉出的音调,这些音调依然具有她往昔那么熟悉的全部魅力,而在这种魅力的驱使下,她一向没有力量保持独立的意志。怎么这一切又同样发生了呢!又是那个靠着墙拉琴的形象;他那个擦了油、像墩布一样的大脑袋,还有在墩布下面双眼紧闭的脸孔。
开头那一阵,她陷入奇想,动弹不得,随后那用熟悉的手法演奏出来的那种熟悉的曲调,使她哈哈大笑,同时又泪流满面。后来跳舞队形的尾部,有一个男人的舞伴走了,那个男人就伸出手来,招呼她去接替空下来的位子。她不想跳舞;她用手示意,恳求让她就那样待着,可是她不是在向那个跳舞的男人恳求,而是在向那个曲调和演奏那个曲调的人恳求。这个琴师和他那狡猾的手段,以前一向都能够挑起卡琳跳舞的意愿,现在又和多年以前一样把她紧紧抓住了,可能热乎乎的金酒和啤酒混合酒也起了促进的作用。她固然很累,还是用手抓住她的小女儿,一头扎进跳舞队形的尾部,和其余的人一起旋转起来。她发现,和她一起跳舞的大多是附近小村庄和农场的人,比如花区尽头儿、麦斯托克、柳盖特和其它等地的人。她不停地拼命跳,逐渐就给大家认出来了,她希望“墩布”停下来,好让她的心脏还有她的脚能休息一下,他让她两只脚都跳疼了。
过了长长的许多分钟之后,这场舞停下来了,这时大家劝她再喝些金酒和啤酒混合酒来提提神;她喝了,感到浑身发软,被歇斯底里的激情压倒了。她强忍着不揭开面纱,如果可能,好让“墩布”不知道她在场。有几个客人已经走了,卡琳匆匆擦了擦嘴唇,也转身要走;可是,据几个留下没走的人说,就在这个当口,有人建议来一场五人跳的瑞乐舞,其中有两三个人邀请她参加。
她借口累了而且还要步行去斯蒂克福,不肯参加,这时“墩布”开始挑逗似地拉起d大调《我的情郎》,大家踏着这个曲调的节拍跳起瑞乐舞来。虽然她还不知道,他一定是早就认出她来了,因为她最无力抗拒的就是这个曲调——他们初次认识的那天,当她倚靠在桥上的时候,他拉的就是这个曲子。卡琳感到绝望似地和其他四个人一起走到了屋子的中间。
附近这一带,精力充沛的人,在此刻都采用瑞乐舞来消减过剩的精力,因为普通的花样舞蹈用力还不够大,不足以把它全部耗尽。每个人都知道,跳这种瑞乐舞的五个人站成一个十字形,每行都是三个人,两行交替舞蹈,跳舞的人一个接一个走到中心的位置,和两个方向的人一起跳起舞。卡琳很快就发现自己站在这个位置,也就是整个表演的轴心,而且没法走出来,因为曲子不给她机会就又回到开头那一部分去了。现在她开始怀疑“墩布”真是看出她来了,所以故意这么做,虽然她每次偷偷看他的时候,他那双紧闭着的眼睛总像在表示,除了他自己的脑子以外,对一切都茫然无知。她跳的路线形成了一个“8”字,她就沿着这个“8”字继续不断地跳。这时拉琴的人在他的音调中加进了一种过于精细入微、惟妙惟肖的声音,其中饱含着那种粗野狂暴而又令人痛苦的甜蜜温馨;它凄楚哀婉,忽高忽低,变化无穷,刺激她的神经,激起令人痛楚的痉挛,虽然饱受痛苦的折磨而又觉得无上幸福。屋子里天旋地转,乐曲无尽无休,大约一刻钟的工夫,舞蹈队中的另一个女人精疲力竭退场了,跌坐在一只板凳上气喘吁吁。
瑞乐舞即刻变成了四人跳的。卡琳本来可以不顾一切一走了之,但在“墩布”演奏这样一些曲子的时候,她没有——或者说她自以为没有——力量这样做。就这样又过了十分钟,现在尘土飞扬,缭绕在蜡烛周围,石铺的地上撒上了细砂。又一个跳舞的人掉了队,这是一个男人,他走到过道上找酒喝去了。转眼的工夫,队形就变成三人瑞乐舞了,“墩布”在这同时把曲子转成了《仙女舞》,这样就更加适合缩减了的动作,而且这支曲子由他的弓拉出来,同样也是一种爱情滋补剂,总是一向让她心醉神迷。
跳三个人的瑞乐舞,根本就不可能休息,跳上四五分钟,她那剩下的两个舞伴就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了,他们跳完最后那一小节,就像前面那些人一样,一瘸一拐地到隔壁房间去找点儿什么喝喝了。卡琳戴着面纱憋得半死,现在只剩下她一个人在跳,屋子里现在除了她自己、“墩布”和他们的那个小女儿以外,已经没有任何人了。
她摘掉面纱,用眼睛看着他,好像是在恳求他,让他把他自己和他那具有磁力的音响从周围撤走。“墩布”张开了他的一只眼珠子,好像还是第一次似地,死死盯着她,而且梦幻似地微笑着,他刚才没舍得把全部感情浪费在规模很大、吵吵嚷嚷的舞蹈上,现在把留下的那一部分没有流露出来的感情,全都倾注到他的乐曲里去了。大量细小的半音阶纤巧变化,足以使石人落泪,而今都立刻从他那把古老的提琴里抒发出来,似乎它在意大利或德国某个城市里制作成形,发出音响,然后离开那里以后,感情一直幽禁在里面,因而几乎压抑得快要绝命似的。“墩布”那一只阴沉沉的眼睛,表现出来的就是这种神情,仿佛在说:“亲爱的,你走不掉,不论你愿意还是不愿意!”而这却反而使她突然拼命挣扎起来,坚决不让他把自己累得精疲力竭。
她继续一个人跳着,自以为这是在抗拒他,可事实上却奴颜婢膝百依百顺地完全随着旋律的一起一伏而跳动,而蛊惑她的人那只睁开的眼睛就像一把锥子一样锐利地盯着她察看,同时脸上还一直挂着微笑,仿佛故意认为,依然是她自己乐意继续跳着。如果她要走掉,那么对他说些什么呢——这个极其为难的问题,起了难以察觉的作用,使她滞留不去,这种奇怪的情势,开始让那个小女孩儿觉得难受了,她走上前去,哭哭啼啼地说:“站住吧,妈妈,站住吧,我们回家吧!”一边抓住卡琳的手。
突然,卡琳摇摇晃晃地倒在地上,她翻滚过来把脸朝下,平平地躺在地上。“墩布”的小提琴这时像一个淘气精一样发出了最后一声尖叫;他迅速从他的演奏台——那个装九加仑啤酒的大桶上跳下来,走到小女孩儿身边,她当时正弯下身去伤心地看着她妈妈。
那些到后面房间去找酒喝和换空气的客人,听见发生了什么不同寻常的事情,都蜂拥着跑回这里来,他们竭力要让可怜衰弱的卡琳醒过来,朝着她放声大喊,并且打开窗子。她丈夫内德,前面已经说过,在卡斯特桥耽搁了一下,这时候正沿着大路走过来。他从打开的窗子听到人们激动的声音,而且感到非常吃惊的是他们提到他妻子的名字,于是他走进来,与别人一起来到出事的地点。卡琳这时正在抽搐,大声哭泣,有很长一段时间,对她没有一点儿办法。希普克若夫特一边请人找大车,好把她送回斯蒂克福,一边焦急地打听是怎么会弄成这样的。在场的人告诉他,以前在这一带很出名的一个提琴师,最近回来访问他过去经常出没的地方,今天晚上他不请自来,到这个小客店拉琴,组织了一场舞会。
内德问到这个提琴师的名字,他们说是欧拉摩尔。
“哎呀!”内德大喊了一声,四下打量,“他在哪儿?我的小姑娘——她又在哪儿?”
欧拉摩尔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那个孩子也是一样。希普克若夫特平日是个不声不响、温驯善良的人,可是现在他脸上现出使大家担心的一种毅然决然的神情。“该死的东西!”他大声叫嚷,“我要把他的脑瓜凿个粉碎,哪怕明天为这件事上绞架,我也不在乎!”
他冲到火炉旁边,拿起拨火棍,急忙跑过过道,大家都跟在他身后。屋外大路的那一边,黑压压的一片荒原阴沉沉地向上隆起,通向人迹难以接近的深处,那是一片谿谷纵横的高原,直刺天空。几英里以外的地方,约伯瑞的灌木林紧接着米斯托弗的枞树林,此刻,那里正是但丁描绘的那种阴森处所,一个炮队都可以在那里藏得严严实实,更何况一个男人和一个孩子呢。
有几个人和他一起向那里冲去,更多的人则沿着大路往前走。他们走了大约二十分钟,就毫无结果地回到小客店去了。内德坐在高背长靠椅上,双手捧着自己的前额。
“唉,要是这个男人以为那个孩子是他的,像是看着那样,那么他该多愚蠢,这些年来一直都是!”大家小声嘟囔着,“可谁都知道,不是那么回事!”
“不,我知道这个孩子不是我的!”内德从自己的手上抬起头来粗声粗气地说,“可她是我的!我没有抚养她吗?我没有养活她,教育她?我没有跟她一起玩?啊,小凯瑞——跟那个流氓走了——走了!”
“毕竟你还没有丢了老婆呀,”大家安慰他说,“她把酒吐出来,这会儿好些了。那个孩子又不是你的,她总比一个小孩子更要紧吧。”
“她才不呢!她对我可并不那样了不起,特别是现在她又把那个小姑娘弄丢了!凯瑞才是我的心肝宝贝!”
“噢,很可能,你明天会找到她的。”
“啊——可是,我能找到吗?不过他是没法儿伤害她的——肯定他没法儿!嗯,卡琳现在怎么样啦?我准备好了,大车来了吗?”
大家把她抬上了车,他们垂头丧气地赶着车向斯蒂克福走去。第二天,她安静一点儿了,但有时还是发作;并且她的意志几乎完全消沉了。对于那个孩子,她好像并不感到特别焦心,可内德却因为对那个并非他亲生的孩子满怀强烈的父爱被弄得心烦意乱,几乎发疯。尽管如此,大家还是期望,那个专爱捣鬼的“墩布”只是出于异想天开,过一两天之后就会把孩子送回来。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了,既没有听到他的消息,也没有听到孩子的消息。希普克若夫特小声嘟囔,猜测着也许他也在对孩子施加某种邪恶的音乐魔力,就像他曾经对卡琳本人施加过的那样。过了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他们一点儿也没得到提琴师或是那个女孩子究竟在哪里的消息。“墩布”怎么能够诱骗她跟着他走,这始终是一个不解之谜。
内德在这一带只能找到一些临时性的零活儿干干,于是对这片故土他突然产生了仇恨。一天,他从警察那里听到一种传闻,说是在伦敦附近一个集市上看见过类似的一个男人和一个孩子,男人拉提琴,女孩子踩着高跷跳舞,这使得希普克若夫特又对首都产生了新的兴趣,强烈到几乎来不及收拾行装就动身了。然而,他并没有找到那个失去的孩子,尽管他干完活儿以后全部的工作就是在僻静的小街上到处游逛,希望能找到她。他时常在晚上突然惊醒,说“那个流氓靠折磨她来养活他!”他妻子总是懊恼地回答他说,“别老是这样苦恼自己,内德!你都不让俺休息一会儿!他不会害她的!”然后又睡着了。
大家的意见是,那个凯瑞和她父亲移民到美国去了;毫无疑问,“墩布”已经把她训练出来,用她跳舞赚来的钱养活他。他们现在可能还在那里以某种身份演出,虽然他这个老流氓已经七十靠边,而她也是一个四十四岁的女人了。
(1893)
* * *
[1] 指一〇六六年诺曼底公爵威廉征服英国。
[2] 捷格舞为一种古老的三拍子舞,轻松快速,曾广泛流行于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在爱尔兰流行最久。
[3] 瑞乐舞为苏格兰与爱尔兰的一种三拍子的民族舞蹈,节奏很快,音乐流畅,而爱尔兰的节奏更快。通常由两对舞伴对舞,有时多对参加。十八世纪末在英国舞厅颇为流行。
[4] 方舞最初盛行于法国拿破仑第一的宫廷,一八一六年传入英国后立即流行,舞者如醉如狂,作曲家甚至据以写成歌剧。
[5] 飞旋舞为活泼快速的二拍子圆舞,源出日耳曼,十九世纪中叶传入英法等国。后不再单独跳这种舞,而是作为方舞中的一段。
[6] 为《圣约·旧约·诗篇第一百首》谱的曲子,曲成于十七世纪中叶。
[7] 即上面提到的内德,内德为爱德华的爱称。
[8] 兰贝斯,当时伦敦的一个穷人区。
[9] 指一八五一年在伦敦海德公园内为世界博览会建“水晶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