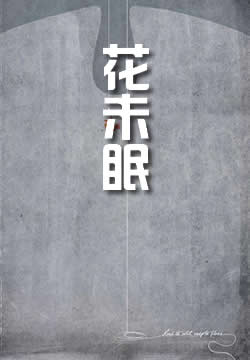the few and the many
【§1—2.缘何重审雅俗之辨】
这本小书,想做个试验(try an experiment)。文学批评历来都用于评判书籍。暗含其中的对读者阅读的评判,都衍生于对书籍本身的评判。准此理路,坏的趣味(bad taste)[2],顾名思义,就是对滥书之喜好(a taste for bad books)。我想看看,如果把这一推导过程颠倒过来,会是怎样一种情况。让我们把区分读者或阅读类型作为基础(basis),把区分书籍作为推论(corollary)。我们且来考查一番,把好书定义为以某种方式阅读的书,把滥书定义为以另一种方式阅读的书,可行性究竟有多大。
我认为这值得一试。在我看来,常规套路一直隐含着一个谬误。我们常说,甲喜爱(like)女性杂志,或女性杂志符合甲的趣味(taste);乙喜爱但丁[3],或但丁符合乙的趣味。这仿佛是在说,“喜爱”和“趣味”二词用于二者之时,意思没有变化;仿佛是在说,虽然对象(object)不同,动作(activity)却毫无二致。然而据我观察,至少在通常情况下,事实并非如此。
【§3—7.对书的两种爱:多数人与少数人】
至少从学生时代起,我们一些人就对好的文学初生兴发感动(response)[4]。其余大多数人,在学校读《船长》杂志[5],在家则读从流通图书馆(circulating library)借来的短命小说。那时就很明显,多数人对他们所读书籍的“喜爱”,很不同于我们对自己所读书籍的“喜爱”。现在依然明显。二者之别一目了然。
【§4.读书不等于读过】首先,多数人从不重读任何书籍。盲于文学之人(an unliterary man)[6]的标志就是,他把“我读过”(i have read it already)当作拒绝阅读一部作品的充分论据。[7]我们都知道,有些女性对一部小说的记忆非常模糊,得在图书馆里站上半小时,把小说翻阅一过,才敢确定自己确曾读过。一经确认,就会立即把书丢开。对这些人而言,书是死的,就像燃尽的火柴、旧火车票,或昨天的报纸;他们已经用过它了(have already used it)。[8]相反,阅读伟大作品的人,一生中会把同一部作品读上十遍二十遍,甚至三十遍。[9]
【§5.读书不等于消遣】第二,多数人尽管也经常读书,却并不珍视读书。他们转向阅读,只因百无聊赖。一旦有别的消遣(pastime),当即欣欣然弃之不顾。读书是给坐火车、生病、闲得发慌时预备的,或是用来“催睡”的。他们有时一边读书一边闲聊,也常常一边读书一边听广播。而敏于文学之人(literary people)总在闲静之时阅读,心无旁骛。如果无法专心一意、不受干扰地读书,哪怕只几天,他们也会感到若有所失。[10]
【§6.读书变化气质】第三,对敏于文学者(the literary)而言,初次阅读某部文学作品的体验,其意义之重大,只有爱情、宗教或丧亲之痛这类体验,方可与之相提并论。他们的整个意识(whole consciousness)为之一变。变得面目一新。在其他类型的读者中,则无此迹象。他们读完故事或小说,基本无动于衷,或者根本无动于衷。[11]
【§7.敏于文学者优游涵泳】最后,不同阅读行为的自然结果就是,少数人所读之书,常常萦绕心际,多数人则否。前者在独处时默念最为心喜的诗行、段落。书中场景和人物提供了一种图像(iconography),他们借以解释(interpret)或总结(sum up)自身经验。他们互相探讨读过的书,细致而又经常。后者则很少想起或谈及他们的阅读。[12]
【§8.常规套路用taste和like二词,含糊其辞】
显而易见,假如多数人心平气和且善于辞令,他们就不会指责我们喜爱不该喜爱的书,而会指责我们根本不该对书如此在乎。我们视为幸福之重要组成部分的东西,他们认为可有可无。因此,他们喜爱甲而我们喜爱乙这一简陋表述,一点也不符合实情。假如“喜爱”(like)是个正确字眼,可用来形容他们对书之待遇,那么就得给我们对书之待遇另找一个词。或者反过来说,如果我们“喜爱”自己所读的一类书,就不能说他们“喜爱”任何书本。如果少数人有“好的趣味”(good taste),那么我们或许就不得不说,不存在所谓“坏的趣味”(bad taste)这种东西。因为,多数人那种阅读倾向(inclination)完全是另一码事,根本谈不上趣味,假如我们用趣味一词不含糊其辞的话。[13]
【§9.对艺术和自然美的两种喜爱】
尽管下文几乎全谈文学,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态度差别同样也反映在其他艺术及自然美之中。许多人爱听流行音乐,边听边哼曲调、打拍子、交谈、吃东西。这一流行曲调一旦过时,他们也就不爱听了。爱听巴赫(bach)的人,表现截然不同。有些人买画是因为墙上“没画就光秃秃的”;等买回家一个星期后,他们对这些画就视而不见了。但是有少数人,对一幅伟大画作经年乐此不疲。至于自然,多数人“和别人一样喜爱美景”(like a nice view as well as anyone)。他们一点也不反对这一说法。然而比方说,把风景视为选择度假地的重要因素——把风景纳入与豪华宾馆、好高尔夫球场和阳光充足的气候同等的考量等次——在他们看来则显得做作不堪。像华兹华斯那样与自然美景“为伍”简直是矫情。[14]
* * *
[1] 【译按】藉阅读方式定文学趣味之高下,或许可行。之所以不按常规套路,以书之好坏区分趣味高下,是因为,甲喜爱女性杂志乙喜爱但丁,这两种“喜爱”大不相同。“多数人”与“少数人”之阅读,区别有四:1.读过与阅读;2.消遣与阅读;3.依然故我与变化气质;4.过目即忘与魂牵梦绕。质言之,盲于文学者与敏于文学者之根本区别在于,他们认为不应对书如此在乎。这一分别也适于欣赏艺术与自然。
[2] taste一词,作为一个文学理论或美学关键词,汉语学界通译“趣味”,拙译从之。虽然译为“品味”,可能更为传神。
[3] 但丁(dante,1265—1321),意大利最伟大的诗人,以其不朽的叙事诗《神曲》而被誉为“神的诗人”。《神曲》反映了基督教对人的现世与永恒的命运的深刻看法,表现出作者惊人的想象力、渊博的学识和语言方面的独创。(参《不列颠百科全书》第5卷134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
[4] 原文是already in our schooldays some of us were making our first responses to good literature. 其中response一词,依叶嘉莹先生之名文《古典诗歌兴发感动之作用》,意译为“兴发感动”。
[5] 《船长》(the captain),英国1899—1924年间发行的一份少年儿童杂志,月刊。因刊登沃德豪斯(p. g. wodehouse,1881~1975)的早期校园小说而闻名于世。参维基英文百科。
[6] literary与unliterary二词,乃本书一对核心概念,使用频率最高。与此二词相呼应的,还有使用频率不高的extraliterary与antiliterary二词。此四词作为读者类型之限定语,徐译本《文艺评论的实验》,将literary与unliterary译为“文学性”与“非文学性”,将extraliterary与antiliterary译为“超文学”与“反文学”。这一翻译,中规中矩。可问题在于,literary与unliterary二词还有其他用法,此译法顿时捉襟见肘,徐译本不得不随文转译。窃以为,理论著作之核心概念,自当统一译名,不可额外增加读者诸君之阅读负担,故暂不从徐译。为求强行统一,姑将literary与unliterary二词,译为“敏于文学”与“盲于文学”; extraliterary与antiliterary,译为“超文学”与“反文学”。至于the literary一词仅谈职业身份之时,方兼顾语境,译为“文人”。强行统一译名之灵感,来自钱锺书先生《释文盲》一文。钱先生说,不识字者固然为文盲,但还有另外一种文盲,即文学盲,艺术盲。路易斯所说的the unliterary,即钱先生所说的文学盲。
[7] 路易斯的这一区分,不由令人想起埃利希•弗洛姆所区分的两种生活模式:占有(having)与存在(being)。这表现在知识领域,就是“我有知识”和“我知道”之别;在信仰领域,就是“有信仰”和“在信仰中生活”之别;在爱情领域,就是占有对方和爱对方之别。参见\[美\]埃里希•弗罗姆:《占有还是生存》,关山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第2章。
[8] 注意“用过”(used)一词。路易斯将人对书及艺术品之态度分为两种,一为使用(using),一为欣赏(appreciating)。见本书第三章。
[9] 程子曰:“颐自十七八读《论语》,当时已晓文义。读之愈久,但觉意味深长。”路易斯在《给孩子们的信》(余冲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中说:“我一生都在断断续续地读《傲慢与偏见》,而一点儿也没有厌倦过。”(第44页)在名为unreal estate那场对谈中,路易斯说,一本书假如没有读过第二遍,便是未曾读。见c. s. lewis, on stories: and other essays on literature, ed. walter hooper, ny: harcourt, p. 146。
[10] 贾岛有诗云:“一日不做诗,心源如废井。”此之谓也。
[11] 程子曰:“今人不会读书。如读《论语》,未读时是此等人,读了后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读。”卡夫卡有言:“一本书必须是一把能劈开我们心中冰封的大海的斧子。”这段话出自卡夫卡《致奥斯卡•波拉克》(1904.1.27):“我认为,只应该去读那些咬人的和刺人的书。如果我们读一本书,它不能在我们脑门上猛击一掌,使我们惊醒,那我们为什么要读它呢?或者像你信中所说的,读了能使我们愉快?上帝,没有书,我们也未必不幸福,而那种使我们愉快的书必要时我们自己都能写出来。我们需要的书是那种对我们产生的效果有如遭到一种不幸,这种不幸要能使我们非常痛苦,就像一个我们爱他胜过爱自己的人的死亡一样,就像我们被驱赶到了大森林里,远离所有人一样,就像一种自杀一样,一本书必须是一把能劈开我们心中冰封的大海的斧子。我是这么认为的。”(《卡夫卡全集•第七卷》,叶廷芳主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第25页)
[12] 路易斯在《文学趣味之差异》(different taste in literature)一文中说:在文学领域,滥艺术之“消费者”,特征更易界定。他(或她)可能每周都亟需一定小说配给,如果供应不上,就会焦灼。可是,他从不重读。敏于文学者(the literary)与盲于文学者(the unliterary)之分际,在此再清楚不过。敏于文学者重读,其他人只是阅读。一经读过的小说,对于他们,就像昨天的报纸。有人没读过《奥德赛》或马罗礼或包斯韦尔(boswell)或《匹克威克外传》,这不奇怪。可是,有人告诉你他读过它们,从此就万事大吉,(就文学而言)这就奇怪了。这就像有人告诉你,他曾洗过一次脸,吻过一次妻子,散过一次步。滥诗是否有人重读(它可能沦落到空卧房里了),我有所不知。可是,我们有所不知这一事实却意味深长。没人发现,两个滥诗爱好者会称赏诗句(capping quotations),并在良辰美景之夜专心致志讨论他们的心爱诗行。滥画亦然。买画人说,无疑真心诚意地说,他看它可爱、甘甜(sweet)、美丽、迷人或(概率更高的)“妙”(nice)。可是,画一挂起来,就视而不见了,也从不再盯着看了。(见c. s. lewis, on stories: and other essays on literature, ed. walter hooper, ny: harcourt, p. 120—121)
[13] 分析哲学的这一技巧,路易斯很是熟谙。但路易斯显然对分析哲学评价不高,甚至认为分析哲学乃是将现代世界引入虚无之帮凶。详参拙译路易斯《人之废》(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一书。亦可参路易斯《空荡荡的宇宙》(the empty universe)一文,文见拙译路易斯文集《切今之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14] 华兹华斯(wordsworth,1770—1850),英国主要的浪漫主义诗人和桂冠诗人。他与s.t.柯勒律治合写的《抒情歌谣集》促进了英国浪漫主义运动的兴起。其作品的主要主题是人与大自然的关系。诗人把自己描绘为“大自然的崇拜者”,人们也常称他为“大自然的祭司”。(参《不列颠百科全书》第18卷3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