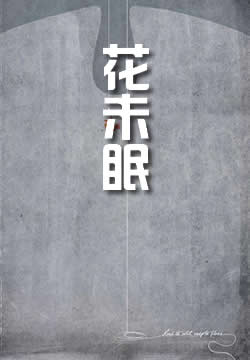false characterisations
【§1.以“少数”“多数”形容,只是权宜之计】
从逻辑意义讲,说一类读者是多数而另一类读者是少数,只是个“偶然”(accident)。这些数词不能标示两类之别。我们讨论的是,不同的阅读方式。平素观察,已足令我们描述大概。虽如此,我们尚须更进一步。首先,须排除一些区分“少数”和“多数”的草率做法。
【§2—5.几点显见的澄清】
【§2.多数人非所谓俗人】一些评论家写到那些文学上的“多数人”时,仿佛他们方方面面都属于多数,甚至属于群氓似的。这些评论家斥责他们没文化(illiteracy)、未开化(barbarianism),其文学反应“愚钝”、“粗鲁”、“套板”[2]。(言下之意就是)这些反应,必使他们在生活各方面都显得迟钝麻木,成为对文明的永久祸害。[3]这有时听起来像是在说,读“通俗”小说关乎道德堕落。我发现这并未得到经验证实。我认为这些“多数人”中的某些人,在心理健康、道德品性(moral virtue)、精明谨慎、礼仪举止和适应能力等方面,与少数人中的某些人相比,非但不逊色,甚或更出色。况且我们清楚得很,在我们这些“文人”(the literary)[4] 当中,无知、卑鄙、畏缩、乖戾、刻薄之人,比例不在少数。对此置若罔闻,一概而论地乱搞“种族隔离”,我们势必什么都做不了。
【§3.少数人与多数人,并无固定藩篱】如此二分即便没别的毛病,仍然过于死板。这两类读者之间并无固定藩篱。有人曾属多数,却变为并加入少数。也有人背弃少数而成为多数,就像我们遇见老同学时,常常遭遇的沮丧那样。那些对此艺术属于“大众”水准的人,欣赏彼艺术,则可能造诣颇深;音乐家之诗歌偏好,有时实在不敢恭维。还有,许多对各门艺术都没什么感觉的人,照样可以有过人之智识(intelligence)、学问(learning)及敏锐(subtlety)。
【§4.文学专家是少数人,却往往大跌眼镜 】后一现象,并不让我们感到特别惊讶。因为他们的学问与我们不同,哲学家或物理学家之敏锐亦不同于文人(a literary person)之敏锐。令人更为惊讶且不安的是,那些因职位所系,理应对文学有深刻、恒久鉴赏力的人,实际上却并非如此。他们只是专家(professionals)。[5]或许他们曾满怀兴发感动(had the full response),然而“山高水远举步维艰”[6],早已将之消磨殆尽。此刻我想到的是国外大学里那些不幸学者。他们得不断发表文章,必须就某些文学作品说出新意,或必须显得说出新意,不然就无法“保住饭碗”。[7]或者说我想到的是,忙得不可开交的书评家,他们尽可能飞速翻阅一本又一本小说,就像小学生预习功课那般。对这些人来说,阅读只是活计(mere work)。摆在他们面前的文本,并非自在之物(exist not in its own right),而仅仅是原料(raw material);是黏土,他们用来造砖。于是我们经常可以发现,在业余时间,他们之阅读与多数人毫无二致,假如业余时间他们还阅读的话。[8]我仍清楚记得曾经的一次冷遇。我们刚开完主考官会议出来,我冒失地向其中一位提起某一伟大诗人,好几个考生答卷上都写到这位诗人。此人态度(我忘了原话)可以这样表述:“天哪,伙计,都好几个小时了,还想接着讨论?没听见下班铃声?”对于这些因经济原因和过度劳累而落到如斯境地的人,我唯有同情而已。不幸的是,野心勃勃和争强好胜也会导致这一境地。而且,无论何以至此境地,它总是摧毁欣赏(appreciation)。我们所寻找的“少数人”不能等同于行家(cognoscenti)。吉伽蒂波斯[9]和德赖斯达斯特[10]必然也不位列其中。
【§5.附庸风雅者】附庸风雅者(the status seeker)就更不用说了。[11]恰如现在或者曾经有一些家庭和社交圈,把对狩猎、郡际板球或军官名册的兴趣,几乎视为社交的必要条件。现在同样也有其他家庭和圈子,他们热议(因而偶尔一读)众口交赞的文学作品,尤其是令人瞠目的新作品,以及遭禁的或以其他方式颇有争议的作品。你想拒不谈论,则需要十足的独立性。这类读者,可称其为“小俗之人”(small vulgar)。他们在某一方面的表现和“大俗之人”(great vulgar)[12]并无二致。他们完全受风尚(fashion)支配。[13]他们适时丢下乔治王朝时期的作家,开始崇拜艾略特先生[14];适时赞许把弥尔顿[15]“拉下宝座”,发掘出霍普金斯[16]。如果你书上的献辞以“to”开头,而不以“for”开头,他们就不会喜欢。然而,这一家人在楼下讨论正欢之际,唯一真正的文学体验或许出现在楼上最尽头的卧室里:一个小男孩正躲在被窝,靠手电筒读《金银岛》(treasure island)。[17]
【§6—10.少数人非文化信徒】
【§6.文化信徒】作为一个人(as a person),文化信徒(the devotee of culture)要比附庸风雅者可敬得多。他除了读书,还参观画廊、参加音乐会。这样做不是为了使自己更受欢迎,而是为了自我提升,开发潜力,成为更完整的人(more complete man)。[18]他真诚,或许还很谦虚。他绝不追随风尚,而更可能是全身心扑在各个时期各个国家的“知名作家”(established authors)、“世界上最优秀的思想和言论”[19]上面。他基本不尝试冒险,也基本没有钟爱的作家。但这位高尚之人(worthy man),就我所关心的阅读方式而言,也许根本谈不上是真正的文学爱好者。就像每天早上练哑铃,也许根本不是爱好运动。体育运动通常有助于体格健全;然而,假如体格健全成为运动的唯一理由或主要理由,运动就不成其为运动(games),而只是“锻炼”(exercise)了。
【§7.两种不同的爱好】毫无疑问,一个爱好(has a taste for)运动(同时也爱好大吃大喝)的人,当他给自己定下规矩,给予运动爱好一般的优先权,那么他的行为就会恰好合乎健康动机。同理,一个既乐于好的文学作品又乐于用垃圾作品来打发时间的人,基于文化理由,基于原则,会理性地选择前者。在这两个例子中,我们都假定了一种真正的乐在其中(a genuine gust)。第一个人选择踢足球而放弃饕餮大餐,那是因为他乐于运动,也乐于大餐。第二个人读拉辛[20]而不读埃•莱•巴勒斯[21],那是因为《安德罗玛克》[22]对他确有吸引力,《人猿泰山》[23]也是。不过,只是出于卫生保健的动机,参加某一运动,可就不是玩(play);只是渴望自我提升而读悲剧,那也不是接受(receive)悲剧。这两种态度让人最终只关注自己。二者都把有些东西当作一种手段。可是这些东西,当你在玩或阅读时,必须因其自身价值而予以接受。你应该考虑的是进球,而不是身体健康;你的头脑应该沉浸在一盘精神象棋中,它以“雕刻为亚历山大体的激情”为棋子,以人类为棋盘。[24]假如真能沉浸其中,哪还有时间考虑文化(culture)这么一个空洞抽象的概念?[25]
【§8.新批评与文学清教徒】这类孜孜矻矻的错误读法,恐怕在我们这个时代格外盛行。使英国文学成为中小学和大学的一门“学科”(subject),[26]其不幸结局之一就是,勤勉而又听话的年轻人从小就被灌输这样的观念,即读大家名作是值得称道之事。如果该年轻人是不可知论者(agnostic)[27],其祖上是清教徒,那么你将得到一种令人遗憾的心灵状态。[28]清教道德意识仍在起作用,却没了清教神学——就像空转的石磨;又像消化液在空胃工作而导致胃溃疡。这个不幸的年轻人,把其祖上曾用于宗教生活的所有道德顾虑、清规戒律、自我检省、反对享乐,统统用到了文学上;恐怕不久还得加上所有的褊狭和自以为义(selfrighteousness)。瑞恰慈博士[29]的学说宣称,正确地阅读好诗具有良好疗效,这印证了他的清教徒态度。[30]缪斯女神充当了复仇女神欧墨尼得斯[31]的角色。一位年轻女士带着深深的负罪感向我的一位朋友坦白,想看妇女杂志的罪恶欲望不断引诱着她。
【§9.认真之人与认真学生】正是由于这些文学清教徒的存在,我才没用“认真”(serious)一词来形容正确的读者和阅读。初看起来,这正是我们想要找的字眼。然而它致命地含混。一方面,它可以指“庄重”、“一本正经”之类;另一方面,则可以指“一丝不苟、全神贯注、奋发向上”。因此,我们说史密斯是个“认真的人”,是指他不苟言笑;说威尔逊是个“认真学生”,是指他学习刻苦。认真的人,可能浅尝辄止或是个半瓶子醋,而绝非认真学生。认真学生则可能像迈丘西奥(mercutio)[32]一样好玩。认真做某事,可能只是此意义之“认真”,而非彼意义之“认真”。为了健康而玩球的人,是个认真的人:真正的足球运动员不会把他称作认真玩家(serious player)。他对游戏并非全神贯注;并不真正在意。他作为一个人的认真,恰恰导致他作为一个玩家的轻佻。他只是“玩玩而已”(plays at playing),假装在玩。真正的读者,认真阅读每一部作品,也就是说他全神贯注地读,尽可能使自己善于接受(receptive)。正因为此,他不可能阅读每部作品都庄重严肃。因为,“作者以什么心意写”,他就“以什么心意读”[33]。作者意在轻快,则轻快地读;作者意在庄重,则庄重地读。读乔叟的故事,[34]他会“躺在拉伯雷的安乐椅上大笑不止”[35];读《秀发遭劫记》[36],则会报以十足的轻佻。是小玩意,就当作小玩意来把玩;是悲剧,就当作悲剧来欣赏。他不会犯此类错误,把掼奶油当成鹿肉而大嚼特嚼。
【§10.文学清教徒可悲的“认真”】这正是文学清教徒(literary puritans)最可悲的失败之处。作为人,他们太过认真,以至于作为读者,他们无法成为认真的接受者。我曾经出席一个本科生的论文答辩,他写的是简•奥斯汀[37]。仅看他的论文,绝不会看出她小说中一丝一毫的喜剧色彩,要是我之前从未读过奥斯汀的话。一次我做完讲座,一位年轻人陪着我从磨坊巷走回莫德林学院。他痛苦而又反感地抗议道,我不该暗示《磨坊主的故事》[38]。是写来供人发笑的。他认为我的话有害、粗俗、大不敬。我还听说,有人发现《第十二夜》是对个人与社会关系的透彻研究。我们正在培养的,是一批严肃得有如兽类(“微笑从理性中流淌而出”[39]的年轻人;严肃得就像苏格兰长老会某牧师的19岁儿子,他来到英格兰的雪利酒会,把恭维全当成表白,把玩笑全当成侮辱。[40]他们是认真的人,却不是认真读者;他们并未舍去先见(preconception),并未向所读作品,公正而又大方地敞开心扉。
【§11.“少数人”亦非“成熟”读者】
既然以上所有的描述都不正确,我们可否用“成熟”来形容文学上的“少数人”呢?这个形容词当然能说明许多问题:读书的最高境界,和做其他事的最高境界一样,离不开历练和规矩(experience and discipline),因此小孩子无法达致。不过仍然有所遗漏。如果我们认为每个人一开始都像多数人那样对待文学,尔后随着整体心智的成熟,就能学会像少数人那样阅读,我相信我们搞错了。我认为这两类读者在上幼儿园时就已具雏形。识文断字之前,文学对他们而言是听到的故事,而不是读到的故事。孩子们的反应难道不是有所不同?等他们可以自己看书了,两种不同的类型已然定型。有的孩子没事可做才会读书,对每一故事都囫囵吞枣,只想“看看发生了什么”,很少重读;有的孩子则反复阅读,并且深为感动。[41]
【§12.我们自己也是多数人】
正如我所说的,以上对这两类读者特征的种种描述都嫌草率。我提到它们,是为了让它们不再碍事。我们务必亲自体会这些态度。对我们绝大部分人来说,这可以做到,因为我们在某些艺术门类中,大都从此态度转向彼态度。我们所知道的“多数人”的经验,不仅来自观察,也来自自省。
* * *
[1] 【译按】说敏于文学者乃少数,盲于文学者属多数,这只是方便之词。二者之别,不在数量。故需澄清一些可能之误解:1.少数多数之分,与精英大众之分无涉;2.少数多数之分,并无固定樊篱;3.敏于文学者,不等于文学专家,不等于附庸风雅者,更不等于文化信徒(the devotee of culture);4.敏于文学者,亦不能被描述为成熟读者。企图以文化救人救世的文化信徒,混淆了做人之认真与阅读之认真,是以前一种认真去从事阅读。其结果就是,他们并非接受文学,而是使用文学,成了没了清教神学的清教徒。
[2] 套板反应(stock response),心理学术语。朱光潜《咬文嚼字》一文说:一件事物发生时立即使你联想到一些套语滥调,而你也就安于套语滥调,毫不斟酌地使用它们,并且自鸣得意。这就是近代文艺心理学家所说的“套板反应”(stock response)。一个人的心理习惯如果老是倾向于套板反应,他就根本与文艺无缘。因为就作者说,“套板反应”和创造的动机是仇敌;就读者说,它引不起新鲜而真切的情趣。一个作者在用字用词上离不掉“套板反应”,在运思布局上面,甚至在整个人生态度方面也就难免如此。不过习惯力量的深度常非我们的意料所及。沿着习惯去做总比新创更省力,人生来有惰性。常使我们不知不觉的一滑就滑到“套板反应”里去。(《朱光潜全集》新编增订本卷六《我与文学及其他谈文学》,中华书局,2012,第218页)路易斯对“套板反应”则持相反观点。他在《失乐园序》第8章中说,套板反应对人之为人,对人类社会之维系,必不可少:人类对事物不假思索的正直反应,并不是“与生俱来”,但我们总是动不动就用一些刻薄的形容词来抨击,诸如“陈腐”、“粗糙”、“恪守成规”、“传统”。其实,这些反应是经由不断地操练、小心翼翼养成的,得来辛苦,失去却易如反掌。这些正直的反应是否能延续下去,成了人类的美德、快乐,甚至种族存亡之所系。因为,人心虽非一成不变(其实一眨眼间就会出现难以察觉的变化),因果律却永不改变。毒药变成流行品后,并不因此就失去杀伤力。经由不断坚持一些陈旧的主题(诸如爱情是甜美的,死亡是苦涩的,美德是可爱的,小孩和庭园是有趣的),古老的诗歌所提供的服务,不仅具有道德、文明教化上的重要性,甚至对人的生物性存在也至关重要。(见《觉醒的灵魂2:鲁益师看世界》,寇尔毕编,曾珍珍译,台北:校园书房,2013,第291页)
[3] 这里似暗讽新批评,尤其是新批评之先驱、维多利亚时代的诗人及批评家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后者志在以文学或文化救世,让文学或文化发挥过去宗教所所发挥的功能。法国学者安托万•孔帕尼翁(antoine compagnon)在《理论的幽灵》一书中,这样描述马修•阿诺德的事业:“19世纪末,英国作家马修•阿诺德给了文学批评一个任务,即建立社会道德以筑起一道抵挡内心野蛮的堤坝……对于这位维多利亚时代的批评家而言,文学教学,就是要陶冶、教化那些产生于工业社会的新兴中产阶级,使他们变得人性化。文学的社会功能与康德所说的非功利性迥然不同,它的目标就是为职业人士提供闲时的精神追求,在宗教日益衰落之时唤醒他们的民族情感。”(吴泓缈、汪捷宇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第217页)
[4] 此处the literary指职业身份,依语境变化,译为 “文人”。至于该词之其他用法,一律译为“敏于文学者”。
[5] 路易斯《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文学研究》第4章:“各样艺术的历史,都在诉说着同一桩可悲的故事——艺术愈来愈趋向专业化,也愈来愈趋向贫瘠。”见《觉醒的灵魂2:鲁益师看世界》,寇尔毕编,曾珍珍译,台北:校园书房,2013,第381页。或见胡虹译《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第98页。
[6] 此处意译。原文为‘hammer, hammer, hammer on the hard, high road’,乃一则伦敦绕口令(tongue twisters),见sir e. denison ross, this english language, london: longmans, green, and co.,1939, p. xxviii。
[7] 关于人文科研,路易斯一直颇有微词。他在‘interim report’一文中说,牛津和剑桥都有一种“恶”,即“科研”(research)这一睡魔。他认为,在自然科学中讲求科研成果,还有的可说;在人文学科中讲求科研成果,则无异于杀:“在科学中,我总结,刚通过荣誉学士考试的优等生,可以真正分担前辈之工作,这不仅对他们自身有益,也对学科有益。然而,对于新近获得英语或现代语言优等生身份的人来说,情况就不一样了。这样一个人,不能或无须(就其名分而言他不笨)为人类知识增砖添瓦,而是要去获得更多我们已经拥有的知识。他后来开始发现,为了跟上他刚刚萌发的兴趣,他还有那么多的事情需要知道。他需要经济学,或神学,或哲学,或考古学(往往还有更多的语言)。阻止他从事这类学习,把他固定在一些细枝末节的研究上,声言填补空白,这既残酷又令人沮丧。它浪费了一去不复返的青春年华。”故而,他认为以科研成果论学术职位,是一个很坏的习惯。他期望牛津和剑桥合力破除这一坏惯例。文见拙译《切今之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8] 乔治•奥威尔有小说名曰《一个书评家的自白》(《奥威尔文集》,董乐山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第316—319页),其中的那个书评家,与此段描述颇为相似。钱锺书在《写在人生边上》之序言里亦说,书评家的独特本领就是:“无须看得几页书,议论早已发了一大堆,书评一篇写完交卷。”(见钱锺书《写在人生边上;人生边上的边上;石语》,三联书店,2002)
[9] 吉伽蒂波斯(gigadibs),是布朗宁(robert browning)之长诗《布劳格兰主教的致歉》(bishop blougram’s apology,1855)中的人物,一个浅薄记者。在长达1013行的无韵诗句里,面对身为怀疑论者的这个记者的攻击,主教捍卫自己的信仰。
[10] 德赖斯达斯特(dryasdust)是司各特(walter scott,1771—1832)虚构的人物,一个令人厌恶的演说家。司各特的几部小说序言均以“致德赖斯达斯特”的面目出现。
[11] 关于the status seeker(徐译本译为“社会地位追逐者”),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在《芝麻与百合》(英汉对照版,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中论虚荣的一段文字,可以做最好之注脚。他说,他经常收到家长来信,咨询关于孩子教育的问题。但这些来信根本不关心“教育”,而是关心“地位”,孩子受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取某种“社会地位”(station in life):“能让孩子外表体面;能让孩子到豪宅做客时充满自信;能最终帮助孩子建造自己的豪宅。总之,能引导孩子提高人生的品质(advancement in life)。”(第5页)罗斯金说,家长热衷孩子“提高人生的品质”,究其实乃热衷“虚荣”。因为人们所热衷的这种“提高”,并不是“赚很多钱”,而是要让“别人知道我们赚了很多钱”;也不是达到某一伟大目标,而是要让别人看到我们达到目标。我们之所以渴望地位,是因为渴望掌声。在罗斯金看来,满足虚荣心是我们很多行为的动力:对虚荣心的满足是我们辛苦劳作的动力,也是我们休息放松时的慰藉;对虚荣心的满足触及我们根本的生命之源,触及之深,使得虚荣心受伤往往被称作(实际上也是)致命的伤害;我们称之为“心疾”,这种表达和我们把身体的某个部位的坏死或无法治愈的伤口称作“体疾”是一样的。……通常,水手不会仅因为知道自己比船上的其他水手更能管理好这艘船就想当船长,他想当船长是为了听到自己被称为船长。(第7页)同理,牧师想成为主教,主要是因为想被人称作“大人”;人热衷王位,是因为想被人称作“陛下”。想藉助“提高人生的品质”来“融入上层社会”(getting into good society),其原因也是虚荣:“我们想融入上层社会,不在于我们身处其中,而在于在别人眼里我们是身处其中的;我们之所以认为其美好主要是因为它惹人注目。”(第7页)
[12] “大俗之人”,似指前文所说之文学专家。
[13] 路易斯《梦幻巴士》第5章:“坦白说罢,我们的意见原不是诚实得来的。我们不过发觉自己接触到一股思想潮流,因为看它好像很新式又盛行,才投身其中。你晓得,在大学里我们总是机械化地写一些会得高分的文章,说一些会博取赞赏的话。我们一生当中何曾孤独、诚实地对着最重要的问题——超自然的事物实际不会发生吗?我们又何曾有过一时真正地抗拒信仰的失落。”(魏启源译,台北:校园书房,1991,第46—47页)
[14] 艾略特(t. s. eliot,1888—1965),美国出生的英国诗人、剧作家、文学批评家和编辑、诗歌领域现代派运动领袖。代表作有《荒原》(1922)和《四个四重奏》。《四个四重奏》使他被公认为当时在世的最伟大的英语诗人和作家,1948年获功勋奖章和诺贝尔文学奖。(参《不列颠百科全书》第6卷32页)
[15] 弥尔顿(john milton,1608—1674),在英国诗人中地位,仅次于莎士比亚。代表作长篇史诗《失乐园》对撒旦形象的塑造,是世界文学最高成就之一。文学史上对弥尔顿及其诗作的评价,有鲜明的历史性变化。1667年以后,由于j•艾迪生论《失乐园》的文章的发表,弥尔顿的声誉稳步上升,声名远播欧洲大陆。诗人的影响在维多利亚时代逐渐减弱。到了20世纪,庞德和艾略特所倡导的新诗歌与批评强烈地贬低弥尔顿而推崇多恩。但到了40和50年代批评界的态度又发生变化,众多讨论弥尔顿思想和信仰的书籍和文章刊发出来,从而为对其诗歌美学研究带来全新的理解和细致的分析。(参《不列颠百科全书》第11卷210页)
[16] 霍普金斯(gerard manley hopkins, 1844—1889),英国诗人和耶稣会教士,被公认为维多利亚时代最具独特风格、最有力量和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霍普金斯生前出版的诗作较少,直至1918年才由其好友,当时已经是桂冠诗人的r.布里吉斯,将其作品汇编成诗集出版。其作品对20世纪的主要诗人t. s.艾略特、d.托马斯、w. h.奥登、s.斯彭德和c. d.刘易斯都有明显的影响。(参《不列颠百科全书》第8卷162页)
[17] 《金银岛》(treasure island),英国小说家斯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1850—1894)的成名作。故事以少年吉姆•霍金斯口吻自述,讲述了一个海盗寻宝、与海盗斗智斗勇的故事。
[18] 徐译本将the devotee of culture译为“文化爱好者”,分量略嫌不足,故而改译为“文化信徒”。因为路易斯在这里所针对的,乃是马修•阿诺德所开启的“文化信仰”(a faith in culture)的传统。阿诺德有两行形容颇为知名的现代性的诗句:“wandering between two worlds, one dead / the other powerless to be born / with nowhere yet to rest my head / like these, on earth i wait forlorn。”贺淯滨中译为:“两重世界间,徘徊复飘零。其一业已死,另一无力生。吾心何所倚,吾身落此境,但有一匹夫,独候尘埃中。”此诗形容了宗教没落之后,人心之漫无依归,社会亦将沦于无政府状态(anarchy)。阿诺德开出的惩乱之方就是“文化”。阿诺德所说的文化,与汉语语境中所谓中西文化之类的用法很不相同。用他的话来说,文化就是“美好与光明”(sweetness and light)、“美与智”(beauty and intelligence),乃宗教与科学、希伯来精神与希腊精神之完美结合,代表着人类追求完美、自我提升、全面发展的努力。阿诺德说:“文化就是探究完美、追寻和谐的完美、普遍的完美……完美在于不断地转化成长、而非拥有什么,在于心智和精神的内在状况、而非外部的环境条件。”文见马修•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韩敏中译,三联书店,2002,第11页。亦可重点参见此书第1章及译者所附“关键词”。
[19] 原文为“the best that has been thought and said in the world”,语出马修•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阿诺德自陈其“文化信仰”(a faith in culture):“这件事无论我们如何去命名,都是指通过阅读、观察、思考等手段,得到当前世界上所能了解的最优秀的知识和思想,使我们能做到尽最大的可能接近事物之坚实的可知的规律,从而使我们的行为有根基,不至于那么混乱,使我们能达到比现在更全面的完美境界。”(韩敏中译《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三联书店,2002,第147页)
[20] 拉辛(jean racine,1639—1699),法国戏剧诗人和古典悲剧大师。
[21] 埃•莱•巴勒斯(e. r. burroughs,1875—1950),美国小说家。他的泰山故事塑造了一个世界闻名的民间英雄。(参《不列颠百科全书》第3卷261页)
[22] 安德罗玛克(andromaque),特洛伊王子赫克托耳的妻子。1667年,拉辛根据传说创作了诗剧《安德罗玛克》,该剧表现了拉辛最喜爱的主题之一:悲剧性的疯狂和狂热的爱情。(参《不列颠百科全书》第1卷325页)
[23] 泰山(tarzan),通俗小说中享有盛名和流传最久的人物之一,是近30部小说和几十部电影中的丛林冒险英雄。泰山是美国作家e.r.巴勒斯笔下的人物,1912年首次出现在一家杂志刊载的故事里。由于深受读者喜爱,后出版了名为《人猿泰山》的小说和一系列获得非凡成功的续集。小说讲述了一个英国贵族的儿子泰山如何被遗弃在非洲丛林,被一群类人猿养大,并在一系列冒险活动中学会英语、与一位科学家的女儿简相遇并产生爱情,最后重获贵族称号的故事。(参《不列颠百科全书》第16卷460页)
[24] 【原注】对拉辛作品的这一描述源自欧文•巴菲尔德(owen barfield)先生。【译注】亚历山大体(alexandrines,亦译亚历山大诗行),因12世纪末法语长诗《亚历山大的故事》之诗行形式而得名。欧文•巴菲尔德,路易斯之挚友。
[25] 关于因某事本身而喜欢某事,在路易斯看来,其中有“德性”(virtue),有“天真”(innocence)、“谦卑”(humility)和“忘我”等属灵成分。即便是喜欢打板球、集邮、喝可口可乐之类小爱好,若是无关利害地(disinterestedly)真心喜欢,那也是修心养德的“原材料”(raw material)或“起点”(startingpoint),也会因之对魔鬼的攻击有了免疫力。魔鬼引诱人的一大策略就是:“哪怕在那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上,也要用世界、习俗或者时尚的标准(the standards of the world, or convention, or fashion)来取代这个人自己真正的好恶。”故而,大鬼教导小鬼说:“你应该千方百计地让病人离开他真正喜欢的人、真正喜欢吃的东西和真正喜欢读的书,让他去结交‘最优秀’的人、吃‘正确’的食物,读‘重要’的书。我就认识一个这样的人,他抵制住了在社交上的雄心抱负的强烈诱惑,原因是他更嗜吃猪肚和洋葱。”参见《魔鬼家书》(况志琼、李安琴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第十三封信(第50页)。引文中的英文,系本译者所加。
[26] 英国文学成为一门学科,在英语世界,乃一现代事件。恰如语文教育和中文专业,在中国乃现代事件一样。据英国学者彼得•威德森《现代西方文学观念简史》(钱竞、张欣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一书,在英格兰,最早提供英国语言文学教育的是19世纪20年代伦敦的地方“学院”,首位英文教授受聘于1828年。此后几十年,其他郡县学院纷纷效法。牛津与剑桥不为所动。牛津大学在19世纪50年代,曾极力反对将英语教学列入教学大纲。转折点在上世纪初。其标志是,1902年,教育法案颁布;1907年,英语学会成立,“该学会所信奉的是阿诺德的原则,而学会的宗旨是推动、提升英语文学文化在教育中的地位、作用。”有了这样的前提条件,“英语”开始在学校课程表中占有核心地位,成为“在一个充分民族化的教育体系中的一门适合于每一个儿童的基本科目”。(第47页)此后,大学教育中,英国文学又与英国语言(语言学家为英语之专业化的始作俑者)分家,现代大学的“文学”体制由此奠定。1902年,牛津大学首次延请英语文学教授;剑桥则在1912年。虽然在当时,这两位教授认为他们所教的只是“女人味”课程。但是,这毕竟是个开端,“人文研究”殿堂里不再是老主人古典教育,而是来了新客“英国语言与文学”。此后,随着新批评之发展壮大,英国语言文学不止与古典教育分庭抗礼,而且一支独大,几乎将古典教育取而代之。现代“文学”体制宣告形成。(详参《现代西方文学观念简史》第43—49页)
[27] 关于上帝之存在,有三种主要观点:有神论,无神论及不可知论。尼古拉斯•布宁、余纪元编著《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辞典》(人民出版社,2001)释不可知论(agnosticism):[源自希腊词:a(非)和gnostikos(正在认识的人)] t. h. 赫胥黎所用的术语,指这样一种立场:它既不相信上帝存在也不相信上帝不存在,并且否认我们能够有任何关于上帝本性的知识。不可知论即相对于认为我们能认识上帝存在和本性的有神论;又相对于否认上帝存在的无神论。不可知论者认为,人类理性有着固有的和不可逾越的界限,正如休谟和康德所表明的。我们不能证明任何支持有神论或无神论主张的合理性,因而应该中止我们对这些问题的判断。不可知论的态度许多时代以来一直经久不衰,但它在19世纪关于科学与宗教信仰的论争中在哲学上变得重要起来。不可知论也更一般地用来表示,对超越我们直接感知或共同经验的东西这类主张的真假问题应中止判断。
[28] 原文为“you get a very regrettable state of mind”,这里的“你”,指的是劝人读好书、相信文化能救人救世的文化信徒。
[29] 瑞恰慈(i. a. richards,1893—1979),英国语言学家和文学批评家。其著作有《意义的意义》(the meaning of meaning,1923), 《文学批评原理》(principles of literary criticism,1924), 《科学与诗》(science and poetry,1925), 《实用批评》(practical criticism,1929)以及《如何阅读》(how to read a page,1942)。本书中的许多观点,针对的正是瑞恰慈的《文学批评原理》。
[30] 瑞恰慈(i. a. richards)的《文学批评原理》(杨自伍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7)一书致力于让神经生理学为文学批评提供科学基础。在他看来,我们心中有许多相互冲突的冲动,故而,人之心灵健康端赖于冲动之组织(organization)和有条不紊(systematization),从而由“混乱心态”(chaotic state)转向一种“组织较好的心态”(better organized state)。准此,“道德规范这个问题(problem of morality),于是就变成了冲动组织的问题(problem of organization)”;“最有价值的心态(the most valuable state of mind),因此就是它们带来各种活动最广泛最全面的协调,引起最低程度的削减、冲突、匮乏和限制”(中译本第49—50页,英文夹注参照英文原本所加)。优秀文学作品的价值就在于此精神疗效。
[31] muses,希腊神话中九位艺术女神之统称;eumenides,希腊神话中的三位复仇女神之统称。
[32] 莎士比亚戏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人物,罗密欧的朋友。
[33] 原文是for he will read ‘in the same spirit that the author writ’.引号内文字,出自蒲柏之诗体论文《论批评》(1711):“a perfect judge will read each work of wit / with the same spirit that its author writ.”因暂未找到中译文,故拙译采用意译。
[34] 指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
[35] 原文为“laugh and shake in rabelais’ easy chair”,乃蒲柏诗句,出自蒲柏的讽刺长诗《愚人志》(the dunciad)卷一。
[36] 《秀发遭劫记》(the rape of the lock),英国诗人蒲柏(alexander pope,1688—1744)的长篇叙事诗。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出版黄果炘之中译本。
[37] 简•奥斯汀(jane austen,1775—1817),英国女作家。她是第一个通过描绘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使小说具有鲜明现代性质的小说家。她针对当时英国中产阶级习俗创作的戏剧性作品有:《理智与情感》(1811)、《傲慢与偏见》(1813)、《曼斯菲尔德花园》(1814)、《爱玛》(1815)、《诺桑觉寺》和《劝导》,后两部于作家死后1817年出版。(参《不列颠百科全书》第2卷60页)
[38] 乔叟《坎特伯雷故事集》中的一篇
[39] 见弥尔顿《失乐园》第九章239行。兽类没有理性,故不会微笑。)
[40] 不知典出何处。
[41] 路易斯在《为儿童写作之三途》(on three ways of writing for children)一文中说:不把“成熟的”这个语词当作一个纯粹的形容词,而用它来表示一种称许,这样的批评家本身就不够成熟。关心自己是否正在成长中、羡慕成年人的事,以为这样做就是成熟的表现;每当想到自己的行为可能很幼稚,就满脸通红。以上这些现象都是童年和少年的特征。……十几岁时的我读神话故事,总是藏藏躲躲,深恐让人发现了不好意思。现在我五十岁了,却公公开开地读。当我长大成人时,我就把一切幼稚的事抛开了——包括害怕自己幼稚,包括希望自己非常成熟。(见《觉醒的灵魂1:鲁益师谈信仰》,曾珍珍译,台北:校园书房,2013,第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