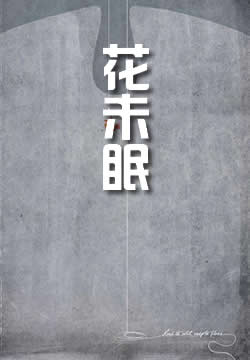the meanings of ‘fantasy’
【§1.“幻想”作为文学术语】
“幻想”(fantasy)一词,既是文学术语,又是心理学术语。作为文学术语,奇幻之作(a fantasy),是指任何关乎不可能之事(impossibles)及超自然之事(preternaturals)的叙事作品。《古舟子咏》[2]、《格列佛游记》[3]、《乌有乡》[4]、《柳林风声》[5]、《阿特拉斯女巫》[6]、《朱根》7[7]、《金坛子》[8]、《真实故事》[9]、《小大由之》[10]、《平面国》[11]和阿普列乌斯[12]的《变形记》,都是奇幻之作。当然其精神及目标各不相同。唯一共同点就是奇幻(the fantastic)。我把这类幻想,称为“文学奇幻”(literary fantasy)。
【§2—5.心理学术语“幻想”之三义:妄想、病态白日梦、正常白日梦】
作为心理学术语,“幻想”(fantasy)有三种含义。[13]
1.一种想象建构(an imaginative construction),以或此或彼的方式令病人(patient)高兴,让他误以为真。处此境况,女性会想象与一位名人相爱;男性则相信,自己出身富贵之家,与父母失散多年,不久将真相大白,与父母相认,享不尽的富贵荣华。再平常不过之事,他们常常别出心裁地加以扭曲,变成自己宝贵信念的证据。对这种幻想我不必想个名称出来,因为我们不必再提到它。妄想(delusion),在文学上没有意义,除非意外。
2.病人持续沉溺于愉快的想象建构,以致成伤,但并不妄想为真。年复一年,重复来重复去的或精心编织的,是个白日梦——梦者知道是白日梦——梦着军事征服或性爱征服,权力或显赫,甚至仅仅是人气。它成了梦者生活的主要慰藉,几乎是唯一快乐。一旦解决衣食住行,他就进入“这种无形的心灵狂欢,这种隐秘的生命放纵”[14]。现实(realities),即便令其他人心喜,对他而言也索然无味。对于那并非只是臆想的幸福,他变得无能为力。梦想无尽财富,却存不下六便士。梦想做唐璜[15],却不会努力,使自己让随便哪个女性觉得顺眼。我把这种活动称为“病态白日梦”(morbid castle-building)。
3.适度而短暂地沉溺于上述活动,恰如临时度假或休憩,却使它理所应当地附从于更着实(effective)、更外向的(outgoing)活动。我们恐怕不必讨论,一个人终其一生与此无涉是否更为明智,因为没有这种人。这类幻梦(reverie)并非总以幻梦告终。我们现在所从事的,往往就是曾梦想从事的。我们所写之书,一度曾为某白日梦中想象自己在写之书,尽管从未如此完美。我管这叫“正常白日梦”(normal castle-building)。
【§6—7.两种“正常白日梦”:“自我型”和“超然型”】
不过,正常白日梦本身可分为两类,而且二者之别至关重要。它们可称为“自我型”(egoistic)和“超然型”(disinterested)。第一类中,梦想者自己总是英雄(hero),一切都透过他的眼睛来看。正是他,作机智辩驳,俘美女之芳心,拥有远洋游艇,或被誉为当代最伟大的诗人。第二类中,梦想者本人并非白日梦境之英雄,或许根本就不出现。因此一个在现实中无缘去瑞士的人,可能做在阿尔卑斯山区度假的幻梦(reveries)。他出现在幻境中,但不是英雄,而是静观者(spectator)[16]。他若真的去瑞士,会把注意力集中在山峦上,而不会放在自己身上;因而,在白日梦中,其注意力同样集中在想象的山峦上。不过有时候,梦者根本不在白日梦里出现。许多人可能和我一样,在不眠之夜靠想象自然景观来自娱自乐。我追溯大河源头,从海鸥鸣叫的入海口,途经蜿蜒曲折、越来越窄、越来越陡峻的峡谷,直到山地某褶皱中,源头之水滴滴答答声强可听闻。可是,我在此并非探险家,甚至连观光客都不是。我出乎其外,看世界。[17]儿童藉助合作,常能更进一步。他们会假想出一整个世界,里面有各式各样的人,自己则在此世界之外。一旦抵达这一步,幻梦之外的东西开始活动:就开始了建构(construction)、创造(invention),一言以蔽之,“虚构”(fiction)。
因而,假如梦者尚有几分才华,超然型白日梦就会轻而易举转化为文学创造。甚至还有这样的转化,从自我型到超然型,进而转为真正的虚构(genuine fiction)。特罗洛普在自传里告诉我们,他的小说如何脱胎于最最令人咋舌的自我型和补偿型白日梦。[18]
【§8—10.自我型白日梦与盲于文学者】
【§8.自我型白日梦与阅读】可在眼下的探讨中,我们关心的不是白日梦与创作的关系,而是白日梦与阅读的关系。我已说过,盲于文学者(the unliterary)钟爱的是这类故事,能使他们通过人物替代性地乐享爱情、财富或名望。这事实上是专门的(guided)或蓄意的(conducted)自我型白日梦。阅读时,他们把自己投射在最惹人艳羡或最令人钦佩的人物身上;或许,读完以后,他感受到的喜悦和胜利,会给进一步的白日梦提供蛛丝马迹(hints)。
【§9.盲于文学者并非总作自我型白日梦式投射】我想,人们时常假定,盲于文学者之阅读都是这种,而且都牵涉到此类投射。我用“此类投射”(this projection)是指,为了替代性(vicarious)快感、胜利及名望而作的投射。毫无疑问,对于所有故事的所有读者来说,都必然对主要人物做某种投射,无论他们是坏人还是英雄,无论他们令人艳羡或令人怜悯。我们必须“移情”(empathise),必须感其所感,否则还不如去读三角形跟三角形的爱情故事。可是,即便读流行小说的盲于文学之读者,假定他们总是做自我型白日梦式的投射,也未免草率。
【§10.原因有二】一则因为,他们中一些人喜欢滑稽故事(comic stories)。我不认为,无论是对于他们还是其他任何人,乐享笑话就是白日梦之一种形式。[19]我们当然不愿成为(to be)穿十字交叉袜带的马伏里奥[20]或掉入池塘的匹克威克先生[21]。我们想必会说,“我希望我当时在场”;但这仅仅是希望我们自己作为旁观者(spectators)——我们已经就是观者了——能处于更好的坐席上。二则因为,多数盲于文学者,喜欢鬼故事及其他恐怖故事;可他们越是喜欢这类故事,就越不想让自己成为其中人物。冒险故事(stories of adventures)有时候得到乐享,是因为读者把自己看作是勇敢而又足智多谋的英雄,这都有可能。不过我并不认为,我们可以确定,这总是唯一甚至主要快感。他或许钦佩此类英雄,眼热他的成功,却不会指望自己有这类成功。
【§11—14.自我型白日梦者厌恶奇幻文学】
【§11.爱幻想者并不喜欢文学奇幻】最后还有一些故事,其吸引力据我们所知,只能依赖于自我型白日梦:发迹故事,某些爱情故事,某些上流生活故事。这是最低层次读者心爱的读物;之所以最低,是因为阅读很少让他们走出自己,阅读只是强化了他们一用再用的自我耽溺,并使他们远离书本及生活中最值得拥有的绝大部分东西。这一白日梦,无论其建造是否得到书之辅助,就是心理学家所谓的“幻想”(fantasy)之一义。设使我们没有做出必要区分,我们可能会想当然认为,这类读者会喜欢文学奇幻(literary fantasies)。反过来倒是对的。做个实验,你将会发现,他们厌恶它们;他们认为它们“只适合小孩子看”,他们看不出,读有关“永远不会实际发生之事”( things that could never really happen)有何意义。
【§12.爱幻想的文艺青年,爱写实之作】在我们看来,显而易见,他们所喜之书充满不可能之事(impossibilities)。他们一点也不反对乖张心理和荒谬巧合。不过他们强烈要求遵循他们所知的那类自然法则(natural laws),要求一种人伦日常(a general ordinariness):日常生活世界里的衣着、用品、食物、房屋、职业及腔调。无疑,这部分源于他们想象力极度迟钝。只有读过千次见过百次的东西,他们才认为真实(real)。然而,还有更深原因。
【§13.现实主义与自我型白日梦】尽管他们并不把白日梦误认为是现实,但是他们情愿感到,它可能是现实。女性读者并不相信,她就像书中女主角那样,吸引了所有眼球;但她情愿相信,假如她有更多金钱,因而有了更好的穿戴、首饰、化妆品以及机遇,他们或许围着她转。男性读者并不相信,他富有且功成名就;可是,一旦他中了头彩,一旦无须才干也能发迹,他也会如此。他知道,白日梦实现不了(unrealised);但他要求,它原则上应当可以实现(realisable)。对公认的不可能性的些微暗示为何会摧毁他们的快感,其原因就在于此。一个故事给他讲述神奇(the marvelous)或奇幻(the fantastic),其实就是暗里告诉他:“我只是个艺术品。你必须如我本然地待我——你乐享我,必须因我之暗示、我之美丽、我之讽刺、我之结构。在现实世界,你不可能碰见如斯之事。”如此一来,阅读——他那种阅读——变得没了着落(poitless)。除非能让他感到,“这可能——谁知道呢——这可能终有一日会发生在我身上”,否则他的整个阅读目的就受挫。因而有一条绝对规律:一个人之阅读越接近自我型白日梦,他就越要求某种浅薄的写实主义(realism),就越少喜欢奇幻(the fantastic)。他情愿被骗,至少暂时被骗;没有东西可以骗他,除非它看上去像真的。超然型白日梦,或许会梦想神酒仙馐,玉食琼浆;自我型白日梦则会梦想熏肉加蛋或牛排。
【§14.引入下章】鉴于我用“写实主义”(realism)一词,模棱两可,故须作条分缕析。
* * *
[1] 【译按】幻想作为心理学术语,有三义:妄想、病态白日梦、正常白日梦。正常白日梦又可分为自我型和超然型。好幻想之文艺青年,并不喜欢文学奇幻,而是喜欢廉价的写实主义。因为这有助于自我型白日梦。
[2] 《古舟子咏》(the ancient mariner),英国19世纪湖畔派诗人柯勒律治的长诗。
[3] 《格列佛游记》(gulliver),英国作家斯威夫特之小说。
[4] 《乌有乡》(erewhon),英国小说家、随笔作家和批评家塞缪尔•巴特勒(samuel batler, 1835—1902)的一部讽刺小说,被誉为《格列佛游记》之后最好的一部幻想游记小说。“乌有乡”——“埃瑞洪”(erewhon)是英文nowhere的倒写,表明其地纯属虚构,假托在新西兰。年轻人希格在新西兰牧羊,无意中来到了“埃瑞洪”。在这里,生病是严重的犯罪,而此地的病人则是英国所谓的罪犯。某位先生诈骗寡妇的财产,寡妇受审判刑,诈骗人却依旧是社会中的体面人士。希格还参观了“音乐银行”(教堂)、“无理性大学”。最后,他坐气球逃离此地。(参徐译本注及《不列颠百科全书》第3卷275页)
[5] 《柳林风声》(the wind in the willows),英国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格雷厄姆(kenneth grahame,1859—1932)的儿童文学作品,安徽人民出版社2013年出版中译本,译者杨静远。
[6] 《阿特拉斯女巫》(the witch of atlas),英国著名诗人雪莱最难懂的一首诗。
[7] 《朱根》(jurgen),美国小说家卡贝尔(james branch cabell,1879—1958)之代表作。作品讲述了一个充满性象征主义的故事,攻击美国正统观念和习俗。(参《不列颠百科全书》第3卷289页)
[8] 《金坛子》(the crock of gold),爱尔兰诗人和故事作家斯蒂芬斯(james stephens,1880—1950)之成名作,因其主题富有浓厚的凯尔特色彩而闻名于世。(参《不列颠百科全书》第16卷206页)
[9] 《真实故事》(vera historia),古希腊作家、无神论者卢奇安(一译琉善,lucian,120—180)的作品。《真实故事》包括两个故事:一个是英雄icaromenippus渴望了解日月,借助鹰翅来到月球。他回望地球,惊讶于它的渺小。但他惹恼了神界,被剥夺了翅膀,无法继续飞行到天堂。另一个故事是一群人的船被飓风吹到月球,他们目睹了那里的一场战争。卢奇安可说是科幻小说的先驱。(参徐译本注)
[10] 《小大由之》(micromegas),法国启蒙哲学家伏尔泰的寓言小说,讽刺人类之自大。
[11] 《平面国》(flatland),英国牧师艾伯特(edwinabbott,1838—1926)的中篇小说。(参徐译本注)
[12] 阿普列乌斯(apuleius,约124—170以后),柏拉图派哲学家、修辞学家及作家。因《变形记》(metamorphoses)一书而知名,记述一个被魔法变成驴的青年之经历。(参《不列颠百科全书》第1卷412页)
[13] 在20世纪文学批评中,“幻想”(fantasy)成为一个特别重要的词汇。其始作俑者乃弗洛伊德,因精神分析之大盛而入驻文学批评与文化研究。廖炳惠的《关键词200:文学与批评研究的通用词汇编》(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释“幻想”一词:在弗洛伊德与文化研究学者的眼中,“欲望”总和“欲求且不可得”的心灵经验密切相关,并特别强调人们如何在记忆和日常生活的欲求中,以幻想作为一种媒介和过渡,将心中的欲求和冲动,以及当冲动无法实现时所压抑下来的欲力,以一种虚幻的视觉和意象在脑海中再现。“幻想”在这样的情境下,因此和再现的符号有紧密联结的关系,和“欲望”本身,则处于一种对等的位置。因为“欲望”是一种永远无法在日常世界中被实践的海市蜃楼,所以只能通过“幻想”及相关的再现策略,和所欲求的对象(虚构、缺席且永远不可企及的对象)之间,形成一种患得患失的关系,并利用“补偿”的心态与方法,在记忆中形成重复的冲动(repetition impulse),借由意象在脑海中的铺陈、建构与组成来进一步掌握对象。路易斯此章谈“幻想”,与当今流行理路迥异。窃以为,相异处主要有二:1. 路易斯严分作为文学术语的幻想和作为心理学术语的幻想,而当今流行批评话语则是后者一支独大;2. 路易斯严分作为心理学术语之三义,而当今流行批评话语只看重路易斯所说的第二义。
[14] 原文为:“this invisible riot of the mind, this secret prodigality of being”。约翰逊(samuel johnson)之诗句,出处待考。
[15] 唐璜(don juan),一个虚构人物,浪荡子的象征。来源于流行的传说。在西班牙戏剧家蒂尔索•德•莫利纳的悲剧《塞维利亚的嘲弄者》(1630)中,首次以文学人物出现。通过蒂尔索的悲剧,唐璜成为世界性人物,堪与堂吉诃德、浮士德比肩。(参《不列颠百科全书》第5卷362页)
[16] 假如把现世生活比作奥林匹克运动会,毕达哥拉斯就会把人分为三种:一种是藉此机会做点买卖的人,这是追逐利益者;一种是来参加竞赛的人,这是追求荣誉者;一种则是看台上的观者(spectator)。毕达哥拉斯赞美沉思的生活,故而,这三种人也就是三等人,以最后一种为人生之最高境界。罗素《西方哲学史》(何兆武、李约瑟译,商务印书馆,1963)中写道:伯奈特把这种道德观总结如下:“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都是异乡人,身体就是灵魂的坟墓,然而我们决不可以自杀以求逃避;因为我们是上帝的所有物,上帝是我们的牧人,没有他的命令我们就没权利逃避。在现世生活里有三种人,正象到奥林匹克运动会上来的也有三种人一样。那些来作买卖的人都属于最低的一等,比他们高一等的是那些来竞赛的人。然而,最高的一种乃是那些只是来观看的人们。因此,一切中最伟大的净化便是无所为而为的科学,唯有献身于这种事业的人,亦即真正的哲学家,才真能使自己摆脱‘生之巨轮’。”(第59—60页)
[17] 王国维《人间词话》第3则: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有我之境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无我之境也。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古人为词,写有我之境者为多,然未始不能写无我之境,此在豪杰之士能自树立耳。
[18]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特罗洛普自传》中译本,译者张禹九。暂未找到相应段落。
[19] 路易斯论“笑”(laughter),详参《魔鬼家书》第11封信。路易斯将笑的起因,分为四种:joy, fun, the joke proper和flippancy。况志琼译本分别译为:喜乐,开心、笑话和嘲谑;曾珍珍则译为:喜乐、愉悦、说笑和戏谑。
[20] 马伏里奥(malvolio)是莎士比亚喜剧《第十二夜》中伯爵小姐奥丽维娅的管家。整日痴心妄想着小姐爱上了他。几个人捉弄他,假冒小姐笔迹给他写信,假称爱上了他,说她愿意看见他穿黄袜子和十字交叉的袜带。马伏里奥信以为真,心花怒放。而实际上,小姐特别厌恶的正是这一装束。见《第十二夜》第二幕第五场。
[21] 《匹克威克外传》是狄更斯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他的成名作。这部既富于浪漫奇想又紧贴社会现实的幽默与讽刺小说,主要讲述的是天真善良、不谙世事的有产者匹克威克带领其信徒们在英国各地漫游的奇趣经历与所见所闻。匹克威克先生滑冰时掉入池塘一幕,见小说第三十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