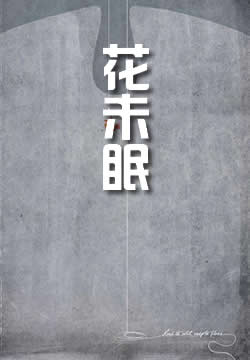on myth
【§1—5.三类梗概】
我们如果想继续深入探讨问题,必须先消除上一章可能引起的误解。
试比较:
1.有一个人,擅长歌唱和演奏竖琴,野兽和树木都聚拢过来听他弹唱。其妻死后,他下到冥界,在冥王面前弹唱。甚至冥王也心生同情,答应还他妻子。但条件是,他走在前面,领她离开冥界,步入阳界之前,不得回头看她。然而,当他们即将走出冥界时,男子迫不及待,回头一看,妻子便从眼前消失,永不复见。
2.“一个人离家多年,被波塞冬暗中紧盯不放,变得孤苦伶丁。此外,家中的境况亦十分不妙;求婚者们正在挥霍他的家产,并试图谋害他的儿子。他在历经艰辛后回到家乡,使一些人认出了他,然后发起进攻,消灭了仇敌,保全了自己。”(这是亚里士多德《诗学》1455b对《奥德赛》所作梗概。)[2]
3.让我们假设——因为我肯定不会写——《巴塞特寺院》、《米德尔马契》或《名利场》[3]同样篇幅的梗概;或者短得多的作品之梗概,如华兹华斯的《迈克尔》(michael)、贡斯当[4]的《阿道尔夫》或《碧庐冤孽》[5]
【§6—8.神话:超文学】
【§6.三类梗概之别】第一则虽只是大致轮廓(a bare outline),可我相信,任何一个有感受力(sensibility)的人,如果他首次遇见这一故事,开头寥寥数字跃入眼帘,定会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第二则读起来就不那么令人满意了。我们明白,基于这一情节可以写出一部好故事,但这一梗概本身并非好故事。至于第三则,也就是我没有写的那个梗概,我们一眼就能看出它毫无价值——不仅是作为该书之再现毫无价值,而且其本身也毫无价值;乏味得不堪忍受,不忍卒读。
【§7.神话超于文学:其价值在自身】也就是说,有一类故事,其价值在其自身——这一价值独立于其在任何文学作品中的体现(embodiment)。俄耳甫斯[6]的故事,凭其自身,就打动人且深深打动人;维吉尔[7]等人把它写成好诗这一事实,与此无关。思及这一故事并为之感动,并不必然思及那些诗人,或被他们感动。没错,若不用文字,此类故事很难抵达我们。不过,这是逻辑上的偶然。假如哑剧、无声电影或连环画也能清晰讲述,根本用不着文字,我们同样会受到感染。
【§8.神话不同于冒险故事】有人或许以为,最粗陋的冒险故事,即写给那些只想看事件(event)之人的那类故事,其情节也有这种超文学品质(extra-literary quality)。然而,并非如此。你不可能用个故事梗概,把他们搪塞过去,而不用故事本身。虽然他们只要事件,但是,事件除非“大书特书”(written up),否则事件无由达致他们。再者,他们的故事再简单,相对于一个可读的梗概,仍嫌太复杂;发生之事太多太多。而我正在琢磨的这些故事,则总有一个极为简单的叙事轮廓(narrative shape)——一个令人满足且不可避免的轮廓,就像一只好花瓶或一朵郁金香。
【§9—10.“神话”定名】
【§9.“神话”一词之含混】此类故事若不用“神话”命名,就很难想到别的名称。然而该词在很多方面都令人遗憾。首先我们须谨记,希腊语muthos并不专指此类故事,而是指任何类型的故事。其二,人类学家会归为神话的所有故事,并非都有我在此所关心的这一品质。谈及神话,恰如谈及民谣,我们通常想到的是最佳范本,而遗忘了大多数。假如我们遍读任一民族的所有神话,所读大多会让我们吃惊。且不论它们对古人或野蛮人有何意谓,它们之绝大多数,对我们而言,大都毫无意义且令人震惊;之所以震惊,不仅因其残酷、淫秽,而且因其愚蠢——几近精神失常。从这片芜秽的灌木丛之中,如榆树般生长出伟大神话——俄耳甫斯、得墨忒耳[8]与珀尔塞福涅[9]、赫斯珀里得斯[10]、巴尔德耳、[11]诸神的黄昏、[12]伊尔玛里宁铸造的神磨[13]等。相反,个体在文明时代创造出来的某些故事,具有我所谓的“神话品质”(mythical quality),却算不得人类学意义上的神话。《化身博士》[14]、威尔斯[15]的《墙中门》(the door in the wall)、卡夫卡[16]的《城堡》,其情节即属此类。皮克[17]先生在《泰忒斯诞生》(titus groan)中所构想的歌门鬼城(gormenghast),或者托尔金教授在《魔戒》[18]中所构想的树人(ents)和“盛开花朵的梦土”(lothlorien)也属此类。
【§10.优选方案:沿用“神话”一词】因有诸多不便,我必须要么沿用“神话”一词,要么另铸新词。我觉得,前者害处稍小。那些根据阅读来理解的人(those who read to understand)——我不考虑文风贩子——会按照我所赋予的意思来理解该词。在本书中,神话指具有以下诸特征的故事。
【§11—16.神话特质】
【§11.特质一:超于文学】1.在我已经说过的意义上,它超于文学(extraliterary)。通过纳塔利斯•科姆斯[19]、兰普瑞尔[20]、金斯利[21]、霍桑[22]、罗伯特•格雷夫斯[23]或罗杰•格林[24]了解到同一神话的人,有着相同的神话体验;它之重要,不仅仅是最大公约数(h.c.f.)。与此相对,从布鲁克[25]的《罗密欧》(romeus)与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中得到相同故事的那些人,仅仅共有最大公约数,这一公约数本身并无价值。
【§12.特质二:不像叙述,更像物体】2.神话之乐,很少依赖用于吸引人的惯用叙事手段,如悬念(suspense)或突转(surprise)[26]。即便首次听闻,也让人觉得非它莫属。而且首次听闻的主要价值在于,它让我们结识一个可作永久沉思之对象——与其说它是个叙述(narration),不如说它更像个物体(thing)——以其独特气息(flavour)或品质(quality)感染我们,恰如一种气味(a smell)或一个和弦(a chord)那般。有时候,甚至从一开始,里面几乎没有一点叙事成分。诸神与所有好人都活在诸神黄昏的阴影之下,这一观念算不上一个故事。赫斯珀里得斯姐妹,还有她们的金苹果树和巨龙,不必加入赫拉克勒斯偷苹果的情节,就已是个潜在的神话(a potent myth)。[27]
【§13.特质三:读者无情感投射】3.人类同情(human sympathy),减至最低。在神话人物身上,我们根本不会有强烈投射。他们像是在另一世界里活动的形体(shapes)。虽然我们确实感到,他们的活动模式与我们自己的生活,有深刻关联,但是我们并不借助想象,使自己进入他们的生活。俄耳甫斯的故事,使我们悲伤;但我们是为所有人感到难过(sorry for),而不是真切同情(sympathetic with)他;至于乔叟笔下的特洛伊罗斯,我们倒是真切同情[28]。
【§14.特质四:奇幻】4.就“奇幻”(fantastic)一词之一义而言,神话总是“奇幻”。它言说不可能之事(impossibles)及超自然之事(preternaturals)。[29]
【§15.特质五:严肃】5.神话体验或悲或喜,但一定严肃(grave)。不可能有喜剧性神话(指我所说的意义上的神话)。
【§16.特质六:神不可测】6.神话体验不但严肃(grave),还令人心生敬畏(aweinspiring)。我们觉得它神圣不可测(numinous)[30]。仿佛伟大时刻的某种东西迥临我们。[31]心灵反复试图把握——我主要是指概念化(conceptualise)——这个东西。人类持续不懈地为神话提供寓言式解释(allegorical explanations),即是明证。试过了所有寓言之后,我们依旧感到,神话本身比这些寓言更重要。[32]
【§17.探讨神话,须区分描述与解释】
我是在描述(describing)神话,而不是在作解释(accounting for)。考察它们如何产生——究竟是原始科学,还是远古仪式之遗存,是巫医之编造,还是个人或集体无意识的外露——不是我的意图所在。我关心的是,神话对心智与我等近似之人的有意识想象(the conscious imagination)所产生的影响,而不关心它们对前逻辑心灵的假定影响(hypothetical effect on pre-logical minds),也不关心它们在无意识中的史前史(pre-history in the unconscious)。[33]因为只有前者,才能被直接观察,只有前者才处于文学研究之射程以内。当我谈论梦,我是在说,也只能在说,醒后还记得的梦。同理,当我谈论神话,我是在说我们体验到的神话:即,可供沉思但不必相信、与仪式无关、展现在逻辑心灵中完全清醒的想象面前的神话。我只关心冰山露出水面的那部分;单单是它就具有美,单单是它就作为沉思对象而存在。毫无疑问,大量在水面以下。考察水下部分的欲望,自有其科学正当性。但我怀疑,这类研究之独特吸引力,部分来源于这一冲动,即,与人们试图把神话寓言化(allegorise)之冲动毫无二致的冲动。抓住、概念化(conceptualise)神话所暗示的某种重要之物,是另一种努力。
【§18—24.盲于文学与超于文学】
【§18.因关心阅读方式才谈神话】既然我藉神话对我们的影响来界定神话,那么在我看来,很明显,同一故事对甲而言可能算是神话,对乙可能不算。假如我的目标是提供标准,藉以把故事归为神话或非神话,那么这就是个致命缺陷。然而,我之目标并不在此。我关心的是阅读方式(ways of reading),正因为此,才有必要拐到神话上来。
【§19.神话读者与盲于文学者只是表面相似】当一个人藉助或寡文乏采或格调不高或粗腔横调的文字,头一次接触到一个他心目中的伟大神话时,他会漠视和忽略糟糕文字而只关心神话本身。他几乎不在乎其写作。只要是讲这个神话,他都乐于接受。而这似乎恰恰是上一章谈到的盲于文学者(the unliterary)的表现。两者都极少注意文字,都只关心事件(event)。然而,假如把神话爱好者等同于盲于文学之大众,我们将大错特错。
【图5.1】波提切利的《维纳斯的诞生》
【§20.神话欣赏并非文学体验】差别在于,两者所用程序虽同,但前者之运用合适且卓有成效,后者则不是。神话之价值并非一种文学价值(literary value),欣赏神话也并非一种文学体验。他接近那些文字,并未期待或相信它们是好读物(good reading matter);它们只是信息(information)。其文学优劣(对他之主要目的而言)并不重要,恰如文学优劣(literary merits or faults)对于时刻表或菜谱那样。当然有时候,给他讲述神话的文字本身,也是优秀文学作品——比如散文体《埃达》(edda)[34]。如果他是敏于文学之人(a literary person)——这样的人通常都是敏于文学之人——他也会因作品本身而悦乐于那部文学作品(delight in that literary work for its own sake)。但这种文学愉悦(literary delight)截然有别于神话欣赏(appreciation of the myth);正如我们欣赏波提切利的《维纳斯的诞生》这幅画,和我们对画作所讴歌的那个神话的种种反应(无论什么样的反应)是两码事。
【§21 盲于文学者与神话爱好者】另一方面,盲于文学者(the unliterary)坐下来,准备“读一本书”。他们把想象力交由作者指挥。但是,他们是半心半意的降服。他们几乎依然故我。[35]任何事情,要想抓住他们的注意力,就不得不加以强调,不得不大书特书,不得不用某种陈词滥调加以包装。与此同时,他们根本不懂得严格顺从于文字(strict obedience to the words)。一方面,比起一个通过古典文学词典里干巴巴的梗概查找并爱上某一神话的人,他们之行止更敏于文学(more literary);更敏于文学,是因为他们受书的约束,完全依赖书。但另一方面,他们之行止如此含糊又草率(hazy and hasty),以至于几乎无法得到一本好书所能赠予的任何好处。他们就像这样一些学生,希望什么都解释给他们,却从来不大注意解释。尽管他们也像神话爱好者一样关心事件,但所关心的事件并非同类,关心本身也并非同类。神话爱好者终生都会被神话感动。他们则不同,那股兴奋劲一旦过去,那阵好奇心得到满足,他们就把事件忘得一干二净。这也很正常,因为他们所珍视的事件,并无资格获得想象力之永久忠诚。
【§22.超于文学与盲于文学】一言以蔽之,神话爱好者之行止,超于文学(extra-literary);而他们之行止,盲于文学(unliterary)。前者从神话中得到神话可以给予的东西。后者从阅读中得到的,连阅读可以给予的十分之一或五十分之一都没有。
【§23.刺激与敬畏】我已经说过,某故事多大程度上是神话,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是谁听或谁读。于是引出一个重要推论。我们切莫以为[36],任何人读一本书,我们都确切知道正在发生什么。因为毫无疑问,同一本书对甲而言,只是刺激的“奇闻漫谈”(an exciting ‘yarn’);对乙而言,则可以从中读出神话或类似神话的东西来。就此而论,阅读莱德•哈格德[37]尤其暧昧不明。假如你看到两个孩子都在读浪漫传奇(romance),你切不可断言,他们有着相同体验。一个孩子只看到主人公的危险(danger),而另一个孩子则可能感到“敬畏”(aweful)。前者因好奇而奔进,后者则可能因惊叹而停顿。对盲于文学的孩子来说,捕象及海难,或许和神话成分一样好看(它们都很刺激),而哈格德通常也能写出与约翰•巴肯[38]的一样好玩的东西。喜爱神话的孩子,假如他同时敏于文学(literary),会很快发现巴肯是位好得多的作家;但他仍会意识到,通过哈格德,体会到了与刺激不可同日而语的东西。读巴肯时,他问“主人公是否能够逃脱?”读哈格德时,他感到“我忘不了这个。这个刻骨铭心。这些形象击中我心灵深处。”
【§24.盲于文学者与阅读神话无涉】因此,阅读神话之方式和盲于文学者(the unliterary)之典型阅读方式,只是表面相似而已。其践行者是两类不同的人。我曾遇见过敏于文学之人,对神话不感兴趣,但我从未遇见过盲于文学之人,对神话感兴趣。盲于文学者,能接受在我们看来全然不合情理(grossly improbable)的故事;人物心理、所写社会状态、命运浮沉等,令人难以置信。但他们无法接受,公认之不可能及超自然(admitted impossibles and preternaturals)。[39]他们说,“不可能实有其事”,然后把书放下。他们认为它“愚蠢”。因此,我们可称之为“幻想”(fantasy)的东西,虽然占据其绝大部分阅读体验,但是他们却一概不喜欢奇幻之作(the fantastic)。这一区别提醒我们,若不界定术语,就无法深入探讨他们的阅读偏好。
* * *
[1] 【译按】神话之特质有六:1.神话是超文学;2.不像叙事,更像静物;3.人类同情减至最低;4.奇幻;5.严肃;6.令人心生敬畏。故而,神话爱好者与盲于文学者虽表面相似,实际却大相径庭。简言之,前者之阅读方式超于文学,后者则盲于文学;前者心存敬畏,后者则寻找刺激。
[2] 陈中梅译注《诗学》,商务印书馆,1996。
[3] 《巴塞特寺院》(barchester towers),英国小说家特罗洛普(anthony trollope,1815—1882)1857年发表的小说;《米德尔马契》(middlemarch),英国女作家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1819—1880)之代表作,1871—1872年出版;《名利场》(vanity fair),英国19世纪小说家萨克雷(w. m. thackeray,1811—1863)的成名作。
[4] 贡斯当(constant,1767—1830),法国—瑞士小说家、政论家,生于瑞士。他的《阿道尔夫》(1816)开现代心理小说之先河。1802年,贡斯当与斯塔尔夫人流亡到瑞士,后又到德国,与歌德、席勒相识。他也是浪漫派思想先驱施莱格尔兄弟的朋友。流亡期间,从事《论宗教的起源、形式及发展》的写作工作,对宗教感情作了历史分析,这部作品也显示了他内心中的自我。(参《不列颠百科全书》第4卷429页)
[5] 《碧芦冤孽》(the turn of the screw,亦译《螺丝在拧紧》),美国批评家及文学家亨利•詹姆斯的中篇小说,是他写过的最著名的“鬼故事”。(参虞建华主编《美国文学辞典:作家与作品》,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第500页)。
[6] 俄耳甫斯(orpheus):古希腊传说中的英雄,有超人的音乐天赋。根据传说,俄耳甫斯是一位缪斯和色雷斯王厄戈洛斯(一说是阿波罗)的儿子。阿波罗把他的第一把拉里琴给了俄耳甫斯。俄耳甫斯的歌声和琴韵十分优美,引得各种鸟兽木石都围绕他翩翩起舞。他参加阿尔戈船英雄的远征,用自己奏出的音乐挽救了英雄们免受女妖塞壬歌声的引诱。出征归来后,他娶欧律狄刻为妻,但妻子不久被毒蛇咬死。为了挽回妻子,就发生了本书描述的故事。(参《不列颠百科全书》第12卷439页)
[7] 维吉尔(virgil,公元前70—公元前19),被罗马人看成是他们最伟大的诗人,这一评价得到后世的认可;他的声誉主要在于他的民族史诗《埃涅阿斯纪》。该诗叙述罗马传说中建国者的故事,并且宣告罗马在神的指引下教化世界的使命。作为一位诗人,其持久不衰的声誉不仅在于诗句的音乐性和美妙的措词,以及大规模地把一部错综复杂的作品创作出来的能力,而且因为他通过诗歌体现了各方面具有永恒意义的经验和行为。他对英国文学影响巨大,斯宾塞的《仙后》和弥尔顿的《失乐园》都深受其影响。(参《不列颠百科全书》第17卷544页)
[8] 得墨忒耳(demeter):希腊神话中司掌农耕的女神,有时还作为健康、生育和结婚之神出现。她的表征为谷物的穗儿,装满花、谷物和各种果实的神秘的篮子。有关她的故事主要与她女儿珀尔塞福涅相关。(参《不列颠百科全书》第5卷225页)
[9] 珀尔塞福涅(persephone):希腊宗教中的主神宙斯和农业女神得墨忒耳的女儿,冥王哈得斯的妻子。荷马的《得墨忒耳颂》记述了她在尼撒谷采集花朵时被哈得斯劫往冥界的故事。她的母亲得墨忒耳得到女儿被劫持的消息后,异常悲愤,不再关心大地的收获或丰产,于是发生了大规模的饥馑。宙斯进行干预,命令哈得斯把珀尔塞福涅交还给她的母亲。但由于她已经在冥界吃了粒石榴子,所以她不能完全脱离冥界,一年要有4个月时间和哈得斯呆在一起,其余时间则在她母亲那里。珀尔塞福涅每年在冥界呆四个月的故事,毫无疑问是要说明希腊的田地在盛夏(收获后)中荒芜的情况,而只有到秋天下雨的时候,它们才得到播种和耕种。(参《不列颠百科全书》第13卷165页)
[10] 赫斯珀里得斯(hesperides):据希腊神话,她们是负责看守金苹果树的嗓音清澈的少女。这树是该亚在赫拉嫁给宙斯时送给她的礼品。她们通常为3人,也有说法说她们多至7人。(参《不列颠百科全书》第8卷55页)
[11] 巴尔德耳(balder):古斯堪的纳维亚神话中主神奥丁与妻子弗丽嘉所生的儿子。他长得英俊,为人正直,深受诸神宠爱。关于他的大多数传说讲的是他的死。冰岛故事则谈到诸神如何向他投掷东西取乐,因为他们知道他不会受伤。黑暗之神霍德耳受邪恶的洛基的欺骗,把唯一能伤害他的槲寄生投向巴尔德尔,把他杀死。某些学者认为巴尔德尔消极忍受苦难的形象,是受了基督形象的影响。(参《不列颠百科全书》第2卷161页)美国著名的“古典文学普及家”依迪丝•汉密尔顿(1867—1963)在《神话》一书中写道:“光明之神巴尔德耳是天上和人间最受爱戴的神祇,他的死亡是诸神所遭遇的第一个重大灾难。”(刘一南译,华夏出版社,2014,第348页)
[12] 诸神的黄昏(ragnarok):也译作“世界末日”。古诺尔斯语,特指斯堪的纳维亚神话中神和人的末日。全面描述这世界末日的,只有约10世纪末的冰岛叙事诗《沃卢斯帕》(即《西比尔的寓言》)和13世纪s.斯图鲁松所写的《散文埃达》。(参《不列颠百科全书》第14卷116页)
[13] ilmarinen,坊间多译为“伊尔马利宁”,《世界神话词典》(鲁刚主编,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译作“伊尔马里能”,芬兰神话中创造宇宙万物的铁匠神,是把铁打造成天穹的神。
[14] 《化身博士》(dr jekyll and mr hyde),19世纪英国小说家史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1850—1894)之代表作,中译本有十余种。
[15] 威尔斯(herbert george wells,1866—1946),英国小说家、记者、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以科幻小说《时间机器》、《星际战争》著称。他的小说使人们认识到20世纪技术世界的危险与希望。(参《不列颠百科全书》第18卷169页)
[16] 卡夫卡(franz kafka,1883—1924),捷克出生的德语幻想小说作家。死后发表的作品,尤其是《审判》(1925)和《城堡》(1926),表达了20世纪人的焦虑和异化。(参《不列颠百科全书》第9卷121页)
[17] 马尔文•皮克(mervyn peake,1911—1968),英国小说家、诗人、画家、剧作家和插图作者。以其光怪陆离的三部曲小说《泰忒斯的诞生》和为自己的小说及儿童读物所画插图而闻名。(参《不列颠百科全书》第13卷97页)
[18] 《魔戒》(the lord of the rings),英国著名作家、路易斯之挚友托尔金(j. r. r. tolkien)的代表作。朱学恒的中译本2011年由译林出版社出版。
[19] 纳塔利斯•科姆斯(natalis comes,1520—1582),意大利神话作家、诗人、人文主义者、历史学家。其主要著作为拉丁文《神话》(mythologiae,1567)十卷,乃古典神话学的范本之一(a standard source)。(参英文维基百科)
[20] 兰普瑞尔(john lempriere,1765—1824),英国古典文学学者,因编写《古典文学词典》(或称《古典名著书目》)而著称。此书后经多位学者编辑,一直是神话和古典历史方面的参考读物。(参徐译本注)
[21] 金斯利(charles kingsley,1819—1875),英国圣公会牧师、教师和作家。他的小说在维多利亚时代被广泛阅读,对英国社会的发展很有影响。在教会人士中,他最早拥护达尔文的学说。(参《不列颠百科全书》第9卷277页)
[22] 霍桑(nathaniel hawthorn,1804—1864),美国作家,擅长写寓言和象征性故事。他是美国文学界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以其《红字》(1850)和《带有七个尖角阁的房子》(1851)著称。(参《不列颠百科全书》第7卷503页)
[23] 罗伯特•格雷夫斯(robert graves,1895—1985),英国诗人、小说家、评论家和古典文学学者。其120多部著作中,包括著名的历史小说《克劳狄一世》(1934)、回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杰作《向那一切告别》(1929)以及博学而又有争议的神话研究著作。(参《不列颠百科全书》第7卷250页)
[24] 罗杰•格林(roger green,1918—1987),英国传记作家,儿童文学作家,与路易斯、托尔金同为淡墨会(inklings)成员。(参英文维基百科)
[25] 即亚瑟•布鲁克(arthur brooke,生平不详)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悲剧史》(the tragical history of romeus and juliet,1562)。此诗据说是莎士比亚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的主要来源。
[26] 亚里士多德贡献了“突转”这一概念。他认为情节是悲剧的根本和“灵魂”。突转和发现是情节中的两个成分,最好的情节是突转与发现同时发生。所谓“突转……指行动的发展从一个方向转至相反的方向”;所谓“发现……指从不知到知的转变,即使置身于顺达之境或败逆之境中的人物认识到对方原来是自己的亲人或仇敌。”(陈中梅译注《诗学》第11章,商务印书馆,1996)。
[27] 赫拉克勒斯(heracles),希腊语作herakles,拉丁语作hercules,即罗马的赫丘利。希腊罗马传说中最著名的英雄。关于赫拉克勒斯盗取金苹果的故事,俄国库恩编著的《希腊神话》(朱志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一开头写道:“这些苹果长在一棵金苹果树上。这棵苹果树是地神盖亚培植的,在赫拉和宙斯举行婚礼的那一天作为礼物送给赫拉。要建立这一功绩,首先必须打听明白,去赫斯珀里得斯姐妹的果园的路径。而她们的果园还有一头日夜永不合眼打盹的巨龙守卫着。”(第116页)
[28] 指乔叟的《特洛伊罗斯与克丽西达》(troilus and cryseyde)。
[29] 关于“奇幻”(fantastic),参下一章。
[30] numinous这一概念,典出德国神学家、宗教史家鲁道夫•奥托(rudolf otto,1869—1937)。奥托在《论神圣》(成穷、周邦宪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一书中指出,本源性的“神圣”乃宗教领域的特有范畴。至于人们说道德之“神圣”、法律之“神圣”,只是“神圣”的派生性用法。这一本源性的“神圣”,才是神学和宗教哲学研究的真正课题。为了帮助人们理解这一本源性的“神圣”,奥托根据拉丁文numen自铸新词numinous。(参见《中译者序》及《论神圣》第1—2章)路易斯在《痛苦的奥秘》(邓肇明译,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2001)第一章,打了三个比方,很形象地解释了奥托所说的numinous:假如有人告诉你隔壁有老虎,你或许会感到害怕(fear)。但如果有人说“隔壁有鬼”而你又相信的话,你会真的感到害怕,可是性质却不一样。这种害怕不是基于对危险的认识,也不单单是怕它会陷害你,而是因为鬼就是鬼。这是“不可思议”(uncanny)多于危险(danger)。鬼叫人害怕的那种情况可以称为畏惧(dread)。既懂得“不可思议”就摸到神圣不可测(numinous)的边缘了。现在假如有人直接告诉你:“房里面有神(a mighty spirit)”而你又相信,那么你的感觉就不仅仅是害怕危险,因为你内心的忐忑不安会深远得多。你会感到希奇(wonder),同时又有一定的退缩(shrinking)——对这样的一位访客感到手足无措,兼有俯伏下拜的心理。这样的一种感觉可以用莎士比亚的句子来表达:“在其跟前我相形见绌”。这种感受可以说是敬畏(awe),而引发这种感觉的便是那位神圣不可测者(the numinous)。(中译本第5页,部分英文系拙译参照英文原本添加)
[31] 原文是:it is as if something of great moment had been communicated to us.
[32] 路易斯《给孩子们的信》(余冲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一个严格的寓言就像是一个有答案的谜语;而一个伟大的浪漫故事,则像是芬芳的花朵:它的香味让你想起一些无法形容的事情。”(第102页)
[33] 路易斯在此暗指人类学与精神分析这两种探讨神话的路径。对这两种在20世纪颇为流行的探讨路径,路易斯颇有微词。详参《心理分析与文学批评》(psycho-analysis and literary criticism)与《人类学路径》(the anthropological approach)二文,文见walter hooper编选的路易斯文集《文学论文选》(selected literary essay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9)。
[34] 古代冰岛著名文学作品,分诗体和散文体两种。
[35] 原文是:they can do very little for themselves。拙译系意译。路易斯在《英语是否前景堪忧》一文中说:“文学研究的真正目标是,通过让学生成为‘观赏者’(the spectator),使学生摆脱固陋(provincialism)。”(见拙译《切今之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第37—38页)
[36] 【原注】我并不是说,我们永远发现不了。
[37] 哈格德(sir henry rider haggard,1856—1925),英国小说家。最为著名的作品,是《所罗门王的宝藏》(1885)这部富有浪漫色彩的历险记。(参《不列颠百科全书》第7卷387页)
[38] 约翰•巴肯(john buchan,1875—1940),苏格兰政治家、作家,以惊险小说闻名于世。其最受欢迎的惊险小说是《三十九级台阶》(1915)。(参《不列颠百科全书》第3卷206页)
[39] improbable与impossible,一般都汉译为“不可能”,但其意思却大有差别。简言之,前者言情理,后者言有无。故而,probability作为一个哲学概念,一般汉译为“或然”、“可然”或“概然”;improbability,则略相当于汉语之“未必然”。作为文学理论术语,improbable与impossible之别,亚里士多德《诗学》第24章里的这一观点足以昭示。他说,组织情节,probable impossibilities比improbable possibilities更可取。陈中梅译前者为“不可能发生但却可信的事”,后者为“可能发生但却不可信的事”(陈中梅译注《诗学》,商务印书馆,1996);朱光潜《西方美学史》则译前者为“一种合情合理的不可能”,译后者为“不合情理的可能”。朱先生解释说:这里“不可能的事”(译按:即impossibilities)是指像神话所叙述的在事实上不可能发生的事。……他区别出“合情合理的(即于情可信的)不可能”和“不合情理的可能”,而认为前者更符合诗的要求。所谓“不合情理的可能”是指偶然事故,虽可能发生,甚至已经发生了,但不符合规律,显不出事物的内在联系。所谓“合情合理的不可能”是指假定某种情况是真实的,在那种情况下某种人物做某事和说某种话就是合情合理的,可以令人置信的。例如荷马根据神话所写的史诗在历史事实上虽是不真实的,而在他假定的那种情况下,他的描写却是真实的,“合情合理的”,“符合可然律或必然律”,见出事物的普遍性和必然性的。(《朱光潜美学文集》卷四,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第78—79页)拙译依朱先生的解释,译probable为“合乎情理”,improbable为“不合情理”;译possible为“可能”,译impossible为“不可能”。 至于probability,作为一个抽象概念,依哲学界之通例,译为“或然性”;improbability则译为“未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