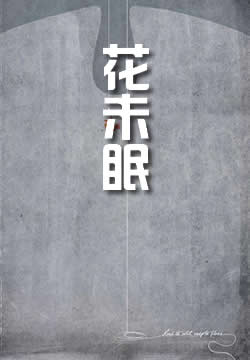the reading of the unliterary
【§1—3.谈艺术,不可概论】
【§1.文学欣赏与音乐欣赏之别】我们很容易区分,听众是对一首交响曲作纯粹的音乐欣赏(the purely musical appreciation),还是把它主要或完全当作起点,以生发非可听闻(inaudible)(因此也非关音乐\[non-musical\])之事物,如情绪和视觉形象。同样意义上,对文学作纯粹的文学欣赏(a purely literary appreciation of literature),却不存在。每篇文学作品都是文字序列;字音(或其对应的字符)之所以是文字(words),正是因为字音将人的心灵带向字音之外。文字之为文字,意在于此。神游乐音以外,走向非可听闻、非关音乐之事物,这或许是听音乐的错误方式。然而,同样神游于文字之外,走向非关言辞(non-verbal)、非关文学(non-literary)之事物,却并非错误的阅读方式。这正是阅读。否则,我们就会说,眼睛一页页扫过用我们不懂的语言写成的书页,也是阅读;否则,即便不学法语,我们也能阅读法语诗了。一首交响曲的第一个音符,要求我们只关注它本身。《伊利亚特》的第一个字,则把我们的心灵引向愤怒;[2]我们了解愤怒,是在此诗和整个文学之外。
【§2.词之为词,在于有所意指】有人主张“一首诗应无它意,只是自己”(a poem should not mean but be)[3],有人反对。在此,我并不企图了却这桩公案。无论孰是孰非,可以确定的是,诗中文字必须有所意指。一个词,“只是自己”(was)、并无“它意”(mean),就不成其为词。这一点,甚至适用于“胡话诗”(nonsense poetry)[4]。boojum[5]一词,在其语境里不只是个噪音。如果把格特鲁德•斯泰因[6]的a rose is a rose,当作是arose is arose,结果就不一样。
【§3.谈艺术,不可一概而论】每门艺术都是自身,而非其他艺术。[7]因此,我们得出的任何普遍原则,运用到各门艺术上时,必须有所针对。[8]我们接下来的任务是,找到适当模式,把“使用”与“接受”之别运用到阅读上。盲于音乐之听众(unmusical listener),只注意主旋律(top tune)及其用场。盲于文学之读者(the unliterary reader)身上,与此相应的是什么呢?我们的线索是,这类读者的行为。在我看来,它有五个特征。
【§4—10.盲于文学者之特征】
1.若非强制,非叙事之作(narrative)不读。我不是说,他们都读小说(fiction)。最最盲于文学之读者,胶着于“新闻”。他每天兴致勃勃地阅读,在某个他从未去过的地方,不知何故,某个他不认识的人娶了、解救了、抢劫了、强奸了,或者谋杀了另一个他不认识的人。高他一等的读者——只读最低级小说的那些人——和他并无本质区别。那些人和他想读到的事件,属于同一类型。区别只在于,他像莎士比亚剧中的莫普萨一样,想要确信“它们肯定是真的”[9]。这是因为他着实盲于文学(unliterary),[10]以至于无法想象虚构(fiction)之合法,甚至无法想象虚构之可能。(文学批评史表明,欧洲用了几百年时间才完全跨过这道坎。)
2.不长耳朵。他们全凭眼睛阅读。最最刺耳的不谐和音,与最最动听的节奏和元音构成的旋律,在他们听来毫无区别。正是凭这一点,我们才发现,一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盲于文学。他们会写出这样的句子:“the relation between mechanization and nationalisation”[11],面不改色。
3.不仅在听觉方面,而且在其他任何方面,他们要么对文风(style)毫无意识,要么会偏爱那些我们本以为写得相当拙劣的书。拿本《金银岛》(treasure island)给一个盲于文学的12岁孩子读(并非所有12岁的孩子都盲于文学),而不是他常看的讲海盗的“血气男儿”故事;或者拿本威尔斯h. g. 威尔斯([12]的《登月先锋》(first men in the moon)给一个只看最低级科幻小说的人读。你常会大失所望。你给他们的书,看来正是他们想看的那种类型,只不过写得太好了:描写是真正的描写,对白令人浮想联翩,人物可以清晰想见。他们走马观花般随便翻翻,就把书丢在一边。书中的某些东西让他们退避三舍。
4.他们所乐享的叙事之作(narratives),文字成分减少到最低限度——连环画故事,或者是对白少得不能再少的电影。[13]
5.他们要进展迅速的叙事。必须不断有事“发生”。他们最爱用“缓慢”、“拖沓”之类术语,表达不满。
【§9.盲于音乐者只要曲调,盲于文学者只要事件】不难看出这些特征的共同来源。正如盲于音乐之听众只想要曲调(tune),盲于文学之读者只想要事件(event)。前者几乎统统忽略了乐队实际奏出的声响;他只想哼哼曲调。后者则几乎统统忽略了眼前文字正在做的一切;他只想知道接下来发生了什么。
【§10.盲于文学者何以有此特征】他只读叙事之作,因为只有在那里,他才能找到事件。他对所读之书的声韵方面,充耳不闻。因为节奏和旋律,无助于他发现谁娶了(营救、抢劫、强奸或谋杀了)谁。他之所以喜欢连环画式叙事,以及几乎没有对白的电影,因为其中没有什么在他与事件之间碍手碍脚。他喜欢速度,因为进展迅速的故事全由事件(events)构成。[14]
【§11—15.盲于文学者缘何喜欢坏文字,不喜欢好文字】
【§11.无人因其拙劣而喜欢拙劣】他之文风(style)偏好,尚需多费唇舌。看上去,我们碰到了对拙劣本身之喜欢(a liking for badness as such),即因其拙劣而喜欢拙劣(for badness because it is bad)。[15]但我相信这不是实情。
【§12.好文字与坏文字:隔与不隔】我们自以为,自己对某人文风之评判(judgement),是逐字逐词即时作出;然而实际上,我们的评判,通常必定尾随字和词对我们的影响(effect),不管间隔多么微乎其微。读到弥尔顿的“斑驳树影”(chequered shade)[16]时,我们发觉自己正在想象某种光与影的分布,感到格外生动、惬意、愉悦。[17]于是我们得出结论,“斑驳树影”写得好。结果(result)证明了工具(the means)之精良。物体清楚可见,证明我们借以观看的镜片(lens)之好。[18]又如,我们读《盖伊•曼纳令》[19]中的一段,[20]主人公仰望天空,看见行星在各自的“液态的光的轨道”中“打滚”(‘rolling’ in its ‘liquid orbit of light’)。行星在打滚,还有看得见的轨道,这实在荒唐无稽,我们根本不会去想象这幅画面。即使“轨道”(orbits)是“球体”(orbs)之误,情况也好不到哪去。因为靠裸眼观察,行星不是球体,甚至连圆盘都不是。我们眼前除了一片混乱,一无所见。于是我们说,司各特写得不好。这是块坏镜片(lens),因为我们透过它看不到东西。与此类似,我们读到的一个个句子,会让我们的内在听觉(inner ear)[21]感到或满足或不满足。依这种体会,我们来评判该作者的节奏是好还是坏。
【§13.判断隔与不隔,需要顺从】以下将会看到,我们据以作评判的一切体验(experiences),都基于认真对待文字。除非我们充分关注字音和字义,除非我们顺从(obediently)文字之约请,去接受、想象、感受,否则,我们就不会有那些体验。除非你真正努力透过镜片(lens)看,否则就无法知道它的好坏。我们永远也无法得知某部作品写得不好,除非我们一开始先把它当成好作品读,最后发现我们对作者的礼遇过了头。但是,盲于文学之读者给予文字的那点可怜关注,只为从中抽绎事件。除此之外,别无它求。好的写作能够给予或坏的写作不能给予的大部分东西,他既不想要,也用不上。
【§14.盲于文学者缘何喜欢劣作】这就既解释了他何以不珍视佳作,也解释了他何以喜欢劣作。在故事连环画中,好绘画不但没必要,还会成为障碍。因为每个人物或物体,必须一下子且毫不费力地辨认出来。绘画不是供仔细端详的,而是当作陈述(statement)来理解的;它们距象形文字(hieroglyphics)仅一步之遥。对盲于文学之读者来说,文字之处境与此相同。用陈词滥调来描述每一种外表和情感(情感可能是事件的一部分),对他来说再好不过,因为一看就明白。“不寒而栗”(my blood ran cold)是形容恐惧的象形文字。像大作家可能会做的那样,试图具体而又细致入微地呈现此恐惧,对盲于文学之读者而言,则是双重意义上的哑口黄连。因为这提供给他的,他不想要;而且这要求他对文字付出某种或某程度的关注,他并不愿意付出。这就好比努力让他买件东西,他用不着,价格还很是不菲。
【§15.盲于文学者缘何不喜欢佳作】对他而言,佳作之所以令他不快,要么因太过俭省,要么因太过详尽。劳伦斯笔下的林地景色,[22]或罗斯金笔下的山谷,[23]细致得令他不知如何应对;另一方面,他也不满意马罗礼[24]的这一描写:“他到达一座堡寨的背后,看到一切的建筑都很雄伟壮丽,后门直对着海面,门外没设警卫,只留下两只狮子在门前;那时月明如昼,可数毫发。”[25]“我不寒而栗”(my blood ran cold)若换成“我极度恐惧”(i was terribly afraid),也不能让他满意。就好的读者而言,这类简单的事实陈述(such statements of the bare facts)往往最能激发想象力。但“月明如昼,可数毫发”(the moon shining clear),盲于文学之读者仍嫌不够过瘾。他们宁愿读到,堡寨“沐浴在一片银色月光中”(bathed in a flood of silver moonlight)。这部分是因为,他们对所读文字之关注,非常不够。什么都要突出(stressed),什么都要“大书特书”(written up),否则,他们就注意不到。更重要的原因是,他们需要象形文字,即能引起他们对月光的惯常反应(stereotyped reactions)的那种东西(月光当然是书本、歌曲和电影中的月光;我相信他们阅读时,绝少用得上对真实世界的记忆)。因此他们阅读方式之缺陷,是双重的(doubly),也是悖谬的(paradoxically)。他们缺乏专注又顺从的想象力(attentive and obedient imagination),无法利用具体而准确的场景描写或情感描写。另一方面,他们缺乏丰富的想象力,无法(在一瞬间)扩充简单的事实陈述。因此,他们要的就是徒有其表的描写和分析,不必用心阅读,却足以让他们感到行动(action)并非在真空里进行——约略提及树木、树荫和草地就代表树林,“噗”地飞出的瓶塞和满桌菜肴就代表宴会。为了这一目的,陈词滥调越多越好。这类段落之于他们,正如布景之于大部分戏院常客。没有人会真正注意它,不过要是它缺席(absence),人人都能马上看出。因此,好作品几乎总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令盲于文学之读者不快。当一个好作家把你领入一座花园时,他要么会给予你此时此刻那座花园的准确印象——不必很长,重要的是选择——要么只说“清晨,在花园”。盲于文学者,对两者都不满意。他们管前者叫“废话连篇”,但愿作者“闲话少叙,言归正传”。他们憎恶后者如真空(as a vacuum);[26]他们的想象力无法在其中呼吸。
【§16.文风贩子反文学,只看文字】
方才说过,盲于文学之读者对文字关注不够,以至于无法充分地利用它。我必须注意到,还有一种读者,对文字之关注过了头,误入歧途。我想到的这种人,我称之为“文风贩子”(stylemongers)。这些人拿起一本书,专注于他们所谓的该书“文风”(style)或其“英语”(english)。他们作评判,既不凭声韵(sound),也不凭其感染力(power to communicate),而是看它是否符合某些武断的规则。他们的阅读,是一种持续不懈的搜捕女巫行动,专挑书中的美语用法、法语用法、分裂不定式和以介词结尾的句子。[27]他们不问,该美语用法或法语用法是增强了还是削弱了我们语言的表现力。他们毫不在乎,最优秀的英语演说家和作家以介词结尾,已有一千多年。他们毫无道理地讨厌某些词。这个词是“他们一直讨厌的词”;那个词“总是让他们联想起某某来”。这个太过常见,那个太过罕见。在所有人中,这类人最没资格谈论文风;因为真正相干的只有两个测试——(恰如德莱顿[28])所说)“声情并茂”(sounding and significant)能做到几分——他们却从未应用。他们评判工具,不是看它是否出色完成本该派上的用途;他们把语言看作“只是自己”(is)、并无“它意”(mean);他们评判镜片,靠的是盯着镜片看(looking at it),而不是透过镜片看(looking through it)。[29]经常听人说,淫秽文学的审查几乎只针对特定词汇,书籍遭禁不是因为倾向问题而是因为用词问题。一个人可以自由地向公众散布效力最强的催欲剂,只要他有本事避免使用禁词(哪个称职作家没这本事呢?)。[30]文风贩子的标准与文学审查的标准,虽出于不同理由,但其离谱程度和方式,却毫无二致。如果说大众是盲于文学(unliterary),文风贩子则是反文学(antiliterary)。他在盲于文学者(他们上学时吃尽他的苦头)之心中,埋下对“文风”(style)一词的恨恶,也埋下对每本据说写得很好的书的极度不信任。假如“文风”一词意味着文风贩子所珍视的东西,那么,这一恨恶及不信任倒很恰当。
【§17—21.盲于文学者喜爱三类事件】
我之前说过,盲于音乐者(the unmusical)挑出主旋律(top tune),拿它来哼唱、吹口哨,并让自己进入情绪化的、想象的白日梦。他们最喜欢的,自然是那些最容易让他们派上这些用场的曲调。与此相类,盲于文学者(the unliterary)挑出事件(event)——“发生之事”(what happened)。他们最喜欢的那类事件,与他们拿它所派用场,协调一致。我们可分出三大类。
【§18.第一类:刺激】他们喜欢“刺激的”(exciting)事件——危险迫在眉睫,逃脱命悬一线。他们的快感在于(替代性的\[vicarious\])[31]焦虑的不断积聚和释放。赌徒之存在就表明,即便是实际的焦虑,也会令许多人产生快感,或至少是快感整体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螺旋滑梯之类的游戏广泛流行就表明,若只有恐惧感而不用真正担心发生危险,这种恐惧感是令人愉快的。胆更大的(hardier spirits)为了获得快感,寻求真正的危险和真正的恐惧。一位登山爱好者曾对我说:“登山毫无意思,除非有那么一刻,你发誓说,‘要是从这儿掉下去我还会活着,我就永远不再登山’。”盲于文学者渴盼刺激,并无神秘可言。我们都有这种渴盼。我们都喜欢观看难解难分的比赛。
【§19.第二类:好奇】第二,他们喜欢自己的好奇心(inquisitiveness)得到调动、保持、加剧,最后得到满足。因而,迷雾重重的故事广受欢迎。这种快感很是普遍,无须解释。哲学家、科学家、学者之快乐,很大一部分就是这个。流言蜚语之乐,也在于此。
【§20.第三类:替代满足】第三,他们喜欢的故事,能令自己——通过人物替代性地(vicariously)——分享到快感或幸福。这有很多种情况。有可能是爱情故事,这些故事要么肉感而又淫秽(sensual and pornographic),要么感伤而又充满启迪(sentimental and edifying)。有可能是发迹故事。这些故事可能关乎上流生活,或仅仅关乎豪奢生活。我们最好不要假定,从这类故事所得的替代快乐(vicarious delights),一定是真实快乐的替代品(substitutes)。并非只有相貌平平、无人垂青的女性才读爱情故事;读发迹故事的人,也不全是失败者。
【§21.分类只是抽象】我如此分类,是为求明了。实际上,绝大多数书籍只是大致属于某类,而非全然属于某类。充满刺激或迷雾重重的故事,通常都会加点“爱情佐料”(love interest),往往还是胡乱添加。写爱情故事、田园牧歌(idyll)或上流生活,不得不加点悬念和焦虑,不管这些东西多么微不足道。
【§22.盲于文学者之盲,非因他们之所有,乃因他们之所无】
我们要清楚,盲于文学者之盲于文学,非因他们以这些方式乐享(enjoy)故事,而乃因他们不会以其他方式乐享。并非他们之所有(what they have),而是他们之所无(what they lack),使他们自绝于充分的文学体验。这些是他们该有的,可有些别的他们则不该没有。因为这些乐享(enjoyment),好读者读好书时也有。当独眼巨人摸索到奥德修斯藏身的那只公羊时,[32]当我们不知道淮德拉(和希波吕托斯)得知忒修斯突然回家后作何反应,[33]当我们不知道班纳特家族蒙羞会给达西对伊丽莎白的爱情带来什么影响,[34]我们会焦急地屏息以待。读到《罪人忏悔录》[35]之第一部,或读到梯尔尼将军[36]的行为变化时,我们的好奇心给大大激发起来。我们想知道《远大前程》[37]中皮普的幕后恩人是谁。斯宾塞对妖人布西兰的庄园[38]的描写中,每一节诗都让我们胃口大吊。至于对假想幸福的替代性乐享(vicarious enjoyment of imagined happiness),田园式作品之存在就确保它在文学中受人尊敬的地位。在别的作品中也一样,虽然我们不要求每个故事都有一个幸福结局,然而当作品出现这一结局,恰如其分且处理得体,我们也一定会乐享书中人物之幸福。我们甚至还准备替代性地乐享(vicariously enjoy),完全不可能实现之心愿得到实现,比如《冬天的故事》中雕像那幕;因为,但愿一个死者,生前遭受我们残酷且又不公之待遇,死而复生,原谅我们并“一切如旧”——还有什么心愿如此之不可能?[39]只在阅读中寻求替代性幸福的那些人,盲于文学(unliterary);然而,那些声称它不配成为好的阅读之有机部分的人,则错了。
* * *
[1] 【译按】盲于音乐之听众只要曲调,盲于文学之读者只要事件。后者有五个特征:1.看热闹;2.无语感;3.不看好书;4.不见文字;5.快速高效。正因为只要事件,只关心接下来发生了什么,所以他们不喜欢好文学而喜欢滥文学。他们所喜欢事件,略可分为三类:1.刺激;2.能满足好奇;3.能提供替代满足。这些只要事件的读者,盲于文学;而那些竭力维护英语纯洁性的“文风贩子”,则反文学。
[2] 《荷马史诗•伊利亚特》(罗念生、王焕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打头就说:“女神啊,请歌唱佩琉斯之子阿基琉斯的致命的忿怒,那一怒给阿开奥斯人带来无数的苦难,把战士的许多健壮英魂送往冥府,使他们的尸体成为野狗和各种飞禽的肉食。”(卷一第1—5行)
[3] 语出美国诗人麦克利什(archibald macleish, 1892—1982)的名诗《诗艺》(ars poetica),该诗写于1925年,被视为现代主义诗歌之美学纲领。全诗如下:“a poem should be palpable and mute /as a globed fruit,// dumb / as old medallions to the thumb, // silent as the sleeveworn stone / of casement ledges where the moss has grown — //a poem should be wordless / as the flight of birds. // a poem should be motionless in time / as the moon climbs, // leaving, as the moon releases / twig by twig the nightentangled trees, // leaving, as the moon behind the winter leaves, /memory by memory the mind — //a poem should be motionless in time / as the moon climbs.// a poem should be equal to / not true. // for all the history of grief / an empty doorway and a maple leaf. // for love / the leaning grasses and two lights above the sea — // a poem should not mean / but be.”一不知名网友译文(http://www.jintian.net/today/html/93/t-2393.html):“一首诗应哑然可触 / 像一种圆润的果物,/ 笨拙 / 像老硬币与大拇指,/ 沉默如长了青苔的窗沿上 / 一块衣袖磨秃的石头—— / 一首诗应无语 / 像鸟飞。// 一首诗应静止在时间里 / 像月亮徐徐升起,/ 离别, 像月亮放出 / 一枝枝缠在夜里的树木,/ 离别, 像冬叶深处的月光,/ 一段段心中的记忆—— / 一首诗应静止在时间里 / 像月亮徐徐升起。// 一首诗应等于:/ 不是。/ 对全部的历史悲伤 / 一个敞开的门口,一片枫叶。/ 对爱 / 一片低草,海上两处灯火—— / 一首诗应无它意 / 只是自己。”
[4] 胡话诗(nonsense poetry,亦作nonsense verse),也就是所谓“没意思的诗”或者“无意思的诗”。英语诗歌之一体,与欧洲中世纪歌谣有亲缘关系。17世纪曾流行一时,但不被文学史家看重。19世纪胡话诗达到发展的顶峰,代表诗人是爱德华•李尔(edward lear)和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
[5] boojum一词,出自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的《追猎蜗鲨》(the hunting of the snark)。《追猎蜗鲨》是胡话诗的经典之作,其中包含一个十人团队出海追猎蜗鲨的荒诞故事,于1876年出版。snark是一个虚构的动物物种,是个混成词,它可以是snake+shark(蛇鲨),snail+shark(蜗鲨),snarl+bark(吼吠)等等。boojum则是snark的一个变种。
[6] 格特鲁德•斯泰因(gertrude stein,1874—1946),美国先锋派作家、怪人和自封的天才。她在巴黎的家,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是主要艺术家和作家的沙龙。在沙龙中,她的文艺评论受到人们的尊重。她随便讲的话可以使人成名,也可以使人名誉扫地。(参《不列颠百科全书》第16卷195页)
[7] 概论之失,钱锺书《中国诗与中国画》里的这段话,是个绝佳提醒:我们常听说中国古代文评里有对立的两派,一派要“载道”,一派要“言志”。事实上,在中国旧传统里,“文以载道”和“诗以言志”主要是规定个别文体的职能,并非概括“文学”的界说。“文”常指散文或“古文”而言,以区别于“诗”“词”。这两句话看来针锋相对,实则水米无干,好比说“他去北京”、“她回上海”,或者羽翼相辅,好比说“早点是稀饭”、“午餐是面”。因此,同一个作家可以“文载道”,以“诗言志”,以“诗余”的词来“言”诗里说不出口的“志”。这些文体仿佛台阶或梯级,是平行而不平等的, “文”的等级最高。西方文艺理论常识输入以后,我们很容易把“文”一律理解为广义上的“文学”,把“诗”认为是文学创作精华同义词。于是那两句老话仿佛 “顿顿都喝稀饭”和 “一日三餐全吃面”,或“两口都上北京”和“双双同去上海”,变成相互排除的命题了。传统文评里有它的矛盾,但是这两句话不能算是矛盾的口号。对传统不够理解,就发生了这个矛盾的错觉。(《钱锺书论学文集》,花城出版社,1990,第4页)
[8] 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董国良译,商务印书馆,1988)中指出,民主社会的知识人对“一般观念”(general ideas)具有一种亘古未有的激情:“我每天一早起来,总是听到人们又发现了我以前闻所未闻的某个一般的、永久的规律。即使是一个平庸的小作家,他也跃跃欲试,企图发明一些可以治理大国的经纶;他要是不在一篇文章中把全人类都写进去,他是决不会心满意足的。”(《论美国的民主》下卷第530页)对一般观念的热爱,形成了这样一种思维习惯:“找出所有事物的共同准则、把大量的事物总括在同一的形式之下、只用一个原因来解释无数事实。”(同上,第531页)这种概论热情,泛滥到艺术理论或文学理论领域,就是无顾各艺术门类之不同,用一个大写的艺术(art)或(中国学者爱用的)“文艺”一词,概括小写的复数的arts。现代以来形形色色的美学理论体系,都有此病。
[9] 莫普萨,《冬天的故事》中的牧羊女。语出自第四幕第四场:“我顶喜欢刻印出来的民歌了,因为那样的民歌肯定是真的。”(《莎士比亚全集》第7卷,译林出版社,1998,第266页)
[10] 钱锺书《释文盲》一文说,不识字者固然为文盲,但文学界也有文盲:“价值盲的一种象征是欠缺美感;对于文艺作品,全无欣赏能力。这种病症,我们依照色盲的例子,无妨唤作文盲。……说来也奇,偏是把文学当作职业的人,文盲的程度似乎愈加厉害。好多文学研究者,对于诗文的美丑高低,竟毫无欣赏和鉴别。……看文学书而不懂鉴赏,恰等于帝皇时代,看守后宫,成日价在女人堆里厮混的偏偏是个太监,虽有机会,却无能力!”(文见钱锺书《写在人生边上》)拙译依钱先生此典,将unliterary译为“盲于文学”。
[11] 原文意为“机械化与国有化的关系”,一经汉译,就会失去原文字句音律之丑。故保留原文。
[12] h. g. wells,1866—1946),英国小说家、记者、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以科幻小说《时间机器》、《星际战争》和喜剧小说《托诺邦盖》、《波里先生的历史》闻名。(参《不列颠百科全书》第18卷168页)
[13] 在这个所谓的“读图时代”或“图像学转向”的时代,此种情形变其本而加厉,甚至还披上了“时代潮流”的外衣。
[14] 朱光潜先生在《我与文学及其他》一书中,曾有一个很形象的比方说,一流小说里的故事,其实只是花架。看小说只看故事的人,其实相当于只看花架不看花:“第一流小说家不尽是会讲故事的人,第一流小说中的故事大半只像枯树搭成的花架,用处只在撑扶住一园锦绣灿烂生气蓬勃的葛藤花卉。这些故事以外的东西就是小说中的诗。读小说只见到故事而没有见到它的诗,就像看到花架而忘记架上的花。要养成纯正的文学趣味,我们最好从读诗入手。能欣赏诗,自然能欣赏小说戏剧及其他种类文学。”(《朱光潜全集》新编增订本卷六,中华书局,2012,第23页)
[15] 参第三章第18段译者脚注。
[16] 弥尔顿《欢乐颂》(l-allegro,或译《欢乐的人》)第96行。参见殷宝书译《弥尔顿诗选》,第5页。
[17] 《红楼梦》第四十八回,香菱跟黛玉学诗一段,可证路易斯所说之理:香菱笑道,“据我看来.诗的好处,有口说不出来的意思,想去却是逼真的;有似乎无理的,想去竟是有理有情的。”黛玉笑道:“这话有了些意思,但不知你从何处见得?”香菱笑道,“我看他《塞上》一首,内有一联云:‘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想来烟如何直?日自是圆的。这‘直’字似无理,‘圆’字似太俗。合上书一想,倒像是见了这景的。若说再找两个字换这两个,竟再找不出两个字来。再还有‘日落江湖白,潮来天地青’,这‘白’ ‘青’两个字也似无理,想来必得这两个字才形容得尽。念在嘴里倒像有几千斤重的一个橄榄似的。还有‘渡头馀落日,墟里上孤烟。’这‘馀’字和‘上’字,难为他怎么想来!我们那年上京来那日下晚便挽住船,岸上又没有人,只有几棵树,远远的几家人家作晚饭,那个烟竟是碧青,连云直上,谁知我昨日晚上看了这两句,倒像我又到了那个地方去了。”
[18] 路易斯所谓“物体清楚可见,证明了我们借以观看的镜片(lens)之好”,王国维《人间词话》谈“隔”与“不隔”,可资为证:问“隔”与“不隔”之别,曰:陶谢之诗不隔,延年则稍隔矣。东坡之诗不隔,山谷则稍隔矣。“池塘生春草”,“空梁落燕泥”等二句,妙处唯在不隔。词亦如是。即以一人一词论,如欧阳公《少年游》咏春草上半阕云:“阑干十二独凭春,晴碧远连云。千里万里,二月三月,行色苦愁人。”语语都在目前,便是不隔。至云“谢家池上,江淹浦畔”,则隔矣。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写情如此,方为不隔。“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写景如此,方为不隔。
[19] 《盖伊•曼纳令》(guy mannering, 又名《占星人》,1815)是司各特(sir walter scott,1771—1832)的历史小说。司各特乃苏格兰小说家、诗人、历史学家、传记作者,常被认为是历史小说的首创者和最伟大的实践者。(参《不列颠百科全书》第15卷148页)
[20] 【原注】第三章最后。
[21] inner ear,直译为“内心之耳”,参照美学史上著名的“内在感官”(inner sense)说,意译为“内在听觉”。18世纪英国学者夏夫兹博里(the earle of shaftesbury,1671—1713)最早提出审美的“内在感官”、“内在眼睛”,即后来的所谓“第六感官”说。他在《论特征》中说:“我们一睁开眼睛去看一个形象或一张开耳朵去听声音,我们就马上见出美,认出秀雅与和谐。我们一看到一些行为,觉察到一些情感,我们的内在眼睛也就马上辨认出美好的,形状完善的和可欣羡的。”(朱光潜译,见《西方美学家论美和美感》,商务印书馆,1980,第95页)夏氏之门生哈奇生(f. hutcheson, 1694—1747)发展了这一学说,将这一学说系统化。他认为外在感官只能接受简单观念,得到较弱的快感;内在感官却可以“美、整齐、和谐的东西所产生的复杂观念”,得到“远较强大的快感”:“就音乐来说,一个优美的乐曲所产生的快感远超过任何一个单音所产生的快感,尽管那个单音也很和婉、完满和洋溢。”(朱光潜译,上书第99页)
[22] 劳伦斯(d. h. lawrence,1885—1930),20世纪英国最重要也最有争议的小说家之一。主要小说有《儿子和情人》(1913),《恋爱中的女人》(1920)和《查泰莱夫人的情人》(1928)。后者曾被认为有伤风化而在一些国家遭禁。(参《不列颠百科全书》第9卷505页)劳伦斯笔下的自然景观,常常写得栩栩如生,具有灵性,与人的心灵感受息息相通。如《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中所描写的林地场景:“一阵阵阳光忽明忽暗,奇异地明亮,照亮树林边上榛树下面的燕子草,它们像金叶似的闪着黄光。树林一片寂静,越来越静,但却不时射来一阵阵阳光。早生的银莲花已经开放,开得满地都是,一眼望不到边,树林里一片洁白。”(赵苏苏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第103页)
[23] 罗斯金(john ruskin,1819—1900),英国著名作家、学者,维多利亚时代英国最伟大的艺术评论家,在英国享有“美的使者”之称达四十年之久。主要著作有《现代画家》(五卷)、《芝麻与百合》、《建筑的七盏明灯》等。(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中译本《现代画家》)罗斯金笔下的山谷,见其《金河王》(the king of the golden river)一书:在很久很久以前,斯德里亚有一座与世隔绝的山。山中有一条大峡谷,那里的土地非常肥沃,四周山岭环绕,山顶常年积雪,并有瀑布从山间流过,派生出许多湍急的小溪。其中,有一条从东向西的瀑布,流过悬崖峭壁,顺势而下。因为那悬崖很高,太阳出来的时候,凡是太阳照得到的地方,闪烁出耀眼的光芒,如流金一般,而低处则黯淡无光,所以附近的人都称这条河为金河。(程湘梅译,中国青年出版社,2013,第1—2页)此时,正是夕阳西下的时候,山上的岩石呈现出万紫千红的颜色,天空中的晚霞如火焰一般艳丽,在高山上、岩石周围漫天飞舞,而那金河从山上直流而下,流过悬崖和峭壁,如流动的金子,比以往更加鲜艳夺目。在水花飞溅的河流上,形成了一道美丽的彩虹,随着河水延伸,颜色越来越淡。(同上,第23—24页)薄雾带着水汽在山谷中环绕,一望无际的远山在薄雾后徘徊,低处的峭壁躲在淡淡的阴影里,在雾中几乎辨认不出来,只有山顶,在阳光的照耀下,方显出它的本来面目。阳光沿着棱角分明的悬崖,穿过青翠欲滴的苍柏,放射出万丈光芒。远远望去,那高处的怪石,宛如被风雨蚕食的城堡,外表参差不齐,形状各异;偶尔在某处,有残雪未化,在阳光的照耀下如闪电一般耀眼。山上终年不化的积雪在蓝天的映衬下,比天上的云更加洁白、纯净。周围一片沉寂,沉寂如在梦乡。(同上第36页)
[24] 马罗礼(sir thomas malory,创作时期约1470)。英国作家,身份不明,因《亚瑟王之死》一书而闻名。此书是英国第一部叙述亚瑟王成败兴衰及其圆桌骑士们的伙伴关系的散文作品。(参《不列颠百科全书》第10卷409页)
[25] 【原注】caxton版十七章14行(vinaver版1014行)【译注】马罗礼《亚瑟王之死》,黄素封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第878页。
[26] 亚里士多德有“自然憎恶真空”(nature abhors a vacuum)之说。文中当用此典。
[27] 汉语界所谓维护“汉语纯洁性”之运动,与之相当。
[28] 德莱顿(john dryden,1631—1700),英国诗人、剧作家和文学评论家。17世纪后期英国最伟大的诗人,写过30部悲、喜剧和歌剧,对诗歌、戏剧作过富有才智的评论,对英国文学做出宝贵而持久的贡献。在文学上的成就为当时之冠,文学史家将其所处的时代称为“德莱顿时代”。(参《不列颠百科全书》第5卷416页
[29] 路易斯在《工具房里的一则默想》(meditation in a toolshed)一文中,曾区分了盯着看(looking at)与顺着看(looking along)。文见《被告席上的上帝》(god in the dock),拙译该书将于2015年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佛家亦有“见月忘指”之说。见指不见月,即路易斯所说的这种情形。
[30] 英国曾有法律规定,认定一部书是否淫秽,就是看是否出现four-letters words。所谓four-letters words,是指由四个英语字母构成的几个庸俗下流的词,都与性或粪便有关,是一般忌讳不说的短词,如cunt, fart, homo。路易斯认为,这一法律极为愚蠢。原因就在于,名副其实的作家都有本事躲开这些词。他在《正经与语文》(prudery and philology)一文中也说:“现有法律以及(难于出口的)现有趣味,并不能真正阻止任何名副其实的作家,去说他想说的话。假如我说当代人对文字媒介如此生疏,以至于无论写什么主题,都不能逃脱法律,那么,我是在侮辱他们,说他们低能。”(见拙译《切今之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第153—154页)
[31] vicarious,心理学术语,一般汉译为“替代性的”。由《心理学大词典》(林崇德等编,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词条“替代性宣泄”(vicarious catharsis),可略见vicarious词意之一斑:一译“替代性疏泄”。宣泄的一种。通过观看他人的攻击行为,以释放或发泄自己的攻击驱力和被压抑的情绪过程。如无辜受挫、情绪压抑的人观看武打片或激烈的体育比赛,可减弱其攻击倾向和愤怒情绪。该过程同亲身实施的攻击行为一样,可助人求得紧张解除和安宁感,且不会造成不良后果。(见1234页)
[32] 见《荷马史诗•奥德赛》第九卷第444行。
[33] 忒修斯,雅典国王,希腊神话中声名仅次于赫拉克勒斯的英雄。忒修斯的续弦淮德拉,恋上了与她同年的前妻之子希波吕托斯。求爱遭拒,因羞恨而自缢。留下遗书说:“希波吕托斯要侮辱我。这是逃避他的唯一方法。与其不忠于丈夫,不如一死。”当时,忒修斯不在雅典。(参\[德\]斯威布《古希腊神话故事》,楚图南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第214—215页)
[34] 指简•奥斯汀(jane austen,1775—1817)小说《傲慢与偏见》(pride and prejudice,1796)。
[35] 《罪人忏悔录》(the confessions of a justified sinner),詹姆斯•霍格(james hogg,1770—1835)的小说,译言网古登堡计划译出该书,纸质文本似未出版。
[36] 简•奥斯汀小说《诺桑觉寺》(northanger abbey,1798)中的人物。
[37] 《远大前程》(great expectations,又译《孤星血泪》),狄更斯晚年之教育小说。
[38] house of busirane,斯宾塞(edmund spenser, 1552—1599)的六卷本长诗《仙后》卷三中的一段重要情节。台湾地区学界译为“补色宫”,大陆汉语界译为“布西兰的庄园”。因《仙后》暂无中译本,又为求文意通畅,姑且译为“妖人布西兰的庄园”。
[39] 莎士比亚传奇剧《冬天的故事》第五幕第三场,也即整出戏最后一场之情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