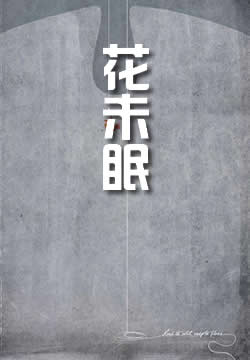on misreading by the literary
【§1—5.敏于文学者特有之毛病】
【§1.敏于文学者亦有毛病】现在,我们必须返回上一章推迟讨论的那一点。我们不得不考虑阅读中的一个毛病(fault),这毛病正好打破了我们对敏于文学与盲于文学之分际。前者之中一些人,犯有此病;后者之中一些人,则无有此病。
【§2.两种读者均混同生活与艺术】质言之,它牵涉到混同生活与艺术,甚至难以容忍艺术之存在。其最粗鲁的表现形式,在一则古老故事中传为笑谈:一位莽夫在剧场顶层楼座看戏,开枪打死了舞台上的“坏蛋”。[2]我们在最低级的读者身上,也能发现这个毛病,他们喜欢耸人听闻的叙事,然而,除非它们作为“新闻”提供给他,否则他们就不会接受。在高一级的读者身上,这个毛病表现为这样一种信念,相信所有好书之所以好,主要是因为它们给我们知识,教给我们关于“生活”的种种“真理”。剧作家和小说家受到赞誉,仿佛他们所做之事,本质上与神学家和哲学家该做之事一样;忽视的则是,其作品作为创作和构思产物所具有的那些品质。他们被尊为教师,然而作为艺术家,却未得到充分欣赏。概言之,德昆西的“力的文学”,被当作其“知的文学”的一个子类。[3]
【§3—4.少不更事之时,我们藉小说获取知识】首先,我们可以排除一种把小说当成知识来源的做法。尽管严格说来,这一做法是盲于文学,但在一定年龄段则情有可原,而且往往限于一时。12岁至20岁间,我们几乎都会从小说中获取关于我们身处其中的世界的大量信息,包括大量错误信息:关于各国饮食、服饰、习俗和气候,关于各行各业之工作,关于旅行方式、礼仪、法律和政治机器。我们汲取的不是人生哲学,而是所谓的“普通知识”(general knowledge)[4]。在特定情况下,即便对于成年读者,一部小说也能起到这个作用。苛政之国的居民,藉助阅读我们的侦探故事,或许能逐渐明白我们的原则:一个人在被证实有罪之前是清白的(在此意义上,这类故事是真正文明的有力证明)。[5]但一般来说,等我们长大了一点,就不再如此使用小说。往常需用小说加以满足的好奇心,要么已得满足,要么不复存在;如果好奇心尚还存活,则需要从更可靠的来源获取信息。与小时候相比,我们更少愿意拿起一部新小说,这就是其原因之一。
排除这一特例之后,我们现在可以回到真正的主题了。
【§5.许多盲于文学者不会犯此错误】显而易见,一些盲于文学者误以为艺术是现实生活之写照(account)。恰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些只为自我型白日梦而从事阅读的读者,如此做无可避免。他们情愿被骗;他们想要感受到,尽管这些美好事物他没碰上,但是他可以碰上(“他可能会眷顾我,恰如故事中公爵眷顾工厂女孩一样”)。同样显见的是,很大一部分盲于文学者,并未处于此种状态——他们比其他任何人都远离此危险。不信拿你家园丁或食品杂货商做个实验。你不能拿书去试,因为他很少读。不过,一部影片会同样奏效。假如你向他抱怨,其大团圆结局全无可能,他极有可能回答说:“嗨,我猜他们加此结局,只是为了好收场。”假如你抱怨,在男人冒险故事里强塞些无趣而又拙劣的“爱情佐料”,他会说:“你知道的,他们通常不得不加那么一点。女人喜欢。”他深知,影片是艺术(art),并非知识(knowledge)。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其“盲于文学”(unliterariness),使他并无混淆二者之虞。除了是短短一时且不大重要的娱乐之外,他并未期望影片还是别的什么。他从不梦想,任何艺术可以在娱乐之外,给他更多。他去看画,不是为了学习,而是为了放松。说所看之画,会修正他关于现实世界的一些观点,这在他看来简直可笑。你是否会把他当作傻瓜?不谈艺术了,跟他谈生活——跟他嚼舌,跟他讨价还价——你就会发现,他之精明,他之现实感(realistic),不亚于你恨不得拥有的。
【§6—9.大而无当的悲剧哲学】
【§6.流行的悲剧哲学】相反,在敏于文学者中间,我们发现这一错误,其表现形式微妙而又隐晦。我的学生常跟我讨论大写的悲剧(tragedy),却很少主动跟我讨论一部部剧作(tragedies)。[6]我时常发现他们有个信念,相信悲剧之价值、悲剧之所以值得观赏或阅读,主要是因为它传达了某种所谓的悲剧的“人生观”或“生命感”或“人生哲学”。虽然这一内容之表述形形色色,但是,在其流布最广的版本中,看上去包含两个命题:(1)巨大悲苦(miseries),源于悲剧主人公之性格缺陷;[7](2)这些悲苦,推至极致,向我们展示了人类以至宇宙的某种壮丽。尽管苦痛巨大,但它至少并不卑下(sordid),虚无(meaningless)或一味阴郁(merely depressing)。[8]
【§7.生活中并无悲剧式庄严】无人否认,现实生活中也会出现,有如此起因又有如此结局之悲苦。然而假如把悲剧当作这意义上的人生评点(a comment on life),即我们旨在由悲剧得出结论说,“这就是人类悲苦典型的、通常的或最终的表现形式”,那么,悲剧就成了痴人说梦(wishful moonshine)。性格缺陷固然导致苦痛(suffering);可是,炸弹及刺刀,癌症及小儿麻痹,独裁者及飙车族,货币贬值及职场动荡,还有毫无意义的偶发事件,则会导致更多苦痛。苦难(tribulation)随时可能降至性格完整之人,顺应颇良之人及审慎之人,恰如其随时降至其他任何人。真正的悲苦,并非在一阵鼓声中落下大幕,以“心中宁静,一切的愁云消散”[9]而告终。将死之人,很少做豪壮的临终演讲。眼睁睁看他死去,我想,我们之举止很少像悲剧死亡场景中的次要人物。因为,很不幸,戏还没完。我们不能“悉数散场”(exeunt omnes)。真正的故事并未结束:接下来要给治丧者打电话,要付账单,办理死亡证明,找到遗嘱并作公证,还要回复唁函。其间并无庄严(grandeur),亦无结局(finality)。真正的悲伤既不结束于轰轰烈烈,亦非结束于凄凄切切。有时候,经历了但丁那样的精神旅程之后,落至谷底,然后一阶一阶,攀爬所受痛苦之山,最后可能升入平静——然而这一平静之严酷,并不亚于悲伤本身。有时候,悲伤保持终生,像个心灵泥潭,扩散,弥漫,越来越伤身。有时候,它只是逐渐消歇,跟其他心境一样。这几种情况,一种庄严,可惜不是悲剧式庄严;另两种情况——丑陋、缓慢、多愁善感(bathetic),毫不起眼——对剧作家毫无用处。悲剧作家,不敢呈现苦痛之全貌,它通常是苦难与渺小之不雅混合(uncouth mixture of agony with littleness),不敢呈现悲哀之全部有失尊严和无趣之处(除了怜悯)。那样会毁了他的戏。那样只会导致沉闷和压抑。他从现实中撷取的,只是他的艺术所需要的;[10]艺术所需要的,就是不同寻常的(exceptional)。相反,带着悲剧式庄严的观念,接近一个遭受真正不幸的人,曲说他正披着“王者华服”[11],这样做不仅愚不可及,而且令人作呕。
【§8.悲剧人生观骗人】我们喜爱没有悲伤的世界,退而求其次,我们应该喜爱其中悲伤总是既意味深长(significant)又崇高(sublime)[12]的世界。不过,倘若容许“悲剧人生观”(tragic view of life)令我们相信,自己正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我们将会受骗。我们的双眼是更好的老师。大千世界之中,还有什么比一个大男人涕泗横流、哭得不像样子,更难看、更有失尊严么?其背后之原因也可爱不了多少。那里既无王者,也无华服。
【§9.看似直面人生的悲剧哲学,实是闭眼不看】在我看来无可否认,被视为人生哲学的悲剧,是所有“愿望的达成”(wish-fulfilments)[13]中最顽固、伪装得最好的一种。正是因为悲剧中的假象看起来是如此写实。他们声称,悲剧直面最糟境况。他们得出结论:尽管境况最糟,仍保留着某种崇高和深意。这一结论的可信程度,恰如一个目击者的违心之词。但是声称直面最糟境况——反正就是最常见的那种“最糟”——在我看来完全是错的。
【§10—14.悲剧哲学与悲剧无关】
【§10.悲剧作家首先考虑的是艺术,而非哲学】这一声称欺骗某些读者,并非悲剧作家之错,因为悲剧作家从未如此声称,是批评家如此声称。悲剧作家为他们所从事的艺术,选取他们的主题故事(经常基于神话及不可能之事\[impossible\])。根据悲剧之定义,这类故事几乎都是非典型(atypical)、惊人的(striking),而且以其他不同方式适应此目的。选择具有崇高又令人满意之结局(finale)的故事,并不是因为这类结局是人类悲苦之典型,而是因为这是好戏之必需。
【§11.悲剧与喜剧之别不在哲学,而在文体】也许是出于此悲剧观,许多年轻人抽绎出这一信念,即悲剧本质上比喜剧更“忠于生活”。在我看来,这全无根据。每一戏剧体裁从现实生活中,选择它所需要的那类事件。素材在我们身边比比皆是,驳杂参差。造就两种戏剧之分的,并非哲学,而是选材(selection)、剪裁(isolation)及文章(patterning)。这两类产物之相互对立,不会超过同一花园中采撷的两束花。只有当我们(并非剧作家)把它们变成“这就是人类生活样貌”之类命题时,才有对立。
【§12.闹剧如田园牧歌一样不写实】蹊跷的是,那些认为喜剧没有悲剧那么真实的人,却经常认为闹剧(broad farce)是写实的(realistic)。我经常碰见这一观点,说乔叟写完《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再写市井故事(faibliaux),是向写实迈进了一步。我想,这起于未能区分描述之写实与内容之写实。乔叟的闹剧,富于描述之写实,而非内容之写实。虽然克瑞西达(criseyde)与阿丽生(alisoun)这两个女人,同样合乎情理(equally probable),但《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中的事,却比《磨坊主的故事》中的事合乎情理得多。[14]闹剧世界之理想化(ideal),几乎不亚于田园牧歌世界。它是笑话的天堂,天大巧合也能为人接受,所有一切联合起来引发笑声。现实生活很少能做到像精心创作的闹剧那样滑稽,就算做到也持续不了几分钟。这就是为什么人们遇到现实情景的喜剧性时,会强调地说“这差不多像出戏”。
【§13.悲剧、喜剧和闹剧,都是制作】这三种艺术形式,各有各的剪裁。[15]悲剧略去真正的不幸中的笨拙而又显得毫无意义的打击,略去真实伤悲中有失尊严的乏味的渺小。喜剧则无视这一可能性,即恋人之婚姻并不通常导向长久之幸福,遑论完美无缺之幸福。闹剧则排除了对嘲笑对象之怜悯,在现实生活情境中,他们则应得到怜悯。三种戏剧,都不对生活作高谈阔论。它们都是构造(constructions):用真实生活材料做成的东西(things);乃人生之补充(additions to life),而非人生之评注(comments on life)。
【§14.将艺术哲学化,乃唐突艺术家】当此之时,我必须竭力避免误会。伟大艺术家——抑或说伟大的文学艺术家——不可能是思想或情感浅薄之辈。无论他所选取的故事如何不合情理(improbable)如何反常,在他手中,都会像我们所说的那样,“获得生命”(come to life)。这一生命,必定孕育于作者之智慧、知识及体验;甚至说孕育于某种我只能模模糊糊称之为他对实际生活的体味或“感受”的东西。正是这一无所不在的体味或感受,使得劣作如此令人作呕或令人窒息,使得杰作如此震撼人心。杰作使得我们临时共享某种“仁智”(passionate sanity)[16]。我们还可以期待——重要性略小一些——在其中发现许多心理真相以及深刻反省,至少是我们深刻感受到的反省。然而进入我们脑海、而且极有可能奉召从诗人那里出来的(called out of the poet)这一切,只是一部艺术作品、一出戏之“酒精”(\[spirit\]在准化学意义上使用此词)。将之体系化为一种哲学,即便是一种理性的哲学,并将实际戏剧主要视为此哲学之载体,就是唐突诗人为我们所制作的东西。
【§15—17.诗首先是“艺”其次是“道”】
【§15.诗作首先是物件】我故意用“东西”(thing)和“制作”(made)二词。关于诗歌是否“只是自己而无它意”(should not mean but be)[17]之问题,我们虽已提及但却并未回答。好的读者之所以不把某一悲剧(a tragedy)——他不会谈论“悲剧”(tragedy)之类抽象——当作真理之载体,正是因为好的读者始终意识到,它不仅“有它意”,而且还“是自己”。它不仅仅是“道”(logos,所说),而且是“艺”(poiema,所做)。[18]对于一部小说或一首叙事诗,也是如此。它们都是复杂而又精心制作之物件(objects)。[19]留神物件本来之所是(the very objects they are),乃第一步。因其可能引起的反思,或因我们从中抽绎的道德,去评价它们,就是明目张胆地“使用”,而非“接受”。[20]
【§16.切莫混同两种秩序】我用“物件”(objects)要表达的意思,并不神秘。每一部好的虚构作品之首要成就,都与真理或某种世界观根本无关。它是两种不同秩序(order)之成功调适。一方面,全部事件(情节梗概\[the mere plot\])都有其历时的因果的秩序,这是在真实生活中也会具有的。另一方面,所有场景或作品的其他条块,都必须遵照一些构思原则(principles of design)而相互联系,恰如一幅画中之色块,或一首交响乐中之乐章。我们的感受和想象,必定被引导着,“一样接着一样,有条不紊,引人入胜”[21]。明与暗、迟与速、质朴与繁富之对比(还有预兆和回响),必定类似某种均衡(balance),却从来不是某种过于完美之对称(symmetry),因而我们就会感到整部作品之造型既必当如此又令人满意(inevitable and satisfying)。然而,切莫将这第二种秩序混同于第一种。《哈姆雷特》剧首由“城墙望台”切换到宫廷场景,《埃涅阿斯纪》卷二与卷三所设置的埃涅阿斯的叙述,或《失乐园》前两卷地狱之黑暗上升至卷三中天庭之光明,就是简单例证。然而,还有另外之要求。单为它物而存在的东西,应尽可能减少。每一插曲(episode),每一解释(explanation),每一描述(description),每一对话(dialogue)——理想状态下则是每一语句(sentence)——都必须因其自身而兴味盎然。(康拉德的《诺斯特罗莫》[nostromo]的一个缺陷就是,在看到核心故事之前,我们不得不读很长篇幅的仅为核心故事而存在的伪史)。
【§17.第一事与第二事】一些人可能会将此斥之为“雕虫小技”(mere technique)。[22]我们当然必须同意,这些安排,脱离其对象,连“雕虫”(mere)都不如;它们是一些“非实体”(nonentities),恰如脱离身体之外形,是一种非实体。然而,“欣赏”雕塑,无视雕像之外形(shape),却津津乐道雕塑家之“人生观”,则无异自欺。正是藉助外形,雕像才成其为雕像。正是因为它是一座雕像,我们才进而提及雕塑家之人生观。[23]
【§18—21.好的阅读,搁置信念】
【§18.忙于抽绎哲学或伦理意涵,乃使用,非接受】当我们经历了伟大戏剧或叙事之作在我们心中激起的有序运动(the ordered movements)——当我们亦步亦趋(danced that dance)或参与仪典(enacted that ritual)或服从节文(submitted to that pattern)[24]——那么,自然而然,它会引发我们许多有趣之反省。这一活动的结果,可以说,我们“长出心灵肌肉”。我们或许应为此“肌肉”而感谢莎士比亚或但丁,但是最好不要走得更远,把我们用此“肌肉”所派的哲学或伦理用场,也加在他们头上。[25]一个原因是,这一用场不太可能高出我们自己的日常水准,尽管可能会高出那么一丁点。人们从莎士比亚那里抽绎出来的人生评注(comments on life),中才之人没有莎翁之助,照样可以获致。另一原因则是,它定会妨碍对作品本身之接受。我们或许会重温作品,但却主要为了进一步确证我们的信念,它教导我们如此如彼,而不是为了重新沉浸于它之所是(what it is)。就像一个人拨火,不是为了烧水或取暖,而是希望昨日形影重现火中。既然对铁了心的批评家而言,文本“不过是一只小山羊皮手套”[26]——既然任何事物都可以是一个象征(symbol),或一个反讽(irony),或一个复义(ambiguity)——我们就会轻易发现我们想要的。反对这样做的最大理由,与反对一切艺术之“大众使用”(popular use)一样。我们忙于拿作品派用场,以至于我们没有给它多少机会,让它作用于我们。于是,一而再再而三,我们只遇见我们自己。[27]
【§19.文学之价值在于帮我们走出固陋】然而,艺术的主要作用之一就是,让我们不再端详镜中面庞,把我们移出此类孤境(solitude)。[28]阅读“知的文学”(literature of knowledge),我们希望其结果是,思考更正确更清晰。阅读想象之作(imaginative work),我建议,我们不应关心着改换自己的观念——尽管有时候当然有此果效——而应关心着,全心投入到他人之观念,并进而投入到他们的态度、感受及体验之中。在日常心智(ordinary senses)之中,谁会藉助阅读卢克莱修或但丁,在唯物论和有神论之主张之间做一决断?然而,在文学心智(literary senses)之中,谁又不乐意从他们那里得知,成为一个唯物论者或有神论者是什么样子呢?
【§20.好的阅读,搁置信念】在好的阅读之中,不应有“信念问题”(problem of belief)。我读(read)卢克莱修和但丁,正当我(大体上)同意卢克莱修之时。我逐渐(大体上)同意但丁之后,我又读过(have read)他们。我没发觉,信念变化会给阅读体验带来多大改变;也没发觉,它会根本改变我对他们之评价。[29]真正的文学爱好者,在某种程度上,应像一个诚实考官那样,尽管不同意甚至厌恶考生之观点,但是只要其论述有力、措辞得体、论据充分,他仍打算给以最高分。[30]
【§21.学科建制鼓励误读】我在此反对的这种误读(misreading),很不幸,却因作为一门学科的“英国文学”日益重要而得到鼓励。[31]这导致其兴趣根本不在文学的一大批有天分、有才华且勤勉之人,从事文学研究。被迫不停谈论书本,除了竭力把书本变成他们可资谈论之物,他们还能做什么?因而对他们而言,文学成为一种宗教,一种哲学,一个伦理流派,一种心理治疗(psychotherapy),一种社会学——什么都可以是,但就不是艺术作品之总集。[32]轻松一些的作品——消遣之作(divertissements)——要么遭到蔑视,要么则遭曲解,仿佛它们看似轻松,其实严肃好多。然而,对一个真正的文学爱好者而言,一部精心结撰的消遣之作,相对于一些强加在大诗人头上的“人生哲学”,则要可敬得多。一个原因就是,它比后者要难得多。
【§22.文学中的释经学与讲道术】
这并不是说,那些从其心爱的小说家或诗人那里抽绎此类哲学的批评家,其作品统统毫无价值:每位批评家都会把他所相信的智慧归于他所选择的作家;而他所看到的那些明智都取决于他自己的才干。假如他是下愚之才,他就会发现并钦羡愚蠢;假如他资质平平,他所心爱的也不过是老生常谈。假如他本人是个深邃思想者,那么他大加赞赏并详细阐明的所谓作者之哲学,或许值得一读,尽管那实质上是他自己的哲学。我们或可以将他们比就一连串神学家,他们基于曲解经文,写出富于启迪且雄辩有力的布道文。这些布道文,虽然是糟糕的经文注疏(exegesis),但其本身则常常是好的讲道术(homiletics)。[33]
* * *
[1] 【译按】敏于文学之读者混同艺术与生活,在艺术中寻找人生哲学,寻找微言大义。其典型表现就是流行的悲剧哲学或悲剧理论,其中悲剧成为大写的tragedy。批评界的此类流行论调,忘记了诗作既是“道”,也是“艺”,忘记了作品首先是“作”出来的。盲于文学者的这种阅读,实际不是“接受”,而是“使用”,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如此阅读,读者走遍天涯海角,找到的还是自己。
[2] 此类笑谈,似乎不少。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1936)也举了此类例子:一个观剧者看见演曹操的戏,看到曹操的那副老奸巨猾的样子,不觉义愤填胸,提起刀走上台去把那位扮演曹操的角色杀了。一般人看戏虽不至于此,但也常不知不觉地把戏中情节看成真实的。有一个演员演一个穷发明家,发明的工作快要完成时,炉中火熄了,没有钱去买柴炭,大有功亏一篑的趋势,观众中有一个人郑重其事地捧上一块钱去给他,向他说:“拿这块钱买炭去罢!”(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第26页)
[3] 德昆西(thomas de quincey)的名文《知的文学与力的文学》(literature of knowledge and literature of power,1848)指出,纠正文学概念之含混,与其寻找更好的文学定义,不如更明晰地区分文学功能。他说,在社会有机体中,那种我们称之为文学的东西,可以分为两厢(two separate offices)。两者当然会相互交融,但却相互排斥:有两类文学,其一是“知的文学”(the literature of knowledge),其二是“力的文学”(the literature of power);前者之功用在于教导(teach),后者之功用在于打动(move):前者是船桨,后者则是舟船。前者只对推论性理解力(the mere discursive understanding)发话,后者虽然可能最终对更高的理解力或理性发话,但却总是通过快感及同情之感染。(http://www.clas.ufl.edu/users/pcraddoc/deq.htm [2013—9—2])
[4] 关于普通知识之重要,e. h. 贡布里希的《普通知识的传统》一文有专门论述,文见贡布里希《理想与偶像》(范景中译,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9)。贡布里希说,所谓“普通知识”,就是指某一社会中的文化人都知道的一些典故、隐喻或故事。比如,把paris’judgement(帕里斯的裁判)理解为“巴黎的裁判”,不知“堂吉诃德式”或“浮士德式”一词何意,缺乏的就是普通知识。普通知识只是道听途说的知识,并不真实,严肃学者必须对之保持怀疑。虽如此,普通知识却是社会之为社会的一个必要条件,因为它是一种“知识的共享”,是谈话交流中的一枚“通用硬币”。丧失了普通知识的传统,这个社会就趋于解体。20世纪,古典教育式微,则意味着普通知识的传统正在消亡。
[5] 指法律中著名的“无罪推定原则”(the presumption of innocence)。无罪推定与有罪推定相对。无罪推定是一种典型的直接推定,无须基础事实的证明,即认定当事人无罪。换言之,证明被告犯罪的责任由控诉一方承担,被告并不负有自证清白的义务。而所谓有罪推定,则首先假定当事人有罪,除非当事人自证清白。 汉语界耳熟能详的“你身犯何罪,还不从实招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均是有罪推定。
[6] tragedy与tragedies之别,很是巨大。大致说来,大写的tragedy是被抬高到宇宙哲学或生命哲学高度的悲剧,现代林林总总的以所谓“生命的悲剧意识”、“悲剧精神”或“悲剧感”为题的著作,均是这种用法。汉语学界,自五四以来,反复追问中国有无悲剧,无疑与此有关。至于单数小写的tragedy,只是表示与喜剧或闹剧相并列的一个文体。复数小写的tragedies,则是指一部部悲剧。由于汉语没有形态变化,故而,tragedy与tragedies之别,汉语很难表述。为突出区别,前者译为“大写的悲剧”,后者译为“一部部剧作”。
[7] 这是悲剧理论中著名的“过失说”,其源头是亚里士多德《诗学》第十三章中讨论悲剧人物的这段话:第一,不应写好人由顺境转入逆境,因为这只能使人厌恶,不能引起恐惧和怜悯之情;第二,不应写坏人由逆境转入顺境,因为这最违背悲剧的精神——不合悲剧的要求,既不能打动慈善之心,更不能引起怜悯或恐惧之情;第三,不应写极恶的人由顺境转入逆境,因为这种布局虽然能打动慈善之心,但不能引起怜悯或恐惧之情,因为怜悯是由一个人遭受不应遭受的厄运而引起的,恐惧是这个这样遭受厄运的人与我们相似而引起的……此外还有一种介于这两种人之间的人,这样的人不十分善良,也不十分公正,而他之所以陷于厄运,不是由于他为非作恶,而是由于他犯了错误,这种人名声显赫,生活幸福,例如俄狄浦斯、堤厄斯特斯以及出身于他们这样的家族的著名人物。(罗念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第38—39页)朱光潜《悲剧心理学》(张隆溪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第六章,对“过失说”有专门讨论。
[8] 朱光潜在《悲剧心理学》(张隆溪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中说:一个穷凶极恶的人如果在他的邪恶当中表现出超乎常人的坚毅和巨人般的力量,也可以成为悲剧人物。答丢夫之所以是喜剧人物,只因为他是一个胆小的恶棍,他的行为暴露出他的卑劣。他缺乏撒旦或者靡非斯特匪勒斯那种力量和气魄。另一方面,莎士比亚塑造的夏洛克虽然错放在一部喜剧里,却实在是一个悲剧人物,因为他的残酷和他急于报复的心情之强烈,已足以给我们留下带有崇高意味的印象。要是没有这一点悲剧的气魄,他就不过是一个阿巴贡式的守财奴了。对于悲剧来说,致命的不是邪恶,而是软弱。(第96页)“心灵的伟大”正是悲剧中关键所在,从审美观点看来,这种伟大是好人还是坏人表现出来的好象并无关大局。(第97页)
[9] 弥尔顿《斗士参孙》(朱维之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之末行。
[10] 写作是省略或剪辑的艺术。《特罗洛普自传》第1章:“把什么都写出来,我办不到,任何人也办不到。谁肯承认自己干过见不得人的事?又有谁没干过见不得人的事?”(张禹九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第1页)自传尚且如此,何况艺术创作?
[11] 弥尔顿《沉思颂》第98行。
[12] sublime通译“崇高”,亦译为“壮美”。在18世纪美学中,是与beauty(优美)相对立的一个审美范畴。
[13] wish-fulfilment一词,因弗洛伊德《梦的解析》中“梦是愿望的达成”(the dream as a wishfulfilment)一语,成为一个学术关键词。
[14] 克瑞西达(criseyde)是《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的女主人公,阿丽生(alisoun)是《磨坊主的故事》中老木匠的年轻妻子。
[15] 朱光潜在《给青年的十二封信》中说道:“斯蒂文森论文,说文章之术在知遗漏(the art of omitting),其实不独文章如是,生活也要知所遗漏。”(《朱光潜全集》新编增订本第1卷,中华书局,2012,第54页)张爱玲《烬余录》一文里的这段话,亦可参证:“现实这样东西是没有系统的,像七八个话匣子同时开唱,各唱各的,打成一片混沌。在那不可解的喧嚣中偶然也有清澄的,使人心酸眼亮的一刹那,听得出音乐的调子,但立刻又被重重黑暗拥上来,淹没了那点了解。画家。文人。作曲家将零星的、凑巧发现的和谐联系起来,造成艺术上的完整性。历史如果过于注重艺术上的完整性,便成为小说了。像威尔斯的《历史大纲》,所以不能录于正史之列,便是因为它太合理化了一点,自始至终记述的是小我与大我的斗争。”
[16] passionate sanity一词,殊难翻译,其意思是指热忱又不失明智。不得已,以“仁智”一词意译,取仁爱而又多智之意。
[17] 见本书第4章第2段。
[18] 路易斯在此言说的,乃古典艺术观。古代的“艺术”和现代的“艺术”,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据波兰著名美学史家塔塔尔凯维奇考证,艺术(art)一词源自于拉丁文ars,意为“技艺”(skill)。这个意思从古希腊一直延续到文艺复兴。故而,建筑、雕刻、裁缝、陶瓷、战略等均视为art。(参塔塔尔凯维奇:《西方六大美学观念史》,刘文潭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第13页)关于艺术观的这一古今之变,亦可参见常宁生、邢莉的《美术概念的形成》一文。文见http://www.aesculit.cn/article/show.php?itemid=854 \[2008—12—30\]。
[19] 中国古人有“作文”、“缀文”、“属文”之说,其背后的隐喻就是:文章乃是“作”出来的,像编织或制作一样,是个手艺活。如陆机《文赋》序云:“每自属文,尤见其情,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李善注曰:“属,缀也。”所谓缀,即编织之意。路易斯在《给孩子们的信》(余冲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中亦说:“对于文学作品来说,主意本身并不像‘怎么表达主意’这么重要。”(第41页)
[20] 关于艺术作品这一二重性,路易斯在《失乐园序》(preface to paradise lost,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2)中,有更精妙之论述:“每一首诗可从两个路径来考量——把诗看作是诗人不得不说的话(as what the poet has to say),以及看成一个他所制作的事物(as a thing which he makes)。从一个视点(point of view)来看,它是意见或情感之表达(an expression of opinion and emotions;);从另一个视点来看,它是语词之组织(an organization),为了在读者身上产生特定种类的有节有文的经验(patterned experience)。这一双重性(duality),换个说法就是,每一首诗都有双亲——其母亲是经验、思想等等之聚集(mass),它在诗人心里;其父亲则是诗人在公众世界所遇见的先在形式(\[preexisting form\]史诗、悲剧、小说或其他)。仅仅研究其母亲,批评家变得片面。人们很容易忘记,那个写了一首好的爱情十四行诗的人,不仅需要爱上一个女人,而且需要爱上十四行诗。”(第2—3页)他认为,研究诗歌之次第应是,先研究其父亲,后研究其母亲。现代批评,则本末倒置。
[21] 原文为:“taste after taste, upheld with kindliest change.” 语出弥尔顿《失乐园》卷五第336行。此处用朱维之先生之译文。
[22] 借扬雄“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之语,意译。
[23] 路易斯严分the first thing(第一事或首要之事)与the second thing(第二事或次要之事)。路易斯之所以严分二者,首要之事必需居首要地位,将次要之事置于首要地位,不独抛弃首要之事,而且也得不到次要之事。路易斯认为这是一项定律:无意对谈,越像对谈。把一条宠物狗当作生命中心的那个女人,到头来,失去的不只是她做人的用处和尊严,而且失去了养狗的原本乐趣。把饮酒当作头等大事的那个男人,不仅会丢掉工作,而且会丧失味觉,丧失享受醉酒之乐的全部能力。在人生的那么一两个时刻,感到宇宙的意义就集中在一位女人身上,这是件光荣事——只要其他义务或欢乐还能把你的心思从她身上移开,就是件光荣事。然而,诸事不顾,只是一心想她(这事有时行得通),后果会如何?当然,这一定律早被发现,但它还是经得住一再发现。它可以表述如下:每一次取小善舍大善、取部分之善而舍全体之善,此等牺牲的结果就是,小善或部分之善也一同丧失。……把次要之事放在首位,你无法得到它;你只能藉把首要之事置于首位,取得那次要之事。(路易斯《首要及次要之事》[first and second things]一文第6—7段,文见路易斯论文集god in the dock,拙译该文集将于2015年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24] 古代礼乐中的乐舞仪文,是路易斯颇为钟爱的比方。
[25] 美国学者诺埃尔•卡罗尔《超越美学:哲学论文集》一书第四编中,对此观点有出色发挥,虽然他可能不知道或不在意路易斯。他说:“大多数叙事性艺术品并不向观众讲授新的道德情感或新的道德原则,它们刺激了以前存在的道德情感和道德原则。”(李媛媛译,商务印书馆,2006,第477页)
[26] 莎士比亚《第十二夜》第三幕第一场中小丑的台词:“一句话对于一个聪明人就像是一副小山羊皮的手套,一下子就可以翻了过来。”(朱生豪译)
[27] 帕斯卡尔《思想录》第14段:“当一篇很自然的文章描写出一种感情或作用的时候,我们就在自己身上发现了我们所读到的那个真理,我们并不知道它本身就在那里,从而我们就感动得要去热爱那个使我们感受到它的人;因为他显示给我们的并不是他本人的所有,而只是我们自身的所有;而正是这种恩惠才使得他可爱,此外我们和他之间的那种心灵一致也必然引得我们衷心去热爱他的。”(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5,第9页)
[28] 路易斯在《英语是否前景堪忧》一文中说,文学教育之目的在于使学生走出固陋:文学研究的真正目标是,通过让学生成为“观赏者”(the spectator),使学生摆脱固陋(provincialism)。即便不能观赏全部“时代及实存”(time and existence),也须观赏大部。学生,甚至中小学生,由好的(因而各不相同的)教师带着,在过去仍然活着的地方与过去相遇,这时他就被带出了自己所属时代和阶级之褊狭,进入了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见拙译《切今之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第37—38页)
[29] 路易斯《空荡荡的宇宙》一文末尾说,我们纵然不同意作者观点,亦无妨欣赏作品,即便是理论之作:令人激动及令人满意的经验……在某些理论著作中,看起来都部分地独立于我们最终同意与否。只要我们记起,当我们从某一理论体系的低劣倡导者转向其大师(great doctors),即便是我们所反对的理论,在我们身上发生了什么,那么,这一经验就会很轻易被分离出来。当我从普通的存在主义者转向萨特先生本人,从加尔文主义转向《基督教要义》(institutio),从“超验主义”转向爱默生,从有关“文艺复兴柏拉图主义”的论著转向费奇诺,我曾有此经历。我们可以仍然不同意(我打心底不同意上述这些作者),但是现在,我们第一次看到,为什么曾经有人的确同意。我们呼吸了新鲜空气,在新的国度自由行走。这国度你可能不能居住,但是你现在知道,为什么本国人还爱它。你因而对所有理论体系另眼相看,因为你曾经深入(inside)那一国度。从这一视角看,哲学与文学作品具有一些相同品质。我并不是指那些文学艺术,哲学观点可以藉以表达或不能藉以表达的文学艺术。我是指艺术本身,由特殊的平衡和思想布局和思想归类所产生的奇特的统一效果:一种愉快,很像黑塞笔下的玻璃球(出自同名著作)能给我们的愉快,假如它真的存在的话。(见拙译《切今之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第145—147页)
[30] 苏珊•桑塔格的《反对阐释》一文,其实并不反对阐释,并非说艺术品不可说。她的问题是:“它们可以被描述或诠释,问题是怎样来描述和诠释。批评要成为一个什么样子,才会服务于艺术作品,而不是僭取其位置?”(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程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第13页)为此,她开出如下药方:首先,需要更多地关注艺术中的形式。如果对内容的过度强调引起了阐释的自大,那么对形式的更广泛、更透彻的描述将消除这种自大。其次,需要一套为形式配备的词汇——需要一套描述性词汇,而不是规范性词汇。最好的批评,而且是不落常套的批评,便是这一类把对内容的关注转化为对形式的关注的批评。(同上,第13—14页)
[31] 参本书第2章第8段及译者脚注。
[32] 关于现代学术之专业化对艺术和文化之戕害,美国文化史家雅克•巴尔赞(jacques barzun,亦译巴森、巴尊)在《我们应有的文化》一书中,有颇为痛切的论析。他指出,专业学术保护不了文化和艺术,而是破坏了文化和艺术。中信出版社2014年出版该书之中译本,译者严忠志。
[33] 朱熹解释“以意逆志”的这段文字,完全可作本章之注脚:今人观书,先自立了意后方观,尽率古人语言入做自家意思中来。如此,只是推广得自家意思,如何见得古人意思!须得退步者,不要自作意思,只虚此心将古人语言放前面,看他意思倒杀向何处去。如此玩心,方可得古人意,有长进处。且如孟子说诗,要“以意逆志,是为得之”。逆者,等待之谓也。如前途等待一人,未来时且须耐心等待,将来自有来时候。他未来,其心急切,又要进前寻求,却不是“以意逆志”,是以意捉志也。如此,只是牵率古人言语,入做自家意中来,终无进益。(《朱子语类》卷第十学四读书法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