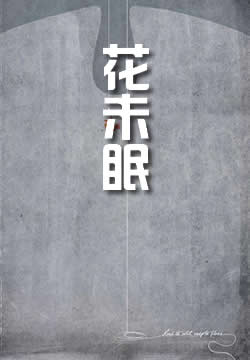survey
【§1—6.前文小结】
现在是时候,把我所竭力摆明的观点,总结如下:
【§2.“使用”缘何不如接受】1.任何艺术作品,要么可“被接受”,要么可“被使用”。当我们接受它,我们遵照艺术家所作之文章(pattern)[2],运用感官、想象及其他多种能力。当我们使用它,我们把它当作自身活动之辅助。借用一个老比方来说,前者就像有人带我们骑车旅行,他知道我们从未走过的路径;后者则像给自己的自行车装上小马达,踏上熟悉的旅程。这些旅行本身,可能或好或坏,也可能无所谓好坏。多数人对艺术之“使用”,或许内在地庸俗、堕落或病态,或许不是。二者皆有可能。“使用”之所以不如“接受”,乃是因为,假如只是使用艺术而非接受艺术的话,艺术只能给我们的生活提供方便、增添光彩、舒缓压力或提供慰藉,并未使我们的生活有所增益。
【§3.文学接受:视内容为目的】2.当该艺术是文学时,情况会变得复杂。因为“接受”表意文字(significant words),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使用”它们,即通过它们并超越它们,抵达本身无由言表的想象之物(imagined something)。“接受”与“使用”之分,呈现为另外一种样式。姑且把“想象之物”称为内容(content)。“使用者”想要使用这一内容——用作无聊时光或磨人时光之消遣,用作益智游戏(puzzle),用作白日梦之助力,甚或用作“人生哲学”之来源。“接受者”则居留于此内容。[3]对他而言,此内容至少暂时就是目的(end)。这种方式,上可比就宗教沉思,下可比就一场游戏。
【§4.文学接受,顺从文字之强制力】3.然而吊诡的是,“使用者”从不充分使用文字,而且的确只喜欢那些无法充分使用之文字。就他之目标而言,对内容之粗略而又现成之理解,足矣尽矣,因为他只因其当前需要而使用它。无论这些文字约请何种更为精确之领会,他一概无视;无论何词,只要非精准领会不可,他一概视为绊脚石。对他而言,文字只是指示(pointer)或路标(signposts)。另一方面,在对好书的好的阅读之中,尽管文字当然也会指示(point),但文字所做之事,以“指示”名之则过于粗糙。文字是一种强制力(compulsion),细致入微(detailed),加在那些愿意并且能够承受强制的心灵上。正因为此,用“魔力”(magic)或“勾魂摄魄”(evocation)形容某一文风(style),这一隐喻不仅关乎情感,而且十分贴切。正因为此,我们才被迫谈论文字之“色泽”(colour)、“滋味”(flavour)、“肌理”(texture) 、“声气”(smell)或“来处”(race)。正因为此,内容与文字之分这一无法避免的抽象,对伟大文学造成极大伤害。我们想要申明,文字非但不是内容之外衣(clothing),甚至并非内容之化身(incarnation)。这是真的。恰如我们企图分开橘子之形状与色泽。然而为了某些目标,我们必须在思想中加以分别。[4]
【§5.声韵与文学】4.因为好的文字,可以如此强制我们,如此引领我们进入人物心灵之角角落落,或者使得但丁之地狱或品达笔下诸神眼中的岛屿[5]栩栩如生、独一无二,所以好的阅读常常既关乎视觉,亦关乎听觉。因为声韵不仅仅是外加之乐,尽管它或许可能如此,而是强制力的一部分;就此而言,它也是意义(meaning)的一部分。即便是一篇好的实用散文,也是如此。读萧伯纳式前言,尽管多有浅薄、夸大之处,但我们仍心满意足于其明快、迷人、欢愉的绝对自信(cocksureness);这主要靠节奏(rhythm)传递给我们。使得吉本[6]如此振奋人心的,是其中的征服感(the sense of triumph),是在奥林匹亚式平静中安排并沉思如此之多的苦痛与庄严。这是复合句(periods)在起作用。每个复合句,就像一座宏伟的高架桥,我们以不变的速度平稳过桥,跨越或宜人或骇人之峡谷。
【§6.好的阅读与自我型白日梦】5.全然包含在坏的阅读里的东西,也可能作为一个成分进入好的阅读。兴奋(excitement)及好奇(curiosity),显然如此。还有替代性幸福(vicarious happiness);好的读者并非为了它而去阅读,但是当幸福(happiness)无可厚非地出现于小说中,他们步入其中。然而,当他们要求一个幸福结局时,他们不是出于这一理由,而是因为在他们看来,从多方面看作品本身要求幸福结局。(死亡及灾难,可以像婚礼钟声一样地“造作”,一样地失谐。)在得体读者(right reader)心里,自我型白日梦不会存活很久。不过我怀疑,自我型白日梦或许会把他交给书本,尤其是在年幼之时,或在郁郁不乐的日子。有人认为,特罗洛普(trollope)甚至简•奥斯汀(jane austen)对多数读者之吸引力在于,读者可以在想象中逃遁到另一时代,在那里他们这一阶层或他们所认同的阶层,比现在更安全更幸运。亨利•詹姆斯有时倒或有此作用。在他的一些书中,主人公所过生活,与仙女和蝴蝶一般,我们绝大多数人可望不可即;没有宗教,没有劳作,没有经济负担,没有家庭及邻里关系之要求。然而,它只能是初始之吸引力。一个人阅读詹姆斯、简•奥斯汀或特罗洛普,主要或强烈想要做自我型白日梦,一定坚持不了多久。
【§7.不必轻蔑“娱乐”】
形容两类阅读之时,我刻意避开“娱乐”(entertainment)一词。即便加个“纯”(mere)字做一限定,仍嫌含混。假如娱乐一词意指,轻松活泼之快感,那么我想,它恰是我们应当从有些文学作品中得到的东西,比如说普赖尔[7]或马提雅尔2[8]的小篇什(trifle)。假如娱乐一词意指,“抓住”通俗浪漫传奇读者的东西——悬念、兴奋等等——那么我要说,每本书都应该娱人。一本好书更应娱人,而非相反。就此而言,娱乐就像资格考试。一部小说假如连此都不能提供,那么我们就不必再深究其更高品质了。可是,“抓住”甲读者的东西,不一定能抓住乙。令聪慧读者屏息之处,愚钝读者则可能抱怨无事发生。但我希望,通常被(轻蔑地)称作“娱乐”的绝大多数东西,都能在我的分类中各得其所。
【§8—10.文学教育不可教学生从事批评】
【§8.所谓“批判阅读”,乃误导】我也避免把我所赞成的那种阅读,形容为“批判阅读”(critical reading)。这一短语,假如并非随便称呼,在我看来则是极大误导。我在前面一章里说过,我们评判任何语句甚或任何文字,只有藉助看它是否起到其应起作用。效果必须先于对效果之评判。对整部作品,也是如此。理想情况下,我们必须先接受,而后评价。不然,我们没有什么可供评价。不幸的是,这一理想情况,我们在文学职位或文学圈待得越久,就越少实现。它主要出现在年轻读者中间。初读某部伟大作品,他们被“击倒在地”。批评它?不,天哪,再读一遍吧。“这必定是一部伟大作品”这一评判,或许会姗姗来迟。可是在后来之生涯里,我们都禁不住边读边评;它已经成为一种习惯。我们于是失去内心之清静(inner silence),不再能倒空自我(emptying out of ourselves),以便为全面接受作品腾出空间。[9]假如我们阅读的当儿,知道我们有义务表达某种评判,内心清静就更是难上加难:比如我们为了写书评而阅读一本书,或为了给朋友提意见而阅读他的手稿。于是乎,铅笔在页边空白上开始工作,责难或赞赏之词在我们的心灵中渐具雏形。所有这类活动,都阻碍接受。[10]
【§9.慎言文学批评】正因为此,我颇为怀疑,文学批评作为练习,是否适合男孩和女孩。一个聪明学童对其读物之反应,最自然的表达方式,莫过于戏仿(parody)或摹仿(imitation)。好的阅读之必要条件是,“勿让自己挡道”(to get ourselves out of the way);我们强迫年轻人持续表达观点,恰是反其道而行。尤其有害的是这种教导,鼓励他们带着怀疑,接近每一部文学作品。这一教导,出于一种颇为合理的动机。处身一个满是诡辩与宣传的世界,我们想要保护下一代免遭欺骗,就要让他们警惕印刷文字往往提供给他们的虚情假意或混乱思想。不幸的是,使得他们对坏的写作无动于衷的习惯,同样可能使得他们对好的写作无动于衷。过于“明智”的乡下人,进城之时被反复告诫谨防骗子,在城里并不总是一帆风顺。实际上,拒绝颇为诚恳之善意、错过诸多真正机会,并树立了几个敌人之后,他极有可能碰上一些骗子,恭维他之“精明”,结果上当。这里亦然。没有一首诗会把其秘密透露给这样一个读者,他步入诗歌,却把诗人视为潜在的骗子,下定决心不受欺骗。假如我们打算得到什么东西,我们必须冒受骗之危险。对坏的文学之最好防范,是对好的文学的全心体验(full experience );恰如真正并深情结交诚实人,比起对任何人之习惯性的不信任,能更好防范坏蛋。[11]
【§10.让孩子从事批评,只能是迎合老师】说实在的,孩子们并未暴露出这一训练的致残后果(disabling effect),因为他们并不谴责老师摆在他们面前的所有诗歌。令逻辑及视觉想象无所适从的混杂意象,假如在莎士比亚作品中碰见,将会受到赞扬;假如在雪莱[12]作品中碰见,则会被得意洋洋地“揭露”。可这是因为,孩子们知道对他们的期待。基于颇不相干的根据,他们知道,莎士比亚应受褒赞,雪莱应受谴责。他们得到正确答案,并非他们的方法所致,而是因为他们事先知晓。有时,当他们事先不知,他们有时会给出一个发人深省的答案,会使教师冷静怀疑那个方法本身。
* * *
[1] 【译按】倘若本书前文并非虚言,那么,读者自不必轻视娱乐,因为“乐”,乃文学作品之及格线。为使学生乐享文学,文学教育切莫教学生从事批评。尤其是所谓批判阅读,乃误导学生,使学生自绝于文学接受。
[2] 路易斯所用pattern一词,殊为难译。按理,以古人所用“文”字译之,颇为传神。然而由于汉语之现代化,译为“文”字,不只晦涩难解,而且显得突兀。百无其奈,不得不随语境变化,译法有所改变。此处译为“文章”,乃取“文章”一词之古义:“青与赤谓之文,赤与白谓之章。”它处亦译为“文理”,亦取古义:“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还译为“节文”,取孟子所谓“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之义。
[3] 依郭熙《林泉高致•山水训》所谓“可行可望可游可居”之意,意译。郭熙云:“世之笃论,谓山水有可行者,有可望者,有可游者,有可居者。”
[4] 关于内容和形式是否可分的问题,门罗•比尔斯利(monroe c. beadsley)做了个很好的廓清,足与路易斯此语相参证:可以从内容中分析出来形式吗(can form be distinguished from content)?在我们可以离开其中一个谈论另一个这一点上当然是可以的。内容和形式紧密相连(connected)吗?当然如此……形式和内容可分(separable)吗?确实不行。将可分析性和可分离性混淆,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monroe c. beardsley, aesthetics: problems in the philosophy of criticism, cambridge: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1981, p. 167—168.)
[5] 【原注】fragm. 87+88 (58).
[6] 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1737—1794),英国历史学家,《罗马帝国衰亡史》之作者。
[7] 马修•普赖尔(matthew prior,1664—1721),英国诗人,外交官。(参英文维基百科)
[8] 马提雅尔(martial,40?—104?),古罗马诗人。参徐译本注。
[9] 所谓“内心清净”(inner silence),古人称为“虚静”,所谓“倒空自我”(emptying out of ourselves),古人称为“虚心”。二者于读书之重要,《朱子语类》(卷第十学四读书法上)多有论及:读书须是虚心切己。虚心,方能得圣贤意;切己,则圣贤之言不为虚说。看文字须是虚心。莫先立己意,少刻多错了。又曰:“虚心切己。虚心则见道理明;切己,自然体认得出。”圣贤言语,当虚心看,不可先自立说去撑拄,便喎斜了。不读书者,固不足论;读书者,病又如此。凡看书,须虚心看,不要先立说。看一段有下落了,然后又看一段。须如人受词讼,听其说尽,然后方可决断。看前人文字,未得其意,便容易立说,殊害事。盖既不得正理,又枉费心力。不若虚心静看,即涵养、究索之功,一举而两得之也。苏轼有诗云:“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亦可供参证。
[10] 路易斯《诗篇撷思》(曾珍珍译,台北:雅歌出版社,1995)第9章里的这段文字,似乎对我们所谓的批判性阅读更是不恭:……当人陶醉在某件事物中时,自然会对它涌出赞美,除非羞涩或怕烦扰人,才刻意保持缄默。人间真是到处充满着赞美——坠落爱河的男人赞美他们的情人,读者赞美他们最欣赏的诗人,远足的人赞美野外的风光,……其实,发出赞美愈多的人,往往是最谦虚、心智最均衡、胸襟最宽广的人;至于性喜挑剔、适应不良、不易满足的人,则只会埋怨,极少赞美。好的文评家能在众多有瑕疵的作品中,找出值得赏读的篇章;差劲的文评家不断删减可读作品的书目。一个健康又口味清醇的人,即使生长环境优裕又尝遍各样美味,粗茶淡饭仍可让他吃得津津有味;倒是消化不良,凡事过度讲究的人,什么都不对胃口。除非逆境大得让人苦不堪言,否则,赞美几乎就是心理健康的外在表现。(第79页)
[11] 萧伯纳曾说:“对说谎者的惩罚,不是没有人再相信他,而是他不再相信任何人。”路易斯这里说的道理,与此相类。
[12] 雪莱(percy byshee shelley,1792—1822),英国浪漫派大诗人,与拜伦齐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