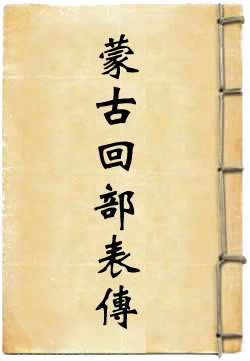丁履进
一九四六年春,校长张伯苓先生由重庆飞北平回天津。
有一天晚上,施奎龄打电话给我:“咱们老校长明天回来,不愿惊动官府,要我们校友去接他。明天上午十点,我和金城银行的韩大哥到你那里会齐去飞机场。”第二天上午十一点,我们三个人到西苑飞机场接校长。同来的有他的秘书伉乃如先生。我已经二十多年未见过这两位师长,伉先生教过我两年的课,还认识我,向校长说:“这是丁履进。”校长说:“念远(施奎龄字)给我的信里说过,他是中央社北平分社的负责人,胜利后第一个到北平的新闻记者,干得不错。”我们送校长进城,到西皮市胡同银行公会休息。
那时校长已是七十一岁高龄,长途飞行之后,精神奕奕,并无倦容。我们陪他吃过午饭,陪他到休息室,他半坐半倚地靠在床上和我们闲谈。几个小时的谈话,由校事到国事,都曾涉及,谈得高兴的时候,他那敏锐的眼神随时由墨晶眼镜的后面隐若地闪露出来。他说:“北大、清华已经复校,归还建制,我决定摆脱政治,回来办理复校的工作,继续从事教育。”谈到国事,他说过几句话,到现在我还记得:“咱们国家的前途,用望远镜看是美丽的,用显微镜看,内部有许多腐烂的问题,如何化腐朽为神奇,全靠咱们自己,天真的美国人帮不了多少忙。”那时北平军调处执行部成立不久,美国人居间调停国共的争执,国人对美国的调处寄以很大的希望。当时校长的谈话,对于美国的调处工作,言外之意,似乎并不乐观。校长急于要回天津,平津铁路局局长石志仁特别在当天的夜车上给他安排了铺位,并通知天津方面接车,我们几个人就送他上火车回天津去了。这是我和他最后一次会面,也是毕生难忘的一次谈话。
抗战时期,北大、清华、南开合成西南联大。胜利后,北大、清华很快恢复了建制。我在北平,因为职务的关系,和北大的傅斯年、陈雪屏、胡适及清华的梅贻琦时常见面,对于北大、清华复校后的情形非常熟悉,对于南开母校复校情形,虽然平津咫尺,却非常隔膜。
提到南开,就想到张伯苓,这是世人普遍的印象。张伯苓与南开是不可分的,也可以说,张伯苓就是南开,南开就是张伯苓。
张伯苓先生毕业于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毕业后,在严修(范孙)先生家教私塾,最近在台北逝世的台大医学院教授严智钟就是当时在私塾受业的诸公子之一。由严家私塾而南开中学,更发展为举世闻名,与北大、清华并驾齐驱的南开大学,都是张伯苓先生一手创成,一生心血精神灌溉溶化的硕果。北大、清华都是国家力量所经营,而南开则纯为私人创办,其难易相去不可以道里计。
昔人对道德高尚、学问渊博、志行贞固、传业迪世的大师硕儒,不论是受业门人或私淑弟子,多仿效古代谥法之义,私谥名号奉献,表示尊师重道的敬意,如汉之郭有道、宋之张横渠都称为“有道先生”“横渠先生”而不名。近代洋人对绩业卓越之士,亦常以其姓名与事业相连而称为“某某先生”,如美国共和党人塔虎脱之被称为“共和党先生”,即其一例,与我国私谥之义若合符节。我建议:凡我南开校友,应以“南开先生”之名奉献于张伯苓先生,以垂永久,而表敬意。
我是一九一五年考入南开中学的,现在台湾的田炯锦、郑通和、张平群是我同班或同年级的同学,一九一九年毕业,读过大学第一班,一九二〇年转学北平。我对“南开先生”张校长的印象和学校的故事,都以此一时期所目睹感受的为多。
一九一五年秋季始业,第一次上星期三的周会,看见一位方面平头、阔背挺胸、戴墨晶眼镜、穿长衣皮鞋、身材魁伟的先生,站在大礼堂的讲台上,声音洪亮地对全校师生谆谆训话,这就是校长张先生给我的第一印象。以后每星期三都有同样的聚会。南开是以周三的聚会,代替当时各中等学校所必有的修身课程。这样的修身课程对学生的影响最大,收效最宏。每次周会,除了校长对学生讲授为人做事、处世治学的道理之外,亦常请当代名流、专家学者到校演讲。四年期间的周会,听过上百次的演讲。现在记忆犹新的是胡适讲白话文学,胡适的老师美国哲学家杜威博士讲“思维术”(杜氏名著how we think),胡适给他老师做翻译,北洋军医学校校长全绍清讲“卫生之道”。这都是连续讲演过几次的,当时同学间流行模仿胡适和全绍清的口语,如“白话!”“白话!”“鼻子的卫生!”“眼睛的卫生!”随处可闻。(胡适讲白话文学,常在古诗中举例,每举一例必加断语曰“白话!”每次演讲中,“白话”特多。全绍清讲演时,每到一个段落,常说是“什么的卫生”,提醒听众注意。)印象之深,数十年不忘。一九四五年,我在北平和胡适之、全希伯两位先生晤面闲谈时,还常以当年的“口语”相戏语。
“南开先生”常在周会上以“咱们南开”或“南开精神”勉励学生苦干实干。有一次,他模仿在天津中等学校联合运动会上得百码第一名的郭毓彬和得二百码第一名的王文达最后冲刺的姿态,握拳,眦目,昂首前进,说:“嗯!到啦!这就是南开精神!”接着,他说:“不怕难,不怕苦,干!干!干!什么事都会成功的。”
“南开先生”深知事业与学问相济相需的道理。一九一七年,他的胞弟张彭春(仲述)先生由美学成回国,他将校务交张仲述代理,自己远赴美国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研究院深造,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国,开始扩办南开大学的计划。
“南开先生”赴美后,天津发生大水灾。一天的夜间,突然大水漫淹了学校,自张仲述以次全校教职员奋力抢救住校的学生脱险。我回到北平的家里,正想可以无忧无虑地过一个快乐的中秋节,讵意不到五天,接到学校通知,要学生即到天津河北法政专门学校报到上课。学校因南开洼(南开所在地)积水短期难消,商妥河北法专借址上课。我们在那里读了一个学期,第二年春季始搬回本校。我提出这件事,是说明南开的教职员确实受张校长的感召,能发扬临危不乱、处变不惊、苦干实干的南开精神。我想当时住宿学校现在台湾的校友们,当会记得那时学校淹水,夜间仓皇离校的情形。
私人创办大学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财力、人力都要煞费周章。“南开先生”本着宗教家与人为善、爱人以德的精神,向拥有财富、籍隶北方的各省军政首长苦口婆心,劝善捐资,用他们的非分之财办利国利民之事,如李纯、陈光远、齐燮元、许兰洲、孟恩远等都曾大破吝囊,捐出巨资,赞助南开大学之创办。大学第一班即于一九一九年在南开校本部旁边的新筑校舍中开课,以哲学博士凌冰为大学部主任,以喻传鉴为中学部主任。以后在八里台逐渐兴建了规模完备的南开大学。
“南开先生”热爱国家,热爱民族,平时常以民族气节训诲学生。其灌输学生的南开精神素为野心勃勃、蓄意侵略中国的日本人所大忌。日人侵占华北,张氏即舍弃其毕生精力所寄的南开,率领其干部华午晴、伉乃如等南走重庆,办理已创立一年的南渝中学。远在日军发动侵略中国战事的十余年前,张氏即洞烛日本人的狼子野心。我深切记得张校长旅行东北归来,在周会上对学生讲话,分析日人在东北的情形后,他说:“不到东北,不知中国之大;不到东北,不知中国之险。”十余年后,吴铁城先生赴东北斡旋易帜南返,亦说过同样的话,当时成为名言。在七七事变十余年前,张氏即有如此透彻之看法,可谓先知先觉。
“南开先生”善用贤能的干部和延揽高明的师资,这是他办学成功的主要秘诀之一。中学时代,像华午晴对学生生活管理的周到和亲切,像时子周对学生课业督导的认真和切实,身受其教的校友大都不会忘怀。就师资而论,亦为当时一般学校所望尘莫及。以我亲受教诲的老师为例:教国文的有墨学大师张纯一,教文字学的有小学名家陈文波,教数学的有电机专家孙继丁,教英文课程的前后有李道南、英人穆尔小姐、美人罗德伟,教外国地理的有时子周,教西洋历史的有余日宣,他们都不是当时一般学校所能延揽的大学教授级的名师。大学时代,由凌冰以至徐谟、何廉、方显廷、梁启超等都是当代一流的学者。
德、智、体、群四育并重,南开实开风气之先。德智之培育在课堂,体群之辅导在课外。仍以中学为例,学生课外活动,如社团之组织,普遍而积极。励志社、青年会、敬业乐群会均于课余之暇举办各种活动,辅导群育之推行。《校风报》尤为出色,每周出版一期,从无脱漏,其编辑发行均由学生办理,我和周恩来曾被推同时担任编辑工作一年。张仲述到校后,更于课外推动文艺活动,不遗余力。如蜚声华北一带的南开话剧运动,即于此时开始。周恩来以演《一元钱》中的孙大小姐,获得河北女师学生邓颖超的青睐,结成“红色夫妇”。时子周以演《一元钱》中为富不仁的孙思富而驰名平津(时先生北伐后参加常务工作,任国民党中央委员,在台湾逝世)。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北平军调处执行部成立之初,马歇尔率周恩来飞抵北平,在北京饭店举行酒会招待各界。我和周恩来在酒会上见面,他对我说:“你想不到我会穿上将军服吧!”我笑答:“在我的印象里,你仍然是《一元钱》中的孙大小姐,不应该穿庄严的军服。”他也笑了,指着我向采访新闻的同业说:“他是我南开的同学,校中比赛国文,曾得过第一名。”因为他提到南开的旧事,我问他:“咱们校长近况好吗?”他以惋惜的口吻说道:“校长是卓越的教育家,不是政治家,他不应该参加国民参政会这类的政治工作。”我以郑重的态度回答:“校长是热爱国家、热爱民族的人,为了抗战,为了团结,他参加参政会,是爱国精神的表现。他的学生都应该效法他这种爱国家、爱民族的精神。”
“南开先生”是现代中国的大教育家,他的绩业、他的名字在教育史上光辉永在。
“南开先生”和南开学校永垂不朽!
原载《传记文学》第二十六卷第四期(一九七五年四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