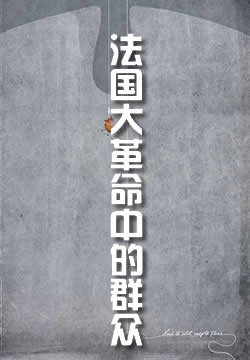一
这里丘陵草原绵延起伏;地势高朗,微风习习,一派葱绿,经过那动荡的年月以后就再也没有丝毫改变。从来没有一具犁耙翻耕过那儿的草地,当年长在最上层的草现在也依然还在最上层。这里以前有过营房,这里当初为骑兵的坐骑在山坡上开出的道路,现在还清清楚楚,原来堆过马粪的地方也仍然明显可见。夜晚,我独自走过那杳无人迹的地带,在轻风吹过枯草和蓟类植物发出的飒飒声中,总不可避免地要听到昔日的喇叭和军号声,马笼头碰撞的咔哒声,总不禁要看到一排排影影绰绰的帐篷和辎重。从营篷里传出那种喉音很重的外国话的只言片语[2],还有那思念祖国的一句半句的歌声,因为他们大多是隶属国王的德国兵团的那些团队,那些士兵当年就睡在帐篷柱子周围。
那是将近九十年前的事。那时候英国军队的制服还佩饰着大得出奇的肩章,怪里怪气的三角帽,还有马裤、绑腿、沉重的子弹匣、带扣的鞋子等等,现在看起来就显得不顺眼而很粗野了。思想观念已经改变,发明一个接着一个。那时候,军人是景仰尊崇的对象。国王无论在何处都还让人奉若神圣;战争则给看做光荣的事情。
与世隔绝的庄园住宅和小小村落分布在这些山丘之间的峡谷和低地上,在国王乐于一年一度到南面几英里距离的海滨浴场[3]洗浴之前,这里很难看到一个陌生人;但是从那以后,一营营的士兵就开始南下,云集在附近的旷野里。那许多各具特色的故事,远从那个独具特色的时代开始,直到如今还多多少少支离破碎地在这一带流传,难道还有必要再加叙说吗?其中有一些我重复讲过,更多的我已经忘记了;可有一个我从未讲过,而且肯定是不会忘怀的。
这个故事是菲莉斯亲口对我讲的。她那时已经是一位七十五岁高龄的老小姐了。听她讲故事的是个十五岁的少年。她叮嘱我,在她“去世,下葬,让人遗忘”之前,对她和这件事的关系要闭口不谈。她讲这个故事以后又活了十二年,到现在她已经去世将近二十年了。她因为腼腆谦卑而总想让人忘掉她,可是这种愿望却并未完全实现,结果不幸使人留下了对她不公正的看法,因为当年流传到国外而且一直保留至今的有关她那些片片断断的故事,显然还是对她的名誉极其不利的那些。
这都是从约克轻骑兵团到达开始的,这个团是上面提到的那些外国团队之一。在那天之前,在她父亲的房子附近一连几个星期都难得见到一个人。门前台阶上传来一阵好像是来客衣裙的窸窣声,结果却是随风飘落的一片树叶;有辆马车仿佛驶近门口了,其实是她父亲在花园里磨石上磨他的镰刀,准备干他喜爱的休闲活儿,修剪地界上的黄杨树篱。一个好像是从车上扔下行李的响声,原来是远在海上的炮声;黄昏时分看上去好像有个大高个子站在大门边,原来是一丛紫杉给修剪成了那种精巧细长的样子。如今在乡间再也见不到老辈子那种僻静的处所了。
然而就在那个时候,乔治王和他的朝臣正在他喜欢的那个海滨疗养地,离这里不过五英里。
女儿是与世隔绝得厉害,但是她父亲却与世界隔绝得比女儿更胜一筹。如果说她的社交生活状况是昏暗不明,父亲的则是黢黑一片。然而父亲在他那一片黢黑里还自得其乐,而女儿面对她的昏暗却感到沉闷憋气。这位格若夫大夫曾经开业行医,他爱好独自琢磨玄而又玄的问题,这使他行医减少,最终入不敷出难以为继,此后他放弃了他的医务,在内地这个不起眼儿的角落,以微不足道的租金租下了这座半似农庄半似庄园的破败小房子,用原来在城镇里不足以维持生计的那点微薄进项,也可以保证衣食无虞了。他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待在花园里,随着时光流逝,加上越来越意识到自己是在追求幻想中浪费了生命,所以变得越来越焦躁激动,访问朋友的次数也越来越少了。菲莉斯变得十分羞怯,甚至在户外短暂漫步的时候,无论在哪里遇见生人留神看她,都会感到害羞,走路也变得不自在,脸红到了脖子根。
不过即使在这里也出了个对她表示爱慕的人,而且完全出乎意料地向她求婚了。
前面说过,国王当时正在附近那个小城镇,驻跸格洛斯特行宫;国王驾幸,自然也将郡里许多人招引而至。在这些闲杂人等中间,许多人自称和宫里还有种种瓜葛并且利害相关。有一位是单身汉,名叫汉弗瑞·古德,不老,也不少;不丑,也不俊;举止稳重,不能说是“花花公子”(当时对那些轻薄放荡的未婚男子都这样称呼):大体上是个不文不火的时髦男子。这位三十岁的单身汉拐弯抹角来到丘陵地带的这个村子,看到了菲莉斯,结识了她的父亲,为的是想结识她。她用某种这样或那样的办法在他心里煽起的火焰足以引得他几乎每天都要朝这个方向走了;终于他和她订了婚。
因为他出自当地一个古老的世家,其中有些成员在这个郡里受人尊敬,菲莉斯让他拜倒在她的裙下,对她这样一个处境窘困的人来说,是支出了通常认为非常漂亮的一招儿。她怎么能支出这样一招的,就连菲莉斯本人也不大清楚。在那个年头,人们认为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违反自然法则,而不像比较现代的看法,只是违背了传统习俗,因此,出自海滨胜地中产阶级家庭的菲莉斯,让这样一位上等阶级的人选中,就仿佛是要给引进天堂一般,尽管那些孤陋寡闻的人因为上面说到的这位古德只是一个穷措大,从而看不出这对情侣各自的地位有多大的悬殊。
这种经济状况是他推迟结婚的借口,但是十之八九也可能是实情,而且冬天临近,国王因季节的关系起驾离去,汉弗瑞·古德先生也就动身去了巴斯,应许过几个星期再回到菲莉斯这儿来。冬天来了,他应许的日期已经过了,可是古德迟迟未至,他的理由是他不好把他父亲丢在他们逗留的那个城市,因为老人身边没有其他亲人。菲莉斯虽然感到极其孤寂,也只好心甘情愿了。这位向她求婚的男人,从许多方面来说,都可以做她的如意郎君,她父亲非常赞同他求婚;但是他对她这样怠慢,即使不是让菲莉斯感到难过,也是感到别扭。她对我肯定地说,她从来没有像爱这个字的真正含意那样爱过他,不过她是诚心诚意地敬重他;佩服他有时随兴之所至表现出的那种有条不紊紧追不舍的做派;看重他关于宫廷里现在在干什么、过去干了些什么、将来又要干什么的种种知识,他本来可以有所高攀而却选中了她,对此她也不无某种得意之感。
但是他就是没有来;而春天却姗姗而来了。他按时来信,但是写得刻板正经;既然她的地位并不确定,再加上汉弗瑞在她的心里也没有引起多大的激情,因此在菲莉斯·格若夫的心里产生了一种难以描摹的厌倦情绪,也就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了。春天很快又转成了夏天,而夏天又迎来了国王;可是还是没有汉弗瑞·古德的踪影。在这整个期间,靠信件维持的婚约原封未动。
正是在这个时候,一片金色的熠熠光辉照亮了这里人们的生活,在所有年轻人的心里激起了充满激情的兴致。这片光辉就是前面说到的约克轻骑兵。
* * *
[1] 当年英王乔治第三身兼北德意志汉诺威邦的国王,他在该邦征募日耳曼人参军与法国对抗。
[2] 以德语发音特点暗示军营里讲的德语。
[3] 十八世纪开始流行海水浴,海滨纷纷建起类似内陆温泉疗养地的海滨浴场。此处指乔治第三所喜爱的威默斯。
二
现在的这一代人很可能对九十年前那些大名鼎鼎的约克轻骑兵只有一点儿模模糊糊的印象了。他们是隶属于国王陛下的德国兵团的团队之一(虽然他们后来有点儿每况愈下了),可当年他们那华丽耀眼的制服,他们那雄健俊逸的战马,而首先是他们那外国派头和八字胡(当时都是稀罕的物件儿),他们不管走到哪里,都招来一群又一群男男女女崇拜者。因为国王驾幸附近那座小城镇,他们和其他团队就开来驻扎在这些丘陵和牧场上。
这里地势高爽,视野开阔,前方可以眺望波特兰——投石人之岛,往东可以遥望圣奥德赫姆海角,而往西则几乎可以看见斯塔特岬。
菲莉斯虽然并不是一个地道的乡村姑娘,可是也和大家一样,对这个军事重地很感兴趣。她父亲的家和这个重地多少还有一点距离,坐落在这条小巷斜坡的最高处,因此它和位于教区低处的教堂塔楼尖顶几乎处在同一个高度。她家花园墙外,青草从墙根一直长到很远的地方,一条小路紧靠院墙穿过草地。菲莉斯从小姑娘的时候开始就喜欢爬上这道围墙,坐在墙头——这项本事并不像乍看起来那么困难,因为这个地区的墙都是用小石块砌成,墙面并不涂抹灰浆,所以有很多缝隙让小小的脚趾攀勾。
有一天她正坐在那儿,懒洋洋地看着墙外面的牧场,这时一个独自走在小路上的人引起了她的注意。这个人是声名煊赫的德国轻骑兵中的一员。他两眼下垂望着地面向前走着,他那副样子像是故意要避开别人似的。要不是他的领圈又硬又挺,他的头大概也会和他的眼睛一样垂下来了。等他走得更近一些,她才看出来他脸上现出深深的悲伤。他没有注意到她,沿着小路走过来,差不多马上就走到围墙下面了。
菲莉斯看到一个体面高大的兵士竟有这样一种态度,真是吃惊不小。她对军人,特别是对约克轻骑兵的想法(完全是来自道听途说,因为她这一辈子从来没有和当兵的说过话),总是以为他们的心情和他们的军服装备一样轻松欢快。
正在这一瞬间,那个轻骑兵抬起了眼睛,看见她坐在墙头,她身穿一件低领无袖长袍,白纱巾披在肩头和脖子上裸露的地方,衣装也全都是白色的,在夏天灿烂的阳光下,显得晃眼。这种不期而遇让他有点儿脸红,片刻未停就继续迈步走了过去。
那天这个外国人的面孔在菲莉斯的心里萦回不去。他的面貌那么英俊动人,他的眼睛那么湛蓝,而且流露着悲伤迷茫。也许是再自然不过吧,后来有一天就在同样的时刻,她又在那围墙上向外看,一直等到他再次从那里经过。这一次他是在念一封信,他一看到她,显露出的神情正是又像期待又像希望见到她的那种样子。他差不多是停下了脚步,微笑着,还很有礼貌地敬了个礼。这次会面最后两人还交谈了几句。她问他在念什么,他就欣然告诉她,他在重新细读他母亲在德国寄来的几封信;他并不是常常收到母亲的信,他说,所以只好一再重读那些旧信。这次会面的整个情况就是这样,后来几次也是同样的情况。
菲莉斯老是说,他的英语虽然并不好,可是对她来说,都可以理解,所以他们的结交从来没有因为语言方面的困难而受到影响,每当话题对他掌握的那些英语词汇来说显得太微妙、太细腻、太温柔而难以表达的时候,毫无疑问眼睛就帮助舌头解了围,而且嘴唇又帮助了眼睛——这当然是后来的事儿啦。简单说来,这种结交,固然是毫不留神就发生了,对她这方面来说也够冒失的,却发展起来,而且成熟了。她像苔丝狄蒙娜一样,同情他,倾听他的经历[1]。
他名叫马特豪斯·梯纳,老家在萨尔布吕肯[2],他母亲还住在那儿。他二十二岁,虽然入伍不久,可是已经提升为下士班长了。菲莉斯总爱说,在纯粹英国团队的普通士兵里,根本找不到像他那样文雅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这些外国士兵里有些人举止潇洒、风度翩翩,更像是我们本国的军官而不是队列里的士兵。
她从她这位外国朋友那儿逐渐了解到他自己和他的伙伴们的情况,菲莉斯一点儿也没想到约克轻骑兵竟是那种样子。这个团根本不像那身制服一样轻松欢快,而是弥漫着可怕的忧郁症和长年的思乡病,这种病症让许多人情绪低沉,几乎达到无法出操的程度。病情最严重的是那些刚到此地不久比较年轻的士兵。他们厌恶英国和英国的生活:无论是对乔治王还是他的岛国,他们一概毫无兴趣,一心只想离开它,再也见不到它。他们的人在这儿,可是他们的心思情感却永远在远离此地的他们亲爱的祖国,一谈到祖国,这些勇敢而且在许多方面都不以苦乐为意的士兵,莫不热泪盈眶。害这种乡愁[3]——他用自己的语言这样称呼它——最严重的一个人就是马特豪斯·梯纳,他那耽于冥思梦想的本性,使他感到这种流放生活更加阴沉,特别是想到他把母亲孤零零地抛在家里,无人为她解闷承欢。
虽然菲莉斯对这一切深为感动,对他的经历很感兴趣,并未瞧不起这位大兵的交情,但是有很长一段时间,她一直不肯(至少按她自己所说的)让这个年轻人在纯属友谊这条界线上越雷池一步。的确,只要她还认为自己像是要属于另一个人的时候就一直如此,尽管很有可能在她自己还没有觉察到以前,马特豪斯早已赢得她的心了。那道不可避免的石墙使任何类似亲昵的行为难以逾越;他从未跨越,或者要求跨进花园,所以他们之间所有的谈话都是在这条界线的两边公开进行的。
* * *
[1] 苔丝狄蒙娜是莎士比亚所著《奥塞罗》中的女主人公,她同情敬重摩尔人大将奥塞罗,不顾父亲的反对,和他秘密结婚。
[2] 德国西部城市,靠近法国边境。
[3] 原文为home-woe。
三
但是菲莉斯的父亲有位朋友,曾经给这个村子传来一条关于她那位冷淡和耐心都非常出奇的未婚夫汉弗瑞·古德先生的消息。人们听说,这位绅士在巴斯说过,他认为他对菲莉斯小姐求婚还只达到半约定的阶段,考虑到他父亲因为重病缠身不能关注他的问题,他不得已而将此事置之度外,他觉得最好目前任何一方都不要做明确的承诺,他的确也不能保证,他不会把自己的目光投向别处。
这种说法固然只是一种传闻,因而不能不折不扣地加以信任,然而它与他的来信日渐稀少和信中缺乏热情却是恰相吻合,所以菲莉斯那时并不怀疑它确是实情;而且从那个时刻起,她就认为自己是自由之身,可以把自己的心托付给自己看中的人了。她父亲可不这样想;他声称这件事完全是凭空捏造。他从童年起就认识古德先生这一家。如果说有什么格言可以很好地表现那一家人在婚姻方面的见解,那就是“爱我淡如水,爱我能久长”。汉弗瑞是个高尚正派的人,他对自己的婚约不会那么轻率。“你就耐心等着吧,”他说,“到时候一定事事顺遂。”
菲莉斯听了他这番话,最先设想,她父亲是和古德先生往来通信的,于是她的心猛地一沉;因为不管她原来有些什么打算,一听说自己的婚约已经告吹,她还是得到了解脱。可是她现在又知道,她父亲所听到的关于汉弗瑞·古德的情况,并不比她本人听到的多;而他也不便就这件事情直接给她的未婚夫写信,否则就会被看做诋毁那位单身汉的名誉。
“你想找借口,逗引这个或者那个外国佬用无聊的献殷勤来讨好你,”她父亲对她大嚷大叫,以近来常常对她的那种很坏的态度说,“我看到的比我说出来的还多。没有得到我的允许,你不得走出这座园子的围墙一步。你要是想看看兵营,等个星期天下午,我亲自带你去。”
菲莉斯丝毫不想采取什么行动来违抗她父亲,但是她认为,她在自己的感情这方面是独立自主的。她不再压制她对这个轻骑兵的好感,固然她根本不是按照严肃认真的意思把他当做自己的情人,像对一个英国男人那样。这个年轻的外国兵差不多成了一个她想象中的人物,完全摆脱了居家过日子那种普通人啰啰嗦嗦的事情;一个来了她不知道是从哪里来,走了也不知道是去到何处的人,一个让人魂牵梦萦的对象,仅此而已。
他们现在经常不断地见面,大多数是在黄昏时分,是在太阳落山和最后一遍军号召他返回营帐那中间的短暂时刻。也许近来她的举止不像以前那样拘束了,无论如何,反正这个轻骑兵就是这个样儿了;他一天一天变得越来越温情脉脉,在这种匆匆会面后分手的时候,她把手从墙头伸下来,让他可以握住。有一天傍晚,他紧握着她的手,时间长了一点,她就叫了起来。“墙是白的,地里有人可能会看见白墙衬出你的影子来的!”
那天晚上他逗留了那么久,好不容易费了最大的劲儿才跑过中间那块地,按时进了营地。他下一次等她的时候,她没有在常来的时间在常到的那个地点出现。他失望已极,简直无法形容。他一直瞪着眼睛茫然盯着那个地点,像丢了魂儿似的。归营号吹了,归营鼓也敲了,他仍然不走。
她纯粹是因为一件偶然的事情给耽搁了。她到那儿的时候,心里很焦急,因为时间晚了,她和他一样也听到了表示兵营关门的鼓号声。她恳求他立刻离开。
“不,”他心情沮丧地说,“我现在还不走——你才刚刚到呢——我整天都在想着你要来。”
“但是你回营的时间过了会受处分吧?”
“我才不在乎呢,要不是为了两个人——我挚爱的人,在这儿,还有我母亲,在萨尔布吕肯,那我以前什么时候早就离开这个世界了。我痛恨这个军队。我觉得和你待上一分钟,也比所有那些提升都强。”
就这样他留下没走,和她谈话,告诉她他老家一些有趣的事情和他童年的故事,直到最后她因为他不顾一切硬是不走,越来越担心了。只是因为她坚持要和他道晚安告别,要他离开那道围墙,他这才返回他的兵营。
她下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原先佩戴在袖子上表示军衔的条纹就没有了。他因为那天晚上回营迟到被降为列兵;菲莉斯认为是自己害他受了处分,所以感到十分难受,现在情况翻转过来,轮到他来安慰她了。
“别难过,我亲爱的[1],”他说,“我已经想出了一种补救的办法,不管将来发生什么事情。首先想想看,哪怕我重新赢得了我那些条纹,你父亲会让你嫁给约克轻骑兵团一个没有军官头衔的军士吗?”
她脸红了。在她脑海里从来没有想过,和他这样一个并非现实的人去走这样一种实实在在的一步;而这也只要稍微想一下就行了。“我父亲不会——肯定不会的,”她毫不通融地回答,“这连想都不能想!我亲爱的朋友,就请忘掉我吧,我恐怕我在毁掉你和你的前途!”
“根本不行!”他说,“是你,才让我对你的这个国家有了足够的兴趣,愿意在这里活下去。如果我亲爱的故乡也在这里,而且我年迈的母亲和你都在一起,那么我就会快快活活,尽我最大的努力好好当兵了,可是情况不是这样。现在听我说吧。我的计划是这样。你和我一起回我老家,在那儿做我的妻子,和我母亲和我一起在那儿生活。我不是汉诺威人[2],这你知道,固然我是作为汉诺威人参军的;我的家乡靠近萨尔,和法国和平相处。只要我一回到那儿,我就自由了。”
“可是怎么到得了那儿呢?”她问他。菲莉斯对他的这个主张不是感到震惊,而是觉得惊奇。她在父亲家里的处境,越来越让她感到厌倦和痛苦到了极点;他的父爱好像完全枯竭了。她和她周围那些快快活活的姑娘不一样,不是在本村土生土长的;所以马特豪斯·梯纳对自己故乡,对母亲和家那种情真意切的怀念,对她起了某种感染的作用。
“可是怎样去呢?”她见他没有回答,于是又问了一句,“你要买一张退役证吗?”
“啊,不,”他说,“在当前这是不可能的。不;我不是自愿到这儿来的。我为什么就不应该开小差呢?现在正是时候,因为我们马上就要收拾营房准备开拔,我可能再也见不到你了。这就是我的计划。我要请求你在两英里那边的大路上和我会合,时间可以约好在下星期哪个寂静的夜晚。这件事没有什么不体面,或者让你丢脸的;你不会只是和我一个人一起逃跑,因为我还要带上我那位年轻的忠实好友克里斯托夫,他是阿尔萨斯人[3],不久前才参加我们这个团。他同意帮助我实现这个计划。我和他要先去那边那个港口,在那儿把那些船查看一下,找一条适于我们用的船,然后我们就从那个港口过来。克里斯托夫已经有了一张海峡的航海图。到时候我们就去那个港口,在午夜时分从泊船的地方把船开出来,沿着小岬把船开到别人看不见的地方;到第二天早晨,我们就到法国海岸靠近瑟堡的地方了。其余的事就很容易了,因为我已经攒了一些钱作陆地上旅行用,还可以换掉衣服。我再给母亲写封信,她会到路上来接我们。”
他回答她的一些问题时,又补充了一些详情,这让菲莉斯心里一点也不怀疑这次行动是可以实现的了。不过这次行动是那么重大,简直让她胆战心惊;要不是她那天晚上一进家门她父亲就冲着她讲了那一番事关重大的话,她是否会进一步卷进这次莽撞的冒险,还是很成问题的。
“那伙约克轻骑兵怎么样啦?”他问。
“他们还待在营房里;但是我相信,他们很快就要开走了。”
“你想用这种办法来掩盖你的所作所为,那是白费力气。你一直在和那伙人里面的一个经常会面;有人看见你和他一起散步,这伙外国蛮子,比那些法国佬好不到哪里去!我已经下定决心了——我还没讲完,请别插嘴——我已经下了决心;他们还驻扎在此地的时候,你就别待在这里了。你得去你姑姑家。”
她抗辩说,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他以外,她没和任何一个当兵的或男的一起散过步,她这样说毫无效果。她的抗辩也是软弱无力的,因为他说的那番话固然不是句句正确,实际上也不过只有一半不对。
她父亲姐姐的家对菲莉斯来说就是一座监狱。她不久前在那里住过,领教过那种死气沉沉的气氛;接着她父亲就吩咐她怎样收拾要携带的用品,她简直觉得生不如死了。在后来的岁月里,她从来没想为她在这忐忑焦虑的一个星期中的行为作任何辩解;不过她当年暗自思忖的结果是:她决心参加她的情人和他的朋友的共同计划,逃往那个在她想象中他描绘得如此美妙动人的国家。她总是说,他的建议中有一点独特之处打消了她当时的犹豫不决,那就是他结婚的意图显然是纯洁和直率的。他显得那么勇敢善良和温柔宽厚;他对她那份尊重,是她以前从来没有受到过的。出于对他的信任,所以她才鼓起勇气面向这次显然危险重重的旅行。
* * *
[1] 原文为德文。
[2] 此处指梯纳本人不属于英国乔治王当时领有的德意志汉诺威王国的子民之列。
[3] 阿尔萨斯在法德边界,历史上多次变更所属。哈代小说中所写时期,当属德国,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又两次归属法国。
四
在随后那个星期的一个温和黢黑的晚上,他们实行这场冒险了。梯纳原定在大路上的一个地点和她会合,那儿有条岔路通往村里。克里斯托夫要在他们之前去到停船的港口,划船绕过诺斯——也就是当时大家称呼的了望山——然后在海角的另一边接他们上船;他们则要徒步走过港口大桥,再翻过了望山到达那里。
她一等到父亲上了楼回到自己的屋子,就立刻离开了家,手里提着一个行李卷,沿着那条小道一路小跑。在那种时刻,村子里哪里也看不到一个人影,她走到小道和大路的交叉口上,谁也没有看见她。她找了围栏犄角上一个阴暗的地方,在那里可以看清沿着大路走过来的每一个人,却可以不让别人看见她。
她就这样在那里等候她的情人,不大一会儿——由于她神经紧张,甚至这很短的时间也让她觉得难熬——她没等到她期待的脚步声,却听见了驿站马车驶下山坡的声音。她知道梯纳不等到大路上静无一人,是不会露面的,所以只好很不耐烦地等着马车过去。马车来到她所在的犄角就放慢了速度,并不像通常那样开走,而是在离她几码的地方停下来了。车上走下一位乘客,她听见了他说的话,那是汉弗瑞·古德的声音。
他带来了一位朋友,还有一件行李,行李搁在草地上,马车就继续上路,去了皇家海滨浴场。
“我不知道,那个人和那匹马还有轻便马车现在在什么地方?”从前向她求过婚的那个人对他的同伴说,“我希望我们在这里不必等得太久,我告诉过他,九点半准时到。”
“你给她带的礼物完好无损吧?”
“给菲莉斯的?噢,是的。就在这个箱子里。我希望这可以让她高兴。”
“当然可以。哪个女人收到这种道歉讲和的漂亮礼物,还会觉得不高兴呢?”
“嗯——她理应得到这个礼物。我这一阵子对她不大好。可是最近这两天,我心里一直惦记着她,我都不好意思对别人承认了。唉,好了,我也不再多说这件事了。她根本不可能像他们理解的那么坏。我可以肯定,一个像她这样头脑清楚的姑娘,会懂得最好不去和任何一个汉诺威当兵的纠缠在一起。我不相信她会那样。现在这件事儿就了结啦。”
那两个人等在那儿,不时还漏出几句这类的话;这些话好像一下子让她看明白了,她自己的所作所为简直是罪大恶极。那个人终于赶着车来了,谈话于是中断。行李放进车里,他们上了车,朝着她刚刚走来的那个方向赶车走了。
菲莉斯感到非常内疚,开头她很想跟着他们走了;但是经过一番考虑,她又觉得,只有等马特豪斯来了,老老实实对他解释,她改主意了,这才勉勉强强算得上是公平的——尽管她和他面对面地努力解说会是很困难的。现在她听到汉弗瑞亲口说出的那些话,从中判断出,他一直对她完全信任,于是满怀痛苦地责怪自己,不该听信那些说汉弗瑞·古德对婚约不忠诚的种种传言;不过她也完全清楚地懂得,是谁博得了她的爱情,少了他,她未来的生活看来就会枯燥乏味。然而她越是仔细思考他的建议,就越是不敢接受它了——它是那么鲁莽,那么模糊,那么冒险。她早已经答应了汉弗瑞·古德,只是因为他看来像是不守信用,才让她把原先的诺言看做废纸。他关怀备至地给她带来礼物,让她受到感动,她必须遵守自己的诺言。她得保持自尊。她得留在家里,和他结婚,而且逆来顺受。
菲莉斯就这样鼓起劲头,变得从来都没有过的刚毅果敢。几分钟之后,马特豪斯·梯纳的身影在篱门后面出现了,她向前走了几步,他就轻快地一跃而上。再没有躲躲闪闪了,他把她紧抱在胸前。
“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她让他拥抱着站在那儿,心乱如麻地想着。
菲莉斯那天夜晚如何通过了那场极其严峻的考验,她永远也无法清楚地回想起来。她老是把她的决心得以实现,归功于她那位情人的高尚正直,因为她用微弱无力的话语明白告诉他,她已经改变了主意,觉得自己不能也不敢和他私奔,尽管她这样决定使他感到痛苦,他还是立刻就不再勉强她了。知道她是那么浪漫多情地眷恋着自己,他只要不顾一切地施加压力,无疑一定可以使事情转为对自己有利。但是他并没有采取任何不正当或者不正派的手段来引诱她。
在她这方面,由于害怕他不安全,她恳求他留下不走。他说,他不能那样做。“我不能对我的朋友失信。”他说。如果他只是独自一人,他就会放弃自己的计划。可是克里斯托夫准备好了船,还带着罗盘和航海图在海岸边等着呢;很快就要退潮了;他已经告诉母亲他就要回家了;他一定得走。
他欲行又止,难舍难分,许多宝贵的时间都流逝了,菲莉斯则坚持自己的决心,尽管这让她悲痛欲绝。他们终于分手了,他走下山坡,在他的脚步声就要消失的时候,她心里升起一种渴望,想至少再看一次他的身影,于是悄无声息地跟在他后面跑过去,又对他逐渐消失的形象看了最后一眼。有那么一会儿工夫,她十分激动,简直马上就要跑上去,把自己的命运和他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但是她做不到。在关键时刻埃及的克莉奥帕特拉丧失的勇气[1],也很难期望能在菲莉斯·格若夫身上出现。
和马特豪斯同样的一道黑影,在大路上和他会合了。这是他的朋友克里斯托夫。她再也看不见什么了;他们俩匆匆赶往四英里之外的市镇和海港那个方向。她怀着类似绝望的心情,转过身来缓慢地走上回家的路。
营地里响起了归队的号声;但是现在对她来说没有什么营地了。那里一片死寂,就像摧毁一切的使者经过以后,亚述人的营地里的情景一样[2]。
她悄无声息地进了家门,没有见到任何人,就上床睡觉了。悲伤,起先让她难以入睡,到后来倒让她沉沉大睡了一场。第二天早上,他父亲在楼梯脚口叫她。
“古德先生到了!”他得意扬扬地对她说。
汉弗瑞住在旅馆里,已经登门来问候过她了。他给她带来一件礼物,是一面漂亮的镜子,镶着刻有浮雕的银镜框,他父亲正把这面镜子拿在手里。他答应一小时之内再来拜访,邀请菲莉斯一起去散步。
那时候不像现在,漂亮的镜子在乡下人家里是稀罕物件,所以眼前这面镜子得到了菲莉斯的赞赏。她照了照镜子,看见自己的眼神那么阴沉,于是努力想使它们显得高兴一点。她当时心情凄楚,这种情况会使一个女人沿着她自以为是命中注定的道路,不知不觉地一直向前走下去。汉弗瑞先生以他那种谨慎克制的态度坚守原先的约定;她呢,也得同样行事,矢口不提自己那段行为失检。她戴上帽子,披上披肩;他在原定时间来访的时候,她就在门口等他了。
* * *
[1] 埃及女王克莉奥帕特拉与罗马三执政之一安东尼联姻对抗恺撒,女王率领的舰队临阵逃跑,使安东尼大军惨败。故事可参阅莎士比亚著《安东尼与克莉奥帕特拉》第三幕。
[2] 此处作者引述《圣经·旧约·列王纪下》第19章关于耶和华使者血洗亚述王营地的故事。
五
菲莉斯感谢他送来那件漂亮礼物;不过他们继续散步的时候,就完全是由汉弗瑞一个人在说话了。他对她谈到上流社会最近的风尚——她很愿意谈论这个话题,而不触及任何较多属于个人方面的事情——他那些经过仔细斟酌的话语,帮她把那忐忑不安的心情和思想平静下来。要不是她自己正暗自悲伤,那她一定早就看出了他那种左右为难的窘态了。他终于突然转换了话题。
“我很高兴你喜欢我那件菲薄的礼物,”他说,“说实话,我带它来是向你谢罪的,而且还要请你帮助我从一个巨大的困境中解脱出来。”
对菲莉斯来说,她难以想象,这个无拘无束的单身汉——在某些方面她还钦羡他呢——还会有什么困难。
“菲莉斯——我现在立刻告诉你我的秘密;我有一个非常大的秘密要告诉你,然后才能向你讨主意。事情是,是这样的,我结婚了;是的,我已经偷偷地和一个年轻可爱的美人儿结了婚;而且要是你认识她——我也希望你认识她,你会用各种言词夸奖她的。可是她却不是我父亲要给我挑选的那种人——你和我一样都知道父亲的想法——所以我一直保守着秘密。毫无疑问,将来会有一场了不得的吵闹;但是我想,我要是有了你的帮助,就可以跨过这道难关。只要你愿意帮我这个忙——我的意思是,我告诉了我父亲以后——说你绝不会与我结婚,你是懂得的,或者和这类似的什么话——我起誓这一定会大大地帮助我扫清道路。我十分迫切地希望争取他顺着我的观点,使我和他的关系不至于疏远。”
菲莉斯简直不知道她是怎么答话的,她对他那意想不到的处境,又是怎么提出忠告的。然而他宣布的这件事减轻了她的痛苦,却是可以觉察到的。她痛苦的心灵渴望把自己的痛楚作为回报吐露给他;如果汉弗瑞是个女人,她会立刻把自己的故事向他和盘托出。可是对他,她又害怕坦白相告;而且还确有实际的理由保持缄默:需要等待足够的时间,好让她的情人和他的朋友逃出危险重重的地方。
她一回到家里,又立刻找了一个寂静无人的地方待了很长时间,一方面悔恨自己没有出走,一方面又如梦似幻地回味和马特豪斯·梯纳的那些会见,从刚开始一直到最后结束。他回到自己的国家,处在自己的同乡女人中间,可能很快就忘了她,甚至忘了她的姓名。
她心灰意懒得一连几天都没有出过家门。一天清晨雾霭漫,透过雾霭,晨曦仅仅显露出一片灰绿;帐篷的轮廓,连同拴在绳索上的一排排马匹,也显现出灰绿色。营房厨灶的炊烟沉重地低悬着。
花园尽头有块地方,她以往常常从那里爬上墙头会晤马特豪斯,现在这成了她在英国国土上惟一感到兴趣的一寸土地,尽管那天令人感到不快的雾霭遮天盖地,她还是走出门外,一直走到那个熟悉的犄角。每一片草叶上都沉甸甸地缀着小水珠,蛞蝓和蜗牛都爬出地面。她可以听到从营地经常传来的那种隐隐约约的嘈杂声,在另一个方向则是农夫沿着大路进城的细碎脚步声,因为那天是赶集的日子。她注意到她常常来的这个犄角靠墙有一小块地上面的草都踩平了,而且在她爬上墙头向外眺望时踩过的踏脚石上留下了园中泥土的痕迹。她不到黄昏很少到那里去,所以一直没考虑到,在白天可以看出她的脚印。也许正是这些向她父亲泄露了她的约会。
她站在那里郁郁不乐地看着,觉得营帐那边一向传过来的声音性质有些变化。菲莉斯现在对军营里的事情漠不关心了,可是她还是踏着那些石头磴爬上了那个老地方。她看到的情况开头让她感到恐惧和惶惑,然后她直挺挺地站在那儿,手指头抠着园墙,眼睛使劲努着,面孔死板得像石头一般。
在她面前那片开阔的绿地上,军营中所有的团队都成行排列,在队伍前面居中的地方,摆着两口空棺材。她听到的那种不同寻常的声音,是从一列行进的队伍中发出的。它由轻骑兵团的军乐队组成,边走边奏着葬礼进行曲。接着是一辆出殡车,车里有这个团的两个兵士,两边有卫队,还有两个牧师陪同。后面一群乡下人,是让这一事件吸引来的。这一队垂头丧气的行列沿着队列的前排走过去,又折回到队列的中间,然后在棺材旁边打住,两个判了死刑的士兵在那里给蒙上了眼睛,跪在自己的棺材上;然后稍停留了几分钟,好让他们祷告。
一支二十四个兵士组成的行刑队准备停当站在那里,马枪平端着。指挥官早已拔剑出鞘,挥舞起来做了几个劈刺的动作,最后剑头向下一点,这时行刑队一齐开枪。两个受刑人倒了下去,一个面朝下扑在棺材上,另一个仰面朝天。
就在枪声齐发的时候,格若夫大夫花园的墙头传出了一声尖叫,有人跌倒在墙里面了;但是当时在外面看热闹的人,谁也没有注意到。那两个处了死刑的是马特豪斯·梯纳和他的朋友克里斯托夫。守卫的士兵几乎立刻就把尸体装进了棺材;但是那个团的上校,一个英国人,骑马赶了过来,态度严峻地大喊大叫:“把他们拖出来——示众!”
棺材给竖立起来,两个死去的德国兵脸朝下倒在草地上。然后所有团队都一小队一小队地迈着缓慢的步伐围绕那个地点走了一圈。检阅完毕,尸体又装进棺材,然后运走了。
正在这段时间,格若夫大夫听到齐射的枪声,就疾步跑到花园里,他看见他可怜的女儿一动不动地躺在墙边。她被抱进了屋里,可是过了很长时间才恢复知觉,而且有几个星期,大家对她能恢复正常的神智都丧失了信心。
根据透露出来的情况说,来自约克轻骑兵团的这两个倒霉的逃兵,按照他们原定的计划从邻近海港碇泊处放开了那条船,与另外两个受到上校不公平待遇因而愤愤不平的伙伴,一起驾船平安地渡过了海峡。但是他们迷失了方向,把船开到了泽西[1],以为那个岛就是法国海岸。在那里,他们被人发现是逃兵,于是交给了政府。马特豪斯和克里斯托夫在军事法庭上为另外两个人求情,说完全是由于他们两个人的主张,那两个人才受引诱一起逃走的。因此那两个人相应地判了鞭刑,而领头的两个人则判了死刑。
游客到著名的古老乔治海滨浴场去游览,要是愿意漫步到附近小山下的村子里去,看看殡葬登录表,还可以找到如下的两项:
马特·梯纳(下士)曾在国王陛下约克轻骑兵团服役,因逃跑被处决,葬于一八〇一年六月三十日,年二十二岁,生于德国萨尔布吕肯城。
克里斯托夫·布顿斯,隶属国王陛下约克轻骑兵团,因逃跑被枪决,葬于一八〇一年四月三十日,年二十二岁,生于阿尔萨斯的洛瑟尔根。
他们的坟墓位于小教堂背后,靠近墙边。没有任何纪念物做那个地方的标志。但是菲莉斯给我指出了那个地点。她活着的时候,老是去把那两个坟头打扫得干干净净。但是现在上面长满了荨麻,而且陷下去几乎成了平地。不过年纪大些的村民,从父母那里听到过这个故事,还能想起那两个兵士长眠的地方。菲莉斯就安葬在旁边。
(1889)
* * *
[1] 泽西为英属海峡群岛中的一个岛屿,位于英吉利海峡南部,靠近法国海岸。